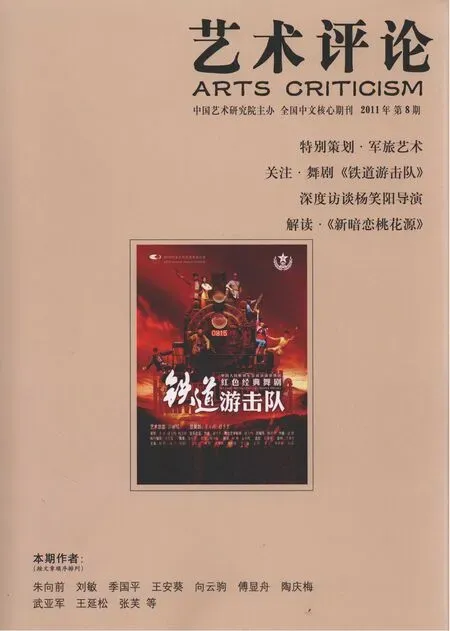全能俯视下的平行视角表达——略析电视连续剧《东方》的文本建构
武亚军



英国著名学者E.H.卡尔曾经在《历史是什么》中转引他人的话说:“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因为,假如历史学家不评价的话,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1]作为一个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其任务显然与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同,创作者要通过一系列有秩序的具有情感意义的符码描述历史事件,甚至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态度,这就构成了历史题材作品。在实际创作中,由于历史事件距离观众“空间和事件的遥远性”,[2]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由于时代背景乃至接受者个人情感的隔膜,观众往往在观赏时会形成审视甚至距离感。作品要想成功表达,就要求创作者们寻找到一条适合的表达策略。
大型电视连续剧《东方》(总导演:唐国强,编剧:刘星,导演:路奇、高升中,主演:唐国强、王伍福、曾秋生等,联合摄制: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八一电影制片厂等),浓墨重彩地表现了1949—1957年之间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文本创作经过剧作者的精心设置,具有了较高的艺术品质。是什么动因让创作者采取了这样一种鸿篇巨制的创作初衷?是什么方法让这个大跨度、多维度的作品巨而不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
全景式的描写是电视剧《东方》最重要的结构特点,“宏大”,是该剧留给观众的第一直感:该剧时间跨度大——前后长达9年。表现人物多——前后有近500个历史角色,既表现了领袖人物,也表现了进步人士、市井小民、老抗联战士;既表现了新生政权的领导人,也表现了仍有争议的国民党将领。表现的事件多——既表现了新中国建立后的正面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又表现了仍在部分地区延续的地下斗争;既表现了国内的政权建设,又表现了国际关系的发展;既表现了新政权的高涨的热情,也表现了国民党对政权崩毁的无奈。
此前,还没有一部影视作品能以这种全景式的方式描写这段历史,即使有所选择,也大多是片段的、局部的表现。如表现公私合营时期上海纺纱大亨改造和转变过程的电视连续剧《上海的早晨》,展现新中国惩治贪官刘青山、张子善的历史事实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新中国第一大案》等。这些作品都从历史的局部进行深入的刻划,而这些历史的局部也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在观众信息交互频繁、极具思辨精神的今天,观众已经不能满足对局部历史的记忆,亟需得到发生这些事件的整体坐标,即希冀把握历史背景的全局。《东方》所构建的宏大的历史图景,正是对观众这些记忆散点的整合,应和了观众以这种“全能视点”进行审视和多维度思考的要求。通过将这些散点事件集合为链条式的发展,观众也从中得到与自身记忆储备的“对位”或者“改写”,从而产生一种“探秘”的欣快感。这种“全能俯视”的关照,使得该剧具有了“通史”式的权威性和超越感。
把握这种“全能视点”下的全景式结构,需要创作者的功力,即对历史事实全面的熟悉和相当的选择编辑能力。电视剧《东方》的创作者,无法也没有采取一般的“起承转合”的四幕剧式的创作手法,而是采用了两段式的方法将这个宏大的结构进行了切分:前一部分着重表现国共军事斗争的继续,即新中国的政权的不断推进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退守,将解放西南作为轴线,并将解放海南岛、进藏进疆、解放舟山等重大事件的展现同时展开,不在于正面表现战斗场面,而在于表现政治家的智慧博弈和某种宿命况味;后一部分主要表现的是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以汽车工业、棉纺织业、科技领域的人才延揽和思想变革为主轴,兼顾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或军事事件,充满了高涨的热情,并让更多的非领袖人物成为作品的主角,表现了他们在此历史阶段的心灵归宿。这样的大结构的切分,符合一般观众的历史知识储备和判断原则,也使全剧逻辑清晰,维度明确。这样的结构方式被有的评论家称为具有“政论内核”的“立体叙事”[3],是十分恰当的。
二
宏大的全景式、“全能俯视”的叙述方式往往会给观众造成接受过程中心理的压力甚至茫然,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作品的完整性。为了将这些线索、人物和逻辑维度展现得更加清晰,基础更加牢固,更易被观众认同,创作者在具体文本操作时,从整体结构的“高位”俯身,利用“平行视角”开掘人物、塑造细节,以期使作品更加坚实、生动。
如在全剧的开篇,创作者回避了观众惯知的开国大典的隆重、热烈的典礼和庆祝场面,而表现了当晚众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看欢庆焰火,宋庆龄走近毛泽东对他表示开国祝贺的这样一个细节。这个场面的处理,既不落入一般性历史复述的俗套,也带有某种历史“揭秘”式的效果,使观众感觉到全剧不是沉闷的历史再现,而可能蕴含着某种创作者对历史的重新拼贴而产生的新奇感。
同样,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创作者也回避了对历史人物教科书式的再现,而是采用了大量具有个人色彩的细节,使人物自身的内心世界表达更富多义性,同时,也加注了创作者自身对历史人物的读解。如,在表现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中,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莫斯科火车站,站台上和车厢内挤满了欢迎他的群众和官员,而毛泽东却泰然稳坐。正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车站钟楼上发出了整点报时的钟声,指针指向正午12点。车厢内的毛泽东脸上浮出了笑容,一拍大腿站了起来:“毛泽东,准点达到!”这个场面在之前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极少表现,至少在笔者的记忆中是没有的。这样的处理,或可理解为表现毛泽东来到莫斯科的心理,或可理解为对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个段落总结。得到答案,都要凭借观众自身的阅历和解读方式,而创作者这种平行视角赋予观众的则是多义性读解的巨大空间。
这种“平视”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对曾经被“神圣化”革命领袖人物的身上,也表现在曾经被文艺作品“妖魔化”的蒋介石等国民党将领的身上。在该剧的前半部分,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不断南撤,蒋介石一直处于焦灼、怀疑、自责和责难他人之中。创作者在此段落着力表现的是在这些危急时刻,蒋“用人生疑”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一贯的行为方式,也表现了他“疑人不得不用”的尴尬境遇,表现了他在行将结束的战争中不断在“守”与“弃”之间的徘徊与低落。在他的身上,创作者加注了不同的情感符码,如失意的政治家、在政治漩涡中的老人、老年的军事将领等等,同时,也通过蒋与其子孙的关系,展现了这个本应含饴弄孙的老人仍周旋在漩涡中心的无奈与无力。特别是表现他溃退到台湾后,创作者经常在拍摄中运用大景别,将蒋置于画面的一个角落,而奔腾的海水、冷峻的礁石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形成一种对立关系,意图表现其孤立无助的心理境况。这种寥落,既是对史实的客观写照,也是创作者主观立意的写照。
这种“平视”的关系,是创作者为观众建立的一个作品内进行情感审视和理性分析的平台。在这个血肉丰满的平台上,创作者通过情节和画面所要表达的情感和话语都能自觉地被观众发现和挖掘,有力地支撑着《东方》的宏大叙事。
三
“全能俯视”的宏大构架与“平行视角”的细节处理成为电视连续剧《东方》成功的重要原因。客观地说,这些处理方式并不是《东方》的首创,而是因为作为长篇影视作品,具有了展开这种构架和进行这种处理的空间与时间,使之可能得以实现。十分可贵的是,《东方》的这种全景式的叙述方式并未因其体量庞大而显得散碎和拖沓,而显得气韵贯穿。分析其原因,是创作者始终围绕着对新中国建立的认同和肯定的基调上进行布局的,这是创作者的一种表态。这种思想上的表态,成为全剧起到勾连和贯穿作用的“向心力”,在此之下,那些处于平行视角的细节就成为在这种向心力牵引下的“离心力”:“离心力体现素材和体裁规律的对抗,体现出艺术家同样十分自然地在描述生活时力求达到最大可能的生活的丰满和生活的从容不迫。”[4]这种“离心力”与“向心力”的聚合关系,成为作品拥有整体性、系统性和丰富剧作肌理的重要原因,也是《东方》通过“平行视角”的细节处理完成“全能俯视”的宏大叙事的前提和基础。应该说,这一点,对于创作同类题材的长篇作品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1] 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5页。
[2]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3] 张东,《立体叙事中的政论内核——评电视连续剧<东方>》,《光明日报》2011年5月9日,第14版。
[4] 霍洛道夫,《戏剧结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