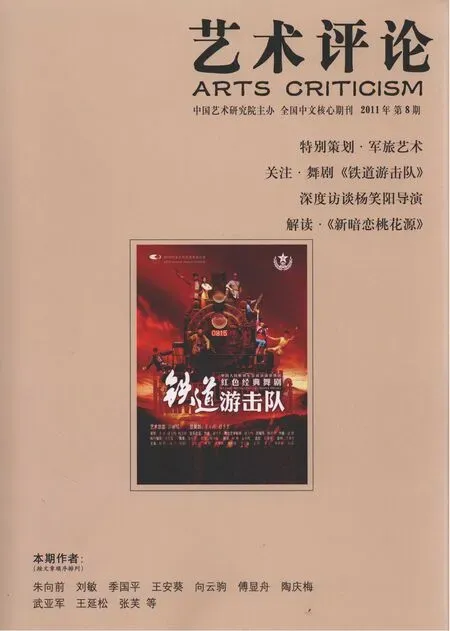方雄遒伟、庄雅简穆——论北魏白驹谷题字
徐福山
徐福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楷书早在魏晋之际就已经形成,到南北朝时期成为主要的字体,而用于铭石的楷书仍然保留了一些隶书的痕迹,较之当时的日常书写,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状态。在北朝的碑刻里,这种略带隶意的楷书在较长的时期里被普遍地应用着,至北魏中期形成了棱利角出、峻拔沉雄的书风,被后人称为魏碑体。北魏之后这种曾经辉煌一时的楷书由于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南派书风的兴起而逐渐被人所遗忘。清代乘帖学之末流和金石考据学的兴起,碑版书法的艺术价值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兴趣,经过阮元的倡导和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推动,碑版书法取得了与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书法分庭抗礼的地位,被称之为“碑学”,尚碑之风曾压倒了盛行千余年的“帖学”,一度成为书坛的主流。这些朴拙生动,被康有为誉有“十美”的魏碑的创造者却鲜有人留下名字,然而郑道昭的名字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但在碑刻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传为他的题刻特别多,达四十余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就载有“郑道昭云峰山四十二种”,[1]并且均列为妙品上。叶昌炽《语石·总论·南北朝书人一则》中云:“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荜路蓝缕,进入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犀、播龙蛇,而游刃于虚也,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叶氏对郑道昭推崇至极,凌驾于王羲之之上。虽有偏执之嫌,却反应出了清人的审美寄兴。在郑道昭的系列题刻中,有一件创造了北魏方笔榜书之最的作品——白驹谷题字。

白驹谷题字刊刻于益都玲珑山(古名百峰山)白驹谷的西崖壁,当属摩崖石刻。玲珑山位于今山东青州的辖区内,北魏时属青州所辖。此题字实为两刻,一刻为:“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游之山谷也”,为纪游之作,即《游山谷题字》。三行,每行五字,凡十五字。整个题字高174厘米,宽118厘米。另一刻为:“此白驹谷”,为山谷命名之作,即《白驹谷题字》,仅一行四字,高141厘米,宽45厘米,字径较《游山谷题字》稍大。二刻均为楷书,传为郑道昭所书,字径均逾尺余,为北魏方笔榜书之最大者。由于二者风格相近,均刊于白驹谷,又相距不远,故常将此二者统称为“白驹谷题字”,本文亦将两者合二为一,放在一起探讨。
二刻均无纪年,据张从军《郑道昭年谱》载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光州刺史王琼因“受纳之飧”,被中尉王显所弹劾而罢官,时任司州大中正的郑道昭接替王琼赴光州治所掖县,出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延昌二年(公元513年),道昭接替高植任青州刺史。故可推断二刻当刊于青州刺史任期内,约为公元510—513年之间所刻。
至于包括《白驹谷题字》在内的四十余处题刻是否为郑道昭一人所书,近代争论不休。著名画家刘海粟《读郑道昭碑刻五记》一文质疑了郑道昭诸刻的真实性,他认为:郑道昭所处的时代,出身书香门第,甚至在书法气氛的环境中长大而不工书者亦有之,史书上亦无郑道昭善书的记载。虽然很多题刻中都留下了郑道昭的名字,而《郑文公上、下碑》等大的碑刻却没有署上郑道昭的名字,摩崖上书丹十分吃力,但好名的郑道昭却并未署名,令人费解。儿子为父亲写碑的例子在汉魏六朝并不多见,即使有也不能以第三人称,而应以第一人称。传为郑道昭书写的四十余种刻石作品除《白驹谷题字》外多为圆笔,兼有草情、篆韵之美感,独有《白驹谷题字》一品为方笔,用笔俊俏斩截。所以刘海粟怀疑“这方笔大字的《白驹谷题名》与其他三十余处碑刻,有一种为他人代笔”[2]。因为“一位书法家前后期有变化,包括暮年突然变化,极为自然,一人同时有两种以上面目,也屡见不鲜。但前后期之间,两种绝然不相同的字体之间,每有共性,也有过渡阶段,将前后作品联成一体。突然大变,与前作全不衔接,后者(《白驹谷题字》)又仅一例。”[3]在没有确凿史料证据的情况下,刘海粟采用了平度县博物馆于书亭的说法,在“郑道昭书”的前面,加上一“传”字。据王思礼、赖非《云峰刻石的艺术成就及郑道昭在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所考:“这类方笔大字中百峰山诗碑左侧刻有‘平东府兼外丘参军’款铭,由此确定此类题刻书风皆为郑道昭幕僚所书。”[4]
《白驹谷题字》是否为郑道昭所书?若真如王思礼赖非先生所说为郑道昭幕僚所书,那这幕僚又是谁?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确凿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也认为把《白驹谷题字》看作传为郑道昭书比较恰当。尽管我们目前无法确证它为郑道昭所书的真实性,然而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它的艺术价值的考量。
刘海粟质疑《白驹谷题字》是否为郑道昭所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白驹谷题字》是方笔,而传为郑道昭的其它书刻多为圆笔,认为方、圆用笔的突兀变化难于出自一人之手,并且认为这种“方笔效果不完全出之于笔”[5],而多是镌刻所致。为了证明方笔效果是刻出来的,他列举了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画承及妻张氏墓志》,此志刊刻于章和十六年,相当于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共八行。前五行已经刻过,棱角分明、斩截犀利是方笔,后三行丹书后而未刻,与今人常规书写效果相近。沙孟海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在《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前五行经过刀刻,不像毛笔所写。前后对照,证明有些北碑戈戟森然,实由刻手拙劣,决不是毛笔书写的原来面目。刻字工师,左手拿小凿,右手用小锤击送,凿刃斜入斜削,自然多棱角。”[6]关于碑刻书法的学习,启功先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论述绝句》中说:“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7]并注曰:“余非谓石刻必不可临,唯心目能辨刀与毫者,始足以言临刻本,否则见口技演员学百禽之语,遂谓其人之语本来如此,不亦堪发大噱乎!”[8]启功先生从临习的角度,侧面地阐述了刊刻对书写原貌的破坏作用,并且明确表明“半生师笔不师刀”[9]的学书主张。
包世臣相信好的石刻工匠是能够保持和忠实于书写效果的,他认为:“古碑皆直墙平底,当时工匠知书,用刀必正下以传笔法。”[10]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缀法》中也详尽地阐述了方笔和圆笔的书写技法,并比较了两者之间的异同。延昌十一年的《令狐氏墓表》书丹后并未刊刻,此表中“昌”、“月”、“寅”等字的折角,“迁”、“曹”等字的起笔,“未”、“交”、“后”等字的捺角均是方笔,其方折斩截毫不亚于《白驹谷题字》。延寿十三年《王氏墓表》中的方折笔画亦可佐证。
方折的笔画比圆转的笔画更容易刊刻,因为犀利的刻刀作用于坚硬的石块更容产生棱角分明的方折和直线,反倒是圆转和屈曲的点画不容易刊刻。我们既然相信刻工对于像《郑文公碑》那样圆转笔画书写原貌的忠诚程度,就没有理由不相信比圆笔更容易刊刻的方笔也完全有可能是用毛笔书写出来的。当然即使忠实于书写原貌的石刻作品,也不可能尽像书写的墨迹,毕竟经过了刻工的再次加工和二次创造。
方与圆本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正由于两者的比照才会使彼此之间的特征愈加凸显,亦可相互补益。以写方笔北碑著称的孙伯翔先生,对于方笔和圆笔的应用有着深刻的体悟和理解,他认为:“方笔雄峻,圆笔浑穆,其两者形成魏碑书体之特征,魄力雄强中寓浑穆之气,气象浑穆之外溢魄力雄强之感。方笔与圆笔是外在的形体,切切不可孤立地将方与圆对立起来,方与圆是辩证的统一。”[11]在孙先生看来,书法中的方与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可有所侧重而不能顾此失彼。他还认为“欲得方,必得厚方能称雄,形态易得,质感难求。”[12]“厚”与“质感”当是方笔之神髓了,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我想应该就是寓圆于方了,因为“圆笔浑穆”,得浑穆者必能得厚。圆笔之浑穆正可冲方笔之尖刻,自然朴厚而不失于拧利。《白驹谷题字》的方笔正体现了方圆并施、方中寓圆、圆中寓方、以方为主的用笔方法。其方笔之外,也有圆笔的应用,如“郑”、“道”、“游”、“”等字中的点和短横,“郑”字的右耳旁,“昭”和“谷”的口字旁,“中”和“游”的长竖笔,无不圆润浑厚。也正是这方折笔画中所蕴含的浑朴与圆厚,才使得《白驹谷题字》字大而不失于空怯,反而能凝重雄浑,方折劲拔中又能丰满朴茂,实为难得!

《白驹谷题字》横画的收笔处,重顿笔后又略回锋再轻轻挑起,有鸟虫书的特征,其横向舒展的意态和上挑的笔法,又有隶书之遗意。这种溯古的笔法,无疑为整个题刻增加了几分古意。而同为方笔北碑代表的《张猛龙碑》却无此上挑的隶书痕迹,正如沈曾植《海日楼札丛》中所说“风力危峭,奄有钟梁胜景,而终幅不染一分笔,与北碑他刻纵意抒写者不同。”[13]龙门造像记中却有很多隶书“雁尾”的特征,如《贺兰汉造像记》和《郑长猷造像记》等,隶书的痕迹十分明显,然龙门造像记中的隶尾方折、瘦俏、生硬,不若《白驹谷题字》的饱满与圆浑,终无《白驹谷题字》雄厚浑穆之气象。《白驹谷题字》的结体宽博端庄,行距略大于字距,竖有列,横成行,字体大小均匀。《张猛龙碑》虽然也是横竖成行成列,但字体的大小有变化,结体不同于《白驹谷题字》的平正端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呈放射状,且中宫紧收,内收外放。龙门石刻中造像记的章法较《白驹谷题字》的变化丰富,更为自由。除少数界格分明之外,多为竖行有列,而横行不清,结字也变化自由,大小、长短、肥瘦、宽窄等变化无可端倪。虽然《白驹谷题字》结体端庄平正,但并不缺少变化,方圆、粗细、收放等变化寓于典雅和端稳之中,尽去北朝书刻散漫粗野之气,而代之以端庄净雅。正是由于这种简洁端稳的结体,才使得《白驹谷题字》愈显恢宏与庄重。正如侯镜昶所说:“气势浩然,标学者森严之风,扫俗书粗犷之习,称其为书苑中之‘儒家’,言不诬也。”[14]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说:“学榜书虽别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临写之。六朝大字,犹有数碑,《太祖文皇帝石阙》、《泰山经石峪》、《淇园白驹谷》,皆佳碑也……《经石峪》为榜书之宗,《白驹谷》辅之。”[15]《经石峪》为北朝字径之最大者,被誉为“榜书之宗”,是圆笔北碑的代表,凝重圆浑、宽博雄深。仅次于《经石峪》的则是《白驹谷题字》,字径逾尺,“此白驹谷”四字更大,为北朝方笔榜书之最。写榜书已属不易,苏东坡说:“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16],不仅如此,还难于气势、难于简穆、难于从容。“方笔写榜书最难,然能写者,庄雅严重,美于观望。”[17]《白驹谷题字》不仅“庄雅严重,美于观望”,而且静雅沉稳、遒劲奇伟,深得浑穆简静之致,备受后人推崇。
清代碑学大师赵之谦涉猎广泛,造诣全面,于诸体书中,最青睐自己的北碑体楷书,他说:“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书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18]赵之谦最初取法于颜真卿,得其雍容大度与浑穆沉雄。后“服膺包慎伯”,推崇北碑,取法亦从颜平原转向北碑,并盛赞:“六朝古刻,妙在耐看。”[19]北朝碑刻中尤喜方笔一路,从他传世的作品便可得到证明,其楷书无不方折峻拔。他的作品中,有一件临作,临摹的正是《白驹谷题字》。临作集两刻于一纸,在忠实于原刻的基础上运以己意,点画方折斩截,又得《白驹谷题字》之浑穆朴厚、遒迈奇伟,用笔沉实,力量饱满。而结体不同于原刻的平稳端庄,以欹侧取势,中心从左下向右上角伸展和其创作类同,多出于己意。其俊俏方折又浑穆沉雄的用笔深得《白驹谷题字》之意,应该从中受益匪浅。当代碑派大家孙伯翔也以写方笔北碑而闻名,在他的著作及题跋、落款中也多次提及潜心临习包括《白驹谷题字》在内的传为郑道昭摩崖题刻的体悟与心得,其书法斩截方折、沉厚雄放的质感近于《白驹谷题字》。刘彦湖先生的楷书也多得益于传为郑道昭的摩崖题刻,虽无《白驹谷题字》浑穆沉雄之质,但得其方折劲健、简净端雅。
清代“碑学”的兴起,使北碑颇受激赏和追捧,而代表着方笔极轨的《白驹谷题字》,其方雄遒伟、庄雅简穆的特质对后世影响深远。尽管很难从文献史料中去获取某书家直接取法于《白驹谷题字》的记载,然而,但凡后世能以方笔北碑名世的书家,多少都与《白驹谷题字》方中寓圆、沉雄浑厚的特质有几分肖似。
注释:
[1]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2] 刘海粟:《齐鲁谈艺录》,山东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
[3] 刘海粟:《齐鲁谈艺录》,山东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
[4] 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碑刻摩崖一》,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8月版。
[5] 刘海粟:《齐鲁谈艺录》,山东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版。
[6] 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
[7] 启功:《论书绝句》(注释本),三联书店2004年版。
[8] 启功:《论书绝句》(注释本),三联书店2004年版。
[9] 启功:《论书绝句》(注释本),三联书店2004年版。
[10]包世臣:《艺舟双楫》,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11]孙伯翔:《怎样写魏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12]孙伯翔:《怎样写魏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13]沈曾植:《海日楼札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版。
[14]侯镜昶:《云峰诸山北朝刻石讨论会文献集》1985年10月版。
[15]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16]苏轼:《论书》,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17]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版。
[19] 赵之谦:《章安杂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