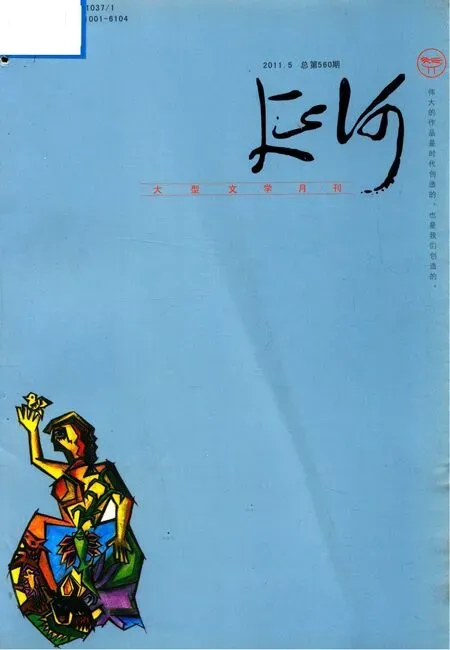黑暗里的女人
王巨成
黑暗里的女人
王巨成
1
小屋很小,像大屋的尾巴,被那么一甩,不小心甩断了。好在没有被甩出多远,遗落在三五米开外的地方,歪歪扭扭的,破破烂烂的,让人担心一场大雨都能给浇趴了,或者一阵大风都能给吹跑了。
但小屋沧桑的模样,又告诉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那是存放锹、耙、犁等等杂物的,有门有窗,门是一扇独门,很小,大人经过这道门时需要弯一弯腰。窗同样很小,一个人的脑袋都伸不进,只有一扇,位于西面墙的正中间,一米左右的高度。一般情形下,小屋不用上锁。
但现在小屋的门锁着,是一把崭新的锁。于是那窗子就显得黑洞洞的了,像一只深远的眼睛了。
大刘庄的男女老少在经过这扇窗子时,他们的脸上会忽然流露出紧张的神情,脚步匆匆,眼睛飞快地扫一下窗子。
除了小宝和刘富贵,没有人会在窗子下停住脚步,那怕只是一会儿。
大刘庄的白天很静,偶尔传出一两声犬吠,间或伴着老态龙钟的老人的咳嗽,孩童去上学了,青壮年去挣工分了。有一只麻雀可能只是想歇息一下,它飞到窗子前,落在了窗台上,偏着头,朝窗子里看去。谁知麻雀悚然地叫了一声,立刻窜上蓝天,飞得不见了踪影。
麻雀被吓着了,是被窗子后的一双眼睛吓着了。那双眼睛长在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上,突出的颧骨使得那双眼睛陷了下去,因为有小屋里的黑暗做背景,使得那双眼睛便不再是眼睛,它们触目惊心地发亮,宛如两束飕飕的剑光。
那两束光直直地射向外面,如刀子扎向那些有翅膀的,扎向那些有腿的。但也有例外,当一个娃迈着双腿向小屋跑来时,那两束光柔和了,柔和得像线。
娃直朝小屋的窗子扑去。
“小宝,别过来!”从窗子里面传出一声断呵。
叫小宝的娃仿佛被人迎面猛推了一掌,踉跄着站下。
“妈——”小宝挪着脚步,冲窗子颤颤地喊着,瘪瘪嘴,像是要哭。
“小宝别哭,妈妈没事!”窗子里面伸出一只手,冲小宝既像是挥手,又像是招手。
小宝的眼泪终于落下来。
“妈……”小宝呜咽着,双肩一抽一动的,“麻子说,麻子说……你活不过十天……”
窗子里面沉默着。
突然窗子里面爆发出一声走调了的声音:“狗日的麻子,老娘偏活给你看!”悲愤的声音把空气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人觉得血淋淋的。
小宝怔了怔,便昂着头,冲村东头吼道:“狗日的麻子,咱妈偏活给你看!”
窗子里面发出了带泪的笑声。
“小宝,妈真想摸摸你的脸啊!”窗子里的眼睛晶莹闪亮。
“妈,咱让你摸!”小宝急急地冲出了一步。
“乖小宝,你别过来!”伸出窗子外的手大幅度地挥着。
小宝不舍地站下。
“小宝,你替妈妈摸摸!”
小宝真的把双手在自己的脸上摸着,一下一下地摸着,轻轻柔柔的,就像妈妈平日那样摸他,小宝那停了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跟妈讲讲学校的事情吧,妈妈爱听!”
于是小宝把学校里的事情絮絮叨叨地讲给妈妈听。有了小宝的讲话,时间走得快多了。
刘富贵从田地里散工回来了。他站在距离窗子三四尺远的地方朝窗子里看,并且咳嗽了一声。
“看啥看,老娘还没有死!快去做饭!”窗子后的声音硬邦邦的。
刘富贵不言语,似乎叹息了一声,然后回屋做饭。
饭做好了,是菜和米混合起来做的,乡下人俗称“菜粥”。刘富贵首先把一碗能照见人影的菜粥由窗子递过去,接着才回屋给小宝和自己盛。
刘富贵和小宝捧着碗,蹲在窗子的对面,很有滋味地把稀粥吸得呼啦啦响。窗子里也有声音,但是小多了。
“你盐放多了,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窗子里的女人每次在吃饭时都要说话,有时说油放多了,有时说米放多了,有时说自己吃的太稠了,有时也说小宝的衣服脏了,语气多是责备的,其中部分话属于没话找话。
刘富贵这时脸上舒舒展展的,要么头点如鸡啄米,要么含糊地“唔”一声,由着里面的人说。女人被关进小屋后,刘富贵开始喜欢这些声音。这些绵绵不绝的声音是过日子的声音,有了这些声音,预示着家还是完整的家。
但窗子里的女人今天却说出惊天动地的话来:“富贵,等会儿你去跟金贵说,咱要出工……”
刘富贵的喉咙咕噜了一声,他直眉瞪眼地盯着窗子,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2
女人必须在小屋里吃,必须在小屋里睡,包括拉撒,她不得走出小屋门槛半步。女人失去了一切行动的自由,更不能去挣工分。
“妈,你要出工?”小宝也是一脸的惊奇,“你能走出小屋了?”
窗子里的女人笑了笑:“富贵,咱思磨过了,咱晚上出工,你要金贵把活给咱留着,咱谁也不妨碍……光靠你一个人,年终咱们吃啥?起码要把小宝吃饱呀,他正长身体呢,可不能把他饿着了!还有,咱早就答应他过年买新衣裳的。”看来,出工的问题被窗子里的女人琢磨了不止一天,她是铁了心要做。
小宝眨着眼睛,抽着鼻子。
刘富贵也眨巴着眼睛,抽着鼻子。
“咱挣一分是一分!咱有力气呢!”
刘富贵把目光远远地放出去,放到村子里大大小小的田地上,像要从里面找到他需要的答案。
小宝的目光在刘富贵和窗子之间来回地移动。
半晌,刘富贵把目光收回来,对着窗子:“咱跟金贵说说。”
“你要往狠处说,他不答应,你就说咱要上他家来闹腾!”
搁了饭碗,刘富贵急急地出了门,后面跟着小宝。刘富贵一脸严肃,小宝也一脸庄重。村上的人见了,也急急地跟过来。
“富贵,玉兰……那个啥,是不是……?”
“玉兰好着呢!”刘富贵大声地把别人的话堵了回去。
“咱妈要出工!”小宝也大声大气地说。
再问,一大一小的两个人都不再理会,头也昂了起来。这样的神情真是令人捉摸不定,也把村人的好奇心吊了出来,于是在刘富贵和小宝的身后跟了一帮好事者,连几条狗也跟上了。
到了金贵家门口,已经跟了几十号人。
金贵刚好用过午饭,还喝了点,红着脸,正用草棒在牙缝里捣鼓。猛一看见这阵势,吃了一惊:“谁?谁打架了?”
“咱妈要出工!”小宝挺到金贵跟前。
刘富贵把小宝拉到身后,跟生产队长刘金贵讲了他女人玉兰要求晚上出工的事,字字句句,讲得清清楚楚。只要在金贵面前说话,刘富贵总有些心虚气短,但这回一点也没有。
所有的眼睛大了,所有的嘴巴合不拢了,金贵手里的草棒无声地落到了地上。
金贵发狠似的把一只脚朝地上的那根草棒踏去,右手指着刘富贵:“这不是疯了嘛?哪有麻风病的人出工的!”
“真是疯了!”“把咱们传染了咋办?”“公社里都没有这样的事!”……人群里发出嗡嗡的附和声。
刘富贵的眼睛像要吃人似的地朝说话的人盯过去,那些说话的生生地被刘富贵的目光锉得矮下去。

仕女像 王济远 油画 102×76.2cm
“张嘴就得吃饭呀!咱也不忍心玉兰得了麻风还挣活路,你们还有啥法子?你们说,咱依你们的!”
村人不看刘富贵,去看队长。
金贵眼睛斜着刘富贵,冷笑:“刘富贵,你他妈晓得麻风是啥个病?”
“咱晓得!”
“晓得还说昏话?”
“队长,你今天不答应也得答应,玉兰要是上你家来闹腾,咱也没法子!”
金贵的脸拉得长长的。不知啥时候,金贵的老婆出现在金贵的身边,她悄悄拉了拉金贵的衣襟。
“咱丑话说在先,完不成任务不记工分!把麻风传给别人,你负一切责任!”金贵说到这里哼了一声,瞪了瞪众人,“晚上没事,你们别在外面鬼转……”
“当心咱妈把麻风传给你们!”小宝接过金贵的话说。
“小兔崽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啦!”金贵勃然大怒。
3
星星一颗一颗在深蓝的天幕上闪烁,驱蚊虫的艾草点燃起来了,一股清香在村子的上空飘荡。
往日的这时候,村子里是热闹的,娃子追逐打闹,女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说长道短,男人则拿着芭蕉扇走东家逛西家。
今晚却是静的,昆虫的浅唱低吟越发衬托出这种静,静得反常。纳凉的人都有些心不在焉,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留意着刘富贵家的方向,期待着啥。
“咱妈出工啦!”小宝的声音忽然在村子里嘹亮地炸响,连空气都颤了颤。
村子顿时滚过一阵骚动,一声声的呼喊四下响起:“狗剩,回家!”“大发呢?大发在哪?快回家!”……伴随着的还有大门被关上的声响。村街忽地空了,狗感觉这发生的一切突兀而莫名,便不解地叫起来。
黑暗中,一双双的眼睛透过门缝或窗子,朝刘富贵家的方向张望着。
模糊中,依稀看见刘富贵家的小屋门开了。
那小屋的门确实开了,是刘富贵开的。开了门,刘富贵退到大屋里,和小宝并排站在门口,两个人都眼巴巴地看着小屋的门。
“妈——”小宝颤巍巍地叫了一声。
刘富贵紧紧抓住小宝的手。
小屋的门口慢慢出现了玉兰,那没有一根头发的脑袋闪着幽幽的光,她迟疑着,但还是一步一步朝前走。
“咱出来了……”玉兰的声音细细的,紧张中透着不尽的喜悦。如果是在白天,会看见玉兰眼睛里汹涌出的泪水。这是她被诊断为麻风关进小屋后第一次走出。最初,玉兰感到天踏地陷了,她哭呀,哭得昏天昏地,哭得整个村子都淹浸在她的眼泪里。她才只有三十多岁,往后的日子就被麻风这只无形的手掐死了。她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她不吃不喝,也不睡,就等着麻风这个恶魔把她收了去。但麻风却是一个狡猾的恶魔,它还没有把玉兰玩弄够,它一时半会还不会把玉兰收了去。
刘富贵哭了,小宝也哭了,为了使玉兰吃点喝点,他们跪在玉兰的跟前。
“你活着一天,你就得吃呀喝呀睡呀,看见你吃呀喝呀睡呀,咱和小宝心里就踏实!”刘富贵的眼泪和鼻涕糊在了一起。
刘富贵的话是一针强心剂,玉兰瘫软了的筋骨又有了力气。玉兰明白了,既然一时半会死不了,就得活着。女人活在男人的身边时,男人的一颗心往往会安分守已地呆在胸膛里,可要是女人没了,日子一久,男人的心就要生出腿脚,生出翅膀,那么娃有后娘的日子也不远了。
仅是为了小宝,她也得活着!
于是小屋安静下来。只要眼睛睁着,玉兰就趴在窗子的前面,看她的大屋,看村街,看小宝和刘富贵的身影。玉兰还多了一个本领,即使小宝和刘富贵不在眼前,她也能看出他们在做啥。
决定夜晚出工,对玉兰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活着不能白吃饭呀!
白天的热气已经退去,清凉的夜风带着大地的芬芳悠悠地吹过,把一切浮躁的东西都吹得平心静气。玉兰在前面走,她走得很慢,但脚步迈得很有劲。麻风怎么啦?麻风照样挣工分。那颗光头不住地朝四周扭着,一只萤火虫企图落在光头上面,似乎总找不到机会。
玉兰是在看大刘庄的一草一木,那些一草一木也在看她。玉兰是在春暖花开的时节被关进小屋的,现在是夏天了。乡下女人对时间的认识,是通过播种、收获,再播种、再收获的轮回来体会的,但玉兰在小屋里对时间有了自己独特的体验,比如,窗口的上方有一只蜘蛛网,有一天蜘蛛网被风吹坏了。在某一个时刻,玉兰忽然看见又一个完整的蜘蛛网出现了,于是玉兰发出感慨:想不到蜘蛛这么快就把新的网织好了!再比如,玉兰希望看见小宝,可是她的眼睛几乎要看穿了,小宝也没有出现在她的眼前。时间怎么过得这般的慢呀!玉兰那个急躁呀。所以玉兰心里的时间是橡皮筋,可以拉长,可以缩短。
小宝和刘富贵在后面保持一定距离跟着,他们都有许多的话说,但又都不愿意打扰玉兰。玉兰要做的活计白天已经被金贵安排好了的,是插稻秧。
玉兰终于站下了,站在一块水汪汪的田地旁。那水里均匀地分布着一个一个的小黑影,那是一把一把的秧苗,它们都静悄悄的,似乎就等玉兰来。看不见的青蛙“咕咕呱呱”地叫着,叫得格外起劲,似乎是它们致的欢迎词。
小宝和刘富贵看见玉兰弯下了腰。是放插秧的绳子,还是卷裤脚?接着听到拨啦的水声了。
“你们回吧。”玉兰的声音有着别样的温柔。
“妈——”小宝忽然叫了一声,酸酸的。
“玉兰——”刘富贵也叫了,动情地。
青蛙忽然没了声音。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影塑像似的立在田埂上。
“你们回吧。”玉兰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是愉快的。
“妈,你别让蚂蝗叮着!”小宝说。
“玉兰,你别累着!”刘富贵说。
“妈,我陪着你,今儿个咱不睡觉了!”小宝握起了拳头。
“玉兰,咱也陪着!”刘富贵咬着牙。
玉兰轻轻地笑出了声。
“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是笑了,咱听见了!”
玉兰更大声音地笑了。
青蛙们大概受了感染,又“咕咕呱呱”叫起来。
小宝到底是孩子,他的眼皮渐渐重了,身子晃了。刘富贵抱过小宝,小宝挣扎着,喃喃地说:“咱不睡,咱要陪妈!”可是不多会,小宝的身子软在刘富贵的怀里。
“你们回吧,”玉兰第三次说,“你明天要出工,小宝明天还要上学,可不能教小宝受凉了!”
只能回去了,刘富贵却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有这么多青蛙陪咱,你怕什么?”
“要是,要是,有歹人……怎办?”刘富贵不放心村里的光棍汉。那些光棍汉像饿急了的狗,逮着啥吃啥。
“咱还怕歹人?不怕死的来呀!”
黑暗中刘富贵的嗓子咕噜响了一声。
刘富贵恋恋不舍地回了。
刘富贵安顿好小宝,烧了一瓶开水,那是给玉兰喝的洗的。刘富贵还做了一碗米饭,纯粹的米饭,没有掺菜,没有掺麦麸,只有过年才吃的米饭,并且在上面浇了一勺香油,然后用一只大海碗严严实实地罩着,压上一块砖头,送到小屋。
刘富贵没有马上走开,脚像被绳子栓住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气里有他女人的气息,他伸出双手,在空气里狠狠揽了一下,就像把女人揽进怀里。
最后把小屋的门带上,套上锁。
做完这些,刘富贵躺到了床上,他没有睡意,眼睛睁得大大的。刘富贵的目光穿过屋顶,穿过黑暗,飞到了玉兰的身边。
4
大刘庄只要能走动的,都聚拢到了地头,就是玉兰在夜晚插秧的那块地。大刘庄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玉兰在没有麻风之前,是村里做活计的好手,但要晓得眼前的秧苗是玉兰在黑夜里插的呀,一行行是那么的直,一簇簇是那么的匀,行距与间距是那么的适中,比白天里的女人做的活还要好。绿绿的秧苗见有这么多的人看她们,便意气风发地在晨风中摇曳,透亮的露珠在上面闪闪发亮。
原本那些眼睛是要挑剔毛病的,尖酸刻薄的话都准备好了的,就放在舌头边,时刻可以跳出来。可现在一双双眼睛直了,嘴巴哑了,只有狗在人群里蹿来蹿去。
一双双眼睛去看大刘庄最高行政长官,而金贵的一只手正摸着胡子拉碴的下巴。村会计抓着记分册,等着金贵发话。
小宝和刘富贵也在看金贵,他们盯着金贵的嘴巴,那嘴巴可是了不得的嘴巴,那里面说出来的话可以让人笑,可以让人哭,可以让人轻松得多长几斤肉,可以让人累得脱一层皮,可以让一个家庭在年终多分些谷子多拿到些钱。那张嘴巴在许多时候紧闭着,要说的话往往通过眼睛来说,或者通过哨子说。
金贵把手从下巴上拿下,谁也不看,说了声:“十分!”
“十分?”人群里有人怀疑地重复着着这两个字。这可是一个壮劳动力的一天全额工分。
村会计已经刷刷地写下了,似乎写迟了一步,那两个字就变了。村会计拍着手上的记分册,冲大伙儿说:“谁要是得了麻风,谁要是跟玉兰一样夜里插秧,都记十分工!”
没有谁愿意得麻风。
刘富贵的嘴唇哆嗦着,要说啥。还不等他说,小宝跳起来,骄傲得不得了:“这是咱妈插的秧,是咱妈在夜里插的!”
一个被人称为“快嘴”的女人指着田地说:“水里会不会有玉兰的麻风?”
这倒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田埂上的人不由地朝后退着,一个娃不小心跌进水里,没命地喊叫起来,像有人正用刀子割着他身上的肉。
“快嘴,你说的是人话么?”一个白胡子老头说。
快嘴的脸讪讪的,退到人群里。
金贵把哨子放进嘴巴里,边吹边大步走了,村会计小跑着跟上去。
人群顿时散去。
刘富贵还站着,他还没有看够玉兰插的秧。小宝紧贴着刘富贵,仰着脑袋,问:“爸,过年的时候,咱是不是可以穿上新衣裳啦?”妈妈可以挣工分了,过年的时候穿一身新衣裳的梦想可以实现了。
刘富贵疼爱地摸着小宝的头,决然地说:“笃定!”
小宝拿下爸爸的手,放到他的脸上。刘富贵懂了,便像小宝的妈妈那样摸起来。
此刻玉兰还在睡着。这是玉兰在小屋里第一次香甜地睡着,太阳升到了头顶,玉兰还在睡着。
一放学,小宝飞似的跑了回来。在学校,小宝把妈妈夜里插秧的事以及过年能买新衣裳的事,告诉了能告诉的所有人,别人那个惊奇呀,还不相信小宝妈妈能在夜里把秧插得那么好,邻村的同学在回家特意绕路来看了。小宝多想把这些告诉妈妈呀。
小宝没有在窗口看见妈妈。小宝把眼睛凑到小屋的门缝前,看见妈妈还在睡着,发出好听的呼吸声。
小宝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坐在大屋的门槛上,眼睛盯着窗子。妈妈只要醒着,就趴在窗子那儿。
一只母鸡婆“咯咯”叫着来了。小宝忙站起来,把母鸡婆赶走了:“到一边玩去,咱吗在睡觉!”
一只狗来了,它冲小宝摇着尾巴。
“去,到一边去,咱妈在睡觉!”小宝冲狗挥着手。
刘富贵回来了,他正要放下肩上的扁担,小宝轻声说:“慢点呀,妈妈在睡觉!”
刘富贵果然慢点,悄悄把扁担放下。
饭做好了,小屋里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刘富贵把“菜饭”用大海碗罩着,压上砖头,放在窗台上。只要玉兰醒了,她一眼就能看见。
一直到太阳偏西,玉兰才睁开眼睛。这时,一束夕阳的橘红光辉迟疑着从窗子爬进来,照到小屋里的墙上。窗台上的碗像趴着的一只小猫咪。有那么一刻,玉兰疑惑还只是早上,可玉兰很快明白过来,因为只要是晴朗的天气,那束光亮每天都在这时候光临她的小屋,当这束光亮消失的时候,夜幕便降临了。玉兰笑了,睡得那个美呀,好像把一生一世的觉都睡了。
从此大刘庄的白天就是玉兰的黑夜,大刘庄的黑夜就是玉兰的白天。
插完了秧,接下来的活是把那些不能种水稻的田地翻上,种上大豆,种上秋玉米,种上红薯等。
等忙完这些,水稻田里的草该薅了。
薅了草,那些旱谷要培土,要锄草……乡下有永远做不完的活。
所有这些都难不住玉兰。尤其薅草、锄草,这绝对是白天才能做的活,即使在白天还有人不小心把禾苗当草除了呢,更何况是在分不清草和苗的夜晚。但在玉兰身上,却从没有发生过把苗当草,或把草当苗。玉兰真是奇了,神了,玉兰在大刘庄人的眼里简直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了。有人说了,耗子是夜里挣活路的,青蛙是夜里挣活路的,猫咪是夜里挣活路的,玉兰嘛当然也可以在夜里挣活路。
这话说得好像玉兰天生有这样的本领,命该这样。
5
刘富贵一觉醒来,天蒙蒙亮了。他侧着耳朵听了听,小屋那边没有动静。玉兰是不是回来了?刘富贵随手抄起一件褂子披上,下床走了出去。
锁还套在小屋的门扣上,玉兰还没有回来。
那锁是防村里狗的,那些狗不分白天黑夜到处乱逛,如果让狗进了小屋,那么留给玉兰吃的很可能被它们捷足先登了。只要玉兰回来,她会自己拿掉锁走进去,等洗过了身子,泼了脏水,她便在里面用一根木棒把门顶上。这也是防村里狗的。
刘富贵下了锁,把头伸进去。女人的气息像无数的爪子一下子把刘富贵抓住了,刘富贵不由跌进了屋子里。
刘富贵伸出双手,在空气里狠狠揽了一下,就像把女人揽进怀里。这个动作已经被刘富贵不止一次地做了,做了这个动作,刘富贵会心满意足地离开,但刘富贵今天却没有走,他走近了玉兰的床,抱起了玉兰的枕头。
“你咋就得麻风呢?”刘富贵问枕头,是责备。
“那么多的人,咋就你呢?”刘富贵拍着枕头,好似要把枕头拍得说出话来。
习惯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大刘庄的人都接受了玉兰只能待在小屋里,只能在夜晚挣工分的事实,刘富贵也应该接受。然而刘富贵偏偏接受不了,他看得见女人,听到女人说话,闻到女人的气息,女人离他如此的近,可女人又跟他离得是如此的远。刘富贵心里那个酸呀,那个痛呀。在这个天蒙蒙亮的清晨,刘富贵的心里潮水似的涌起一浪一浪对女人的疼爱。他从来没有这样心疼过女人,恨不能把女人衔在嘴里,捂在心里。
眼泪打在了枕头上,刘富贵都不知道,刘富贵更不知道外面已经传来了一个人的脚步声,直到一声尖叫骤然在他身边响起。
骤然响起的尖叫又在半空骤然断了,两个人影像两块磁铁嘭地合在一起,接着床响了,那张床宛如在波峰浪谷中的小船,随时都有散架了的危险。伴随着床的声音,还有像狂风在林子间的呼啸。
终于,床静了,风也停了。小屋里惟有粗粗的喘息声,此起彼伏。
“走,你走,快走!”
“咱不怕!”
“小宝呢?小宝咋办?”
“咱……”
“快走呀……”女人呜呜地哭了。
“咱……身体结实着呢……”舌头似乎短了一截。
“你走你走……”跟着是巴掌击在皮肉上的声音。
刘富贵做贼一样从小屋里溜出来。天光已经大亮了,想想刚刚发生的事情,刘富贵恍惚觉得是在梦中。但刘富贵总还明白着一点,他跟他的女人亲了,不要命地亲了,干柴烈火般地亲了,那么的突然,那一刻他们就像在天上,都把麻风抛到了爪哇国。
刘富贵从天上跌落到地上,他回头看看小屋,小屋的门已经决然地关上了。刘富贵想,他也将是麻风了,他的头发也将落光,他也将被关进小屋。刘富贵甚至想,到时候得把小宝送到他舅舅家,小宝的舅妈连着生了三个女娃,还准备再生,直到生出小子才罢休。
刘富贵很奇怪自己并不慌张,并不害怕。是不是因为将要跟玉兰关在一起?是不是将要跟玉兰一起天天夜里出工?
玉兰也好,刘富贵也好,他们的生活由此多了一项内容:
“你头发落了么?”
“还没有,你看,好好的呢。”
这两句话每天至少要重复三遍。一个心惊肉跳地盯着对方的头发,另一个抓抓头发,咧咧嘴巴,有些难为情。
在田地里,男人也好,女人也好,特别喜欢说些男女方面的事情,那是乡村永恒的话题,单调的劳动,缺衣少食的日子,因了这些话题,多出了几分趣味,时间也走得快了些。现在谈论这些话题时,大刘庄的男女总不放过刘富贵,荤的,素的,含蓄的,露骨的,大杂烩样端到刘富贵面前。他们的本意不是要刘富贵好看,而是属于穷开心。
刘富贵呢,嘿嘿笑着,是有着秘密的笑,是受活的笑。
刘富贵不但笑,可能还会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说一些奇怪的话。这些奇怪的动作和奇怪的话,都和头发有关,比如刘富贵把手把手当梳子在头上一下一下梳,然后把手握着伸眼前,展开,瞧瞧,再然后朝手心吹一口气,说:“你们看看咱的头发!”
刘富贵的头发黑密密的,真教人怀疑玉兰的头发都被他长了。
或者刘富贵突然走到某一个男人的身后,在他的衣领附近,捡出一两根头发:“你的头发落了!”
被刘富贵捡了头发的男人往往不领情,没好气地说:“谁不落个一两根头发?你以为都像你家那个麻风才好!”
刘富贵这时一点也不生气,反而高兴地夸奖对方:“你说的对啊,谁都会落发,特别是在早上梳头时,起码要落五六根,多的要十多根。今儿个早上,咱梳头时,落了十三根头发!”
对头发,女人比男人有发言权,女人梳头要比男人勤一些,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马上搭上刘富贵的话:“可不是,一落就是一大把,特别是秋天!”
刘富贵冲说话的女人点点头,又说:“奇怪了吧?天天落头发,咋就不见头发少呢?”
刘富贵的眼睛在人群中扫来扫去,见没有人回答,得意地笑着把答案说出来:“头发会自己长!”
大刘庄的人都忽视了刘富贵的笑,他们以为刘富贵的笑是一个大男人无奈的笑,是干着急的笑,听了他们的穷开心,不知道他再看见自己婆娘有几多难受哩,或许牙齿都咬了,或许在某一个夜里,他会贼一样地爬到某一个男人不在家的女人床上。并且,他们以为刘富贵奇怪的动作和奇怪的话,目的是要岔开别人的话题,因为那些七荤八素的话题让他难受得要撑不住了。
这样时间到了冬天。
那天天上飘着雪花,大刘庄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队部里,不能走的也被搀来了,扶来了,甚至背来了,那些狗更不要说了。但今天却没有往日的热闹和嘈杂,肃穆的气氛里只听见会计的手指头在算盘上上下翻飞,那些个褐色的珠子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简直是一曲天籁之音。汉子抽着烟,眯着眼,虚虚的目光不时朝金贵和会计瞥过去。女人纳着鞋底,纳得心神不定,她们的身边依偎着娃。那些老人,闭着嘴巴,眼睛一会儿慈爱地看看自家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一会儿看看金贵和会计。
今天是分红的日子,会有谁不来呢?
这时门口暗了一下,是刘富贵来了。刘富贵今天来得可够迟的,接着刘富贵的身后出现了小宝。刘富贵也好,小宝也好,他们脸上分明有着笑,可是那些笑又都被他们努力藏着,藏也藏不住,正从嘴角漏了出来。
到了门口,刘富贵和小宝站住了,脸朝后面看。
“你进来!”刘富贵冲外面招着手。
“你进来!”小宝也冲外面招着手。
还会有谁来呀?一双双眼睛盯着门口。
竟是玉兰来了!玉兰大大的肚子一下子撞上所有的眼睛,撞得那些眼睛生痛,撞得他们一时都忽视了她的头,她的头上生着细密的头发,像初春的草地。
玉兰羞怯地笑着。
小宝大声地说:“咱妈不是麻风了,咱妈要生小妹妹了!”
刘富贵嘿嘿笑着,是把秘密公开在大家面前的的笑,是骄傲的笑。
责任编辑:刘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