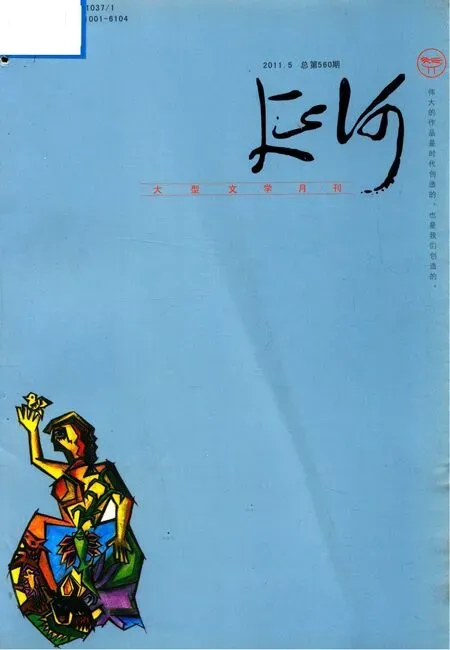小说之外的帕慕克
陈言
小说之外的帕慕克
陈言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宗笑飞 林边水 译
《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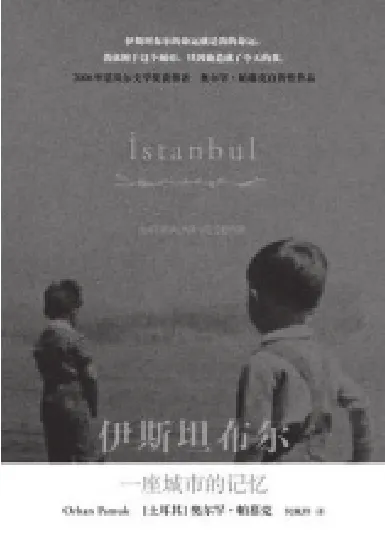
奥尔罕·帕慕克 著 何佩桦 译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本书写的既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更是这座城市的忧伤。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这个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如今作为作家的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杰出天分,重访家族秘史,发掘旧地往事的脉络,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跟随他的成长记忆,我们可以目睹他个人失落的美好时光,认识传统和现代并存的城市历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伤。

奥尔罕·帕慕克 著 沈志兴 张磊 彭俊 丁慧君 译 《雪》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四天四夜里。主人公卡,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借着记者的身份在土耳其偏远小镇卡尔斯城游逛。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宗教……这些冲突把卡尔斯城的人们分为两极,整个小镇的氛围充满了压抑、愤怒、阴谋和暴力。大雪封途,卡尔斯通往外部的一切交通都被割断。大雪下得无休无止,杀人的枪声响起在舞台上,卡尔斯陷入了军事政变的恐怖之中。爱情故事、恐怖谋杀案、历史纠葛及政治冲突,都浓缩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城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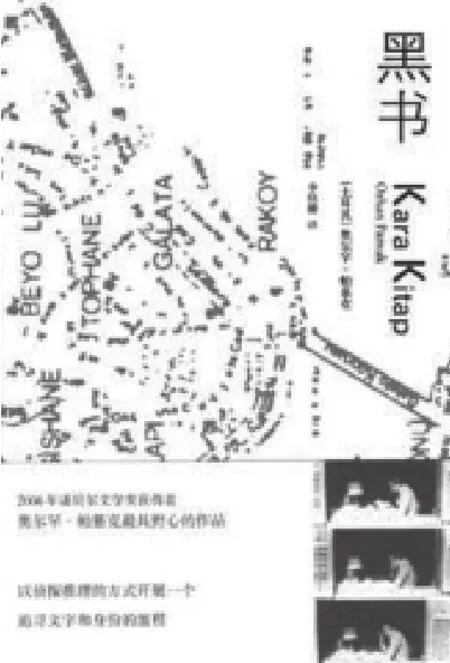
奥尔罕·帕慕克 著 李佳姗 译 《黑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本书是一部迷宫般叙事繁复的小说,而其主题也同样呈现出意义的网络化格局。作者融情节、故事、历史、虚构文本、自传成分等于一炉,各种元素交叉并存,形式和主题都体现出强烈的帕式色彩和鲜明的原创性。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至少是有成为伟大小说的野心的作品。堪称作者集大成的作品。
帕慕克的随笔集《别样的色彩》大约迟到了两年。两年来,我不断从媒体和豆瓣新书推介栏中看到即将上架《别样的色彩》的消息。之后是一再推迟,许是翻译问题,也可能是审查流程?有时也能听到被删节后的《别样的色彩》的传闻,然而,大约因此而增加了我对《别样的色彩》的期待,就像是从前迫不及待地阅读这种或那种所谓的“还原本”。而事实上,我和朋友们当年开始阅读帕慕克的作品完全是因为他所谓的“政治问题”未解决而被暂时拒绝在诺奖门外。
从《我的名字叫红》开始,世纪文景集团基本上出齐了帕慕克的作品,据说多少人因为出帕慕克的书而狠赚了一笔,帕慕克接受访谈的时候有些自豪地提到不完全统计他每本书都有超过五十万的读者在读,如此大红大紫真是使得多少作家和准备成为作家的读者羡慕。大江健三郎说他的书好卖的时候只有五万,高行健未获诺奖之前在台湾出版只销售一两百本,赫塔•米勒的书在国内出版不但打折还用绘有她头像的帆布袋作为促销手段,要是帕慕克的父亲还在的话,肯定是要为此大为吃惊的,他该用怎样的表情和动作去迎接对他惦念和“计较”的儿子呢?帕慕克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偏远一方的伊斯坦布尔会成为世界的中心,而非他从前和父亲一样神往的“欧洲”。
然而,帕慕克说,他为阅读和写作整整进行了三十多年,他感叹歌德、托尔斯泰他们更是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他谈到写作的艰难,这艰难不仅仅在于创作的困难,也在于你对生活的认知。帕慕克提到自己每天都要在写作区工作十个小时,然而,相对于小说中有用的部分,他一天也就平均只写了半页,不过这半页曾怎样反复地折腾着他,让他深陷其中,让他如病人吃药丸一样,他吃着文学的药丸,帕慕克谈到文学写作事实是在依赖文学的药丸,是半死之人,是解瘾的毒品。这话很深刻,然而,本雅明似乎也谈到类似的意思。帕慕克在行文之间一直在探讨“写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他自己给出了不下于十来种的答案,有真切感触的是,独处的意义,生所有人的气,只能靠改变来分享真实的生活,为了渴望写作,为了单纯的快乐。关于“独处的意义”帕慕克给出了有些为难的答案,他“计较”他父亲的地方就在这:缺乏独处的勇气。而所有的作家事实上也只能在“独处”中“低语”,也许,他有时在其中顾影自怜,有时是在建立自由王国,有时他在房间中“颓废”“丧气”,有时他要越过那不曾被注意的玻璃窗,外面的世界又是另一种色彩,有他喜欢的树林和风景,然而,更多的时候,一个作家只能在一堵围墙中“固执己见”。帕慕克又为“学会独处”给出了诸多的理由,然而,他矛盾的是为什么总是疑虑真实的生活已经被他所忽略过去,他不无忧心地想,那么真实的快乐如他父亲那般已经和他擦肩而过吗?在父亲的手提箱中,帕慕克害怕的不是父亲的作品写得差,而是万一父亲在过着另一种他那么嫉妒的生活却写出惊人的作品。不过,帕慕克似乎很早就找到他想要的答案,这答案就在他的写作区。帕慕克认为作家应该把居住区和写作区分开的,因为日常的平淡和乏味会冲击一个作家对艺术的想象和渴望。所以,他总是由居住区走向写作区,要在那里呆上十个小时,也许是毫无收获的十个小时,他就这样坚持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像蚂蚁一般在啃着空白的纸张。和积极介入生活的作家不一样的是,帕慕克的写作或者说“独处”也许更像是要回到书斋中,回到“纯小说”的写作中,帕慕克无奈地阐释优秀的作家介入政治的弊端,他认为写作就是写作,回到纸和笔的呼吸中,大多数被卷入政治的作家是被动的,帕慕克认为那不是为了介入政治,而是他们的自尊被伤害,被羞辱,于是他们捍卫的是一种精神,而非事件本身。帕慕克对政治的态度,是远离和微观,他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来解读政治和生活,然而,我有时觉得,他写到的那些政治和生活本身似乎有些不太可靠,虽然帕慕克用了诸多的影像记录来证明他小说的根据所在。其实,帕慕克的理想是文学化的政治,文学化的生活,文学化的世界,等等。不过,有时却未免也太文学了,导致他的小说和谈论他人小说有流于表面的感觉。这大约只是我个人的粗浅之见。
帕慕克在《别样的色彩》中解读了一些伟大的作家,诸如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等,帕慕克反复强调福克纳和普鲁斯特的意义。只是帕慕克对这些作家的解读未免有些散,他对小说的文本过于重视,而忽视了小说之外的层面,也许,那是因为帕慕克不太感兴趣小说以外的真实。帕慕克在序言中就直接谈到他这本随笔试图和本雅明一样,不着边际,碎片中汇聚着一个框架,恰如他所云,隐含的作者。然而,我并没有从帕慕克的解读中找到眼前一亮的启发,帕慕克更多是对前人的小说感触修修补补。加上,帕慕克不加节制的叙述,他的小说阅读和艺术见解起码是“臃肿”。有时,我读到他的几部小说,感觉可以再压一压。帕慕克对文学太过于“顾影自怜”,也许,换个角度来理解,那是对文学的一种可贵的信念。不过,这可贵的信念到了赫塔•米勒笔下就变得深沉、内敛。也许,库切会更加节制。我在读帕慕克的小说和随笔的时候,总是奇怪地发现,帕慕克的语言缺了点什么,他语言速度也许过于快,过于流畅,对内心的分辨率似乎要求不是很高。前阵子,帕慕克出了一本新的小说,《纯真博物馆》,我总疑心帕慕克写得太聪明了。他的小说张弛有度,故事完整动人,加进了不少的元素,这些元素中帕慕克最喜欢加的是“情”素。也许,那是因为土耳其人身上的浪漫色彩,哪怕是“呼愁”也许也是有些“情”素放纵的可疑。这大约也是土耳其电影或取镜土耳其背影的电影给我的印象吧。然而,帕慕克其实是很有感触的一个作家,他时常会说出一些特别有感触的句子,比如,写作是生所有人的气,思想的自由是内心的愤怒所带有的快乐,如讲述别人的故事一般讲述自己的故事,如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般讲述别人的故事,有耐心和希望才能建造一个深刻的世界,真正的文学始于一个人将自身与作品关在房中之际。等等。
帕慕克的《别样的色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也希望单纯地阅读和写作。如他所言,写作就是为了单纯的快乐,包括快乐地编制故事,快乐地沉浸在故事的绵绵不绝中。只是,这大约是帕慕克书生气的一种表达。我读到帕慕克的几部小说,比如《白色城堡》、《黑书》、《新人生》、《寂静的房子》、《纯真博物馆》、《雪》、《我的名字叫红》以及自传《伊斯坦布尔》,有个感觉就是他的叙述有些过于放松,甚至叙述的视角有些流行的色彩,他的张弛有度,和故事的完整,多有前人的痕迹,他自己说已经探索了实验了,实际上真正走出还是很少。他是属于那种有特点又能综合他人文本特色的作家,然而,因为背后缺少了更为敏感和更为强大的关照,让他的小说整体有点“轻”。也许,慵懒的人都是喜欢“轻”的。最近,我发现,不少红火起来的作家,都是“轻”得可以,类似卡佛、麦克尤恩、保罗•奥斯特、村上春树等。追求故事的完整,叙述的愉悦,谈论的不外是周边的细小事情,可感可发,也许还有赏玩,乃至有了一些小聪明。这也许是文学的另一面。这另一面中是不需要刻板,不需要严肃,不需要耿耿于怀,更不需要不安,大不了就是个人的得失。然而,有时,我想,也许,这是文学吸引人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动枪呢,为什么要“咆哮”,要那么神经质呢?帕慕克说他一直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然而,我并没有发现他笔下的人物有这个倾向,倒是感觉,外国“轻”一代小说,多是用“冷观”的态度看待世界,用“抚摸”的姿势来安慰自己。苏珊•桑塔格在《文字的良心》一文中提到个人在西方世界的进一步演化,她对此是有些感触和态度的,可惜在我们的生活中,个人似乎还没强大到可以演化到另一面的意思,也许那只是出现在得志的人那里,那些有模有样的人的幽居和赏玩,多数人依然是没有“个人”,你对他们喊一声“你个人了吗?”,会是黑色幽默一番。如此,我感觉到在帕慕克他们那里,“轻”成为了可能,而在我们无所不在的“洁本”“净本”中,叙述变得有些微妙和艰难。事实上,帕慕克写到《雪》中卡尔斯为了避免被害和麻烦,他提前就去拜访了警察局长们,他提前的“招呼”也许只会是土耳其式,大约法国作家那里就更为自在了,然而,有时我想,当我们下笔,起码在现在,要写一句“轻”点的话,就容易把自己推到一个尴尬的地方。因为,你已经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你真实的处境。你的处境是什么?真实的?你想要什么处境?你的叙述就在探讨或回避这些?这时候,你真的可以很放松地写吗,你会那么自在自信地以为别人以后就会吃上你开始生产的文学药丸吗,他可是半死之人。这何止是生活和忧虑。
为什么一定要沉重?为什么不可以自在地愉悦地翻阅起帕慕克的《别样的色彩》,然后,你说,很吃惊于他那么单纯地写作和阅读,那么单纯的快乐和坚持。可也许,你忽略了,帕慕克的叙述同样带来了危机,母子的疏远,兄弟的隔膜,国人的警戒,这因为文学不仅仅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那恶魔保证了写作者的健康。
栏目责编:张艳茜 宋小云 刘全德 何超锋 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