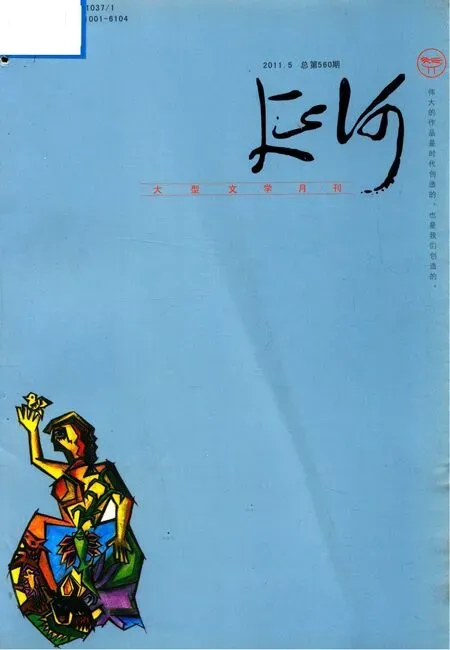把繁哈尔带到夜晚的人
杨永康
把繁哈尔带到夜晚的人
杨永康
九点钟的吉他弹奏者
九点钟,一个胖男人走了过来,别斯兰惊跳起来,立即跟了上去。大胖男人戴一顶圆顶帽,走起路来左右摇晃着,颈项上的红色皱纹像开口微笑但又苦涩的嘴。突然胖男人转过身来……“盖泰街在哪儿?”“盖泰街在哪儿?”鬼才知道盖泰街在哪儿。然后别斯兰向胖男人开了三枪。胖男人与他的圆顶帽子白痴似的倒在地上,脑袋垂在了左肩上……“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许多年后韩麦尔医生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这么兴致勃勃地问我。
九点钟,韩麦尔医生开始谦卑地与病人们打着招呼。“还习惯吧?”“还习惯。”“还行吧?”“还行?”瞧,他就是这么好。好像我们的病老不见好全是他的错似的。然后开始为我量血压,测体温,我总能听见他的心跳。盖泰街在哪儿?”“盖泰街在哪儿?”鬼才知道盖泰街在哪儿。然后别斯兰向胖男人开了三枪。胖男人与他的圆顶帽子白痴似的倒在地上,脑袋垂在了左肩上……“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如果病人不多,韩麦尔医生会一直这么不紧不慢地问下去。最后在我的病历上写上血压、体温等等。有时候也问问鸽子好看还是飞鱼好看,我说鸽子好看,飞鱼也好看。他说要是选一种呢,我说那就鸽子呗。有一天,他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来,是一双漂亮的女式拖鞋,图案是一只白色的鸽子。我说别人送的吧?他说不是不是。老婆的手艺?他说不是不是。最后才知道那是他的手艺。我说真看不出你是个好丈夫,他只是谦卑地笑笑说,算不得好丈夫,算不得好丈夫。

山村小店 倪贻德 1948年 水彩 23.8×28.8cm
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韩麦尔医生。顶替韩医生的是一个姓杜的医生。杜医生量完血压测完体温,就要我们一个个地张大了嘴巴。一直建议我去看牙医,说我的牙里总有一天会长出虫子。常常把他的不带手套的一个指头或者五个指头伸进我的嘴里,开始我还有点恶心,慢慢的就习惯了。有一次吐出一截肠子,杜医生说是虫子虫子,我说是肠子,化验来化验去,还是肠子。为避免更多的肠子被恶心出来,他建议我张开嘴巴的同时伸出舌头。伸出舌头与张开嘴巴简直没有任何关系嘛,他很不高兴地说,叫你伸出舌头肯定有科学道理的。慢慢的我发现,还真有科学道理耶。只要舌头伸着,任你怎么怎么的恶心,也不会吐出肠子什么的。老发现不了虫子,杜医生沮丧极了,我也沮丧极了。我真心希望我的嘴巴里早点出现虫子,以便减轻对韩医生的怀念。我甚至吃了许多带虫子的苹果或者水果什么的,为杜医生也为韩医生。杜医生好像并不领我的情,只是一个劲让我张大嘴巴伸出舌头,然后在对面的一把黑色椅子里耐心地等。我曾自言自语地说:“人类的面孔除了做出表情,其他什么用处都没有,”他一直未予理睬。还好,有一天韩麦尔医生又悄无声息地回来了。老习惯一点未改,九点整,谦卑地与每位病人打着招呼。“还习惯吧?”“还习惯。”“还行吧?”“还行。”然后开始为我们量血压测体温,我总能听见他的心跳。我悄悄地问他,还好吧?还好,还好。应答还是那么谦卑。“鸽子”呢?她不喜欢鸽子。她喜欢飞鱼?她这人既不喜欢鸽子,也不喜欢飞鱼。那就换个小熊、小狗、小猪吧。后来我才知道,他老婆压根就不喜欢他编织的那种鞋子。有一天量完血压测完体温韩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叠散见于大街小巷的那种牛皮癣广告单来。有美容师培训班招生启事,有按摩师培训班招生启事,有去除鸡眼培训班招生启事,有去除狐臭培训班招生启事,有驾驶员培训班招生启事,有健身俱乐部招生启事,有厨师培训班招生启事,有少儿书法培训班招生启事等等吧。我与他开玩笑说,做广告啊!他说他想上这些班呢。这么多啊?他说不多不多,只是没有想清楚先上哪一个。我说这好办啊,随便选一个不就得了。他说不行的,必须是他老婆喜欢的。我说干嘛不上个自己喜欢的班呢。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上一个少儿书法培训班呢。我说那就上这个少儿书法培训班呗,他嘀咕说人家要八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我说现在的培训班哪个不是为了赚钱?后来他一口气上了美容师培训班、按摩师培训班、去除鸡眼培训班、去除狐臭培训班、驾驶员培训班、厨师培训班,唯独没有上那个他梦寐以求的少儿书法培训班。
韩麦尔医生说不见就不见了,病人们心里都空落落的。我也一样,希望他早点学成归来。后来听杜医生说,学成归来个屁呀!韩医生病了,他老婆跟一个身强力壮的三级厨师跑了。病人们都很感激杜医生,总算有了韩医生的权威消息。量完血压测完体温,我们就自觉地张大了自己的嘴巴,伸出了自己的舌头,然后等待杜医生把他不带手套的一个指头或者五个指头伸进我们的嘴里。我们都真心希望我们的嘴巴里早点出现虫子,以减轻杜医生对虫子的莫名沮丧。我们都吃了许多带虫子的苹果或者水果。杜医生并不着急,只是坐在对面一把黑色椅子里耐心地等,等,等,等。电视里说最难对付的就是可爱的女人与可恶的机器,卡夫卡笔下的机器。要我说最难对付的就是这种有十足耐心的人,坐你对面永远一声不吭,永远没完没了。我以前有个同事,整天坐我对面捂着手盯着我看,我找来许多书,在我与他之间垒起一道书墙来,免得他老盯着我看。有一次我在外地的女同学来访,他时不时地假装吸烟什么的站起来向我这边看看,时不时地假装伸伸懒腰什么的站起来向我这边看看,害得我一个劲向老同学鞠躬致谦呢。最难对付的就是这种有十足耐心的人,比如杜医生。最先受不了的不是我,是那些女病人。她们向医院举报了杜医生的所作所为。院长找杜医生谈了话。杜医生一个劲地对院长发誓,一定有虫子一定有虫子,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还告诉院长,他在大街上看见了韩麦尔医生,韩医生嘴里不停老念叨着——别斯兰向那人开了三枪。是的,三枪。那胖男人与他的圆顶帽子白痴似的倒在地上,脑袋垂在了左肩上,左肩……韩医生还告诉每个过路的人他为了他老婆历经千辛万苦上过繁哈尔最好的美容师培训班,最好的按摩师培训班,最好的去除鸡眼培训班,最好的去除狐臭培训班,最好的驾驶员培训班,最好的健身俱乐部,最好的厨师培训班。
我一直为杜医生感到遗憾,人类医学发展到今天,就应该让杜医生从一个小小的嘴巴里找到虫子。有一本杂志上说,科学家已能轻而易举地分离出活细胞,确定维持细胞活动的分子动力。他们研究了细胞如何储藏信息并传给下一代;细胞何时生长和死亡;它们怎样经过特殊演化形成人类。他们也知道了细胞是如何恶变,生成病原菌或无限繁殖而导致癌症的。可是至今没有一种方法让杜医生从一个小小的嘴巴里找到虫子。多年后我走在繁哈尔一条街上,依然为人类医学发展感到遗憾,为杜医生感到遗憾,为那只一直没有出现的虫子感到遗憾。刚刚下过一场雪,空气清新而凛冽。有雪真好,活着真好,健康真好。一辆红色的汽车与一辆灰色汽车追尾,排气管正冒着白白的热气。冒着热气真好,这世界缺的就是冒着热气的东西。是的是的是的,这世界缺的就是冒着热气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别斯兰身上出了一身冷汗。把它放进裤兜里,走在大街总感到那东西像一只螃蟹紧紧地贴在他的腿上他的裤子上。他僵硬地走着,不时的把手伸进裤兜,慢慢的头上就开始冒热气了。有一天胖子还这么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那一晚我与胖子在五七大街吃了好多好多西瓜,我坐在台阶上,胖子坐在一把破旧的椅子里,椅子一直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胖子吃了好多好多西瓜,离开的时候往他的红色电动车上也上不去了,醉了似的。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家伙扶上车。红色电动车一转眼就不见了。红色真好,醉了真好。许多年前繁哈尔出现了一群诗人。一个醉了,纷纷都醉了。一个人哭泣,纷纷都哭泣。醉了真好,哭泣真好,纷纷真好,大家真好。前几天参加一个所谓的文学活动,到处都有人在喊王局长、李局长、张处长,到处都是点头哈腰的人。这世界缺的就是一次真诚的醉与一次真诚哭泣。这世界缺的就是一群天真烂漫时不时会醉、会哭泣的诗人。还有孩子。是的是的是的,还需要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
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停下来观看那些戴着红领巾列队行走的孩子。九点钟,那些小红领巾们会列队走进校门。我常常混迹于那些送孩子的家长们中间,在他们中间呆很久很久。到处都是鲜艳,到处都是笑脸。我一直为他们身上的一些东西着迷。是的是的是的,我一直为他们身上的一些东西着迷,就如同韩麦尔医生为那些我叫得上我叫不上名字的培训班着迷一样。这世界不会因韩麦尔医生而变得好或者更坏,但韩麦尔医生身上确实有许多这世界没有的东西,参加过韩麦尔医生追悼会的人都这么说。杜医生也这么说。韩麦尔医生的追悼会简朴而得体,去了好多好多医生,去了好多好多孩子。韩麦尔医生躺在一口小小的松木棺材里,十分安静。远远的可以望见他略显抑郁与清癯的脸。悼词有力而温馨。韩麦尔医生原毕业与某某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多年来从事颈椎、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与研究。曾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在治疗颈、腰椎病方面获得广泛认可。婚后幸福美满。曾历经千辛万苦上过繁哈尔最好的美容师培训班,最好的按摩师培训班,最好的去除鸡眼培训班,最好的去除狐臭培训班,最好的驾驶员培训班,最好的健身俱乐部,最好的厨师培训班……
再也不会有人每天靠近我的耳边低声地问我,别斯兰就向那人开了三枪么?是的,三枪。左肩么?是的,左肩。再也不会有人兴致勃勃地问我飞鱼好还是鸽子好。再也不会有人兴致勃勃地问我美容师培训班、按摩师培训班、去除鸡眼培训班、去除狐臭培训班、驾驶员培训、厨师培训班、少儿书法培训班哪个好。可是,可是,可是,有一个人还在沿基奈大街拼命奔跑。是的是的是的有一个人还在沿基奈大街拼命奔跑,一些蠢货们正在他身后高喊抓杀人犯杀人犯。于是又传来两声枪响。人们立即叫嚷起来,如鸟兽般地散开,散开散开散开……九点钟,出现第一批人质与第一批受害者,接着是第二批第三第四批……基奈大街第一次显得拥挤。九点钟,全世界的人都被事件与时间绑架。两个穿黑大衣的男子正拼命追赶一辆已经离开车站的公共汽车,车门已经关上。有几个缩着脖子的人在路边修一台油漆斑斑驳驳的抽水机。一个男人正在希思罗机场的一辆婴儿车里酣睡,远远地可以看到他伸在婴儿车外面一只很大很大的脚。九点钟,一个胖男人走了过来,别斯兰惊跳起来,立即跟随其后。那胖男人戴一顶圆顶帽,走起路来左右摇晃,颈项上的红色皱纹像开口微笑但又苦涩的嘴。突然那家伙转过身来……“盖泰街在哪儿?”是的是的是的,“盖泰街在哪儿?”鬼才知道盖泰街在哪儿。然后别斯兰就向那人开了三枪。那胖男人与他的圆顶帽子白痴似的倒在地上,脑袋垂在了左肩上……“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九点钟,别斯兰穿过一家咖啡馆,来到洗手间的尽头,然后用手中的枪对准了自己的前额……九点钟,事物第一次如其所曾是,事物第一次如其所是,事物第一次如其不久以后所将是,草第一次变绿又变灰。肯定有一支超越我们的曲子,肯定有一把兰色的吉他,肯定有虫子在我们的嘴巴里。他们说你有一把蓝色吉他,你弹奏事物并不如其所是。事物如其所是,随着蓝色吉他而改变。但是要弹奏,你必须,一支超越我们的曲子……九点钟真好。
九点钟,我在梅伦车站打开一份很旧很旧的报纸。有人在我背后兴致勃勃地喊了一声:杜——医——生,或者韩——医——生。
无法分辨的萝卜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扛一把巨大的木梯,拖着僵硬的、机械的身躯,在繁哈尔的夜晚奔跑,不觉得饥渴,不觉得累,分辨不出任何东西。繁哈尔的夜晚无穷无尽,繁哈尔的夜晚悄无声息。多么丰沛的夜晚,多么丰沛的时间。有足够的夜色供你奔跑,有足够的夜色供你挥霍。许多失眠症患者都这样的,不知道他们能否分辨出哪儿是夜,哪儿是烟?熬人的夜,呛人的烟。我能分辨出夜与烟。我是说在夜里、在烟里我能分辨出漫无边际的夜与烟,繁哈尔的漫无边际。不是那种呛人的烟,是繁哈尔傍晚袅袅的炊烟,缭绕于繁哈尔茂密的树丛与牵牛花间。借助茂密的树丛与牵牛花可以分辨出繁哈尔丰沛的阳光,丰沛的雨水,丰沛的芬芳,繁哈尔的萝卜与木梨。许多年前,繁哈尔丰收过一次萝卜与木梨,我与叔母在松软的泥土里,拔呀拔,搬呀搬,整个秋天都在拔、都在搬比我的个头、比叔母的个头还要大好多好多的萝卜与木梨。叔母一会儿喊我的名字,一会儿喊萝卜的名字,一会儿喊木梨的名字。繁哈尔的一切都有名字,包括木梨,包括萝卜,包括每一朵花,每一种汁液,每一种丰沛。声音越过繁哈尔的茂密树丛与牵牛花,遥远、神秘、清晰。我最喜欢的是牵牛花,长长的一串。奶奶老说这种花摘不得的摘不得的,一摘,吃饭的时候,碗就会无缘无故地掉在地上,可是孩子们还是喜欢那种花。闹饥荒的那些年,叔母与奶奶就整天带着我满山满野的找野菜。全村人都找,自然这野菜比金子还少,叔母就摘了好多牵牛花。叔母吃,奶奶吃,我也吃。吃后肚子奇胀,叔母就煮熟了给我们吃。许多年后,叔母头巾里还包了许多牵牛花呢,芬芳无比,走到哪都在衣服里面掖着。我问叔母,还在吃花么叔母?叔母说,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还掖在衣服里?掖着心里踏实呗。怎么个踏实法?你闻闻就知道了。找到一朵牵牛花,就可以找到整个芬芳无比与整个繁哈尔。
叔父正安静地坐院子里。有一次我们吵吵嚷嚷着闯进一座空旷的院子,院子有一棵巨大的木梨树,我们在树上树下摘啊吃啊吵啊嚷啊,闹够了,才看见树下坐着一个安静的人,书页在哗啦哗啦地响。孩子们都吃惊不小,嘴巴一下子愣在了那里……那些张开的嘴巴许多年后还那么汁液丰沛纹路清晰。安静的人偶尔过来与爷爷一起喝喝茶。爷爷一辈子都喜欢茶,熬得像油似的茶。一年四季都在喝,茶香在村子里飘了许多年许多年。常看到过路的客商坐下来喝一会儿茶,纳一会儿凉,陪着爷爷天南地北地说着话,我在一旁给爷爷扇着扇子,蒲叶做的那种。客人重新上路的时候行囊里全是淡淡的茶香了。闹饥荒的那些年,村里到处都是红薯干的气味,到处都是饿得发慌的人。有一个人晚上去偷吃村里的喂牲口的萝卜叶子,吃了一晚上,拉了一晚上的绿水,不长时间就死了,听说死的时候整个肉体都透亮透亮的。还有一个人偷吃玉米棒子的芯子,吃太多,排泄不出来,像牲口那样哭嚎了几天几夜,死了。爷爷一直安静地坐在自己的茶房里,喝那熬得像油一样的茶,爷爷常留点吃的给我,怕我饿着。爷爷说,他有茶就行。爷爷晚年半身不遂了,起居勉强能够自理的时候,茶照喝,去世之后许多年爷爷住过的屋子里仍然满是茶香。与爷爷不同,安静的人喜欢喝很淡很淡的茶。喝茶时很少说话。喝完茶,就重新回到那棵巨大的木梨树下,安静地看自己的书。那些年代谁不饿呢,安静的人也饿。每次饥饿难奈的时候树上就会落下许多金黄金黄的叶子。安静的人去世了好多年好多年,那些叶子依然金黄如昔,灿烂如昔,安静如昔。
我一直想看看真实的叔父与真实的叔母,他们的照片开始在一面墙上,后来挪到一个镜框里了,再后来就怎么也找不见了。我问过奶奶,奶奶说哪能说得准呢,那么多年了,也许散落在草里了,也许在哪个柜子里面。我翻遍了几个柜子,找到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一个戴红花的人多么像我。许多年前繁哈尔曾举行过一场隆重的婚礼,宾客们站满了院子,戴着大红花的新郎新娘,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直到繁哈尔的暮色来临。村子里到处都是喝醉了酒摇晃着回家的人,到处都是唢呐声……酒是母亲亲手做的,乡亲们都喝得摇摇晃晃。我也喝得摇摇晃晃,隐隐约约记得自己先是撞在一面墙上,接着撞上了一堆坛坛罐罐,接着坛坛罐罐与空空荡荡剧烈相撞,空空荡荡与一架巨大的木梯剧烈相撞……
对,木梯,现在我正如愿以偿扛一把巨大的木梯,在繁哈尔的夜晚奔跑。总有一些事物比我跑得更快,比如白蚁,比如时光,可以眨眼间让整个繁哈尔物是人非……我们不可能比白蚁比时光更幸运,无法看到更多。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散落在草里的坛坛罐罐。我隐隐约约记得自己先是碰在一面墙上,接着与一堆坛坛罐罐剧烈相撞。母亲为我们的婚事准备了那么多酒那么多酒,几乎装满了繁哈尔的每一只坛坛罐罐。每年入冬,母亲就开始为年节酿酒了,院子里摆满许多坛坛罐罐,有自家的,也有邻家的,院子里整天都是米酒的香。这种酒大人小孩都可以喝。有一个叫小利的,一口气喝了多半碗,爬上了一棵树,在树上唱了一个晚上的红灯记。一会儿李玉和,一会儿王连举,一会儿李铁梅,唱谁像谁。家里人怕出事,怎么喊小利就是不下来。那一夜许多人在雪地里酣睡,许多人变成了小矮人,一个比一个矮。
小利比我小一岁,我们两家住的很近,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点着灯通宵通宵地看书,他有时候过来在我身边坐一会儿,带点他家里的果子什么的。两家间有一段不长的小坡路,若是在深夜,他就一路唱着王连举回去,王连举是坏人,坏人的胆子大,给自己壮胆。小利力气特别大,胆子特别小。我知道他胆子小,在他回去之前,故意给他念一段书里的鬼怪故事,听得小利身体一个劲地往衣服里缩。小利是单亲,父亲文革中是村里的出纳,挪用了村里的钱,上吊了。小利的母亲嗓门特大,骂小利的时候,全村差不多都听得到。小利的母亲开骂的时候,小利就偷偷窜我们家来了。我有时候不忍心,也送一些东西给小利,大半是小人书或者铅笔头什么的。小利不喜欢书,学上着上着就上不下去了,书里有好人的他全撕下来糊墙了,只留着那些坏人,比如王连举什么的。小利说,好人没有啥用,坏人吃得香。铅笔嘛,小利折成几截埋在村里的向日葵地里了。活该小利倒霉,那正是向日葵成熟的季节,小利正蹲地里埋几截的铅笔头呢,让老虎给逮住了。老虎远远地看见小利鬼鬼祟祟在向日葵地里转悠,猜想小利不会干什么好事,一逮还真逮了个正着。
村里的向日葵全由老虎看管,老虎姓韩名虎,我们都叫他老虎。那一年干旱,村里集中了许多丁壮劳力挖井。挖了几十丈深,总算挖出水来,清冽的井水一桶桶汲了上来,你一口他一口抢着喝。老虎没注意掉进刚刚出水的井里了。老虎住了好长时间的院,一条腿残疾了。一般活干不了,就给村里看管这眼机井。井慢慢干涸了,老虎没事干了,村长就把村里的向日葵地交给老虎了。老虎此后就认认真真地看起村里的向日葵地来。也许是在向日葵地里转悠久了,老虎的脚也慢慢没有那么臭了。老虎有点失落,整天打不起精神来。没有多长时间老虎长出一对大门牙来,村里人说那是老虎偷吃村里的向日葵子多了。向日葵地靠着公路,经常有卡车路过。那些年卡车司机倍受女孩子们的青睐,卡车司机也特别青睐女孩子,一招手准停。路长,解解闷。向日葵地多好啊,远远地望去,一片金黄。老虎对卡车司机的歪脑子掌握得一清二楚,这么说吧只要你在这篇向日葵地里动个什么手,动个什么脚的,一准让老虎逮个正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给老虎散根纸烟,老虎一般都高抬贵手了。开始起些作用的,后来碰到这种事,老虎不买账了,卡车司机连话也搭不上了。卡车司机的女朋友有聪明过人的,便一个劲赞美老虎的两颗大板牙来,说她刚好有个妹子对大板牙男人特着迷,她虽然与老虎不沾亲不带故的,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老虎听了高兴,那么漂亮的女人说他的大板牙长的好,肯定好呗。要不是在向日葵地里倒霉地碰上小利,老虎与他的大板牙会一直美好地等下去的。
小利把我给的铅笔折成几截埋在村里的向日葵地里,过几天想那些铅笔了,就溜进向日葵地里挖出来看看,过几天烦了又埋进向日葵地里。小利刚在向日葵地蹲下身子,老虎就一把抓住了小利的领口。干啥呢小利?小利说没有干啥。没有干啥怎么蹲在村里的向日葵地里?接下来就是许多难听话了。老虎走出向日葵地的时候一对大板牙没了。老虎咽不下这口气,回家找出一杆土枪来,里面装满了火药与沙石,对准小利家的烟筒就是一枪,尘土飞得老高老高的,小利憋气一斧头砍倒了老虎家门口的一棵参天大树,惊得树上的乌鸦在村子里盘旋了好多个下午好多个下午……
许多年后我问奶奶,老虎的门牙真给小利打掉了?老虎真的开枪了?乌鸦真的在村子里盘旋了好多个下午?奶奶只是笑笑说,老虎的命不错的,老虎后来娶了媳妇生了子。小利的命也不错,媳妇给小利生了一儿一女,儿子上小学了,得了脑炎,最后伤了。再后来小利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小利力气大,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叫小利来我们家帮帮忙,干干特需要力气的活,比如推着石磨磨磨面,搬搬麻袋什么的。小利干什么都一声不吭,与他一起干活特别闷,特别是磨面这种活,本身够闷了,再加一个一声不吭的小利,简直能闷死人。有一年正与小利推着石磨在我们家磨坊里磨面呢,地震了。我把手里的推磨棍一扔就跑到磨坊外面去了,在村口待了大半夜。回磨坊一看,小利还在一圈一圈地推磨呢。昏暗的煤油灯在磨坊里一闪一闪的,小利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很长。父亲与小利倒挺投脾气,小利干完活,父亲早温好了一壶酒,一杯下肚小利的话就多了起来。一说就是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夏夜麦子打碾时节,父亲躺在我们家的麦场上,小利躺在他们家的麦场上,常常会说一整夜话,月光照在父亲进入梦乡的脸上,小利进入梦乡的脸上,及麦垛旁一把小小的木梯上。夏天的后半夜露水多,我一直想替父亲守守麦场,父亲总是不肯,小利也不肯。我曾代替父亲守过一夜的,我躺在我们家的麦场上,小利躺在他们家的麦场上,月光照在我进入梦乡的脸上,也照在小利进入梦乡的脸上,及麦垛旁一把小小的木梯上,就是一夜无话。小利沉闷,我也沉闷。父亲说还是他守麦场吧。小利外出打工了,我们家的麦场还是由父亲守。我说还是我守吧?父亲说还是他守的好。小利在还可陪你说说话,小利打工去了,还是我陪你说说话吧。父亲说,有明明亮亮的月光呢。我不放心父亲一个人守麦场,抱出了院子里的小狗,这样月光下就有许多东西陪父亲了,明明亮亮的月光,安静的小木梯,安静的麦垛,安静的小狗,如果再加上一壶酒与小利就完美无缺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让城里人耿耿于怀许多年许多年的。
父亲一辈子吃得香,睡得也蛮香,头一挨枕头,就呼噜打得震天响。父亲进入梦乡的时候全村人都进入了梦乡。月光多亮,父亲呼噜照打不误。太阳多烤,父亲照睡不误。一秒两秒钟都可以睡得很香。只是睡觉见不得小狗的,不是见不得小狗叫,而是见不得小狗睡在自己的旁边。我回家总提醒父亲身边有个小狗多好,好歹是个伴。有个好人歹人的,总可以给你提个醒。父亲睡觉总要大开着门户。有一次窜进来一个小偷来,那小偷见我们家门户打开,主人呼噜打得震天响,开始以为是个圈套,在院子里东张西望了许久,发现除了打呼噜的主人外空无一人,便胆子大了起来,干脆登堂入室了,见父亲还是呼噜如故,故意咳嗽了一声,父亲的呼噜仍然是那么响。小偷不好意思下手,就自己找来一袋烟,直到满屋子烟雾缭绕了,又使劲咳嗽了一声两声才笑着离开。父亲听见笑声醒来了。父亲脑溢血后,躺在病床上打点滴,还是平时睡觉的那习惯,呼噜照打,只是永远也没有醒来。作为儿女,我们都希望父亲还像从前那样睡得香。村里人也一样,都希望父亲呼噜打得震天响,世道不靖,有父亲的呼噜在,安全。
听奶奶说,父亲去世后小利得了失眠症,整夜整夜地在村里跑,跑得精疲力竭还是睡不着,眼睛通红通红的,像喝了人血似的。有一个晚上拿着斧头砍光了村子里的所有胡桃树,大树小树一起砍,砍得手里的斧子像掉了牙的锯齿似的。据老虎考证小利不是因为我父亲的离开才得了失眠症,才眼睛通红通红的像喝了人血。老虎说,想想看,高速公路,铁路,普通公路,那得毁掉多少房子砍掉多少树啊。越多赔偿的钱就越多呗,那一穷二白的小利还不成财主了?小利贪啊,小利看见钱眼馋啊,眼一馋眼能不红通通么。老虎的话我一直不信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小利完全应该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而不是一双红通通的眼睛才对。前几天我参加一个活动就碰到过一张红扑扑的脸,我是说应该碰到的是一张红扑扑而不是红通通的脸。我们的市长,赶过来为我看酒,市长说他学生时代最喜欢我的乡土诗了,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说什么好。许多年后乡土诗与乡土一样将在整个繁哈尔彻底绝迹。我在电视里看到市长亲手为整个繁哈尔绘制的宏伟蓝图了,好多村子要集中到小镇上一起住了,一起城市化,一起都市化了。说心里话我不怎么喜欢电视里的这张脸,过于盲目、过于自信、过于专制。与电视里的这张脸相比,我更喜欢那张红扑扑的脸与红通通的脸。我相信许多年前市长一定与我一样与小利一样有一张红扑扑的脸,就像一首诗里的高粱或者小麦一样。许多年前在麦地里,在高粱地里,面向全世界的好兄弟背诵各自的诗歌。“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有时我孤独一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梦想众兄弟,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里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

淡水风景 陈澄波 1935年 油画 38×45.5cm
就如同诗里写的那样,许多年前我们都是好兄弟,热爱诗歌的好兄弟,热爱繁哈尔的好兄弟。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为繁哈尔修建了机场、高速公路、铁路等等,还要历尽千辛万苦让整个繁哈尔城市化、都市化,甚至国际化,直到那个叫繁哈尔的小村子变为一座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烟囱的大都市、大都会,而那个叫繁哈尔的小村子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将就此终结就此消失。小利的孩子、老虎的孩子、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孩子乘坐人类已知的任何交通工具,包括市长历尽千辛万苦为繁哈尔建起的机场、高速公路、铁路,再也无法抵达那个那个遍布牵牛花、遍布黄葵、香气弥漫我们都叫它繁哈尔的小村子。
几天前孩子从外地打来电话说,他梦见爷爷了,爷爷还守在我们家的麦垛旁。我问有无月光,孩子说有,很明亮很明亮的月光,月光下是安静的麦垛与同样安静的小木梯。只是老家的院子因为长期无人看管,十分荒凉。锈迹斑斑的锁、倾颓的屋顶,半截木梯年久衰朽散落在虚空里,像一只伸向虚空的手,等待风干……孩子希望我有时间回老家看看,找人清理清理。我理解孩子的感受,我做过许多次这样的梦了。与孩子的梦不同,我的梦里到处都是干净的木梨与萝卜,只是梦里怎么也叫不上那些萝卜与木梨的名字。说明即便那个叫繁哈尔的村子衰败了终结了消失了,一个叫繁哈尔的国际化大都会诞生了(应该是另一繁哈尔,另一个),我与那个叫繁哈尔的村子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无法割舍。一个喜欢喝茶的人埋在那里,一个喜欢打呼噜的人埋在那里,一个安静的人埋在那里,一朵芳香无比的牵牛花埋在那里。那里月光皎洁,遍布黄葵、萝卜与木梨。
我最热爱的叔母也埋在那里。我整天在一棵树下徘徊,怀揣一枚巨大的木梨或者萝卜。老盼着发生一场大水,最好是洪水,一望无际的洪水,让叔母惊慌的洪水,这样我好爬山涉水义无反顾地去救叔母。叔母年纪轻轻就患了肝病,去世前的一个黄昏我去看她。叔母眼睛深陷,脸色蜡黄,躺在一座黑暗的屋子里,屋子里光线暗淡,床头盛满夏天的水果,有几枚桃子开始腐烂,旁边是一只透明的杯子,里面是一些浑浊的液体。借助浑浊的液体,可以看见干瘪的乳房,可以看见一个行囊简单的旅人。一个问路的旅人。旅人,你在找回家的路吗?是的。说说你看见了什么?浑浊的液体,干瘪的乳房。还看见了什么?一只透明的杯子,几枚正在腐烂的桃子。那么摸摸它。曾经的充沛……曾经很充沛很充沛,如同那些巨大而汁液丰沛的木梨与萝卜。有一年夏天暴雨过后,沟沟坎坎都是水。孩子们扑通扑通跳进了小河里,跳进了雨水四溢的坑坑洼洼里。一个猛子扎下去,只有屁股露在外面。应该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叔母,新娘一样的叔母,我不知道叔母是否看见了我,叔母肯定看见了满河、满渠、满洼、满沟沟坎坎涂满泥巴的屁股。我义无反顾地怀揣一枚巨大而汁液丰沛的木梨或者萝卜冲向了新娘一样的叔母……
多年来我一直想告诉叔母,传说中的洪水并没有到来,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为繁哈尔修建了机场、高速公路、铁路等等,还要历尽千辛万苦让整个繁哈尔城市化,都市化,甚至国际化,可是我们并不幸福。昨天下午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笑嘻嘻地拿出一叠表格,告诉我,为了怕我麻烦,他已经代替甲方、乙方与乙方签约了,合同上说,有下列情形之一乙方将被甲方解雇。一、在试用期间违犯甲方的工作纪律,连续旷工超过十个工作日,或一年内矿工累计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二、试用期内,考试不合格。三、违反工作规定或操作规程发生责任事故或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四、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出国或出国不归的。五、未经甲方同意在外兼职影响本职工作的。六、在聘期内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七、严重扰乱工作秩序,致使甲方或其他单位无法正常进行的。八、符合其他法定事由的。非常完美非常完美,只是有一点未被提及。如果我就是那个失眠症患者,拖着僵硬的、机械的身躯,扛一把巨大的木梯在繁哈尔的夜晚奔跑,是否会被解雇?我想那个月光皎洁,遍布黄葵、萝卜与木梨的繁哈尔总有一天要像我一样前途未卜。总有一天那些扛一把巨大木梯奔跑的失眠症患者,会遍布整个繁哈尔。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不会阻止任何人奔跑,任何人失眠,任何人吸烟,任何人拿着锯齿样的斧头砍一棵树。更不会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阻止任何关于那个月光遍地、黄葵遍地、萝卜遍地、木梨遍地、阳光丰沛、雨水丰沛、芬芳丰沛小村子的怀念,对芬芳无比、牵牛花与叔母的怀念。我最热爱的人就是叔母。我整天在一棵树下徘徊,怀揣一枚巨大的木梨或者萝卜,老盼着发生一场大水,最好是洪水,一望无际的洪水,让叔母惊慌的洪水,这样我好爬山涉水义无反顾地去救叔母。而叔母此时脸色蜡黄,眼睛深陷,躺在一座黑暗的屋子里,屋子里光线暗淡,床头盛满夏天的果实,有几枚桃子开始腐烂,旁边是一只透明的杯子,里面是一些浑浊的液体。借助浑浊的液体,可以看见干瘪的乳房,可以看见一个行囊简单的旅人。一个问路的旅人。旅人,你在找回家的路么?是的。说说你看见了什么?浑浊的液体,干瘪的乳房。还看见了什么?一只透明的杯子,几枚正在腐烂的桃子。那么摸摸,摸摸曾经的充沛,摸摸繁哈尔曾经的巨大而汁液丰沛的所有萝卜与木梨,摸摸整个芬芳无比。
一切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许多东西在我身后发出空空洞洞的响声。无法分辨。
责任编辑: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