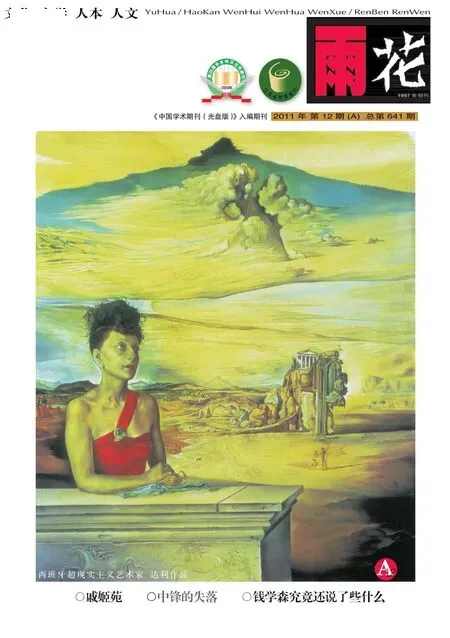撑 船(外一篇)
● 蒙 龙
车多了,船少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水乡人,撑船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我很快意于这种改变。

水乡儿女与船的关系是再亲近不过了。我与船的关系甚于一般。
入小学之前,我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船上渡过的。我的一位义父是渔民,他家有大小两条船,大船是住家的,小船是捕鱼的。所谓大船也就是七八米长、三四米宽,至于小船与舢板无异。我家屋后是一条大河,义父的船就拴在我家屋后的码头边,夏天泊在河心纳凉。很小的时候,我就学着撑船、划桨、摇橹,义父母是两位极慈祥的人,一见我上船,就围着我转,满足我的一切要求,耐心地指导我弄船,当然也保护我的安全。
我的老家是典型的水乡。因此每个生产队都有若干条船,早先是木船,一到夏天就拖上岸维修,换板、练麻、上桐油、晾晒,用工甚细。后来是水泥船,维修极方便,有个小洞,农民自己也会和点水泥抹抹。老家人积肥、卖粮、上街,甚至走远路亲戚,都是船。我的老家不兴划桨、摇橹,驾船的工具是竹篙,驾船的方法是撑船。撑船,就是用竹篙抵着河床,用力而驱船前进。撑船虽是小技,但不掌握要领,船就会在河里打转,尤其是遭遇旁风(从侧面吹来的风)的时候,撑船就更难。俗语“靠船下篙”,说的是处理问题要靠谱,要实事求是,但本义却是撑船的基本要求和方法。老家的男女老幼都会撑船。
我务农的时间不长,说不上是撑船的老手,但还是比较熟练的。记得高中毕业的那年冬天,我被队长派去撑泥船。三四十年前,老家人每年冬天都罱河泥,那时候计划分配的化肥很少,多用“绿肥”(河泥或用河泥与青草沤成的肥料,名称是很前瞻而生态的)。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虽出工很迟,但竹篙一出水就冻,用老家人的话说,篙子像鳗鱼,意指篙子极滑,手抓不住,只得用稻草将篙子包起来撑。撑泥船与撑空船不同,不仅用力大,而且要掌握好方向,否则泥罱子在河底就不平不稳。那是一条五吨水泥船,船的吊帮高,掌控难度较大,由于我小时候就弄船,因而虽然是第一次撑泥船,但应付得还不错,得到大劳力的夸奖。
第二次记忆比较深的撑船经历,是刚工作那年的寒假。校长夫妇要回苏州过年。那时候,要乘车外出,必须先到河口。校长夫妇年纪大了,又带了不少东西,便与我商量,是不是找条小船送他们到河口乘车。校长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启蒙老师。所以,我向生产队借来一条木船,撑着送校长夫妇去河口。那天风很大,又是顶风,竹篙也不很就手,篙子一出水,篙子上的水就呼啦啦直往袖口处涌,才出了村东头的闸口,浑身冒汗,唯独两只手是冷的。就这么赶着赶着,到车站不多会,汽车就到了。折回的时候,惬意多了,坐在船梢,有心无心地用篙子点点河岸,任船顺风而行,颇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
后来,离家外出求学和工作,撑船的机会少了,但与船的关系并没有疏远。我每次回家,爸总是早早地撑一条船到车站旁的小河边等我,每次返回的时候,又是爸撑着船送我。前些时,陪到高邮采风的省作协副主席叶兆言一行在界首芦苇场观光,我又撑了一次船,距离只二三十米,博得在场的农人好评,说我的功夫不错。但这次撑船,不是劳作,也不是生活的必须,而是从中寻找一种乐趣。
随着农村道路的日益改善,船作为交通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弱化了,也很少看到篙子的踪影。现在回家,车子一直开到村口,原来半天的路程,半小时就搞定了,如果村子里的巷子改造一下,可直到家门口。村里的船明显少了,即使有船,一般不再用竹篙撑,而是用挂桨机作为动力,一小时能行十五二十里,速度快多了。村里的各种车子一天天多起来,一到每年腊月底,村后的小型停车场停满了回家过年的车子。
车多了,船少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水乡人,撑船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我很快意于这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