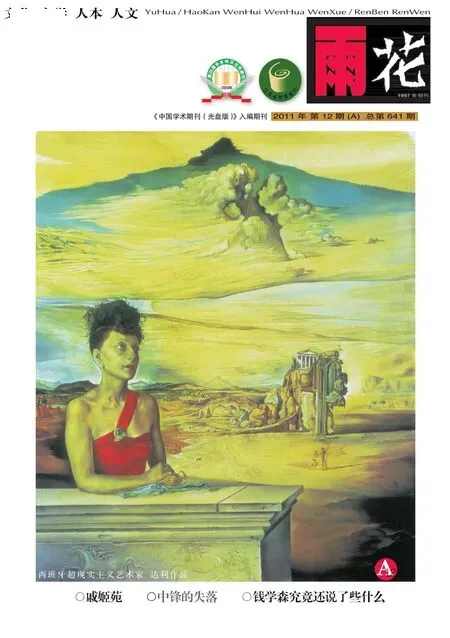城市乡愁
● 金学舜

如果让我选择用一个词去概括那种情绪,我会选择“乡愁”。
我有个族叔自幼父母双亡,不得已去投靠在省城工作的舅舅。他父母的非正常死亡是当时震惊乡里的惨剧:他妈在参加生产队挖水渠的集体劳动时被塌方活活掩埋,他爸——一个一直以来生活在狭小圈子里的脆弱男人,陷入痛失爱妻的哀伤之中不能自拔,没过多久就在一棵歪脖子油桐树上上吊自杀。故乡对族叔而言连接着一段惨痛的记忆。少小离家,光阴荏苒,他在城里长大,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经过几十年的打拼,终于迎来人生丰收时节。他平时跟故乡联系甚少,照说对故乡没有太多眷恋,孰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刚过五十岁就患上不治之症,眼见来日无多,身后事已经安排停当,家人都劝他安心养病,断断想不到他最后的念想竟然是回乡。回乡做什么?家人大惑不解,都在省城待了大半辈子,老家的屋舍久无人居早已破败不堪。但他执意还乡,家人拗不过,只得遵照他的意思先行回去修缮旧屋,再把他送回阔别多年的故乡。连村里人也未曾料想他临末选择的归宿竟然是落叶归根,回到群山环抱的村庄,在童年生活过的老屋里静候人生宿命难逃的落幕。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跋涉在岁月河流上的人们,对人生的源头都满怀浓酽的乡情。而那是一种蕴藉于心的情愫,越久越浓。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诗中的嫦娥,独居月宫,不经意间寂寞蹿上心头,撕咬那颗忏悔无力的心。如果人能够进入传说,设身处地一想,既可认为她是因情伤怀,亦可看作在远隔人间之后心灵无着的极大孤独。这种“嫦娥的忧郁”是千里迢迢迁徙大都市的人常有的一种症状。在每个大城市繁华的背后都有着鸽笼一样逼仄的居所,它们惯常缄默着门脸,开门亦是匆忙互不相认的脸孔,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内心蓦然飘起缕缕乡愁。
我的一位同龄人,医科大学毕业,集全家之力跃出农门,而去了大城市他仍会常常返乡,一呆便是两三月。那段日子他彻底把自己变回一个普通村民,锄禾下地,根本看不出他在大城市已生活多年,也看不出他的乡居只是一种矫情和落魄时的无奈。故乡给游子的感觉既温婉又包容,一如村前那条涓涓溪流,游子还乡她跟你细细寒暄,游子远行她跟你依依话别。“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这是席慕容的《乡愁》,这位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的女诗人,一辈子生活的环境都跟蒙古大草原没有多大关系,她的乡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乡愁、诗意的乡愁。
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们,即使远隔故乡睽违多年,思乡依然是内心深处难解的情结。陶渊明当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挂印归田,故乡是他最倾心最安稳的处所。但有人试图考证陶渊明:原来他“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是因为家境颇为宽裕。但是像他那样率性而为的诗人,还乡何尝不是意料之中的好事!
其实一旦踏上异乡,归——也不是容易事儿。中国的村落往往集族而居,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地扎根于心。刘邦《大风歌》如是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显然在他心目中衣锦还乡不啻是人生一大快事。故乡的期待有时超出游子所能承受之重,会让他对故乡平添回避的想法。李贽知天命之年从姚安知府卸任,族人都盼他回乡主持家族事务支撑门面,结果李贽让族人大失所望,居然移居千里之外的麻城,以半僧半俗的面目示人。从此让乡愁如一轮明月高悬在夜幕的天宇,故乡将永远在意念深处酝酿为一樽陈年老酒。
日本有“物哀”的说法,即睹物生情。李白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早将“物哀”的意境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知道这位出生在异域的大诗人,心中有着什么样的故乡胎记,是祖父辈心中相传的那个故乡么?还是大唐国土每一处值得他萦怀的地方?抑或只是一种永远酽浓的文化乡愁。我忽然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宁可在城市艰难漂泊,衣食无着也不愿返回家乡,那决然不是全球化背景下,对家园理解的冲淡与延伸。故乡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种迥然不同的况味。有的人即使一辈子睽违故乡,对故乡却似乎了然于心,就算漶漫久远,亦会在内心世界重新构建自己的故乡。
有一种背井离乡是为了纾缓生计,人们不惜让自己一度沦为“盲流”。在南方,我见过夜奔的人;见过猝然跳河逃走的人;见过如水月光下饱受隳突之苦的人;也亲历过遣返,这些,都是因为没有那一张暂住证。在拘留所里失去三日自由的经历无形中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然而回乡之旅唯有苦涩,在那种窘迫中,乡愁也不能被抹杀,而是被撞碎成吉光片羽。
暂住和庞大乡愁并没有阻隔我南行的步履,此后的十多年我一直“漂”在南方。我的人生许多岁月都与游子的身份有关。我有将近五年没有回乡,从母亲嘴里我听出一座村庄的没落:年轻人都进城或者外出谋生,剩下的人家屈指可数;许多长者黯然过世;村里再也用不着提倡封山育林,因为根本没人进山砍伐;古老的天井院落正在加速倾圮,青石板铺砌的晒台缝隙杂草丛生。
我一直想找机会回去,用相机挽留一座村庄。但是直面那一片村庄的废墟,我真的能挽留住什么?我童年少年时代浸淫过的田野文化、民风、民俗,都在不知不觉中随着时光流逝。传统民居——不仅是千百年来为村民们遮风挡雨的物态文明,也是田野文化寄居的“躯壳”,是搁置传统村庄人际关系的有机场所。在我的故乡,祠堂无疑就是那片天井院落群的“灵魂”。每年大年初一,村里的男人们都来到祠堂,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膜拜祖宗在天之灵祈祷先人庇佑;然后大家同贺新禧。即便平时结下一点恚怨,此际也随着一声“恭贺新年”而搁置前嫌。然而,眼下天井院落的倾圮,势必牵连到祠堂的破败。留在村里侍弄土地的村民,大都另址建房,他们的新居独门独院各自为政,水泥军团早已入侵,冲淡了传统村居的味道,也在无形中摧毁游子心目中的那座传统的村庄。寻根——起码要知道根还在,终于有一天,我们会无处寻它,黯然神伤。
也许源于对乡愁的理解,我才尝试揭开一座移民城市或浓或淡的底色,那也是移民群体潜形却共有的情绪。不妨先看看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我知道有些去过伊斯坦布尔的游客,天马行空地转了一圈之后,得到的却是与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截然不同的感触,它分明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嘛。因为作为一个游客看到的恰恰是被时尚粉饰过的表象。稍安勿躁,深入一些再深入一些,在千年文明的废墟上待久一些,抑或把生命融入伊斯坦布尔,再感受一下它那无所不在的“呼愁”。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2005年出版过一部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面有专门篇幅来写“呼愁”。伊斯坦布尔史称“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赫赫有名的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一书中,特地写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细节决定命运——茨威格认为仅仅因疏忽而忘记关上的一扇城门,决定了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我们不能忽略该书作者茨威格的悲剧命运,他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许多岁月是在被驱逐和流亡中度过,最终也没等到正义战胜邪恶的那一天。
该如何去界定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的确让人犯难,帕慕克没有向我们讲述千年前“上帝之鞭”阿提拉的赫赫战功;没有展示一座征服者之城的无上荣光;没有提及民族主义者的雄心壮志如何波澜壮阔。跟世界上许多曾经的老大帝国一样,伫立于东西文明交融的桥头堡,积贫积弱的奥斯曼帝国也在西风东渐中饱受挫折,开始变得对自己的文明不自信,在无可奈何的哀怨中颓废下去。帕慕克认为“过去一百年来,伊斯坦布尔人心目中的城市形象是个贫穷、不幸、陷入绝境的孩子”。作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孩子,文化乡愁从一百多年前就深深地扎根于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八十年前,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上台后,竭力倡导全盘西化,从政治制度到传统伊斯兰文化,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凯末尔身体力行经常带粉笔和黑板下乡,向人民讲解新文字。但是也有人认为是他强力割断了传统文化的脐带。“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我肯定‘呼愁’不仅统治着伊斯坦布尔,而且扩及周围地区。‘呼愁’根基于欧洲:此概念首先以法语(由龙蒂耶起,在朋友奈瓦尔影响下)探索、表达并入诗。”一开始在欧洲人看来,往往认定伊斯坦布尔就是他们心目中东方城市的样子——距离产生美感,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欣欣然发现的美正是一种东方与西方杂糅的异国情调。然而作为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帕慕克认为“我慢慢懂得,我爱伊斯坦布尔,在于它的废墟,她的‘呼愁’,他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呼愁”——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所患上的不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也不是可以从中解脱的自来之苦,而是一种自愿承载的忧郁情结。在这里“呼愁”不再是自卑的后遗症,而具有独特的精神魅力,恍若只要面对伊斯坦布尔,每一次呼吸都有忧郁的气息,也就不难理解会诞生帕慕克这样的“呼愁”作家。当发达的欧洲展现于一座颇具历史渊源的城市面前,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碰撞产生了摄人心魄的火花。那是一种置身文明废墟追忆历史的乡愁,一种夕阳残照下不忍抽身离去的迷离与自我陶醉。
关于乡愁,我想起像风像雾,谜一般的吉卜赛人。大概没人弄得明白,永不停歇流浪脚步的吉卜赛人到底在追寻什么?“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对“天地人”三者的会意是何等酣畅淋漓!作为地球村的居民,吉卜赛人的生存意识或许过于超前抑或落后。以至他们不像犹太人那样,在经历二千年的漂泊、饱受迫害屠杀之后,还有强烈的建国欲望。我宁愿相信在吉卜赛人眼里小小的地球村到处都是他们的故乡,那将是一种时至今日看来,依然多么宽阔的情怀!我们所欠缺的不过是如何以一种更宽容的心态,去理解吉卜赛人热衷的职业?杂耍、魔术、乞讨。
萨特评说波特莱尔:“他选择了如同他对于别人是一种自在存在那样,对自己是个自为存在”。因为诗人命中注定是要承受苦难的一类人,当别人奔向光明与幸福的时候,他却孤傲地走向诗人的故乡——疼痛与不幸。
忧郁原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高贵气质,只有当人的思维与天地人之间发生关系,才有可能表现为一种忧郁气质。连大科学家也不免如是,爱因斯坦1930年写道,“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每个人在这世界上只作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还若有所感。”可以说,帕慕克的“呼愁”是人类潜在的气质,只有置身伊斯坦布尔那样的城市才更容易让它散发出来。
中华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论语》开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个“乐”字可谓高屋建瓴。如果说快乐与忧郁是一对仇家,为何结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亦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所言快乐,正是为了对抗忧郁和无所不在的人世之愁。乐观豁达的李白在某个春夜与堂弟们宴饮,他写下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对于生死,秘鲁诗人普拉达亦这样写道,“什么是生活?身在梦乡而没有睡觉;什么是死亡?已经入睡又失去梦乡。”到了荷尔德林那里就成了——人,诗意地栖居——我认为这句写得特别好!
我的目光回到生养我的那个村落,它有一个奇特的名字“当铺金”,听上辈人讲创建基业的先辈在城里开当铺发了财,遂用使自己得以发家致富的行业为村名。整个村落为典型的天井院落群,灰墙黛瓦,门口一口用青石板围砌的风水塘,塘塍边曾有一棵垂柳。村庄整个看上去颇有徽州民居风格。也许在过往那个年代,外出谋生的人即使发了财心里装着的始终还是故乡,回乡起屋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抉择。但如今,年轻一代的思想路线与前辈截然不同,曾经拘谨、安贫、知足的乡亲们如今散落四方,传统宗族观念日渐淡漠。就算“漂”进城里,厕身“草根”阶层也在所不惜,只不愿重复祖祖辈辈困囿的生活,那也是我的生活脉络。一个村落的变迁就是一支时代的城乡变奏曲,它时而清丽时而晦暗,时而给人一种山重水复的感觉,时而带来拨云见日的喜悦。
我在深圳生活多年,关于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我能说些什么?外来移民融入城市的程度不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春运、民工返乡高峰、一票难求,在改革开放二十年里烙上了深深的印记。上世纪末为了回乡过年,我和哥哥辗转取道花都。晚上九、十点才到火车站广场候车,彼时人潮如鲫,忽然我看见远远的杂沓的人流中过来一队民工,他们肩挑被褥手揣凉席,为赶上回家列车一个个急如星火。很显然他们正肩挑临时的“家”,奔返心目中那个位置最重的家。还记得2008年南方大雪成灾,京广铁运郴州段一度停滞,却挡不住人们返乡团聚的热情。有人硬是步行,妄图冲破大雪的围困,漫漫归途情侣失散,引起媒体关注民众揪心感同身受。传统年节团聚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比什么都重要。我看到一座城市平时人们天南地北地赶来,到了年节,就再也抑制不住沸腾的一片归心,在回乡喜悦里糅入淡淡乡愁。
我相信中国人身上有着安居乐业随遇而安的基因,只要有合适的墒情就能让生命之树生根发芽。这种优良的基因也在当代移民身上延续。大量的外来劳务工在为新兴城市奉献青春和汗水的同时,也常常陷入居也不易的困惑和焦虑中,如同打工文学经常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人们千百年来追寻的安生状态,打工者拎起行李毫不迟疑地在城市里辗转,而命运带来的并不是完美的开花结果过程。如果让我选择用一个词去概括那种情绪,我会选择“乡愁”。心底无形之中总把故乡与眼下这个城市经济发展做比较,在故土地主的身份和时下暂住的比照;青春不再岁月蹉跎的感慨!除非这座移民之城用更包容的颜色,踩住乡愁灰暗的底色。使人透过文化的乡愁生出更多人间大爱的情怀,而非颓废与失落。
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认为,由于人类的贪婪基因,地球将变得越来越不宜人居。设若霍金所言非谬,人类大概需要在两百年后移居到别的星球,地球就成了星际移民的故乡。到那时人类是否还有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