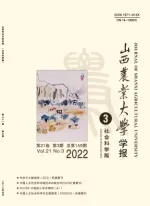“上”、“下”动词性组合语义构成多样性考察
杨子,彭兴旺,周东丽
(1.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3;2.中北大学 外语学院,山西 太原030051;3.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030032)
“上”、“下”动词性组合语义构成多样性考察
杨子1,彭兴旺2,周东丽3
(1.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3;2.中北大学 外语学院,山西 太原030051;3.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030032)
现有关于 “上”、“下”动词性组合及其不对称性的研究均集中在对 “上”、“下”动词性义项的解释分析,鲜有学者以组合中名词词项为研究对象,从名词的语义格与动名搭配的语义构成入手,将 “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名词所充当语义格分为七类,并揭示了这些名词与 “上”、“下”作动作动词的用法结合的五种语义构成方式,进而丰富了对 “上”、“下”动词性组合不对称性的认识。
“上”、“下”动词性组合;不对称性;语义格;言语行为转喻
一、引言
“上”、“下”这一对方位词在汉语中用法多样,除了常见作虚词的用法,还可起名词、形容词、动词等作用。在充当实词角色的情况下,“上”、“下”作名词与形容词解时呈反义关系,意思基本对称,分别指示竖直线上两个相反的方向,组合搭配基本对应,但当二方位词以动词用法出现时,尽管二者的基本义仍旧对称,即竖直方向上的反向移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组合搭配却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如可以说 “上街”、“下棋”,却没有 “*下街”、“*上棋”的对应表达。
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对“上”、“下”动词性组合不对称性的研究均聚焦于 “上”、 “下”的动词性用法本身 (如:沈家煊[1];王 建 军[2]; 卢 华 岩[3]; 周 统 权[4]; 刘 俊莉[5,6];刘国辉[7];杨子、王雪明[8]等),虽然这些研究从传统语法、认知语法等不同视角对“上”、“下”动词性义项的不对称性进行了解释,却忽视了 “上”、 “下”动词性组合中 “上”、“下”后续的名词对不对称现象的影响。
名词 “学”在与动词 “上”、“下”连用时,既可以形成对称性组合 “上学、下学”,也可以形成与 “工作”对应的非对称性组合 “上学、*下学”,这种对称、不对称组合并存的现象除了与动词用法相关外,是否还与 “学”名词性义项解读的不同有关?又如 “厕所”与 “饭馆”均可做处所名词,但前者只有 “上厕所”的表达、不能说 “*下厕所”,后者却有 “上饭馆、下饭馆”的对称用法,要解释该现象,是否也应考虑名词在相应组合中使用的差异性?
鉴于学界在该方面研究的缺失,本文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关注 “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动名搭配语义构成的多样性,试图找出名词使用多样性与 “上”、“下”动词性组合不对称性间的关联,旨在填补现有研究在此方面的空白,以便更深入的认识理解 “上”、“下”动词性组合。
二、“上”、“下”动词性组合搭配中名词的作用分类
要从名词的角度考察 “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心动词与后续名词搭配的不对称性规律,首先需要对名词在这些动词性组合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分类。根据 《现代汉语八百词》[9],“上”做动作动词时有10个义项,分别是1、由低处到高处,由一处到另一处,如上楼;2、向前进,如见困难就上;3、加、添、施加,如上油;4、出场,如从中门上;5、把一件东西安装在另一件东西上,把一件东西的两部分安装在一起,如上刺刀;6、涂、搽,如上药;7、登载,如上报;8、拧紧,如上发条;9、到规定时间开始日常工作或学习等,如上班;10、达到、够 (一定数量或程度),如上年纪。张华[10]认为 “上”还有单纯表示动作的第11个义项 “做、干”,如“上邪活”(即做坏事)。其中义项2、4为不能带处所宾语的自动词,不能进入 “上+名词”的动词性组合,故不在考虑之列,其余的九个义项中自动词义项,即加处所宾语的义项为1、7;他动词义项,即加名词宾语的义项为3、5、6、8、9、11;义项10较为特殊,往往只能加数量宾语,能进入 “上+名词”结构的只有上年纪、上岁数两个词。而 “下”做动作动词时有12个义项[9],分别是1、由高处到低处,如下山;2、降落,如下雨;3、(向下)发布、投递,如下命令;4、进入 (处所),如下乡;5、退场,如旁门下;6、投入,如下功夫;7、比赛,如下棋;8、卸除、取下,如下枪;9、做出,如下结论;10、使用,如下笔;11、生产,如下小猪;12、到规定时间结束日常工作或学习等,如下课。排除不能带处所宾语的自动词义项5,其余的11个义项中加处所宾语的义项为1、4;加名词宾语的义项为3、6、7、8、9、10、11、12;义项2较为特殊,只能加施事宾语。
按吕叔湘先生的说法,剔除 “上”、“下”几种无法后续名词的自动词用法外,“上”、“下”后续名词构成的动词性组合中,名词所起的作用总共有三种:施事宾语、处所宾语与名词宾语。然而,由于名词宾语一词过于宽泛,有碍对“上”、“下”后续宾语现象的深入认识,因此笔者拟按贾彦德[11]对现代汉语语义格做出的划分为依据,将 “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名词的作用进一步细分如下:
施事:上 (几个)人 下雨
受事:上菜 下饺子
处所:上街 下地
材料:上药
范围:上年纪
工具: 下笔
结果: 下崽
以上对 “上”、“下”动词性组合的分类无法与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的分类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对 “上”、“下”动词性组合按名词所起作用进行的语义格分类与按动词义项进行的语义分类之间无重合关系,通过审视动词性义项的语义不对称性只能认识到 “上”、“下”动词性组合不对称性的一个方面,而要更为全面的认识该现象则有必要兼顾其它切入角度,“上”、“下”动词性组合的不对称性还与动名搭配中名词语义格的多样性相关,如当后续名词以范围格出现时,“上”动词性组合不存在 “下”对应,而结果格仅出现在 “下”动词性组合中,不存在对应的“上”组合用法。
三、“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动名搭配的语义构成
“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名词所充当语义格的不同取决于组合中动名搭配方式的不同,而动名搭配方式的不同又在其语义构成上有所反映,因此本节从 “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动名搭配的语义构成入手,进一步认识名词在此类组合中所起的作用。
(一)“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动名搭配的语义构成分类
“上”、“下”动词性组合的语义构成较为多样,至少可分为如下五类:
1.“上”、“下”+后续名词唯一基本义
“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动名搭配最基本的方式为 “上”、“下”动词性义项+后续名词基本义,如 “上/下山”,意思即为沿着山峰向上或向下的运动,后续名词 “山”取其唯一基本义,即在该组合中无其它解读方式,整个动词性组合的语义为其中动词义项与后续名词义项的简单相加。类似的例子还有 “上/下楼”、“上菜”、“下命令”等。
2.“上”、“下”+后续名词多元基本义之一
这类动名搭配较前者复杂一些,原因在于动词性组合中的后续名词具有多个义项,且有不止一种义项可与动作动词 “上”或 “下”的义项结合,如 “上学”,当后续名词 “学”作 “学习”讲时,可分别于 “上”、“下”表示动作开始或结束的义项结合,形成 “上学”与 “下学”的对应组合,表达 “开始学习”与 “学习结束”之意;当 “学”作 “学业”讲时,则只能与 “上”表“做、干”的义项结合,具体表达类似“尚在求学阶段,还未就业”之意,此时的“学”没有与动作动词“下”结合的可能。虽后续名词的具体义项有了非唯一性,但此类动名搭配的语义构成仍为动词义项与后续名词基本义项之一简单相加。
3.“上”、“下”+后续名词的转喻义
转喻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词语的转喻义即由该词语指代与其紧密相关的某种意义,如“厕所”的基本义是 “人用于生理排泄的一个场所”,但该词语可以用于指代与该场所紧密相连的一系列事件,即 “人的排泄活动”,这便是“厕所”一词的转喻义,该语义与动作动词 “上”表 “做、干”的义项结合,整体表达 “进行生理排泄”的意思,故而,“上厕所”这一组合的语义中完全不包含 “厕所”的基本义,即使是在没有一处厕所的茫茫草原上,人们也可以说 “你们先走,我上个厕所就来”。在这种情况下,“上”、“下”动词性组合的语义构成为 “上”、“下”的动词义项与后续名词的词语转喻义之和。
4.“上”、“下”与后续名词基本义的整体转喻义
不同于前者语义构成中的词语转喻,在此类情况下 “上”、“下”动词性组合的语义是在其中动词义项与后续名词基本义简单相加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得出的言语行为转喻义。根据Thornburg&Panther[12]提出的言语行为转喻模式,一则言语行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阶段:前段(行为的准备阶段)、核心段及结果段 (行为的区别性特征,用以表明行为特点及成功完成行为的即时结果)、后段 (行为所带来的预期或非预期的后果),交际过程中由于语言经济原则的存在,话语建构可以使用言语行为的一个成分段去激活和指代另一成分段或全部行为段,而不必在话语中交代各阶段的所有细节。因此以 “下馆子”为例,“下”的动作动词义项 “进入 (处所)”与后续名词 “馆子”的基本义 “外出吃饭的场所”结合,生成 “进入某一吃饭的场所”之义,正好代表了 “外出吃饭”这一言语行为的准备阶段,按照言语行为转喻模式,由对该准备阶段的描述便可以激活整个行为,故而 “下馆子”这一动词性组合最终语义便是 “外出吃饭”这一完整的言语行为。当然,在此基础上,由于动词 “下”还包含 “目的地心理等级较低”的语用含义,加之名词 “馆子”中的后缀 “子”亦包含 “指小、轻视”等语用义,故而整个短语 “下馆子”又隐含了说话人对该言语行为轻视随意的态度。抛开语用附加义不谈,此类 “上”、“下”动词性组合的语义构成也已相对复杂,是在动词与名词义项组合后进行言语行为转喻的结果。
5.“上”、“下”与后续名词基本义的整体比喻义
除了在 “上”、“下”动作动词义项与后续名词基本义组合后进行言语行为转喻外, “上”、“下”动词性组合的语义构成还可能是动词与名词基本义组合后引申出的比喻义,如动词性组合“下海”中,动名搭配的基本义组合为 “进入到海中”,而与陆地相比,大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可观的回报,在此寓意基础上 “下海”便产生了 “放弃传统体制里的各项保障,到新的经济社会空间里去从事风险和回报都非常高的商业活动”意思。这种对 “下海”字面义的引申完全建立在上述比喻的基础之上,故而此类短语的语义构成是 “上”、“下”雨后续名词基本义的整体比喻义。
(二)动名搭配语义构成的多样性与 “上”、“下”动词性组合的不对称性
鉴于 “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动名搭配语义构成的多样性,同一动名搭配可以通过不同的语义构成方式体现不同的意义,如 “下课”,在体现 “上”、 “下”+后续名词基本义时,生成“课程结束”的意思,在体现 “上”、“下”与后续名词基本义的整体比喻义时,又会生成 “停止某人工作”的意思 (如 “世界杯教练因执法过火而下课”)。在体现前种语义构成方式时,“下课”有与之对应的搭配组合 “上课”,而在后种情况下,与其对应的 “上课”用法则相当少见。由此可见,同一 “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名动搭配语义构成的多样性也是形成其组合不对称性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本文从动名搭配的语义构成角度重新审视了“上”、“下”动词性组合,通过分别对动名搭配中名词所充当语义格的多样性以及动名搭配语义构成的多样性进行探讨归类,进一步解释了“上”、“下”动词性组合的不对称现象。由于本文只是对这一新切入视角的简单试水,仅初步揭示了后续名词在“上”、“下”动词性组合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动名搭配语义构成的多样性与“上”、“下”动词性组合不对称性间的关联,对于后续名词所充当语义格的多样性及动名搭配语义构成多样性与“上”、“下”动词性组合不对称性间关联的复杂性及其间的相互制约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1]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2]王建军.“上馆子”与 “下馆子”[J].语文建设,2001(1):13.
[3]卢华岩.由 “到”义动词 “上/下”构成的动宾组合 [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3):18-22.
[4]周统权.“上”与 “下”不对称的认知研究 [J].语言科学,2003 (1):39-50.
[5]刘俊莉.“上/下+馆子/厨房”差异辨析 [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6):83-85.
[6]刘俊莉.认知模式差异对 “上”“下”二词使用的影响 [J].湖北社会科学,2006(1):111-113.
[7]刘国辉.汉语空间方位词 “上”的认知语义构式体系 [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2):13-17.
[8]杨子,王雪明.试析反义词 “上”、“下”在一组动词性组合中应用的不对称性 [J].语言科学,2009(1):42-47.
[9]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73-474,566-567.
[10]张华.“上/下”动词性组合的认知考察 [J].语言研究,2002(特刊):120-123.
[11]贾彦德.对现代汉语语义格的认识与划分 [J].语文研究,1997(3):23-29.
[12]Thornburg L &K Panther.Speech Act Metonymies [A].In W.Liebert,R.Gisela &L.Waugh (eds).DiscourseandPerspectiveinCognitiveLinguistics[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205-219.
Diversity of Semantic Composition in Verbal Constructions in the Form of"Shang/Xia+ Noun"
YANG Zi1,PENG Xing-wang2,ZHOU Dong-li3
(1.SchoolofForeignStudies,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Beijing,Beijing100083,China;2.Schoolof Foreignstudies,NorthUniversityofChina,TaiyuanShanxi030051;3.DepartmentofForeignStudiesBusinessCollegeofShanxiUniversity,TaiyuanShanxi030006,China)
Existent studies on verbal constructions in the form of"Shang/Xia+ Noun"and its asymmetry are all focused on Shang's and Xia's usage as verbs.There's few researchers who studied the noun followingShang/Xiain the construction.In view of this,the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mantic case and semantic composition to study the"Shang/Xia+ Noun"construction.In the paper the semantic case of the noun in the construction is classifi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and the semantic composition of the collocation betweenShang/Xiaand a noun is revealed to have five variants.Through clarify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iversity on the two levels and the asymmetry of Shang's and Xia's collocation with nouns.The paper betters the present understanding of verbal constructions in the form of"Shang/Xia+Noun".
"Shang/Xia+ Noun"verbal construction;Asymmetry;Semantic case;Speech act mytonymy
H030
A
1671-816X(2011)02-0197-04
(编辑:佘小宁)
2010-11-21
杨子 (1982-),女 (汉),山西侯马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