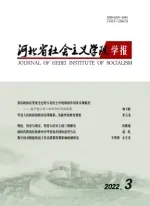身份与行动的逻辑: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构主义分析
周巧生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重庆 400064)
身份与行动的逻辑: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构主义分析
周巧生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重庆 400064)
建构主义身份与行动之间的逻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解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视角。在建构主义看来身份决定行动。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开启于两者对集体身份建构的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敌人角色的互构,将双方引向多年的敌对状态,至今,虽然两党关系得以缓和,但是历史痕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国共合作;身份;行动;霍布斯文化
一、身份与行动的逻辑:建构主义的解读
身份是建构主义中的核心概念。身份意识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有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可以分为四种,分别是“(1)个人或团体;(2)类属;(3)角色;(4)集体。”其中类属身份是指“一种社会类别”,因此,“类属身份具有内在的文化向度”;“角色身份依赖于文化”,“只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集体身份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自我被归入‘他者’。”[1]集体身份建立在类属身份的基础之上,具有相同社会内容和社会特征的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易于产生认同,而高认同度则能够引导行为体之间进行合作。“但是认同通常是与具体问题有关的,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
建构主义的逻辑在于强调行为体在互动中产生了共有知识或文化,“共有知识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2]行为体在具备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采取与之相称的行动。因此,身份和行为之间是一对具有因果关系的变量。在建构主义看来,身份决定利益,而利益影响行为,因此行为体具有什么样的行为从本源上受身份的影响。身份对行为体的影响大致通过三种方式表现出来:“第一种是间接的,也是普遍接受的观点;第二种来自于行为解释的社会身份理论;第三种与角色理论有关。行为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就有与自己身份相对应的行为”。[3]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前,就国共两党关系而言,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大党,有着多年的历史和比较广泛的影响力,共产党则是一个新生的政党,力量弱小,影响力有限。两党具有各自鲜明的阶级基础和立党理论,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和国内革命形势的极度严峻,在什么时间能够产生交集是个不太好预测的问题。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假设,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以及中国国内反革命势力强大,在这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两党开始重新界定对彼此的认知,并且展开构建集体身份的努力,由此而进行了两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合作,但是两党因类属身份的差异而引发的合作中的认同程度低又隐隐的为两党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二、国共两党类属身份差异所引发的合作之难
国共两党在类属身份上具有很大差异。对于国民党来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政治理念在于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本此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4]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们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5]这与共产党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生产资料社会公有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5]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他对“三民主义”的执着与坚持,他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的怀疑毫无疑问会影响着他手下国民党员的思想和观念,这从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可以管窥一二,他说“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6]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已经被其党员认同,并因此而影响到行为,这里实际蕴含着,国民党从决定改组到“三民主义”学说完整阐述的过程中,尊崇“三民主义”学说、认可孙中山进行社会革命的方式以及与孙中山有着相同革命目标的个体已经完成了对“国民党”这个类属身份的建构与认同。
对于共产党来说,其成立之初便严格按照马列建党原则来组建政党组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有着明确的阶级定位和革命纲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以此作为特征,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完成了类属身份的建构。强烈的身份特征使其从成立便将自己与其他党派区别开来。“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7],“在政治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8]
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阶级立场的不同、政治信仰的不同以及革命目标的差异决定了国共两党类属身份的不同,而这点直接影响到了在互动过程中对对方的认同程度,也在国共合作的酝酿之中便创造了难题。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主要任务在于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马林在与孙中山的多次会晤中注意到孙中山不明白“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9]在共产党人这一方,当马林将国共合作的想法告诉陈独秀,同其商量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并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内去开展活动时,这一想法也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维经斯基的信中陈述了 6条共产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的理由,其中就涉及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宗旨及所据基础不同”一条,这实际上突出了国共两党类属身份的差异,这种身份差异在陈独秀看来“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机会”。[10]
三、国共两党集体身份建构的不稳定
集体身份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之上的,而认同又通常与具体问题有关。诱发两党开始建立相互之间认同的根源在于在开展国民革命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两党相互之间要有所借重。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国民党很大但是组织松散,共产党很弱但是组织严密,两党结合,取长补短则能取得国民革命局势的改观。对于国民党来说,“扩展自我边界使其包含他者”的表现主要是对共产党人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的认同。孙中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在《孙文越飞宣言》中他尚且还持排斥态度,但是在他从鲍罗廷处获知十月革命以来六年间,俄国“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复认为俄国革命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奋斗,亦“暗相符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将其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做了阐述,他正式宣称:“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11]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体现了认同。
对于共产党来说,对国民党的阶级成分的重新认识是界定与国民党界限的一个重要方面。1922年 7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各阶级联盟的组织,包括其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侨民、南方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这份报告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在随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就“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强调国民党是由工人、知识分子、华侨和商人四种人组成,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共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5]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中共产生了影响。陈独秀说:“它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它的党员来源是“知识者居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约居十之二、三,小资产阶级约十之一,无职者约十之一;再参看他十几年来的革命历史,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12]陈独秀对国民党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国民党阶级组成的重新认识,使共产党人找到了可以与其进行联合的阶级基础。
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国共之间正式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起了合作的关系。合作关系的确立也意味着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起了集体身份。但是这种集体身份却具有不稳定性的特征,因为集体身份的建构还要依赖于类属身份,而类属身份的差异使得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更容易从利己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个人需要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这些需求在不同程度上与群体需求发生冲突,这就使个人本能得担心自己的需求被群体需求所淹没。一个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也是如此”[1],这必然会导致互动中出现矛盾甚至是冲突。
国民党的组成成分复杂,其中不乏军阀与政客,“这些人在政治上是国民党内彻头彻尾的右派,他们根本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政策”[13],在他们看来“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之争。”[14]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右派成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向孙中山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国民党内不仅有邓泽如、张继为代表的老右派,随着斗争的发展,国民党中还出现一批新右派,这就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戴季陶以及曾经一度是中派的蒋介石等人。“新、老右派在分裂国民党、反共、反革命的策略上有所不同,公开反动有先有后,然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为了一个反动的政治目标,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打击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事件。”[15]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中共在 1924年 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放弃了一开始对国民党执行的自我约束的政策,开始采取比较激进的做法,将国民党内左右之争定位为“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16]主张在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之间的斗争。
国民党右派对中共的攻击以及中共对此进行的反击,必然会加剧两党之间的矛盾,中共虽然在“党内合作”的形式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开展活动,但是在组织结构上保留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以及非常明确的表现了对国民党右派的态度,这些因素必然加剧两者之间的隔阂,造成认同程度低,从而影响到集体身份的稳定性。
四、霍布斯文化下国共两党角色身份的建构
霍布斯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战争中,行为体的原则是不顾一切保全生命,是杀戮或被杀。在该体系文化中,行为体之间互构的角色是敌人。敌人的角色意味着行为体不承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独立存在的权利并且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常用手段。
孙中山去世后不久戴季陶主义出笼。戴季陶先是抛出了要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的论调,后又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戴季陶从哲学基础与方法论上比较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此证明了两个问题:中共与国民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所以,两者在理论上没法统一;他认为不同的政党是不能联合的,所谓:“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17]因此,为了主义的生存、为了社会的生存,必须集中意志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服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指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并且认为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
在戴季陶主义的影响下,首先向共产党发难的是成立于1925年11月的西山会议派。在张继、谢持等主持下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顾问鲍罗廷解雇案》、《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等一系列决议案,公开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反对共产党,且在组织上分裂国民党,另立国民党中央。在西山会议派的进攻下,中共党内此时对于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形式产生很多疑虑,多数党员认为“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主张采取“党外合作的政策”[15],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要求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使得合作能够得以继续维持。不过这种合作得以维持的外力作用大于内在的凝聚力作用,西山会议对于国民党带来的影响是“下层支持西山会议的党员越来越多地开始将共产党视为‘反革命’了。”[5]而中共方面,则联合国民党左派,“竭力赞助左派发展革命运动工作,竭力赞助左派对右派的斗争,竭力扩大左派的组织”[18],同时不断壮大巩固自己的组织,并且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逐渐掌握了国民党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中共对国民党各部门领导权的掌握,在国民党右派看来显然是伤害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向中共展开斗争已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通过“整理党务案”开始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如果说“整理党务案”是对中共展开的文斗,主要目的在于夺回领导权、控制领导权,那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则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这说明,国民党已经以“敌人”的角色建构共产党,把他者再现为敌人。对行为体的行为至少有四种含义,“第一,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第二,决策往往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做准备。第三,相对军事力量被视为至关重要。最后,意味着无限制地使用暴力。”[1]
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标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5]“四一二”之后,陆续发生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马日事变”以及最终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被屠杀,以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两个党,最终在国民党右派疯狂的杀戮之中结束了第一次合作。在认知国民党被右派掌控所展现出来的反动面孔之后,中共汲取教训,开始组织自己的武装,在革命与反革命阵营的划分中,国共之间由合作的伙伴转为敌对关系。
五、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思考——文化可以导致冲突,也可以导致合作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互动可以建构文化,而文化又反过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身份则指导着行动。革命年代,两党互动中的不信任和敌意建构起的霍布斯文化不仅给两党带来了伤害,更是对绝大多数无辜平民百姓的伤害。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两岸关系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时过境迁,虽然两岸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两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频繁,但是岛内滋生的台独思想却严重地阻碍着两岸的统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多次的互动之后虽然两党关系得以缓和,但是在国民党思维中对中共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和认同程度使得两党走向再次合作之路仍然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文化可以导致冲突,也可以导致合作。”[1]我们希望霍布斯文化的思维永远成为历史;今天,中国共产党以及大陆在两岸互动中展现出的包容和诚意也希望会得到岛内居民的善意解读,从而建构起一种可以进行深层次合作的文化,不仅能够推动两党关系的升华,更加能够推动两岸之间关系的升华,早日建构起两岸之间的集体身份,最终化解统一之难的问题。
[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82-289、424、333、330 -331、318。
[2]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J].欧洲,2001(3):6.
[3]Rawi Abedelal,Yoshiko M.Herrera,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TerryMartin(draft paper),Treating Identity as A variableMeasuring the Content,Intensity,and Contestation of Identity. P8,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johnston/identity.pdf.
[4]《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 23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卷)[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11.
[5]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0、15、95、147、229.
[6]《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1924年 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428.
[7]《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3.
[8]《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8.
[9]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372-373.
[10]《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中央档案馆.北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1-32.
[11]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的演说 (1923年1月 26日)//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2.
[12]林茂生.陈独秀文章选编 (中)[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210
[13]李新、彭明、孙思白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83.
[14]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300.
[15]朱建华、宋春.中国近现代政党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95、194、421.
[16]《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1924年 5月 10日 -15日).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68.
[17]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M].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18.
[18]《中央通告第 76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做的工作》(1926年 2月 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二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6-17.
D6
A
1009-6981(2011)03-0055-04
2011-04-15
周巧生(1982-),女,硕士研究生,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多党合作历史研究中心讲师、学报编辑,研究方向:民主党派史与多党合作历史。
[责任编辑郭清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