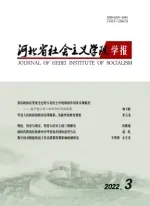美学价值的缺失——浅析过程哲学中“秩序”概念的缺陷
董艳丽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文化研究 】
美学价值的缺失
——浅析过程哲学中“秩序”概念的缺陷
董艳丽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过程哲学所理解的宇宙论统一体所包含的秩序,具体体现在生成的过程中。现实实有从原始材料走向自身的满足,然后消融在下一个满足的生成过程中,促成新的现实实有的形成。宇宙整体始终是一个不断选择和不断丢弃的过程,这一过程创造出宇宙的和谐秩序,并赋予了一切现实实有以存在的合理性。但在这一过程中,适用于美学的鲜活的冲动和想象逐渐消失了,“秩序”这个概念在过程哲学和美学的不同语境中出现了矛盾,表现出过程哲学所存在的缺陷。本文从现实实有的生成过程、“满足”后产生的新实有和宇宙的终极目的的实现三个角度,论证过程哲学中“秩序”概念所存在的缺陷。
秩序;过程;选择;冲动;想象
怀特海所创立的机体哲学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宇宙论体系。这个体系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实体概念,把整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看作无数相互摄入、不断向“满足”生成的过程。巨大无比的星球和微小不可见的尘埃都是过程。任何现实实有的生成和发展过程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逻辑性、实用性和统一性。怀特海不拒斥多样性和特殊性,但一切发展过程都有一种内在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内在的、前定的和谐,是必然存在的,它使现实事态[1]向着“满足”——宇宙统一的发展方向——衍生和前进。这样就使宇宙成了一个既包含着无限丰富的现实实有,又有统一、和谐秩序的有机体,符合了机体哲学的终极目的:“构建一个由诸一般观念构成的一致的、逻辑的且必须的体系,根据这一体系,我们经验中的每一个成分都能得到解释”。[2]
怀特海努力使秩序所构建的宏大的宇宙体系“足以阐释构成文明思想这一复杂织体的那些观念和问题”[3]。但是,这一体系一旦与美学语境中所需要的“冲动”相遇,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无法抵消
了。
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中,“过程”呈线性向前进发,包含有秩序性、和谐性的现实实有是统一的发展趋势,一切庞杂现象和感性因素都自觉地服从于这一趋势,在秩序的规范之下对自身进行改造或消解。这对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可以使经验中的一切都得到解释的宇宙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美学的语境中则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在机体哲学中,命题的不完善、现实实有的不统一、不满足是实现秩序统一性目的的失败;但在美学中恰恰相反,它似乎不需要或很少需要秩序的支配。在美学中,如果现实实有与感性因素也遵守着同样的模式,事物便失去了独到的价值和生机。尽管一切感性的冲动和每个过程生成之前最原始的现实实有都有不合于秩序的一面,但它们同样包含着鲜活的生命力,它们促使想象迸发,激情四射,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总之,在美学中,原始的现实实有所具有的冲动是表现世界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过程哲学中完美的秩序则会限制想象与冲动的创造力。因此,“秩序”在建立起宏大的宇宙论体系时,却出现了与美学的矛盾。它在过程哲学中使纷乱杂多的现实实有走向统一与和谐,同时也使美的因素因逐渐失去了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想象和冲动而变得愈加贫乏。
一、过程所失去的和原始的生命力
“现实实有”是宇宙统一体中最基本的要素,在过程哲学中,它并不特指构成宇宙的某种基本的实体性因素,大到某一颗星球,小到某一粒尘埃,以及一切运动的事态,都可以称为现实实有。一切现实实有永远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中。每一个过程都呈线性发展,我们可以在任意一条线上选取任意两点,甲点和乙点,每一点代表一个现实事态,来比较二者的关系。假定这一过程本身是向着乙点所在的方向发展,那么,相对于乙点来说,甲点尽管是前一阶段发展过程的满足状态,但就包含乙点的过程来说,甲点又成了这一新的过程的起点,它与乙点是甲、乙两点之间的过程的两个端点,相对而言,它便成了暂时没有经过这一生成过程洗礼的、最初的原始状态。因而,它并未与这一过程的秩序相一致,并不是完善的状态。到此,“秩序”的作用在过程哲学和美学的不同语境中的矛盾便出现了。在美学的语境中,未经历生成过程的现实实有可以成为一种完美的状态,因为未经过过程的洗礼就意味着还没有经过秩序的选择而与其他实有相互摄入,意味着这些现实实有可以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的特征,尽管有些特征可能并不符合过程的需要,但不能否认其中一些特征具有很大的审美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过秩序性选择的现实实有就完全失去了审美价值,而是秩序并没有能力将处于甲点的现实实有所具有的特征完全摄入过程中,当有些特征与过程的一致性需要出现矛盾时,它们在进入过程之前就已经面临着自我牺牲了,而这些特征很可能潜藏着极大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秩序”的作用在过程哲学和美学的不同语境中便发生了矛盾。
机体哲学始终潜藏着一个统一的发展方向:现实实有的满足,但不失内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前定而无须过多证明的内在的和谐秩序,二是各现实实有在生成过程中嵌入式的相互作用。这两个条件也预示了现实实有在合生过程中是一个自我消解、不断相互摄入、与其它现实实有互相妥协的过程。
现实实有的生成过程是一个实在的合生过程,即在与该合生相关的现实世界的范围内,诸现实实有在潜在的、前定和谐的条件下,不断生成、趋向统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实实有首先被赋予的是它本身所不具备的确定性。永恒客体作为纯粹的潜能,以“进入”现实实有的方式,在一个特定的现实实有中得以实现,使这一现实实有具有了某种与其相适应的形式要素和确定性。然后它与合生所需要的其他现实实有相互摄入(包括肯定的与否定的摄入)、联系、对比,从而获得新颖性,变成了新的、统一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使各个现实实有祛除了原始摄入的从属性与偏狭性,使它们不能再从整体中抽象而出,只能从整体的角度得到解释,现实实有达到了合生的最终阶段:“满足”,生成过程在某一特定的阶段终止。
这一生长的“满足”最终获得了两个完美的特征,但这两个特征也成了“秩序”在过程哲学和美学的不同语境中产生矛盾的原因。这两个特征:一是“起作用”,即起着整体的支配作用和决定作用,具有了明确性和确定性,将实有通过主观形式鲜明地呈现出来;二是“一致性”,标志着现实实有的生成过程满足了其主观目的,这一“一致性”包含着新颖性又不失多样性。这两个完美的特征意味着对生成之前的现实实有的原始生命的舍弃,而这原始生命恰恰是美学中包含了活力的、较为珍贵的因素。“秩序”造成了美学价值的缺失。
任何现实实有为了过程所必需的秩序性所做出的自我牺牲都是合理的,就像新生的婴儿,尽管它有着最质朴的天真,最单纯的眼神,最娇嫩的肌肤,但它所在的世界并不是让它保持出生的原貌,而是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于是,它的成长过程将是一个为实现人的生存目的而不断接受新事物的合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婴儿原始的特质将被慢慢消磨掉,从而与其他成长所必需的条件相互妥协。这一切妥协都是值得的,因为满足了成长过程的需要。处于过程中的现实实有就像婴儿的成长过程,它向着合秩序性的满足前进,对初生的生命所具有的特征进行合理的选择或丢弃,这体现了获得必然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法则。但对美学来讲,在这一法则的指导下对原始的现实实有的理性选择和舍弃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就审美的法则而言,对现实实有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和理性选择并不是必须的。作为人的审美能力和审美对象,位于某一过程起点的现实实有,在美学的语境中完全可以不经过秩序的选择就可以保持自身原始的特征,也不必然受秩序的制约趋向于某种满足的生成。
首先,人的审美心理可以作为一种不受秩序束缚的、不进入某种特定的生成过程的现实事态而存在。人的审美过程都不受某种秩序的支配,一旦有了其他过程性因素的摄入,美感便很难保留了。例如,我们在看到落日的那一霎那所产生的美感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任何规律和秩序可言,假如我们被询问这美感如何,答案很可能是随机的。有的人可能觉得天尽头的落日是开启一个童话世界的大门,有的人可能将夕阳比作一位有着悲怆情怀的老人,不禁潸然泪下,还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夕阳像一位温柔的少女,向他流露出迷人的微笑,使他心中荡漾起对爱情的无限向往。总之,很难将这一瞬间的审美感受用过程哲学中秩序的学说解释。审美过程不可能是一个不断摄入、合生、向着某个和谐的、有秩序的方向前进的过程,因为审美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在没有任何思考的状态下发生的,它的发生也不是向着某种前定的目标趋近。此外,人的同一种情绪在审美状态下和审美以外的理性过程中很可能产生不同结果。例如,将悲伤看做一种事态,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很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而在面对夕阳的美时,不管产生什么样的审美情感,这种状态都是无利害的,甚至只有在悲伤的时候才会看到夕阳不为人知的美。因此,人的审美能力以及特定情况下的审美状态都不能被纳入具有前定和谐的过程,人的审美心理所产生的审美情感可以不与其他任何审美以外的事态产生联系,可以独立存在。作为一种原初的审美状态,一旦进入被秩序所统治的过程,便可能会因其他因素的摄入而被破坏,就像唯美的湖面突然被抛入了一堆垃圾,虽然也可以漾起水花,但也总飘着一股恶臭。
其次,就审美对象而言,没有经过过程洗礼的现实实有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具有极大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例如,沙漠的原始状态作为一个现实实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并不合适,因而常常被改造,使其符合生态平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做为审美对象,人们可能会觉得沙漠最粗犷、最原始的状态才真正具有大自然的魅力,引起人的敬畏、崇高的情感。这种现实实有最原始的生命力可以通过艺术领域的巨大成就得到证明。表现主义画派曾试图寻找人的内在的、未经净化的、原始的冲动和情绪。这种情绪只能鲜活地存在,而不能被任何理性和秩序所模仿,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梵高的作品中所包含的激情很难被人模仿。印象主义旨在寻找大自然在日光中那种最初的美的印象。各种颜色随着光的变化随意乱铺,没有任何理性的分析和取舍的成分,也不像古典艺术那样,要经过一整套有关绘画的特定的技术性程序的检查,只要画家觉得某个阶段已经完美的表现了某个瞬间的印象,作品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于是一种奇特的艺术效果被创造了出来。尽管这两种艺术的语言都打破了古典艺术的理性分析和完美形式,但艺术的发展很好地证明了它们恰恰是极具潜力的艺术创作方式。
一个未经历过程洗礼的现实实有最具有或单纯、或纷乱、或无秩序、或无理性的特质,这些特质在过程哲学中要么被消解,要么被变成合乎过程性秩序的存在方式。但美学却为这些无秩序的现实实有提供了自由的存在空间。初生的婴儿未加任何修饰,但他体现了生命的原初状态,这种生涩的状态展现的是生命最原始的力量,于是,这种原始的力量由过程哲学中的一个起点变成了美学中理想的存在状态。但是,原始的现实实有如何在过程哲学和美学中同时成为可能,怀特海并未解决。他在讨论过程哲学如何完美的建立起一个宏大和谐的宇宙统一体的同时,忽略了美学很多时候正是要打破这种统一体,将原始的世界所具有的生命力呈现出来。这成为过程哲学的一个缺陷。
二、实在的满足与对矛盾和冲突的追求
现实实有经过合生所实现的新的实有在过程哲学和美学两种语境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矛盾和冲突在这两种语境中的不同地位。
每一个现实实有的合生过程都不是无限延伸的,合生过程要造就一个新的现实实有,这个新的现实实有的出现就意味着合生过程的暂时完成。这一暂时完成阶段被称为“满足”,它是充分而明确的,这种充分性和明确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a)它的发生(b)它的超验创造性的客观特性以及(c)它对其域内每一事项的摄入——无论是肯定的或是否定的”[4]。实际上每一合生过程都是为达到某一主观目标从不一致走向一致、从生涩走向成熟的过程。上一部分已经说过,现实实有在合生过程之前,相对于过程之中的那些被秩序选择和规定了的过程而言,具有杂多、丰富甚至是狂乱的个性,而它的目的是经过合生走向满足和成熟。在合生过程中它是自我创造的,将自己的多样性转变成一个一致的作用,最终达到“满足”的现实实有,成为一个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一”。这个“一”中包含着各个作用一致的“多”,从而使一致性与多样性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成为一个成熟的现实实有。但是,这个成熟的现实实有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冲突和矛盾的消解,因为冲突和矛盾会对达到“一”的过程造成障碍。怀特海只忙于创造一个系统的宇宙统一体,而忽略了冲突和矛盾对美学的重要性。
矛盾与冲突对于合生过程中的满足来说具有自我消解的必然性,但在美学的语境中便会产生出无穷的张力和神奇的力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超现实想象的世界中,钟表可以是扭曲的,公元前一世纪可以与二十一世纪存在于同一个时空中,世界可以是同时失重和受重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在现实的合生过程中有悖于一致性和满足的要求,但在美学的语境中,一致性已经失去了作用,想象允许矛盾和冲突成为最光辉的形象,它是超越现实的奇特的艺术品。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四岁的孩子可以画出比房子大的花朵,画出彩虹唱歌的样子,而一个四十岁的人可能会武断地说这个孩子没有绘画的天份,画什么不像什么。恰恰相反,在审美的世界里,孩子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他用矛盾与冲突展现出一个无比神奇的世界。实际上,他只是不懂得合生过程的规则,因此不受其束缚,创造了一个不合逻辑却鲜活感人的世界。四十岁的人经历了无数合生过程的重复,思维已定格于那种消解了冲突与矛盾,并达到满足的现实实有,因此认为符合过程性的秩序是唯一的必然性,并不会意识到这恰恰是美学的灾难。
满足后的现实实有是合生过程的唯一方向——合生过程不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方向,因为这很可能会与创造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宇宙统一体的目标相悖。方向的唯一意味着结果的唯一,结果的唯一便排除了现实过程和秩序之外的一切不合理因素。当然,这种唯一也适用于美学范畴,这是一种具有和谐性质的喜剧效果[5],是平缓、优美的艺术形式。古典艺术便在这一规则的指导下,使用这样一种和谐、静止的线条构造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形式。相对而言,还有一种更加感人的形式,即巴洛克艺术。它抛弃了一致性的作用,运用主角与背景的冲突,造就一种生命的运动效果,以提升作品的戏剧性,使之更加激荡人心。对矛盾与冲突使用最为深刻、最为崇高的艺术形式是悲剧。柏拉图从现实要不断趋向理式——也就是趋向完美和一致的角度 (他曾明确拒绝理式世界中包含坏的理式),拒绝了悲剧的积极作用,因为悲剧中包含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带有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形式,与理式的一致性并不统一,与理想城邦中审美教育的目标也背道而驰。但后世的哲学家很快就证明了柏拉图在美学上犯的错误。审美与艺术并不能在秩序性世界中发挥到极致。悲剧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恰恰是冲突与矛盾,宣泄和净化了人的审美情感,冲突与矛盾在悲剧中往往得不到解决,矛盾和冲突越是激烈,就越是激荡人心。黑格尔在以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为例分析悲剧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冲突说,主张悲剧的伟大效果是由两种互相冲突、互不相容的力量所导致。
尽管怀特海企图将传统哲学中潜在的过程与有机体的思想明朗化、体系化,使现实实有摆脱孤立的、机械的存在方式,实现内部超越,更加完美地趋向和谐,但他对矛盾与冲突的处理显然有缺陷。因为他只强调了现实实有服从合生过程的秩序和一致性,而忽略了包含在现实实有中的矛盾与冲突所特有的能量和魅力。从美学的角度看,在某种程度上,怀特海又回到了柏拉图的时代。矛盾与冲突在过程哲学中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只能用秩序的力量将其转换化为和谐的存在,或者将其直接消解掉。但矛盾与冲突又不可能在美学中消失,因为很难说生命仅仅是在现实的三围空间中生长,否则,想象与梦境便没有存在的空间了。怀特海虽然为否定的摄入,也就是因为含有矛盾和冲突而对于某一特定的生成过程不适用的现实事态,找到了另一种存在和起作用的方式,即在其他合生过程中的肯定参与,但那些不被任何过程所邀请的否定摄入仍然落入了时间的缝隙中。因此,合生的过程的实现是以失去了矛盾与冲突的张力为代价的。
三、秩序的选择性与非秩序性的冲动和想象
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的前言中就明确地说道:“我要努力表明:这一体系足以阐释构成文明思想这一复杂织体的那些观念和问题”[6]。庞大的宇宙体系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即一切合生都趋向一个一致的统一体,一切文明思想都能在这个统一体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能支持这个统一体的是“秩序”。一致性是自由,秩序是关于自由的规定,“每一个现实实有的生命都是内在规定了,而外在是自由的”[7],这意味着一切合生的过程都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作为有秩序的宇宙统一体是选择之后的必然结果,但这一选择的结果将不符合一致性的冲动和想象扼杀掉。秩序强制性地赋予了一切现实实有永恒性,将永恒的东西植入本质上流动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对永恒性的获得是以牺牲自身的冲动和想象的生机为代价的。怀特海自己也承认,“秩序,作为达到优秀的条件,秩序,作为扼杀生机的因素”[8]。这便是“秩序”在过程哲学和美学不同语境中的终极矛盾,也是过程哲学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哲学达到了终极目的,而美学失掉了一切。
过程哲学的这一缺陷首先是由过程的重复引起的。宇宙统一秩序的实现是靠众多合生过程的重复,一个现实实有在一个合生过程中的参与,是以不断摄入的方式趋向其主观的满足,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新的实有产生,这个新的实有又成为了下一个合生的起点。重复使得现实实有向满足状态的趋近成为一种自然的、主动的选择,选择肯定性的摄入所带来的合秩序性,排除否定性的摄入所带有的矛盾和冲突。这种选择最终遵循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原则——那些无秩序不合逻辑的疯狂冲动和想象被直接地、自觉地排除在外了。
造成“秩序”的缺陷的另一个因素是怀特海对时间观念的处理。时间观念与现实实有的永恒性相关,现实实有的生成过程最终达到的满足是一个新的生成,但被摄入的现实实有并未消亡,而是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它在新的现实事态中发挥部分的作用。一个现实实有的生成永远不能脱离之前的实有,于是每一个现实实有都是有意义的,都在宇宙统一体中或明显或潜在地发挥作用。因此,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每一个新生成的实有都保留了之前的实有的种种特质。例如,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旧生命的灭亡,而是意味着全新生命的开始,因为肉体在消失之前已将其自身的特质,包括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以遗传的方式注入了新的机体。因此,就时间而言,人是永恒的,是一个不断吸纳新颖性的过程。但时间对现实实有广泛的、有秩序的容纳,使世界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怀特海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他说,“它一方面渴望新颖,另一方面却又心怀恐惧,唯恐失去过去,连同它的那些为自己所熟悉所珍爱的东西”[9]。这样,“秩序”在合生过程中所丢失的,连同它不愿意舍弃的过去,都不断缩小着想象和冲动的空间,种种突如其来的、大胆的、跨越式的东西都成了不合秩序的怪物。宇宙达到统一、和谐的时候,便为美学留下了一个最为贫乏的世界。
怀特海承认想象与冲动是美学与艺术的必要因素,承认它们是生机的源泉,但这种想象和冲动在他所谓的能解释一切的体系中得到的却是不完全合法的地位,“秩序”这一概念所存在的缺陷以及它在过程哲学和美学的不同语境中所存在的矛盾得不到解决。这使怀特海不能完成在《过程与实在》开始时提出的伟大目标。他在著作的结尾略提及了的“秩序”的缺陷,但并未找到一种合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过程哲学中“秩序”所存在的缺陷,将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注 释】
[1]在过程哲学中,现实实有和现实事态的含义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更加强调发展过程的事件性和动态性。
[2][3][4][6][7][8][9]怀特海:《过程与实在》第一卷第 3页,第 34页,第 1页,第 37页,第 465页,第 467页,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5]注释:此处所说的喜剧效果与喜剧的含义不同,指的是消解了矛盾的现实实有的状态,而后者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
B83-0
A
1009-6981(2011)03-0081-05
2011-04-23
董艳丽,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袁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