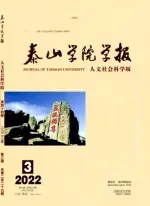城市、商业、市民——大都杂剧繁荣的客观条件
傅秋爽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 100101)
戏剧,是一种群体消费型的艺术,它不同于诗文、小说这类语言艺术,可以无视接受者的存在,其生存、发展始终要依赖于消费群体。同样,杂剧的发展和兴盛,也有赖于该种文化消费群体规模性的成长。宫廷性的各种娱乐演出,自古有之,但是要形成一种能够立足于世的独立样式,非走向民众,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可。杂剧早在辽代就已经具备了其基本形制和名称。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外交宴请场合,用杂剧演出招待来宾也已经成为惯例。当时这些杂剧主要流行于燕京一带。经过金代的发展,杂剧依然未成气候,还停留在宫廷而没能真正走向民众。到金末元初,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城市性质的改变和真正意义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为杂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广泛的消费群体。
对于杂剧兴盛与经济发展、城市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少学者持肯定态度。但是在发展和繁荣的内涵上却有很大的分歧。一种是正面的、积极意义的“繁荣说”,如: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认为,元代杂剧“是宋金时代戏剧合乎规律的发展,是在城市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繁荣起来的。”[1]阿英在《元人杂剧选》中也强调说:“关键性的保证了元曲加速成长的,是元代的经济关系。元代经济繁荣,促进了元曲的发展。”另外一种论点是与之相反的“畸形繁荣”说。他们认为元代在蒙古贵族统治下,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但由于统治者把财富集中到了少数大城市,把大量工匠赶到城市组织消费品生产,同时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也陆续流入城市,从而导致了城市的畸形繁荣。围绕这些问题,长期以来研究者们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分歧依然。
事实上,所谓“畸形繁荣”说的立论根基,依然是以中国传统经济模式重农轻商的保守思想为基础的。这种思想基础之上所制定的发展国策,必然导致中国长久以来的农业立国,广袤的农村从事着落后的农业生产,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孤立地、分散地、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发展停滞不前,缺乏生机活力。如果以农村与城市的数量以及二者之间人口规模相比较,农业立国的中国传统经济模式才是失衡的、不成比例的、“畸形”的,同时也是制约了生产力发展、腐朽而落后的。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必须有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产业的规模化聚集,科技、商贸、交通、运输的全面配合,市场的有效开发,经济才能获得发展活力,城市才能健康成长。就像是衡量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就看生产力是否得到解放一样简单的道理,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元朝科技的发展水平,生产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文化的广泛影响,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判断出这个王朝所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充满生机活力的还是腐朽衰败的。整个元代,手工业的生产力与两宋和辽金相比,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纺织、陶瓷、酿酒、制盐、冶炼、开矿和兵器制造业等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生产工具得到改良,技术水平极大提高,产品种类和数量都大为增加,国内外市场急剧扩大。在发展商业方面,蒙古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利诱商贾”挖池蓄水的措施,将大都的商贸税率压低到了四十分之一到六十分之一,甚至是“置而不税”,以此来吸引天下商贾。如此背景之下,大都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的确超过了历史上其他时期,它甚至一跃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而这是与元帝国广袤的疆域,强大的实力,先进的科技,广泛的商贸往来相匹配的,是元朝发展经济的努力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它的辉煌是有目共睹的,曾经让世界震惊。至于社会的不公和贫富的差距,那是政治层面上问题,我们并不能因为政治上的失败而否定经济上的部分成功。明代文学家、戏曲作家李开先的认识更为客观。一方面他强调汉族士子“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以其有用之才,寓于声歌,“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另一方面则承认“词肇于金而盛于元,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乐于心而声于口……传奇戏文,于是乎侈而可准矣。穆玄庵谓‘不可以胡政而少之’,亦天下之公言也。”这里所说的“乐”是不事科举、自得其乐之乐。他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归纳为“以见元词所由盛,元治所由衰也。”的辩证关系,表现出客观、理性、科学的精神。
世界戏剧发展史表明,任何国家或地域戏剧的发展繁荣,一定是以城市的规模,商业的繁荣,建筑业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依托的。如希腊悲剧的繁荣,有赖于雅典城邦工商业繁荣,建筑业发达,人口集中,政治活跃。后来罗马戏剧的兴盛也是如此。在东方,因为中国始终都是较为纯粹的农业国家,以农立国,重农轻商,工商业发展比较缓慢。因此,戏剧辉煌时期的到来要晚许多,比古希腊戏剧至少迟了一千多年。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着以其辉煌足以傲世的著名城市,如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但是,中国以农业立国的性质,决定其都城更多发挥的是政治、文化中心的效能。因而尽管长安、汴梁等城市当时手工业、商业也都非常繁盛,也都为戏剧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如唐代出现了戏剧的雏形参军戏,宋代作为戏剧商业演出场所的瓦舍勾栏大大兴盛,但它们终因城市的各项功能基本都是紧密围绕国家政治中心这个枢纽在运转,是以为宫廷和统治集团提供服务和物质保障为核心的,所以并非真正意义的商贸城市,庞大的较为富裕的市民阶层也没有能够真正发展壮大。
元代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从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古军队攻占燕京,到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将燕京立为陪都,之后又正式确定为首都,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大都已经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最大的城市。蒙古政权因其经济基础与汉族传统政权重农轻商不同,历来重视手工业生产和商贸活动,所以在城市功能和性质上,从单纯的服务向生产、流通、服务并重转化,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贸聚集财富,在促进城市功能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繁荣发展。蒙古政权对工艺技艺也有特殊的偏好,蒙元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杀人如麻,惟独将医、巫、金银工、画家、塑匠、陶瓷、瓦木工等工匠艺人视为财富,不予人身性命伤害,而是抢掠据为己有。由于统治者对工艺美术特别重视,元代手工艺者和艺人这些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被视为雕虫小技的“末业”之人,身价大幅度提高,如雕塑家阿尼哥、刘元等都曾得到皇家特殊礼遇,封官并给以特权,许多画家也因为其艺术技能而封官进爵。蒙古政权他们在武力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从西域和全国各地迁到京师大都大批的能工巧匠,工匠尤其是高等工匠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且在完成规定的生产额度之后,产品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买卖,获得一定报酬。商人,尤其是大商人的利益得到了特殊的关照与保障,许多蒙古王室贵族将他们在战争中聚集的巨额财富,委托给色目人代为打理经营,谋取暴利。因而,色目大商人们的商业行为,往往具有王室或者贵族的政治背景,有些行业甚至具有官商垄断性质。为手工业和商贸提供一切尽可能的便利,这在首都城市规划和建设上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大都兴建之前,无论是辽南京、金中都,其城市格局都是继承汉唐坊里制,城市居民被隔离、封闭、限制居住在坊墙之内,通过宵禁等制度进行出入管理,公共娱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大都在规划建设时,虽然保留了坊的形式,依然有坊门,规划整齐对称,但是坊基本只作为管理单位而存在,高大封闭的坊墙已被废除,实行空间开放的模式,出入便利,活动自由。
元代城市建设中,非常注重公共活动场所的设立,有些公共场所大多与商业市场相连,这使得包括杂剧演出能够随时吸引更多的居民。大都城内民间演出戏剧主要是在专业的勾栏或歌台酒楼。勾栏很多,例如位于皇城西(在今西四南大街)“羊市街”就是一条著名的娱乐街。元李好古杂剧《张生煮海》中有一段人物对白就特别提到“砖塔胡同”、“西院勾栏”。在其附近,是羊市、牛市、马市、骆驼市等,商业交易频繁,流动人员也多,所以自然也就成为勾栏演出非常活跃的地方。元熊梦祥《析津志·岁纪》记载说:“二月八日,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寺之两廊买卖富甚太平,皆南北川广精粗之货,最为富饶。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其华丽。……教坊诸等乐人、社直、鼓板、大乐、北乐、清乐……互相夸耀。于以见京师极天下之丽,于以见圣上兆开太平与民同乐之意。”
杂剧演出的另外一个场所,就是歌台酒楼。这里的演出可能不像勾栏之中那样正规,行当、服装、配乐未必齐全,应该是类似于清唱或者杂剧片段演出。元无名氏[般涉调·耍孩子儿]《拘刷行院》套曲中[十三煞],曾对歌台酒楼里的戏剧演出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穿长街蓦短衢,上歌台入酒楼。忙呼乐探差祗侯,众人暇日邀官舍,与你几贯青蚨唤粉头。休辞生受,请个有声名旦色,迭标垛娇羞。”从这段话可以得知,歌台酒楼就坐落在市民可以方便进出的街上,而演员的演唱是随时可以付钱邀约的。位于皇城以北的“斜街”是元代很著名的歌台酒楼集中之地,这条街位于钟楼、鼓楼一带,与海子(即今积水潭后海)毗邻。因这里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商贸繁荣,人气鼎盛,所以在这条街上,“率多歌台酒馆”。诗人宋褧词[望海潮]《海子岸暮归金城坊》就描绘出海子边斜街歌舞繁华的盛况:“山含烟素,波明霞绮,西风太液池头。马似游龙,车如流水,归人何暇夷犹。丛薄拥金沟,更萧萧宫树,调弄新秋。十里烟波,几双鸥鹭两渔舟。暮云楼阁深幽,正砧杵丁东,弦管啁啾。淡淡星河,荧荧灯火,一时清景难酬。马上试冥搜,填入耆卿谱,摹写风流。明日重来柳下,携酒教名讴。”著名杂剧艺妓张怡云就居住在这里。除了大都城内,城外周边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如门头沟等地的杂剧演出也非常活跃,演出场所遍布。
大都居民的构成非常复杂,概括地说是多民族、多职业、多等级,多文化。早在蒙古军队攻占金中都之前,这里的民族成分就已经非常复杂,最多的是汉族,还有女真、契丹等少数民族,数量也很可观。随着蒙古军队的进驻和政权的建立,蒙古民族和随之而来的西域各少数民族的数量大量增加。忽必烈确立大都为国家首都之后,蒙古宗王贵族及其家属、随从、仆役一同迁来,他们来自草原,虽然定居皇城,依然保留了许多草原生活习性。皇家卫队以及拱卫首都的嫡系部队,主要由蒙古族和色目人组成。宫中的嫔妃宫女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她们面容姣好,很多人能歌善舞。在京的各级官署机构也容纳了大量的官员吏属,还有从事文化、教育、宗教职业的各种专业宗派领袖,他们及其生徒、追随者更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当然,都城中,人口最多的还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工匠,职业繁多,行当齐备,几乎囊括了当时生产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许多技艺都处在国际先进水平。从蒙古国时期,大批的工匠从西域少数民族地区迁来燕京,从事手工业生产,其管理单位为工匠总管府。一个总管府管辖的工匠少则数百,多则数千。而大都所设立的工匠总管府多至数百。由此推断,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加上工匠的家属,数量更为可观。这些工匠及家属成为大都常驻人口的一部分。此外大都四通八达的交通,为商贸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大都成为百物汇聚之处,天南地北的物产被运送到大都城。所谓的“四海为家天地开,诸侯方物集燕台”这里因此而聚集了为数众多的商人,除了国内的坐贾行商外,还有大批来自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的商旅。《马可波罗游记》描述说:“应知汗八里城(即大都)城内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供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2]据王恽记载,中统年间,燕京路有回回商人二千九百余户。来自周边国家日本、朝鲜以及中亚、南亚、乃至欧洲、非洲的使团和商队络绎不绝。此外,由于蒙古政权对外交往的广泛,各国经济、文化使团的到访也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和数量。进京觐见的宗教使团也是络绎不绝,据记载,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前,罗马教廷就曾多次派出教团前来蒙古都城,忽必烈即位后,教廷又派出教团到大都,争取对他们在中原地区传播基督教义的支持。佛教的寺庙、道教的道观以及大都的各类专门的教育机构,不仅容纳了大量常驻的专业人士,机构管理人士,也随时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同业者、学习者、朝觐者、游历者,这些共同构筑了大都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大量人口,产生了对文化商品的大量消费,数额极为惊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曾经记载说:“汗八里(即大都)……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那里有二万五千名娼妓。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朝廷所吸引,不断地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娼妓数目这样庞大,还不够满足这样大量商人和其他旅客的需要。”[2]这里所谓的娼妓,并非单纯色相售卖,更多的以歌唱、舞蹈、音乐等文化技艺供人消遣。
反过来,城市的繁荣,经济的发达,生活的便利、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首都所独有的个人发展机会的优势,又使得城市吸纳能力急剧增强,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和人才到此定居。时人已经关注到大都这一特殊的现象,危素指出:“京师众大之区,四方士苟负一艺一才,远者万里,近者数百里,航川舆陆,自东西南北而至。”这反过来又使得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壮大。据记载,至元顺帝时,大都已号称“人烟百万”,绝对称得上是人口众多较为庞大的世界城市了。这么一个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语言和交流方式不同,杂居混处的庞大市民群体,使大都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形态。大都人口的基本构成、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是观众决定了杂剧的基本面貌。
英国近代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在他的《剧作法》一书中,开头就指出:“戏剧除了对于观众以外是毫无意义的。它是用一种特殊的手法描绘出来的生活图景,这种手法本来设计得就是为了要用这种生活图景深深打动聚集在某一指定场合的相当数量的观众的。有句话说得很好:‘观众构成剧院。’”[3]弗·萨赛也说过:“任何戏剧作品,都是为了演给由若干人组成的一群观众观赏的,这就是戏剧作品的真正本质,这就是一个剧本存在的必要条件。”[4]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的《戏剧剖析》说的更为干脆明确:“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戏剧。”[5]其原因,用阿契尔的解释是:“用戏剧叙述故事的艺术,必然与叙述故事的对象——观众——息息相关。你必须先假定面前有一群处于某种状态和具有某种特征的观众,然后才能合理地谈到用什么最好的方法去感动他们的理智和同情心。”[3]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也表达了近似的意见:“戏剧是和整个戏剧表演的物质领域——包括它的拥挤的观众和普遍的感染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之为转移的。”[6]大都杂剧的繁荣是建立在同样的根基之上的,与当时当地观众的社会生活和普遍心态有着密切关系。表面上看,杂剧艺术是依靠杂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来完成的,但实际上,创作什么样的作品,表达怎样的思想却是由观众所决定的。因为作为文化消费品的杂剧,要想赢得更多的观众,就必须针对消费对象考虑他们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应该说,有什么样的观众,才能产生什么样的杂剧。大都观众的指向,决定了大都杂剧创作中人物的选择和塑造,决定了其思想的表达、道德的评判、是非的抉择和审美意象。正如学者姚华所言:“曲为有元一代之文章,雄于诸体,不惟世运有关,抑亦民俗所寓。”[7]
由于史料的缺失,文字记载的匮乏,今日我们对于大都杂剧观众的了解知之甚少。但是正如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所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象一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8]同样,从大都杂剧作家留给我们剧本中,虽然遥远但是依然可以清晰地听到了大都观众的回响。我们从现存杂剧剧本中,可以窥视出当时观众的构成,和他们所关心的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及其命运。一般来说,观众更易对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联系或者相似的人物命运倾注更多的关心。关汉卿的创作,将目光投射到社会下层人物的身上,歌颂他们的反抗、正义、善良。应该与当时观众的社会身份、地位以及接受心理相关联的。因为就观众的接受心理而言,人们总是将戏剧作为一面镜子,来实现对自身生活与命运的观照。人们经常说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实际上观众的欣赏活动又何尝不是呢?他们同样更希望欣赏那些与自己生活密切关联的作品。大都杂剧创作,题材极为丰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和人们情感的复杂多面。
这首先表现在对于文学样式的选择上。历史学家翁伯赞在《读郑振铎<关汉卿戏曲集·序言>》认为:“元代由于中西商路的畅通,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居住在城市的商人和富裕地主,在厌倦于物质生活的时候,他们也要求文化艺术的享受。而且他们对文化艺术的胃口,愈来愈大。他们已不能满足于单调的说唱和歌舞之类的艺术,要求更高级的文化艺术享受。戏剧正是适应这种要求繁荣起来的。”杂剧观众的主体是否是城市商人和富裕地主,还值得进一步商榷,此处姑且不论。但是人们不再满足单调的说唱和歌舞之类,要求更高级的文化艺术享受却是符合客观规律和历史真实的。顾学颉认为“杂剧是一种市民文艺的较高级形式,事实上超越了以往的市民文艺形式”,所以在元代得到市民阶层广泛欢迎,“突出地、活跃地、成功地发展起来,并达到非常兴盛的地步”[9]。无疑,杂剧这种更高形式的文化产品,是迎合了观众们日益提高的文化艺术品位而产生的。说明人们对文化的消费档次提高了,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戏剧的形式,又是大都观众身份复杂、文化程度参差、欣赏口味差别化等矛盾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杂剧是集音乐、歌唱、舞蹈、诗歌、美术、朗诵于一身的综合艺术,以叙事为手段,以启发思想,拨动情感,传播审美为目的。杂剧这种手段、形式的多样化,使之较之以往诗、词、歌、赋体式的单纯或者是音乐、舞蹈、歌唱的单一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语言不通,可以欣赏华丽的装扮,优雅的舞蹈和身段;韵白不懂,可以品味优美的唱腔,享受悠扬的音乐;即使仅仅明了故事,也能够随着剧情牵挂着主人公的命运和结局,为他欢笑,为他哭泣。也就是说,无论你的审美重点在哪里,你在杂剧中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个位置。这种新的杂剧样式要比宋杂剧、金院本容量大得多,正如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所言:“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其丰厚的内涵,能够满足观众不同的审美需求,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剧场。
不同的生活形态、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欣赏习惯以及交流方式,都可能对人们选择怎样的文化消费品产生影响。除了部分“应差”——即用于宫廷、官府等行政性的演出——之外,杂剧在元代基本上是市场化的文化商品,观众对杂剧有着最大的选择自由。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能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同时,文化产品又反过来影响更多的消费者。今日我们赞叹的杂剧题材的广泛、思想的丰富、风格的多样,其实都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密切关联,更与观众们所关注的问题密切关联。例如,山东因地缘关系,民众有着浓郁的水浒情结,所以那里的水浒戏尤为发达。杂剧发展后期,中心转移到了江南,在题材上就发生了转变,家庭伦理道德剧大量增加,这说明那里民众的关注点与北方有很大的不同。大都杂剧创作搬演之所以悲剧、喜剧、悲喜剧诸体兼备,公案戏、三国戏、水浒戏、神道剧、爱情剧、社会剧全面繁荣,恰恰说明了大都观众社会层级涵盖面的广泛。试想,如果观众的主体是城市富商,杂剧中怎么可能大量充斥着对商人负面形象的无情刻画和尖锐嘲讽?如果商人之外杂剧的另外一个观众主体只是富裕地主,那么杂剧也许只是搬演一些《老生儿》《破家子弟》之类也就罢了。大都杂剧是如此丰富多彩,朱权《太和正音谱》将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拔刀赶棒,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十二曰神头鬼面。”说明当时的观众涵盖极为广泛。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有官员,有商人,有娼妓,有市民,有士子,有匠人,有僧侣,有信徒,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所以,宫中搬演《伊尹扶汤》,百姓观赏《窦娥冤》,青年男女被爱情剧吸引,僧侣信徒更愿畅游神道世界,落魄的士子希望在剧中实现登科翻身抱得美人归的理想。他们的诉求如此不同,有多少种观众,就有多少种杂剧题材。同样的题材,有些以感天动地的悲剧表现,有些用轻松、幽默、机智、嘲讽的喜剧手法出之,通过不同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塑造不同领域中的各种人物,以便观众认知社会、感悟人生:窦娥的冤屈(关汉卿杂剧《窦娥冤》)触动了普通民众对社会不平的愤慨,激发了对黑暗统治和官僚极度腐败的反抗;关云长英武豪迈(关汉卿杂剧《单刀赴会》),不甘强权,忠贞信仰理想的形象,“引导苦难的元代人民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理想、更高的品质”[10]。这使得所有的观众都能在相应的杂剧中找到自己的感动,灵魂在观剧中一次次受到震撼、洗涤、升华。元杂剧所表现出来的总体思想趋势,正是当时大都观众市民意识的主要特征和主导倾向。同时,观众“谛听忘倦,唯恐不得闻”的强烈艺术反应,也足以说明大都观众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欣赏兴趣广泛,他们关注历史、现实、政治等重大社会问题,易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同时也颇具幽默素养。如此,杂剧才能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这是杂剧繁荣的民众基础。
除了文化根基方面的原因之外,杂剧繁荣于大都的另外一个不可忽略因素,是这里民众与杂剧具有语言、音乐等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亲近感,这是一份得天独厚的优势。杂剧与散曲是盛开在大都文坛的一对并蒂莲,杂剧在唱腔与散曲曲调为同一系统曲牌,在语言习惯、音韵腔调、表达方式上本于一源。大都是散曲肇源地,又是元代散曲鼎盛之都。散曲较之杂剧创作参与者更多、文化层次更高,杂剧较之散曲有更广阔的观众市场和民众基础,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促进。散曲上口便利,不择场地条件,学习较易,传播亦广,这就为欣赏杂剧艺术作了“预演”、“顺耳”的准备,使得杂剧具有了更广泛的民众基础。杂剧具有文学特性,但从传播角度考察,更主要的是依赖于其表演特性,周德清总结说:“要耸观,又耸听;格调高,音律好,衬字无,平仄稳。”耸观,就是书面读起来要美,耸听,是要易于演唱,易于理解。从接受角度考察,音乐的旋律,歌唱的曲词,都要依靠耳朵聆听方能达到欣赏的目的,所以“造语必俊,用字必熟;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太文则迂,不文则俗”,太文了,普通观众听不懂;太俗了,粗鄙不堪,没有美感。在“观”与“听”和“文”与“俗”之间把握平衡,都是为了达到广泛顺畅传播的目的。由于语言、用韵、音律等方面杂剧和散曲一样,都是以中原之音为正声的。元人孔齐曾明确提出:“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这种的“中原雅音”就是以大都语音为基础的类似于后世“普通话”的官话,应用广泛,“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杂剧、散曲的创作及演唱,皆是以此为标准音,此即所谓“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正声”即“中原之音”、“中原雅音”。其时元曲创作、传播之盛“自绅及门阎歌咏者众”,覆盖达官勋贵、吏员僚佐、文人士子、艺伎优伶在内的各个阶级、阶层的成员,范围极其广泛。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杂剧所用词语也都是大都话语,夹杂着一些流行大都的方言、俗语、非汉族的输入性语言,这些对于大都观众来说,耳熟能详,不仅不会造成理解的难度,甚至还可以增强语言的幽默感、风趣性。大都观众在观赏、聆听和理解、欣赏杂剧方面既无语言障碍,又无音韵旋律不适应的隔膜,这是大都观众的优势,也是杂剧原产地生长的优势,同时也是杂剧繁盛于大都的客观因素之一。
建筑业的发达,使得城市中用于杂剧艺术表演场所勾栏的建设非常容易。虽然大都戏剧舞台的实物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我们以文物考古、相关文献作参考,依然可以推断出其大致形制、结构。与现在山西遗存的元代戏台作比较,大都的舞台在形制、容纳观众规模、数量,以及观众观摩时舒适度方面当有较大区别。因为现在山西遗留的戏曲舞台,多数位于村庄的核心地带,是较之周边几十户人家一个聚落的小村庄要稍微大一些的乡村或者小镇,一般是依庙而建,保留了古代社戏敬神、娱神的功能。尽管当时也用作杂剧表演,但这些演出并非经常性的,而是在庙会、节日、庆典时才有,是临时性的活动场所。十里八乡的人聚拢来,面向舞台,或者搬来长凳坐下,但更多的恐怕是站在那里观看一两出也就散了。杜仁杰散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则描绘了杂剧演出的标准场地:“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那是一个提供了科学的观看角度,能够坐下的半圆型的剧场,不仅合理,而且方便、舒适。它不像乡村舞台是开放式的,而是空间基本封闭或半封闭的,必须经过有人把守的门才能进去,进去之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个合适观看的位置。杜仁杰散曲中所描述的勾栏设在不大的城镇,应该属于比较简陋的临时或半临时性的建筑。大都相同的设施理应更为富丽堂皇,那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也许类似古代罗马大剧院或者角斗场吧。因为既然马可波罗这些西方的宗教、商界人士和文化使者能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通商、进行文化交流,那么他们把在欧洲业已发展了千年的戏剧演出场所的形制样式介绍到中国来,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无论如何,对于聚集着大批能工巧匠,建筑水平高超的大都来说,勾栏建设即使规模再宏大,装修再富丽,技术要求再高应该也都不在话下。
要之,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文化消费诉求,必然要通过某种形式得到满足。因此,经过辽、金多年酝酿,宫廷、节庆反复演练的戏剧,在加入了诸多新的元素后,逐渐完善,成为广受民众欢迎的成熟的艺术形式。与其说杂剧引导了民众的文化消费趋向,不如说是城市民众特有的文化需求呼唤了杂剧的产生。
[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马可·波罗游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3]威廉·阿契尔.剧作法[M].吴钧爕,聂文杞,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
[4]约翰·霍华德·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M].邵牧君,齐宙,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
[5](英)马丁·艾思琳.戏剧剖析[M].罗婉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6](英)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M].徐士瑚,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7]姚华.曲海一勺·述旨[A].吴国钦.元杂剧研究[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8](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9]顾学颉.前言[A].元人杂剧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0]宁宗一.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