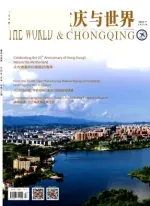略论公孙龙子与经院哲学的共相观之异同
赵渊杰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呼和浩特 010021)
略论公孙龙子与经院哲学的共相观之异同
赵渊杰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呼和浩特 010021)
通过将生活在公元前 250多年战国时期中国哲学家公孙龙提出的共相观与公元 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波菲利的共相观进行对比,介绍东西方哲学家关于所谓共相的不同阐释,以及东西方就潜存事物的不同分析方法。
公孙龙;经院哲学;共相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曾说:“现代新实在论者谓个体存在 (exist);共相潜存 (subsist),既不在时空中占有位置,而亦非无有。”这一点正可以运用公孙龙《坚白论》中“坚”的性质来说明,即冯友兰先生所谓:“如坚虽不与物为坚,然仍不可谓无坚。此即谓坚藏,即谓坚潜存也。知‘坚藏’之义,则《公孙龙子·指物篇》可读矣。”[1]236这里,冯先生已经将东西方不同时间、不同地域所探讨的几乎同一的哲学命题放在了一起来探讨,但是由于该书旨在着重介绍中国哲学名家的主要思想,所以未将西方现代实在论共相与公孙龙的所指做进一步具体分析。本文将在冯友兰先生的启发下,进一步论述共相与“指”,并进行对比分析,意在分析、对比出东西方就潜存事物的不同分析方法,希望为人们对比东西方哲学思想提供些许思路。
公元 12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提出了关于“共相”的 3个经典问题:
共相是否独立存在,或者仅仅存在于理智之中?如果他们是独立存在,他们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果他们是无形的,他们究竟与感性事物相分离,还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并与之一致?
并且波菲利曾预言“这些问题是最高级的问题需要下功夫研究”[2]。波菲利的 3个问题实际上是从 3个不同的层面探讨所谓“共相”的属性:共相究竟独立存在还是存在于理念之中,共享是否具有具体的形体,共相与具体感性事物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指物论》中,公孙龙阐述了他的共相观即“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他以“指”与“物”(实体、现象、个体)相对,“指”含有动词“指认”“称谓”和名词“名称”的意思,这里主要指共相。因为在这里,公孙龙已经把“指”与“物”划分成了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对应的概念范畴,可以说“指”就是物的反映。“公孙龙强调,概念和所指谓的物是不同的。天下有物,而人用概念去指谓它。另一方面,没有物是不由概念来指谓的。”[3]“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①引自《指物论》。其意为,现实世界并没有“指”这种东西,指谓物的指其本身与它所指谓的物是不同的。总之,不能将“指”与其所指谓的对象物相等同。同时,“物莫非指也”强调出,物必须要有“指”来指谓,不存在不由“指”来指谓的物。公孙龙的共相观大致可以归纳为,共相是不变的,知性概念以确定性为根本的表征思想。对比公孙龙与波菲利关于共相阐述的方式角度,大致可以分析出,波菲利谈到共相问题,一开始便将有关共相的问题分为 3个大的板块罗列出来,即,(1)共相是否独立,(2)共相是否有形, (3)与可感事物的相互关系。这 3个问题看似以并列的方式提出来,但是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假设共相独立,则是共相有形的最基础条件,因为我们很难设想会有概念层面尚不足以独立存在的事物会有形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共相假设具有了独立有形两种性质,再来探讨它与可感事物的关系似乎更为顺理成章。因为又假设存在的情况,就同时蕴含了假设其不存在的可能性。这样来看,共相问题上述的 3个板块则直接构成了一直以来唯名论与实在论关于共相问题的直接矛盾交锋点。可见,波菲利在最初提出共相观三大板块问题时,就已经为共相问题的探讨空间提供了广阔的维度。而公孙龙在论证有关共相问题的时候,则是以一连串的逻辑推理将他所认为的共相以及共相与物的关系呈现了出来,但是与波菲利不同的是,公孙龙在这里采用了结论式的说明方式论证“指”与物的关系。与波菲利假设式的说明相比,似乎压缩了对于共相探讨的空间,这也许是在西方形成了唯名论与实在论的长期争执,而在东方却并没有形成关于“指”问题进一步激烈争论的原因之一。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院哲学对于共相分析的过程,是一个不同年代不同派系哲学家不断论证的过程。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凝结了历代哲学家关于共相的争论与推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唯名论与实在论两个主要派别。可以说,西方的关于共相观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讨论争辩的形成过程。而在中国,则主要是名家关于共相的论述,其中以公孙龙最为典型,而并没有就共相的问题展开类似于西方经院哲学那样激烈而且旗帜鲜明的争论。因此,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共相学术系统主要是个人著述,而非对话论辩的形式。
《公孙龙子》中大多以主客问答的形式来表现论证内容,其中,“客”将概念认为成一种语言外壳,是便于表达的一种符号而已。可见,在这里,“客”的共相观将共相极度具体化,认为共相无非就是一种语言符号,因而是认为附加在具体事物上的。通过这个论证,推得所谓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的共相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里,“客”将共相首先理解为一般概念,但是不论是一般概念还是具体概念,其最终都将以语言、符号、声音变现出来。而上述所有的表达方式,也都无法最终脱离于具体的感性事物而独立存在,就此,排除了共相作为独立于事物个体存在的可能性。“客”的这种推理,基本与经院哲学中以罗色林为代表的极端唯名论者不谋而合,因为极端唯名论者认为共相只是名词,如果说他们是实在的话,这种实在不过是“声音”而已。可以说是达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所谓“客”与极端唯名论者的共相观,无非是将共相客观存在的空间极度压缩,使之仅局限在语义学的名词概念上,甚至是物理学的声学概念上,而否定了共相 (“指”)的独立实在性,同时将“共相”定位在从属寄生于具体事物的概念。对此,公孙龙作为“主”的回答与经院哲学中的唯实论者有着诸多的相同与相异,相同点在于公孙龙与唯实论者都反对“客”与唯名论者将共相概念作为具体事物的从属概念提出。公孙龙指出:“且指者,天下之所无。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①引自《指物论》。在这里,公孙龙认为,虽然没有“指”这种实在事物,但是,“指”对于物的存在性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不由“指”来指谓的事物,而唯实论者恰恰也否认否定“共相”独立性的做法,强调突出“共相”的主体作用。而公孙龙与唯实论者的理论论述逻辑推理又具有着明显的差异。公孙龙承认了单纯作为“指”(“共相”)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即否认了“指”(“共相”)的客观存在;而唯实论者则认为,共相既是一种心灵的一般概念,又是这些概念所对应的外部实在,从而肯定了“共相”概念的实在性。说它实在是因为它既存在于人们一般心灵感觉的空间中,也有着具体的外部事物与其相对应。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共相存在于人们的一般心灵概念中,并非像一般事物那样可见,另一方面,共相虽然有具体的外部事物与它对应,但是绝对不应当将共相与一般事物相等同,这样似乎确定了共相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成立的依据。
以上论述,着重介绍了公孙龙、唯实论者、唯名论者关于“共相”的认识以及探讨。总体来说,公孙龙论证共相观的方法更具有中和性。
之所以说公孙龙论证共相观的方法更具有中和性,是因为公孙龙的“共相”即“指”较中和地处理了唯名论与唯实论共相观分歧产生的矛盾点。实际上,“共相”概念成立的前提本身就应该具有较为明确的形而上学性质,因为以简单的实际经验来判别,所谓共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不能用简单的肢体感官去解释“共相”的实际内涵。唯名论者所谓的将共相归结为一种声音或语言,本身已经脱离了形而上学的层面,而脱离了形而上学去将“共相”强制性的与肢体感官对号入座,再来探讨“共相”的形而上学概念就意义不大。因为唯名论的共相观实际上本身就没有把共相与具体事物相分离,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可直观感受的事物,二者概念层面尚存在着粘连,这样的比较实际上是将具体事物与具体事物相比较,而不是将共相与具体事物相比较。
而极端实在论者的共相观念却将“共相”的形而上学性过于夸大,认为共相可以独立于物体存在,并且承认共相是区别于物体之外的实体,但是在逻辑论证层面确有着独断论的嫌疑。因为他并没有严格的理论论证说明为什么在具体可感事物之外存在绝对独立的共相,可以说极端实在论者为了保证共相概念的独立性,极端地割裂了共相与具体事物的内在联系,因此又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另一个论证共相存在的极端。
公孙龙“指”的“共相”观念更为趋近于温和唯实论与温和唯名论的共相观,公孙龙并未脱离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讨论“共相”概念。按照公孙龙的说法,世界上既然不存在不由“指”来指谓的事物,换言之不由“指”来指谓的一定不是事物,这就明确肯定了“共相”对于事物概念成立的重大作用,并且能够“由现象分析到共相分析,由事实分析到语言分析”,使得“人类用心智借助知性概念去认识‘物’背后的共相语言则凝结着知性对共性的认识”[3]。但是,公孙龙并没有主观夸大“共相”的形而上学性,他认为“指”并不能脱离事物存在,因为世界上是不存在没有指谓对象而仅仅存在指谓行为的,与人建立联系的事物,必须通过“指”即共相来指谓。可以说在公孙龙那里,对于认识的主体人来说,所谓“共相”与具体可感事物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脱离了物的“指”(“共相”)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了“指”(“共相”)的物,对于人来说,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无。
正是公孙龙论证了共相与物的相互依存的相对平等性,才很好地避免了上文中提到的极端唯名论与极端唯实论的分歧点。其实,无论是极端唯名论还是极端唯实论都是在论证“共相”与物二者时,夸大一者而使之凌驾于另外一者之上,进而不可避免地落入极端主义的深渊。公孙龙则通过缜密、中和的论证思路,将“共相”与物放在了平等的位置来考量“共相”与物的关系,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告诉我们,共相与具体事物是一组互相对应互相辅助成立的概念,对于人来说,只具有概念而不具有任何实体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而只具有实体却没有任何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概念,这种情况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应当平等看待共相与具体可感事物的平等关系。但是,作为哲学的命题,笔者并不提倡一律简单地通过中和来解决问题,因为哲学探讨的问题,多具有较为明显的逻辑思维性质,突出求真的重要性。如果一味用简单的中和来解释说明一个命题,似乎是顾及到了各种观点,但往往也会陷入理论层面的自相矛盾。这样不仅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增加了更多的障碍。对于共相与具体事物的争辩,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理论层面展开不同的探讨,具体说,当将共相与具体事物放在一起探讨二者关系时,在理论层面就应更多地关注其内在的联系性,即共相与具体事物一一对应。如果为确定共相作为一个概念独自成立时,则应当回避具体事物的直观性,而有针对性地来探讨共相本身的含义。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011-03-03
赵渊杰(1988—),男,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B21
A
1007-7111(2011)04-0071-03
(责任编辑 张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