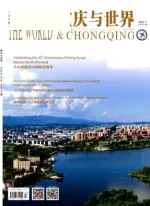论倒置的法律推理①
齐建英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郑州 450002)
一、倒置法律推理的实质在于主体对逻辑顺序的刻意颠倒
法律推理的基本逻辑顺序是从前提推出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可以是“转换”的、“跨越”的、“跳跃”的,但作为一种推理形式,它具有从理由得出结论的最本质的特征。要使法律裁决的证立可被接受,在形式向度上,裁决必须从证立所提出的理由中得出[1]。正是因为这种形式上的逻辑限制或要求,法律推理才能实现同案同判,成为保障司法独立的有效屏障,成为司法判决可沟通性的基础,成为限制自由裁量的手段,实现司法正义的途径,成为“通向正义之路”。所谓倒置的法律推理就是先确定结论,然后,依据结论再对前提和理由进行筛选,从而表现为一种逻辑颠倒的法律推理。如在赵作海案中,先有几个相关部门的协调会上决定的赵作海具备了故意杀人罪的起诉条件,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然后,再由检察院起诉到法院,由法院对前期的证据和线索进行选择,将有罪线索定位为判决理由,而对无罪线索和证据则视而不见。这样的法律推理不符合起码的逻辑顺序,是无效的,是掩盖非正义的烟幕。
要想理清倒置的法律推理的涵义,还必须将之与法官对裁判预测、直觉和法感的依赖区别开来。裁判预测是在裁判中,法官了解案件事实之后,对案件处理结果形成了预测,然后寻找法律依据并最终做出裁判的过程。有倒置的特征。裁判预测客观存在,有学者指出,裁判预测既不可怕,也不可恨,它能有效避免推理过程中的盲目和无绪。裁判预测到裁判结论的推理逻辑过程为:裁判预测——外部证成——内部证成——裁判结论。倒置的法律推理与预测到结论的推理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忽略了法律推理的外部证成与内部证成这个检验的过程[2]。法官的直觉来源于以往的审判经验,它产生在查明案件事实之后,而且直觉本身只是获得结果的一个审判指向,随时准备修正。法律推理倒置过程中所产生的判决结果并不是来源于法官的审判经验,而是基于其他的考虑基础上作出的,是先入为主的裁判;法官为了达到该结果而进行法律手段的选择,甚至是案件事实的调查,完全是一种主观行为,已经违背了法律的正义[3]。拉伦茨认为:“仅以法感为基础的判断,只有对感觉者而言是显然可靠的,对与之并无同感之人,则否。因此,法感并非法的认识根源,它至多只是使认识程序开始的因素,它促使我们去探究,起初‘凭感觉’发现的结论,其所以看来‘正当’的原因何在。”[4]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倒置的法律推理中,前期的结论并不是一个导向,而是最终的结论。它不是一种预测,不是一种感觉,不是认识的起源,而是认识的结论。倒置的法律推理不是客观的认识现象,而是人为的处理结果。是人为选择的一种处理案件的方式,推理的方式。倒置的法律推理是利用先期已经确定下来的结论对案件事实及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裁剪,而不是在充分掌握、全面考虑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的感觉或预测。因此说,倒置的法律推理的实质在于人,人对逻辑的主观刻意颠倒。这样的倒置的法律推理,将非正义的力量掩盖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比缺省的法律推理对我们的法治建设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和伤害性。因为,缺省的法律推理,它直接就没有说服力,可以被人们直接对此进行攻击和批评。而倒置的法律推理在判决书中则被颠倒过来,看似从理由推出结论,是一个完美的具有说服力的判决和结论,殊不知这个结论是在推理前已经定好的,这个理由是根据结论而裁剪的。
从理由推出结论,或者说先有预感或预测,然后通过对预感或预测的检验和验证而得出结论是正常的逻辑顺序,那么,为什么会有推理主体对这一基本的逻辑顺序进行违背和颠倒呢?
二、语境是法律推理倒置的根源
法律推理是在具体语境中进行的,同样的前提结合不同的语境就能推出不同的结论。从外在的视角看,语境是非常宽泛而难以捉摸的,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但从内在视角看,语境是主体建构出来的,每一个推理主体所建构的语境都是具体的,特定的。法律推理是结合语境,在推理主体之间不断沟通和对话的基础上动态进行的。对话的过程,也就是说者向听者明示自己的观念,听者理解说者观念的过程。在对话中,听者和说者之间的身份不断地发生转化。针对听者而言,语境起到解释作用。在法律推理中,它可以通过补足被省略的信息,来解释语言中人为或自然的模糊现象,消除歧义,推断出说者的弦外之音,进而理解说者所表达信息的确切含义。针对说者和听者而言,语境都起到制约作用。“语境制约着整个谈话过程,对于表达和理解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参数。”[5]语境制约着说者的表达方式、语言形式的选择,制约着表达的省略程度;制约着听者对表达的理解;制约着双方的互动方式。语境建构的过程也是推理主体之间进行对话沟通的过程,即针对各自所建构的语境进行讨论,最后得出各方交叉或重叠的语境,即共识性语境,然后再结合该共识性的语境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这时的推理才是恰当的,有效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讲,语境又是法律推理有效性的取消机制。法律推理的有效性包括逻辑有效性、内容的共识性、程序的对话性和恰当性等,其中,恰当性是关键所在。恰当性,即与语境的协调性和契合性。当语境发生变化,法律推理与语境的协调性和契合性丧失;原来的共识性语境遭到破坏,共识性失去了现实依托;推理主体之间还需要针对新语境进行新一轮的沟通和协调。在特定的语境下,也许推理主体就失去了语境建构的参与权,漠视推理语境的共识性,推理的基本逻辑形式也可能遭到破坏,甚至颠覆。
依据正常的法律推理,与案件直接相关的利害关系人,是法律推理的最重要的主体。在赵作海案中,公安机关以赵作海与“被害者”一直有过节;赵作海在村里的口碑不好;赵作海曾在“被害者”失踪前一天与之发生过流血冲突;有人认出现场赵作海家的尼龙袋;赵作海在审讯中做了“有罪供述”等为由,报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经审查核实,发现尸源问题没得到最终确认;压在尸体上的三个五六百斤的石磙,不可能是赵作海一人所为;难以排除逼供、诱供的行为;肢解尸体的刀具没有找到,因此做出了因证据不足而退卷的决定。两次退卷之后,公安系统要么撤案放人,要么变更强制措施[6]。在此过程中,虽然赵作海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并没能作为法律推理的主体出场,甚至难以排出被逼供、诱供的可能,但检察院的立场和观点在客观上代表了他的立场,整个推理还基本恰当。但在后来,推理的语境发生变化。公安机关并没有变更对赵作海的强制措施,而是一直在超期羁押。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整顿超期羁押的运动,政法委针对赵作海的超期羁押第二次召开协调会,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政法委都作为法律推理的主体出场,他们就自己所建构的语境进行沟通,最后,积极响应国家针对超期羁押的政策,不错放疑犯成为压倒性语境。在此语境下,赵作海案具备起诉条件,定性为故意杀人犯的推理结论很快形成。要想实现这样的结论,必须将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形式进行倒置。于是,法官们根据这一结论向前回溯,对原有的案件事实和线索进行筛选和剪辑,演绎了一场从结论到理由的倒置的无效的法律推理。
三、重构推理语境,矫正倒置的法律推理
赵作海案等一些因倒置的法律推理所酿成的冤假错案不仅残酷地伤害了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身心,而且严重地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度,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败笔,应该尽早予以矫正。
矫正法律推理倒置要从重构语境入手。语境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Mey认为:“语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是言语交际时不断变动着的环境。交际者在这样的环境里进行言语交际,并且从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对交际言语的理解。”[7]言语交际中的语境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静态的既定集合体,而是一个随交际的需要不断被创造的变动体,是一个随交际的展开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是听者关于世界假设的子集。正是这些假设,而非实际的客观世界,制约了话语的解释。”[8]15交际中的语境“不再是一个被适应的对象,它时时处在交际主体的不断选取中,它完全可以被创造。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并非一味适应语境,更多的时候是打破固有语境的束缚,创造语境,创造有利于交际效果的语境”[9]。在法律推理中,推理主体不仅是被动地接受语境的制约和限制,更重要的是可以主动地选择和建构语境。在语境的创造和建构中,应该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语境建构主体的多样性。推理主体是语境的选择者和建构者,在语境的创设中起着关键作用。法律推理的主体是复数的,包括法官、双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法学家、社会大众等。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推理主体是法官、双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其他的推理主体只能是在法庭外发表自己的评论和意见。只有最核心的推理主体建构出来的语境,才是直接影响审理结果的推理语境。在赵作海案中不难发现,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成为推理主体,没有参与到语境的建构中来,而是被动地作为语境和推理结论的接受者出现。相反,其他一些不该直接干预案件处理的单位则介入到推理中来,直接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推理语境的形成。
其次,语境建构过程的互动性。语境作为推理主体的心理建构体,由于各自所处的立场、掌握的经验和建构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各个推理主体之间存在差异。“我们并不能建构同样的心理表征,因为一方面我们狭义上的物理环境不同,另一方面,我们的认知能力不同……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掌握了不同的概念,结果,人们能够建构不同的心理表征并做出不同的推理。他们也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推测以不同的方式与他们的经验相关。因此即使他们都共享同样的狭义上的物理环境,但我们所称之的‘认知环境’仍然是不同的。”[8]38然而,任何单一主体所建构的语境都需要接受其他主体的检验和审视。语境建构的过程就是各个主体把自己建构的语境表达出来,与别人讨论,并在讨论中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语境的过程。
最后,语境建构结果的共识性。多个推理主体就各自建构的语境进行讨论甚至辩论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共识,达成理解。达成共识的语境才是最恰当的语境。只有结合具有共识性的语境进行的法律推理才具有恰当性和合理可接受性。
[1]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M].张其山,焦宝乾,夏贞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3.
[2]王庆丰,张尚谦.从裁判预测到裁判结论:“先见”、正确裁判及其过程[M]//吕伯涛.司法能力建设的新视角: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462.
[3]郭卫华.“找法”与“造法”:法官适用法律的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7.
[4]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
[5]周礼全.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14.
[6]刘刚.还原赵作海冤案形成过程:乡村道德审判成推手[EB/OL].(2010 -08 -01).http://henan.sina.com.cn/news/2010 -06 -03/184225788.html.
[7]Mey J L.Pragmatics:An Introduc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Second edition,2001:40.
[8]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Second edition,2001.
[9]胡霞.认知语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