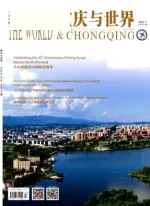暗化的文学读者——数千年来一直被忽略的群体
曹学庆
(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淮安 223003)
西方接受美学对读者地位进行热烈讨论多年来,我国研究者虽然也对接受美学颇感兴趣,但是对于读者地位的讨论仍然不多,甚至可以说仍处于暗化地位。这一现象一点也不为怪,跟人们的传统观念、思维定势等不无关系。其实无论是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还是从古希腊文明开始的西方,文学批评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模仿和教化,即文学如何模仿现实,教化读者如何实现对文学作品的教条性接受。由于对模仿和教化的专注,及由此产生对价值判断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界对文学读者的明显忽视。而古代的作家们也普遍认为:“诗歌语言的威力必须加以控制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此,当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剧作《蛙》中借人物之口宣称:悲剧作者必须提供‘智慧的忠告以造就更好的公民’,他不过是在反映很普遍的看法而已。在古代,作者被视为国家的公民,作者则是公民德行的塑造者,而批评家更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1]他们都重视文本的教化功能,甚至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文学读者不会思考,被动到愚蠢的地步,对所读的作品既不会作出高明的道德判断,也不会进行灵巧的分析,文学上不成熟,甚至连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都没有。
一、暗化读者地位的原因
对读者地位的研究,近来越来越引起许多文学批评家的关注,特别是接受美学主义的关注,从而让传统文学研究集中于作者、文学本体研究有了新的研究视角,即从接受者——文学读者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这一文学视角研究的拓展,扩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为实现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那么,数千年来,读者的地位一直受到暗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文化文学传统
文化传统对读者处于接受地位起着主导因素,中西方都是如此。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流思想,长期以来文人骚客一直受到这一思想熏陶和教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教育以育人为主,围绕教育的各种文献资料,当然包括文学作品都是教化读者为主,虽然许多名篇也会抒发作者的情怀,但是对于读者,抑或接受者来说,仍是学习先人之得失,以教化学习为主。儒家的社会功利思想对以作者为中心地位的观念可谓不能撼动。如:孟子的“以意逆志”的解诗方法和“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等,都强调作者或诗学(文本)的主导地位,鲜见读者地位论。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的科举制度、八股文等进一步强化了教条主义,读者主要是教条性地接受,乃至至今中国的教育也烙上教条的印痕——填鸭式教育。不能不说,中国这一文化传统对读者地位的暗化可谓影响深重。再看看西方文化传统,数千年来读者基本上也是处于受教化的地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和朗吉努斯等古典批评家在探讨文学时,主要是从文学对读者或观众的影响入手。这一文学批评传统一直占主流地位延续到20世纪初。
读者一直处于暗化地位离不开古今文学的思想观念。特别是现代文学,约1800年以后的文学的定义和评价方式。它的观点是:好的文学应该是无功利的,即应该没有世俗追求,也不乏写作意图,但是那是为了读者,而在客观效果上,却似乎不是为了读者而写。这项无功利的批评方案——它的范围使它足以成为一条批评准则。“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它在批评、美学和已经形成成规的文学想象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关于读者和读者对文学反应的想法,还没来得及有计划地孕育就流产了。”[2]事实上,柏拉图以后的很多批评家和理论家都以某种方式承认文学对人的影响,但认为读者是被动的这个观念却难以灭绝。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是20世纪西方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小说家。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在1905年2月回乔伊斯7日的来信中说,一定不要在乎读者是否喜欢他的作品。乔伊斯实事求是地回信说:“我不可能忸怩作态,一言不发而憋死,也不打算为我的艺术的完美辩护而上十字架。我不喜欢听到有人为我摆出英雄姿态。”[3]其实这种忽视读者的现象在西方很多大家身上都有体现。
(二)读者的被动心理定势
由于长期处于暗化地位,读者自己也觉得自己就该是对文本的被动接受,接受作者的观点、思想,甚至创作模式。由于这一思想的生根,读者对文本即使有自己的见解,一般也不表达出来。这也迎合了过去文学理论总是预设原文有一个确定的客观实体供读者在不断的挖掘过程中靠近。所有的这些主客观因素造就了读者的被动心理定势。
二、读者——创造性叛逆的主体
随着读者知识层次的提升、审美趣味的多元化和文本交互能力的不断加强,读者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评论、价值取向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读者要真正实现创造性叛逆,离不开几个方面要素的影响。首先,要明确一下读者“创造性叛逆”的内涵。之所以称为“创造性叛逆”,不是对文本或文本作者的抛弃,而是为传统重视文本和作者研究的一个拓展,提升美学批评的研究视野。所谓“创造性叛逆”是读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本题研究范畴的同时,运用自己的解读方式、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和人生体验大胆地对作者、文本提出自己的意见。即由原来的单向传递信息转换成双向甚至多元交互。这种“创造性叛逆”现象在读者阅读外国文学时尤为突出。
(一)读者的个人文学素养
文学修养是读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要素。由于文学作品主要是文字形式存在,这就要求读者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它同于图画、影视等依赖听觉或视觉就可以解读、欣赏和批评臆见作品。文字作品需要读者具有好的文学素养来和作品进行多元交互。例如,莎翁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一对山盟海誓的苦命鸳鸯只能做一夜夫妻。朱丽叶盼着夜色降临,好挂着一条软梯在楼窗前,让他新郎在流浪前能爬上她的闺房和她共度销魂一夜。她手里拿着一盘没有解开的软梯,自语哀怨道:
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ed.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本要借你登上我的床,但可怜的我,一个处女,活守寡,到死还是个处女。当然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读者就可以弄明白她的心思和想法。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如是译:他要借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当然此时他的身份既是读者也是译者。他用概念错位搭配,让译作的读者,毫无疑问也包括他自己,对此情此景产生无尽遐思。如是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读者的文学素养对于他们“创造性叛逆”地解读文学作品是不争的事实。
(二)读者所处的政治道德环境
读者所处的政治道德环境及其他各种环境中,使他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审美批评、价值取向等都会产生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他对原文学作品的叛逆。如在后儒家代表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标准之后,中国人对性意识观念是隐讳的。因此,写于明代中叶的《金瓶梅》历代被列为禁书。由于古时读者,甚至现代读者长期受到中国伦理道德标准的束缚,读者主要是从性隐讳的角度来看待此书,很少有人探讨它的深层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也有不少文学大师提出自己深层的评论。如张竹坡《天下第一奇书》评论中就指出:“是淫者自见其为淫者。”鲁迅也曾就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认识:《红楼梦》“中国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他们都一针见血地道出读者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都会对文学作品产生“创造性叛逆”。
(三)读者的情感因素
读者由于自己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感情境遇中对作品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从而实现对原作品的“创造性叛逆”。如大家都熟悉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4]
一个人如果有和徐先生类似的经历,故地重游,却不见昔日恋人,可能会产生共鸣。也会体会到“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蕴藏了诗人深深的“康桥情结”。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昔日爱情生活的回忆,以及对眼前无奈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也会体会到诗人再次面对康桥美丽的景色,林徽音那纯净优雅、亭亭玉立的形象,久久地在心头荡漾,就连眼前“那河畔的金柳”,也是他梦中的新娘。相反,一个没有陷入情感纠葛,爱情幸福甜美,故地重游某地的读者,则会把它看成一首委婉柔美的诗歌,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对于自己此次故地重游,见到的“河畔的金柳”,“夕阳中的新娘”可能是另一番遐思,尽情享受此情此景,陶醉此情此景,而不会留有任何遗憾。不容置疑,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所处的情感状态,会对原作产生不同的诠释,实现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
三、读者主体地位的确立
读者主体地位的确立首先体现在文学批评家实现从文本本体批评、作者批评到读者主体批评的转换。读者反应批评思潮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波兰文艺理论家罗曼·英加登(Ingarden Roman)和美国女批评家路易斯·罗森布拉特(Rosenblatt Lousise)是这一思潮的两位先驱。英加登在其《文艺作品:关于本体论、逻辑和文学理论的边缘研究》(The Literary Work of Art: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orderlines of Ontology,Logic,and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和《文艺作品的认识》(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等著作中提出了读者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的主张,并提出艺术作品与其“具体化”的区别和艺术作品与审美客体的区别。他的理论成果为后来的接受美学代表人物沃·伊赛尔等人直接吸收并加以系统发挥。罗森布拉特在她的《作为探索的文学》(Literature as Exploration)一书中,提出了文学沟通的概念,认为文学作品是通过作者进行再创造和努力全面掌握那些有机联系着的感觉和观念,因为作者是竭力想通过些感觉和观念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世界观的。她的这些观点成为英美批评界研究读者反应的导火线。虽然他们的观点一时因新批评派的崛起而淹没,但是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在默默中蓄势待发。20世纪后半叶读者反应批评迈入兴起、快速发展时期。文学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理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读者的接受上,强调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认为,读者不仅是文学作品的欣赏者、接受者,而且是作品意义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读者对于作品不是无条件地、被动地接受,而是文本意义的建构者。他们在阅读之前由其全部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构成对作品的一定的鉴赏趋势和心理定势,即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潜在地支配着他对作品的接受方式和程度。因此,读者文化层次、欣赏能力与创造能力对于作品的接受就至关重要了。读者的接受主体地位要求读者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相应的审美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适应艺术的接受需要。
读者主体地位确立还体现在作者为了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在考虑读者原有阅读传统和习惯的同时,开始注重打破、更新读者的审美期待。尧斯(Hans Robert Jauss)的美学接受理论认为,同一个时期的读者和作家的阅读和写作都要受到这一时期人们所特有的看法和文学成规的规约,它们包括对体裁、风格、形式等文学自身的看法,也包括文学产生背景的看法,由此形成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期待视域,读者便是带着“先有、先在、先识”这些先入之见去读作品的。每一部文学作品的读者都是在这一时期主导的“期待视域”之下进行阅读的[5]。在这一时期主导的“期待视域”之下进行阅读提供了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作为创作主体是整个过程中首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作者的创作并不是仅仅为了自我欣赏与陶醉,为了“孤芳自赏”或者“束之高阁”,而是为了向广大读者传递信息(包括作者的创造意图、作者的创作意境和对待人、事的态度及哲学观)或传播文化,促进交流,让他们一起来欣赏、陶醉、探讨、交流。没有读者这个接受主体,文学作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在读者的作用被长期忽视后,我们利用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充分肯定了读者的主体性意识和地位,打破了作者是文学作品的唯一主体的传统观念。作者作为创作主体,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共同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实现过程。可以说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是读者对文学价值评判一种最为直接的体现。读者与文学作品总处在一定的价值关系中,在读者和文学作品进行对话时,“这种关系呈现为双向运动的交互作用:作品作为价值客体作用于读者,在读者身上产生影响与效果,达到价值的实现;同时,读者作为价值主体也反作用于作品,对作品在自己身上的影响与效果做出反应,并理性化为对作品的价值评判,这就是批评。”[6]
读者主体地位确立还体现在读者自身的觉醒。读者对于自己和文本对话产生的共鸣或冲突,能够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拥有所有“80后作家”的特质的步非烟,曾经是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宗师的忠实读者。“我小时候曾经是一个很自闭的人,正是武侠让我改变。因此我由衷地感谢这个由金庸古龙创造的江湖世界,他们给了我勇气,给了我信心,给了我一场非凡的梦境。初中的时候,曾为了为金庸说好话,被老师骂哭,被家长撕书……”她曾经如斯对记者说。就是这个不羁、富有想象力、野心勃勃,其独创的“侠即逍遥”的武侠理念,唯美华丽的背景营造,虚与委蛇的精巧布局,与金庸、古龙、温瑞安等开创的古典主义武侠观大异其趣,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金庸这座几乎不可逾越的武侠丰碑面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步非烟以不可思议的勇气誓将金庸先生“拉落马下”,一副“彼可取而代之”的铿锵面貌若隐若现。天真抑或自负?大无知抑或大无畏?无从判断。重要的是,从文化嬗递的角度讲,绝对应该激赏小女子步非烟“蚍蜉撼大树”的事功。在古典主义武侠观及文本滋养和笼罩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中,读者一心地崇拜,追随,甚至失去了自我。可以说步非烟是读者反映觉醒的杰出代表。另外随着大众教育的普及,读者的文化层次、审美多元化,更加成熟。就像沃德雷所说的“成熟的读者”,或者弥而顿所说的“合适的读者”,或者像美国著名读者反应批评家斯坦利·菲什(Fish Stanley E.)所认为的“有知识的读者”。他认为有知识的读者是:1)一个对构成那篇作品的语言那语言运用自如的说话者。2)一个完全掌握了“一个成熟的……听者竭力想理解的语义知识”的人。这里所说的语义知识包括有关各类词组的知识,有关搭配可能性的知识,有关成语的知识,有关专业用语和其他行话的知识等(也就是说,既包括使用语言的经验也包括理解语言的经验)。3)一个具备文学能力的人[7]。这就是读者反应批评家们心中最“理想的读者”。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这一“理想的读者”也逐步成为现实的读者。
实现从文学本体论向读者中心转移的研究,为美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当然,重视读者的研究不是否认以往的文学本体论,而是拓展研究的视野,丰富美学研究的理论。
[1]汤普金斯.读者在历史上:文学反应的演变[M]//读者翻译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259-260.
[2]罗斯玛琳.暗化读者:读者反应批评与《黑暗深处》[M]//张中载,赵国新.文本·文论:英美文学名著重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38.
[3]艾尔曼.乔伊斯传[M].金隄,李汉林,王振平,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4]杨芳芳.新月派诗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5]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254.
[6]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82.
[7]菲什.文学在读者:感情文体学[M]//读者翻译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