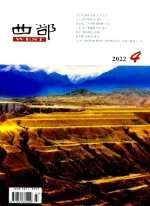易拉罐与木桶里的格瓦斯
石彦伟
一个个青皮小罐无孔不入地藏满我的书包,肥硕的包身长出鼓囊囊的肌块。有三四罐醉醺醺地趴倒在小说集旁的罅隙;有一罐贼头贼脑地躲在叠好的衬衣里,很难被侦探出来;还有两罐包里实在挤不下了,干脆赤裸在左右两侧的网兜里,显得羞涩和委屈。我记得趁母亲老眼昏花一不留神时,已偷了好几罐撇出去,可上了火车一拽拉锁,见又长脚一样跑了回来。
我愤怒地给母亲打电话:说过多少次了不带不带,咋又塞了那么老多,沉死我啊!
母亲辩护道,没咋带啊,车上不得解解渴么!
解渴,解渴也不用这么老多啊!
我焦躁地挂了电话,心说,让你带带带,急眼一扬脖全给喝了!边发着狠,边掘出一罐掐在手上,手指掰得嘎嘣作响,就要去抠那没脾气的铝环。
车皮底下响起了粗砺的摩擦声,我的鞋底一阵酥动。凝重的月台在迟缓的游移中变得模棱。蓄势待发的手指如临电击地僵硬了起来。刹那间,我涌起满心的怜伤。
采风般的探亲日,就这么蒸发掉了。
时光,亏折的时光!
我忽然决定把这些负重的易拉罐一个不落地背出站台,背进地铁,背上自行车,一直背进胡同小宅。我背着它们吭哧吭哧地走啊走啊,一想到那些液汁在罐子里哗啦啦地摇晃奔突,怒冲冲地咕咕着气泡却找不到发泄的出口,我就宛如施虐一般得意。我要把它们像祖母和外祖母的君子兰一样养起来,齐整整地排列好,等候某一个忽然寂寥或伤感得无法消睡的静夜,再一罐罐拿出来慎重地拉开——绝不告诉母亲。
愈真挚的心绪,愈容易说得矫情。
在被京腔京韵鸡毛蒜皮油饼豆汁封锁得密密实实的老胡同里,能够警惕我别稀里糊涂地感染上京腔,别忘了胡同往北还有一片湿润茂密的东北森林的,好像唯剩这些青绿衣装的易拉罐了。它们卑微而哑言,内壁里紧缩着一个清冽澎湃的气场。来北京谋生后,我愈发稀缺这种气场的补给和保护。那一声拉环被抠开时大气粗鲁从不拐弯抹角的脆响,那坚定决然地浓酽在口腔深处久不退避的麦芽香,那不打招呼直接钻进食道就开始激情燃烧的气泡,俨然暗中提示着我的立场,修补着我的彼岸。
俄文一样繁缛的铺叙,只为说出你,格瓦斯。
后海酒吧里粉黛一新饮尽铅华的北京人和伪北京人未必知道你,但在东欧平原和中亚细亚大陆的许多城市和田间,一些民众正在为你痴迷。
我对格瓦斯的痴迷史,仅有六七年可溯。
九十年代初,当我在三姓街大院和小伙伴们拔橛子打水枪飞檐走壁热汗淋漓时,盼得跺脚的汽水似乎唯有小铺卖的冰镇大白梨和桔子露,分明不知什么格瓦斯;到了世纪末的宣庆小区时代,至多加一款小雨点。直至在长春读大学,过年回家才在餐桌上初见那琥珀色的饮料。母亲说,多少年了,这格瓦斯又卖起来了,整两瓶回来尝尝,看变味没。我说长这么大为啥没见过。母亲说不知道啊。我说不知道就不知道吧,我先整一口。
但那时年轻的我已行了斋拜,啤酒般的澄黄色泽使我迟疑。抓起瓶子,转着配料表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所有回民对待陌生食物以及陌生人给的食物最惯见的动作),没有找到酒精,却被泛起的酒花弄得纠结。我忍下了,次日去问教门最好的大舅。他说格瓦斯就是液体大列巴,喝吧孩儿,哈俩里(合法的)。
抿一口,再难放下,犹如新烤好的黑麦面包的浓香中,弥散着甜,勾兑着酸,拉拢着苦,还有些什么味道却说不清了,只知胃里刷刷地胡乱滚着,一个回肠荡气的粗嗝冲杀上来,喉咙一松,头脚都轻捷通透了起来。
人与饮料,原也需要配型,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那味道感冒。父母亲就仿佛不怎么着迷,但从前两年搬到文景花园,每次回家,橱柜里窗沿上餐桌边再无可乐,只有越堆越多的格瓦斯,有得莫利的,也有秋林的。后来出现了易拉罐,青色表皮上用墨绿的细线勾勒着秋林的老模样,还有急了拐弯的俄文。深夜写作,启开一罐,比咖啡都舒爽。回长春,后来回北京,也都塞几罐送同学同事,只一句:家里的特产,没多带,尝个新鲜!心里美得不行。年关逛家乐福,大瓶小罐噼里啪啦往推车里扔,黄橙橙明晃晃的半车子,满场最是惊艳。
常有顾客指着问:你们买那老多的是啥玩意儿?
格瓦斯呗,没听说?
听说是听说,没咋喝过。那玩意儿好喝么?
问答得多了,隐隐觉察出一种冷峻:入驻哈尔滨百余年、张口闭口被唤作特产的格瓦斯,其实远未融入这方水土。一条中东铁路让俄国人选择了哈尔滨,高傲的哈尔滨人愉快地接纳了石铺的长街、拱顶的教堂、一大堆念出来土了咔嚓的俄语单词,爱上了锅盖大的列巴、皮硬心软的塞克、瘦瘠嘎啦的红肠以及酸黄瓜苏伯汤马迭尔冰棍。
唯余格瓦斯,百年间若即若离,带着一丝苦涩的微笑。
听祖父讲,幼年闯关东落脚时,秋林公司确有格瓦斯在卖。穿戴考究的苏联门童替客人恭敬地拉开门,这排场,总使穷孩子不自在,便不常往。客居的滨江大院,都是关里来的老回回,房东是松花江上的一个货船长,常年跑苏联,会一口嘀哩咕的俄国话,但祖父也未因这样的背景喝上一口格瓦斯。
赶等哈尔滨的街头巷尾能见得到了,当是光复后老毛子上街的时节。苏联大兵口边离不开这东西,百姓却也只是远远看着,并不觉得与自己有关。略显得惯常,大约已是五六十年代。那时父母还小,学校开运动会,家里才给带一瓶,一毛五,很奢侈了(平常只喝一分钱管够的凉水);大人去江北野游了,单位便发一个列巴,一瓶格瓦斯,晌午填补填补。再往后,工艺也一度流入长春吉林,用的是大白梨的那种老瓶,汽儿很冲,面包味却做不太像,便加香精,兑出了雪梨草莓橘子味,也还叫这洋名字。
此时的格瓦斯,虽存其形,魂已不复。
很快就有传闻,说是由于灌制的气压过大,经常爆瓶,便下了禁令。其实反苏修的时节,也早有所禁忌(连果戈里大街都改成了奋斗路)。格瓦斯到东北转悠了大半个世纪,还是没能摆脱消隐落幕的悲剧。
如今那一抹澄明清澈的琥珀色,重新苏醒,仍只是点染在超市货架或专卖店里,带着一丝贵族气质,孤立无援地等着粉丝来找。
真正立稳脚跟的,怕还是啤酒。1900年,哈尔滨诞生了中国第一家啤酒厂,近年啤酒年销量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慕尼黑。说是用哈尔滨人一年喝下的啤酒易拉罐,能修三座松花江大桥。遍地凸起的啤酒肚,还给哈尔滨招来了一个中国最懒城市的殊荣,与丽江、拉萨齐名,无辜得可以了。
失宠于哈尔滨的格瓦斯,在它的原乡大地,却身披大美。
那个有点吝啬的小饭馆主人肯定想不到,他把食客掉在桌上的黑面包渣划拉起来倒在水桶里,却在第二天奇异地闻到了浓郁的酵香之后,这种意外发明的饮料在东欧大陆风行的前夜,已经被暗示。在冬季漫长而高寒的大地上,对俄罗斯、鞑靼、乌克兰等民族的人们来说,格瓦斯意味着驱寒的火种、饥饿的慰藉、劳作的力量,“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普希金语)。修道院、兵营、医院、农舍,大地上到处流荡着酿造的气息。汗湿的男人刚进家门,能来上一杯女人做的格瓦斯,是劳作后最大的安慰。吃完奶制品和牛羊肉,再来一杯格瓦斯,闹腾的五脏六腑马上就消停下来。在俄罗斯,能酿制出可口格瓦斯的女人是能干的女人,是贤惠的女人,也是受尊敬的女人。
土地上流传着这样的话:“有了面包格瓦斯,我们就有了一切。”
人们甚至在说:“不起眼的格瓦斯好过圣水。”
对一种饮品,竟能有宗教般的敬重与向往,奶茶、酥油茶、盖碗子(绝不包括可乐与酒)可能都是亲近的参照,但唯有格瓦斯,被忧伤坚韧的俄罗斯民族,赋予了最贵重的品性。
苏联解体后,千奇百怪的外国饮料涌入俄罗斯。这个国度的民众,绝不让自己的格瓦斯倒下去,每一次经过超市货架,都会本能地拿几瓶放进购物车里。他们都该记得,1982年国际清凉饮料评比中,格瓦斯曾以超过一半的分数力压可口可乐而夺冠。那种胜利的快乐,显然不仅源于饮料之间的制衡。俄罗斯人在格瓦斯的滋养中,发酵着一个印象:护住民族精神的乳汁,就是护住这个民族的元气和尊严。
格瓦斯面朝民众,旗一样地站着。
在莫斯科做生意的表哥回来说,一身醒目黄色的大闷罐圆桶车,骄傲地遍布莫斯科街头,可乐却是少见的。腰扎围裙的马达姆(女士),把一杯杯颜色和口味都很浓重、决不轻易变淡的格瓦斯,递向焦渴的人们。散放着的密封铁皮桶里,拧一下开关,冰镇的格瓦斯便如啤酒般汩汩流出,花上六个卢布就可以买一杯。
那是一种穷人也能端庄自在地喝上几大杯的饮料,是洇润在民众灵魂深处、亲手可制、触手可得,而不必排在麦当劳肯德基的柜台前举钱乞讨才能等来的饮料。
只此一个理由,唯它贵重,唯它佳美。
这样激动地想着,不禁对故乡有了几分伤憾。纵使再留下十条欧化建筑鳞次栉比但一进去就怕挨宰的中央大街,却独缺一杯在街上随意可饮的格瓦斯,哈尔滨又有何面颜以“东方莫斯科”的洋名自喻?或许只能一叹:舶来的格瓦斯,终究质地不纯。
轻浮的判断,很快被击碎了。
那是2007年的夏天,我刚从西海固拍完片子,在固原城死缠烂打买到一张两天一宿的站票,去新疆参加笔会。初到乌鲁木齐,已是晚上七点多,城市仍是一派白昼的喧哗。我在老网友天山安排的旅馆洗了澡、换了衣服,又接上我所尊敬的回族作家杨峰先生(中学就在读他的《托克玛克之恋》),天色才有黯淡的迹象。我忽然发现浑身只剩两块钱了(本来在火车上有十二块,半夜求一坐,被勒去十块),心想初次见作家,做晚辈的应该像模像样地请个客,便央求停车找银行。
当然未能得逞。那是新疆,不是上海。天山一脚油门,直把一行五六人,拉到了小聚的夜市。天山说,我们都在这里聚的,拉个话,随便。
还未走近,浓香已经扑来,那么长的一条街,全是风味各异的西域小吃,我有些受惊,眼神木木地,胡乱找排档坐下了。天山已娴熟地叫起菜来。
杨老师喝个啥?天山礼貌地问。
还是卡瓦斯(译音上略易一字)吧,让小石头也尝尝。
我眼睁睁地盯着服务员端着晶莹剔透的大扎杯,到街壁的大木桶前,轻巧地拨开水龙头,清澈澄明的琥珀色液汁哗啦啦流淌出来,很快漾满了杯子。端来一碰,冰凉沁人。
如临异域,真临异域。
我羞赧极了。
我真不该只因生在哈尔滨,就自负地以为格瓦斯唯其独有。我真不该可耻地遗忘,除却黑龙江流域,与俄国接壤最多的其实是广袤的新疆。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显然先于中东铁路修建的十九世纪末),俄国没落贵族已将格瓦斯带入伊犁、阿勒泰、塔城、乌鲁木齐一带。与哈尔滨不同,格瓦斯一与新疆大地接吻,便直接迎向了最底层的民众。不饮酒的维吾尔、哈萨克、回回等穆斯林,当然也包括汉人,把它盛进了壮硕的木桶,安插在每一个聚落的夜市和民族餐厅。
大地之大,大在襟怀。
那一晚,杨峰先生与我谈了许多:文学的追寻,理想的阻遏,民众的心情。没有酒精的格瓦斯一杯杯地续着,我醉倒在乌鲁木齐丰富辽远的眼神中。
这些年来,母亲坚持把一个个青皮小罐,在临行前刻,强行藏满我的书包,掰扯不过,也就由她像孩子一样藏着。回到胡同后,我也像孩子一样,一罐罐把它们翻找出来,再像积木一样排列整齐。听说北京已有秋林专卖店可以买到格瓦斯,终于有理由告诉母亲不必再带。实际上,我还从未去找过那些店,也从无这样的打算。对这些带着故乡体温的易拉罐,我心存感激,但见过更大的天地以后,迫切想念的,唯有夜色下一个个体胖心宽的大木桶。
此后凡去新疆,必想方设法从宾馆逃遁出来,哪怕只一会儿,跑到夜市上,亲手接两杯瓦凉瓦凉的格瓦斯。到了那拉提草原边上的伊犁小城,更要胆壮声高地要杯格瓦奇(译音上又易一字),不必担心店家脱销或是怠慢。
那是一片俄乡之外喝格瓦斯真正要去的土地。
真正对味的土地。
我并未忘本地觉得木桶里的味道,一定比易拉罐醇香和本色,但它输送给我一种清冽动人的感受:人民的格瓦斯,永远要把它还予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