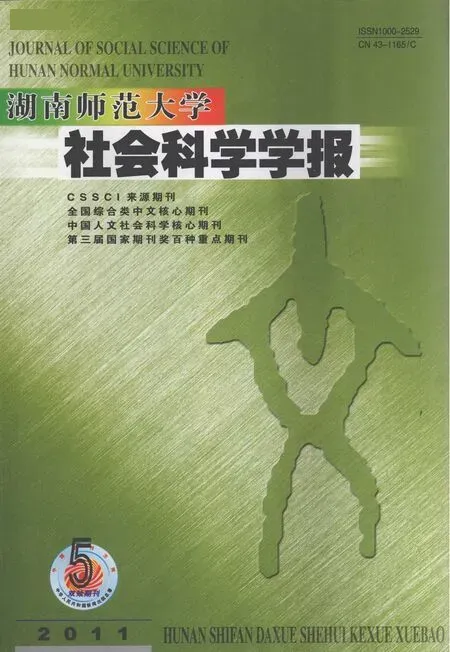论费希特柏林时期的法权概念
张东辉
(湖南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201)
论费希特柏林时期的法权概念
张东辉
(湖南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201)
在新知识学的哲学背景下,费希特柏林时期的法权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法权概念的演绎起点从自我变成上帝,从而使他的法权哲学呈现出浓厚的宗教特点。当然,这种神性的法权思想又与耶拿时期有着本质的关联。从费希特对柏林时期法权概念的规定谈起,进而述及这种法权概念的形成条件和实现途径以及国家在法权概念的实现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最后,对费希特法权思想作出评价,认为它上承奥古斯丁的神性政治,下启当代的德性政治,体现出非自由主义的特质。
法权概念;知识学;自我;上帝;国家
费希特在德国古典时期成就斐然的各家法权学说中,作为第一位根据先验原则系统阐述法权思想、建立法权体系的哲学家,成为德国先验论法学传统的典型代表,在法律思想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费希特法权思想、尤其是他在柏林时期的晚期思想基本没有受到关注。即便有人零星提到他的法权思想,国家主义、极权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头衔”,也往往是这时被使用得最为频繁的字眼。究其实质,这在很多时候都是研究者将费希特的思想简单化和庸俗化导致的结果,是在抛开费希特为其命题设定的诸多条件和限制的情况下断章取义的结果。费希特晚期的《法权学说》和《国家学说》尤甚,其思想深度与理论意义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低估和扭曲。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费希特柏林时期的法权概念简要加以述评,希望唤起国内学界更多地关注和思考费希特哲学。
一、新知识学背景下的法权概念
1.知识学的转变
1800年出版的《人的使命》可以看作费希特柏林时期知识学演变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该书中,上帝既不像在《试评一切天启》里那样是人的主观东西的外化,也不像在《关于我们信仰上帝统治世界的根据》里那样是发挥效用的道德秩序本身,而是一个不可名状的无限者,它有其自身的知识与意愿、生命与行动,它与人息息相关,人的知识与意愿、生命与行动都是从它那里来的,因此,人应该以虔诚的态度坚信这个无限者的天意,以顺从的态度尊重这个无限者的安排。我们看到,费希特这时开始从哲学向宗教过渡。撇开“无神论事件”不谈,在学理上直接促成这种过渡的是费希特与谢林之间的哲学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在于最高的哲学原理,争论的结果则是知识学能否成为唯一的哲学体系的问题。经过争论,费希特终于在《知识学阐述(1801~1802)》中将绝对知识看作其知识学的主题。他指出,“绝对知识必须通过一种对其本身的同样绝对的直观加以把握”,“一方面它全然是其所是,靠自身、在自身静止不动,全然固定不动、坚定不移和独立完满;另一方面它之所以是其所是,全然是因为它是由自身和靠自身存在的,完全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因为除了绝对以外,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外来东西,相反地,一切不是绝对本身的东西都消失不见了”[1](P145)。在 1804~1805年,费希特首次较全面地把他的知识学发展成为一种与耶拿时期截然不同的体系,即以“绝对”(das Absolute)为最高原理的知识学。他认为绝对是一切实在性最坚实的基础,只有从绝对中才可以推演出现实性的各种形态。因此,如果把以本原行动为最高原理的耶拿知识学称为主观的先验唯心论,那么现在以绝对为最高原理的柏林知识学就可称为客观的先验唯心论。费希特将绝对设定为最高原理,既保证了知识学作为唯一的哲学体系所占据的地位,而不再被贬低为谢林同一哲学的一个与自然哲学相并列的分支,又一改耶拿知识学把从自我到非我与从非我到自我的路线尖锐对立起来和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方式对待这一矛盾的路径,依靠绝对这个存在与思维的统一体来解决这一矛盾。
同时,知识学体系的这种演变为它自身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费希特说:“对绝对的爱、或对上帝的爱,是理性精神的真正要素,人只有在这种精神中才会发现安宁和极乐;但绝对的最纯然的表述则是知识”[2](P137)。知识无非是将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的认识,只是费希特在本体论上把这种认识客观化为绝对的表现形式。所以,世界出于知识,知识本于绝对。在这门新的第一哲学的基础上,他开始重新阐述各门应用哲学,包括宗教哲学和道德哲学、法权哲学和自然哲学,相继发表了《宗教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原理》(1805年)、《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806年)、《关于学者的本质及其在自由领域的表现》(1806年)和《极乐生活指南》(1806年)等一系列的演讲。在《宗教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原理》中,费希特表示,任何学说都必须以最实在的根据即绝对为出发点。因此,他主张,应当先研究宗教学,再由之推演到伦理学和法学。宗教学崇尚的彼岸天国与伦理学追求的道德至善在费希特那里是一回事,而调解尘世纷扰的法学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在道德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应当存在一门作为它们的联系纽带的法学即关于人的自然法权的学说”[2](P79)。
费希特柏林时期的知识学虽然在1804年就已确立起来,并且在1805-1806年通俗演讲中还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阐述,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知识学已经臻于完善。1809年秋,费希特再一次修订了新知识学,并主要在《知识学纲要》(1810年)和《关于学者本质的演讲》(1812年)两次系列讲演中公开讲授。在这一时期,费希特新知识学的变化尤其表现在其与宗教的融合,费希特甚至认为“真正的、从事科学工作的感召力要么始于宗教,要么通向宗教”[3](P163)。在此期间,费希特还讲授了《意识的事实》、《先验逻辑》、《法权学说》、《伦理学》和《国家学说》等课程。费希特柏林时期的法权思想就是他依据最新的知识学原理对法权哲学所作的重新阐释,这主要体现在他分别于1812年和1813年写的讲稿《法权学说》和《国家学说》之中。在此,我们探讨的主要就是这两部手稿中的法权思想。
2.法权概念的转变
费希特指出,“法权学说是一门纯粹而真实的科学”,这种纯粹性是从形式方面对法权学说作出的规定,即“对作为应当(Sollen)的先天法权概念所作的一种分析”[4](P1-6),而真实性则是从内容方面作出的规定,因为法权学说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耶拿和柏林时期分别为费希特法权学说奠定基础的知识学原则的区别。在《自然法权基础》中法权概念是从早期知识学的最高原理“绝对自我”推演出来的,而在《法权学说》中演绎出法权概念的出发点却是他晚期知识学的最高原理“上帝”或“绝对”。因为上帝这个存在者必然要显现自身,把自身显现为一种既包含能知的主体也包含所知客体的知识,而只有在这种知识中才能演绎出法权概念。因此,虽然这里所说的“先天法权概念”仍然使用的是像耶拿时期一样的表述,但内容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法权概念现在是从绝对者上帝那里经由知识推演出来的。知识作为“上帝的显现(Erscheinung)”,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由许多自我组成的系统”,“这些自我都必须被看作是在一个共同的活动领域从事活动的”,于是就必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一个共同的作用范围相互发生影响”;如此一来显然就需要各个自我的活动保持统一性和协调性,因此,在作为纯粹理性规律的道德法则尚未支配人类的这个活动领域之前,就需要法权规律作必要的调控和监管,“在这个共同领域里,一个人的自由可能妨碍他人的自由,而只有法权规律才能消除这种妨碍”[4](P7)。法权规律规定,所有人都应当将他们的自由看作他们彼此共同处于一种综合的思维中,在这种概念中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当扬弃他人的自由。“法权概念=思维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把所有人都看作自由的和共同处于综合统一的概念中[4](P9)。
像《自然法权基础》一样,法权规律探讨的是“众多自由存在者的这样一种彼此共处,即一切人都应当是自由的,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妨碍任何他人的自由”[4](P2-3)。但关于自然法权,费希特作了三点概括:1)自然法权就是理性法权(Vernunftsrecht),一切自然法权都是“先天固有的理念”(angebore Ideen);2)一致赞同并不就是自然法权,因为它本身还必须以理性为根据,所以人们缔结的法权和成文的法典决不代表自然法权;3)单有纯粹的自然而没有人为行为(Kunst),单有自由的意志而没有契约,决不会产生一种合法的状态;只有在签订了契约的地方,合法状态的形式才会得到实现,因此“自然法权=合法状态”,在国家之外不存在自然法权,“一切法权 = 国家法”[4](P5-6)。可以说,这里是费希特对《自然法权基础》中“自然法权”概念的反思和总结,把这个概念的内涵更加清晰明白地阐释出来,同时也明智地放弃了使用它。
然而,所有这些区分又似乎都只是表面现象,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在根本上仍可以理解为一以贯之的。对于这一点,国外学者至今也没有定论。费希特早期的绝对自我绝对地确立自身,并且设定非我,同时通过非我重新意识到自身的自我的存在,它与造物上帝还有什么分别?我们不妨试想把这里的三个自我,即绝对自我、非我和自我与晚期知识学的上帝、世界和个体一一对应起来:绝对自我是上帝,非我则是上帝创造的世界,而个体就是沟通上帝与世界的中介。在这里,不论是个体、世界,还是法权关系,都体现出一种崇高的神圣性,因为它们都是上帝之光的显现。我们似乎也有理由认为,尽管在费希特哲学中存在从耶拿时期向柏林时期、从理性哲学向宗教哲学的过渡,但他的宗教哲学仍然是一种遵循知识学原则的先验的理性哲学,在本质上仍是早期知识学的延伸,也就是说费希特的基本哲学精神并未改变。法权哲学的过渡,亦是如此。
二、法权概念的条件和实现
1.法权概念的条件
费希特从他晚期知识学的原则出发,详细列举了法权规律发生效用需要的三个条件,并进行了论证。首先,需要众多自由存在者处于一个共同的、相互发生效用的领域。费希特是这样论证的:“因为道德命令借助作为个体的各个自我来实现上帝的形象。但是,对每个人作出的命令仅仅构成这个统一形象的一部分,这个形象应当借助所有人的共同力量来实现;上帝的统一形象在所有人的相互关联中才是可直观的,每个人只能实现其中一部分。所有人通过共同力量必然获得塑造这个统一形象的一个共同的客体和领域”[4](P7)。因此,我们必须把众多的自我设定为在一个共同的作用范围相互发生影响的存在者。法权概念的第二个条件是,在这个共同领域里,一个人的自由可能妨碍他人的自由,“没有妨碍的可能性,就没有法权规律”,因为如果“每个人的自由都以他体现上帝的统一形象的一部分为根据,由于这种统一是由向所有个人颁发的命令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些命令就决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或建立在一种争议之上的: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另一个人不会想要,反之亦然”[4](P7-8),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扬弃了法权规律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在有妨碍自由可能性的地方,才有法权可言。从第二个条件直接引申出第三个条件,即历史地看,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尚未达到完全的道德自律。概言之,法权概念的三个条件为:“1)众多理性存在者;2)共同的领域和妨碍的绝对可能性;3)这种妨碍不会由于另一种更高的[道德]法则而被扬弃。”[4](P8-9)
2.法权概念的实现
法权概念不应当是空洞的思想,而是要加以实现的。在费希特看来,只有当法权概念成为所有人的意志的法则,即一个人想要在他们各自自由作用的范围内侵害他人是绝对不可能的,法权概念才能得到实现。[4](P11)因为显然,在自然状态中自然允许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活动,甚至包括侵犯他人。费希特像耶拿时期由原始权利演绎出强制法一样,认为必须产生一种类似于机械规律的、对意志颁布命令的法则,使得一个人打算侵害他人权利的企图必定成为不可能。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涉及法权概念的形式和内容。在《法权学说》中,法权概念的形式一般是指缔结契约这种方式,而法权概念的内容则是指以缔约者的人身自由为前提和基础的契约内容。要把法权概念付诸实践,必须做到法权的形式与内容的绝对统一,缺一不可。费希特说:“一般法权要求一种财产契约。如果签订了财产契约,由此一般法权就获得了形式。但正如我们必须留意的,法权要求不仅涉及这样一种一般契约的签订这一形式,而且涉及这种契约的一种确定内容。”[4](P16)
关于法权概念的形式,我们看到,单个人的自我约束毫无意义,必须全体所有人都绝对地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界限以内,才能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这个共同结果。所以,费希特指出:“只有当所有人都服从法权并且为了法权这个目的,才存在一种法权状态,因为法权状态不是单个人的状态,而是所有人的状态。谁不服从于这种法权状态,他就不属于这个全体,并且不享有任何法权,既然在这种状态中所有人都毫不例外地把自己对自由的要求建立在法权之上,他也就失去了对自由的要求。”[4](P13-14)这样,费希特就不仅重申了《自然法权基础》的法权思想,任何个人的权利都要受到必须承认任何其他人的权利的限定,撇开这个条件,任何人都不享有法权;而且他还进一步强调法权概念关涉的对象是共同体中的所有人,而不是个别或部分的人。所以,要做到所有人都服从法权规律并且承担各自的义务,就只有让所有人都达成一致,签订契约,因为契约能够在所有人自由作用的范围内消除可能发生的关于自由的争论,为每个人规定他们各自固有的作用范围,即他们的财产。也就是说,个人所有权的获得是以承认他人的所有权这一义务为前提的。这样,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法权的形式条件就建立起来了。
但这个条件对法权概念的实现来说仅仅构成形式的方面,法权概念仍需从内容上获得规定。这个内容就是费希特所说的财产契约的确定内容,在其中人的人身自由构成财产契约的前提和基础。但如果空有法权的形式而无法权的内容,就根本不会达到一种法权状态,用费希特的话说,“虽然第一个条件得到了满足,但第二个条件却没有。签订了一项财产契约,这是合乎法权的,但是契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契约就会符合法权,因为法权并不会通过契约就得到实现”[4](P16)。以卢梭为例,他说:任何拒不服从公意的人,全体成员就有权强迫他服从公意,强迫他自由[4](P25-26)。哪怕卢梭取消人的天然自由是为了重新赋予人以更大的社会自由,按费希特的观点分析,这种做法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无视人的人身自由,破坏了法权概念由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从而损及契约的基本内容,使契约成为不可能。
3.国家权力的形成
仅仅单纯地宣布承认他人的自由,并不能确保法权概念的实现,法权必然要求权力(Macht)的建立,以此获得实现法权的保障力量。我们要求每个人除了使自己拥有在财产契约中业已阐明的意志之外,必定不可能拥有其他的意志,这种不可能性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建立才能形成[4](P22)。由此,费希特引出国家权力概念。他说:“通过法权概念的实现,一种绝对的必然性、自然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或自然原则,因而一种权力,被建立起来。……权力是通过对法权的希求(亦即对在社会中签订的特定财产契约的希求)和对不法的绝对厌弃(Nichtwollen)运作起来的。法权、并且惟有法权,才是权力意志的内容。”[4](P19)
对此,费希特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命题:1)只有一个希求法权的共同体才能合法地产生法权的权力或国家权力;2)一个希求法权的共同体必然地产生国家权力,正如法权必然地希求国家权力一样。[4](P20)针对第一个命题,他解释说:“如果以第一种方式[即部分人拥有法权]通过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形成了一种统治权力,那么,即使完全产生了法权的内容,而法权的形式也是始终缺乏的。因为那些反对这种统治权力的意志和观点的人被强迫处于法治状态,他们被迫成为法律上自由的。现在如果不希望这种强制出现,所有人就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希求法权,并且为了法权而希求一种国家权力。我们的主张的意义在于:国家权力只有通过所有人才能够以符合法权的形式建立起来。”第二个命题则旨在再次强调不仅“权力是法权的条件”[4](P22),而且权利与权力构成统一关系和同一关系。这两个命题对于理解费希特的法权和权力概念及其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观点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其实,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费希特就已经洞察到法权与权力的同一性。他指出:“法权必须是一种权力”;法权概念和“最高权力概念,必须综合统一起来。法权本身必须是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必须是法权,两者是同一个东西”;而且,“法权必须是行动”[5](P110,114)。
除此之外,费希特还着重强调了以下三点要求作为对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补充说明:1)公民在某种程度上要受国家的支配,是国家的工具;国家意志是首要的东西,而个人意志作为国家意志的产物则是次要的。他认为,应当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法权才得到保障。但是,每个公民的意志并不是倾其所有,完全从属于国家意志,而只是部分地受国家支配调控;也就是说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具有一定的界限,费希特将这个界限规定为两个限度,即个人自由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前者是公民的财产权不受侵犯,后者是为自己和国家的生存而劳动。国家意志之所以高于个人意志,是因为国家要创造一种更高的自由,即一切人的道德自由,“国家自由的首要产物是创造更高的自由”,“国家的最终目的乃是道德自由”[4](P48-49)。
2)国家既拥有法权,也负有义务。自由是人的绝对人身权利,如果人不能确保获得自由,那么人就根本没有权利,也就根本无法与他签订法权契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国家中确保获得自由,那么国家就不是法权的意志,也就根本不是国家。“国家既是绝对的强制性机构,又是绝对的义务性机构。国家拥有法权,或者更真实地说国家就是法权本身,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自然权力;但是,国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拥有这种法权,即承担确保所有人的更高自由和对于国家的独立性这一义务。如果国家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就谈不上拥有法权,因为它损害了法权的核心,它本身就是非法的,是单纯的强制和奴役。正如个人只有通过履行义务才能获得法权一样,国家不承担一切人的自由和独立性的义务,就绝对没有法权。”[4](P49-51)简言之,一切人的绝对自由必须通过国家才能得到保证,国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成其为国家。但是,国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费希特主张靠教育实现人的自由。
3)国家只有建立对所有人进行教化(Bildung)的教育机构才能使他们达到道德自由。面向所有人的普遍的教育机构是所有人的绝对共同的财产,这种财产是所有其他财产的顶点和终点。兴办教育机构,达到自由应当成为任何合法国家的义务。这就重又回到费希特早期所主张的通过文化(Kultur)达到自由的观点。在这里他再次强调,教育机构的目的决不是驯兽,亦即训练民众成为他人意志的工具,并使他们达到熟巧程度。把人民当作动物加以训练是独裁者和暴君的做法,而国家则是要教育人民,使他们获得自由。费希特说:“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专制的标准就是:在国家中是盛行教化,还是驯兽。自由的首要发展就是,国家作为干预意志的原则消失了。国家的目的在于扬弃自身,因为国家的最终目的是道德,而道德扬弃了国家。独裁者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所拥有的目的决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目的。国家早已把所有人的必然目的,亦即所有人的自由确立为自己的目的。相反,独裁者的目的是压迫和奴役。”[4](P51-53)我们在此可以看到费希特向来主张的一个观点:国家最终是要被扬弃的,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国家本身成为多余。
三、思考与评价
第一,费希特将他晚期知识学的最高概念上帝或知识引入法权学说,并以之为法权概念演绎的出发点和整个法权体系的最高原则。这样一来,法权规律就成为上帝为世俗世界安排的一种理性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不是为了自身的自由能动性或原始权利,而是为了共同分有上帝的形象,才与他人达成法权关系,组成法治共同体。我们可以由此得知,费希特的法权哲学这时就可能导致如下两种倾向:1)转向神权政治,2)国家在尘世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个人权利的地位势必减轻。其实,早在1805年费希特就指出,绝对虽然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但它的“绝对的行动之光”可以被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自我所感知,自我是上帝之光不可分割的投射。也就是说,上帝的定在(Dasein)就在我们身上,上帝的在世行为(existentiale Akt)在我们身上得到映现,我们就是上帝的形象[2](P17-20)。尤其关键的是,费希特现在强调,只有所有个体组成的全体才能完整地映现上帝的形象,而单个的个体只能映现上帝形象的一部分。这就产生了两个正好相反的后果:一方面,个人所能发挥的效用微乎其微,不足为道,它只有在整体中并且作为整体的一分子才有意义,所以个人的地位必然式微,尽管他作为那根由尘世通向上帝的无尽链条的一环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所有个体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代表着上帝的形象,手握通往天国的钥匙,是受上帝垂青和眷顾的神圣理性王国,其地位之显赫自不待言。由此,在《法权学说》中,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再次发生微妙的变化。费希特说:“一个人只有通过他对建立国家权力所做的贡献才能毫无争议地表明自己是一个法权主体,并获得财产权和人身权。惟有做出这种贡献才是对法权的贡献,没有这种贡献,在法权学说的单纯领域里任何人都毫无权利。”[4](P2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一再强调国家公民对国家、对强制法的服从(Unterwerfung),认为人民是工具和驮畜,而国家是目的和监工。这样一来,在《自然法权基础》中建立起来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平衡,在这里重新被打破。
在此,费希特关于君主的规定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他再三强调君主的良心,认为君主做任何事情都要凭自己的良心[6](P436,437,440,441,445,446);二是君主同时也是教育者。第一点再次涉及统治者的个人品德与法权规律的关系问题,表明费希特越来越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水准之上,这体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和法权思想的宗教友爱倾向。第二点则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1)这是费希特对君主权力即第一点的限定。他赋予了君主(Zwingherr意即专制君主、暴君)以最高的统治权,他是上帝任命的,在感性世界不受任何权力的制约;但尽管如此,人们仍不必担心君主会恣意妄为,有恃无恐,因为君主本身就是从教育者阶层挑选出来的,他是最贤明、最智慧的人,他的教育者本质决定了他的个人品格和执政能力,这两者本身是同一的。也就是说,费希特在1813年的讲座中试图通过一种调解原则即教育来对统治者的权力适用范围进行限制,以此提供一种政治他律的解决方案。正如马·伊法尔多所说:“这种调解原则(教育)使得以下的情况成为可能,即自由能够维护其自身的价值论和政治的优先地位,同时能限定强制手段作出一种有限的使用。”[7](P215)2)他试图通过君主同时兼具教育者的职能以达到逐步取消君主和国家本身的目的。君主惟有在起到敦促法权概念的实现和教化民众的时候,才是合格的和合法的;只知道运用强制权力压迫人民,而不懂得教育人民以使他们洞察法权规律乃至道德自律的君主就是暴君。当然,君主的最终和最高的目的是使君主本人成为多余,因为到那时,在教育者的指导和教育下,人人都成了教育者,成了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君主和国家也就被扬弃了。3)深层地看,与其说这是费希特忽视立法权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他对现实政治的悲观绝望,从而寄希望于理性王国、寄希望于上帝指派的基督教君主的结果。
第二,费希特日益成型的宗教政治学立场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1)费希特说“你们应当被强迫成为自由的”,这句话从宗教政治学的角度考虑,是完全不同于卢梭的含义的,因为费希特看到了政治社会的正义与自由的无望,例如:他认为人们签订契约只是出于“自私”的考虑,“自私”这一词汇的使用在他以前的契约论阐述中是从未有过的,他现在对政治社会抱以绝对悲观主义的态度,看到政治充满贪欲(用奥古斯丁的话说是libido dominandi[统治欲]),尘世尽是自私和贪欲,发现正义和自由在政治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于是索性放弃了政治自由的追求。这与奥古斯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看法是十分契合的,他说:“不侍奉上帝的人能有什么样的正义呢?如果灵魂不侍奉上帝就不能正义地统治身体,那么理性不侍奉上帝也就不能正义地统治各种邪恶”;“对上帝的真正崇拜能够获得真正的美德”[8](P937,221);此外,他也将政治社会的契约看做集体自私之爱的结果。费希特对政治自由失去了信心,转而求诸宗教自由。所以,他要求人们把尘世中的奴役与劳作当作甘受上帝惩罚和信爱上帝的神圣活动,信仰上帝和爱上帝的人当下就活在上帝之城,就行在通向永恒至福的上帝之城的朝圣途中,只需安然等待末日的到来和审判,到那时回到上帝的身边。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这就是我们不幸的生活状态,就像大地上的地狱,除了通过基督,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的上帝和主的恩典,我们无法逃避这个地狱。”[8](P1135)在他们这里,正义和自由都变成了一种超验的、末世论的宗教现实。2)费希特的这种对尘世社会的悲观主义和对上帝天国的乐观主义的立场,尽管决然地否定了尘世社会的绝对“正义”与“自由”的可能性,但并不是主张政治权力的消极无为,而是认为建立一定程度的理性秩序和法权关系仍是必要的,《法权学说》的论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和限度内展开的。奥古斯丁亦是如此。虽然他极力为上帝之城辩护,但并没有要求人们全然放弃地上的城,反而要求人们顺应世俗的统治,在俗世过天国的生活是可能的。3)尘世国家之所以有资格作为监工驱使臣民不停劳作,不是因为它是政治国家,而是因为它是宗教国家,承载着上帝托付的神圣使命。但是,费希特与奥古斯丁的宗教政治学的归宿和目的毕竟是不同的,这反映了主教与学者之间的角色差异: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在本质上旨在传教和护教,费希特《法权学说》则相反,由于他清醒地洞察到人类政治社会的丑恶和困境,用他的话说“人太坏了”,任何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都无法杜绝道德的败坏和政治的丑恶,所以他试图在政治法权领域引入基督宗教来唤起人心的本善之性,以此挽救人类的政治困境。
最后,从自由主义公民政治的视角看,费希特这种解决政治领域的自由与必然的神学途径,肯定会被看作一种枉然和危险的尝试。剥夺人的现实自由,而许诺我一个未来的自由,必定是悖谬的做法。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说辞往往被专制者使用,诱使公民们牺牲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为他的私欲和野心开道。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用鲜花铺成的。在当代,卡·波普尔(Karl Popper)所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萨·哈耶克(Salma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已对诸如此类的说教作过严厉的批判。然而,如果我们“仅仅”这样来解读费希特,未免太把费希特简单化了!这种观点其实也是与费希特本人的观点相悖的,因为如前“法权概念的实现”所述,法权概念的基本内容,即缔约者的人身自由没有得到保障,就是不合法的。但也可能正是在这里,费希特的深邃往往非常遗憾地被误解为专制和极权,而他在这里对现代政治的社会批判意义却被忽视了。这种批判意义在于,政治社会的恶使得任何法制制度和法权关系的建立都化为泡影,如果说人类社会还尚存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希望就是基督宗教的皈依,是回溯到上帝创世之初的人性的自然之善。费希特法权思想从耶拿时期向柏林时期的转变,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其核心目标从“正义”或“自由”向“性善”的根本转变。我们甚至可以把奥古斯丁对西塞罗的反驳与费希特晚期对早期的反思类似地对应起来。西塞罗在《论法律》中明确将正义确立为一个国家的主要构成要素,主张一种建立在绝对自然正义基础上的国家模式,强调理性秩序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罗马共和国的道德败坏和腐朽没落正是由于其丧失了早期所具备的绝对正义和美德,所以他总是以慕古之情追忆罗马的早期历史。奥古斯丁赞同前者,却反对后者,他认为罗马从来都不曾有过真正的正义,在本质上有的只是“统治欲”,真正的正义或自由是一种超验的、末世论的宗教属性,只能在由基督创建和统治的国家才能找到。“爱邻人”,就是基督教的善的社会结构的具体表现,与“统治欲”正好相对。当然,费希特晚期的非自由主义立场在这里也是非常明确的。直接受到费希特这种法权德性化影响的哲学家首推黑格尔,他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伦理生活”(Sittlichkeit)成为法权的最高形态。当代政治哲学领域列·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古典保守主义和阿·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德性政治,在费希特柏林时期的法权思想中都能找到踪影。
[1]J.G.Fichte-Gesamtausgabe. Ⅱ .Bd.6.[M].hrsg.von Reinhard Lauth und HansGliwitzky.Stuugart-Bad Cannstatt:Friedrich Frommann Verlag,1983.
[2]J.G.Fichtes Werke Bd. Ⅶ.[M].hrsg.von Immanuel Hermann Fichte.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 Verlag,1975.
[3]J.G.Fichtes Werke Bd. Ⅺ.[M].hrsg.von Immanuel Hermann Fichte.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 Verlag,1971.
[4]Fichte.J.G.:Rechtslehre. [M].hrsg.von Richard Schottky.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80.
[5]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梁志学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J.G.Fichtes Werke Bd.Ⅳ(2)[M].hrsg.von Immanuel Hermann Fichte.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 Verlag,1965.
[7]Marco Ivaldo.Politik,Geschichte und Religion in der Staatslehre von 1813 [J].in Fichte-Studien Bd.11.Amsterdam:Rodopi Verlag,1997.
[8]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晓朝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On Fichte’s Concept of Right at the Period of Berlin
ZHANG Dong-hui
(Philosophy Department,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Xiangtan,Hunan 411201,China)
Under the philosophical context of new Wissenschaftslehre,Fichte’s concept of right at the period of Berlin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especially the start-point of his right concept’s deduction from Self into God.therefore,his right philosophy takes up strong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This theological right thought,of course,is linked essentially to that at the period of Jena.This paper starts from a discussion about Fichte’s concept of right at Berlin period,and then expounds this right concept’s forming conditions and realization approaches as well as the key role of state in the realization process.Finally,this paper remarks Fichte’s right thoughts,and points out that his thoughts inherit from Augustine’s theological politics,bear on contemporary morality politics and reflect the non-liber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cept of right;wissenschaftslehre;self;god;state
B516.33
A
1000-2529(2011)05-0047-06
2011-05-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德国古典法权哲学的逻辑历程”(10YJC720057)
张东辉(1976-),男,湖北宜昌人,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