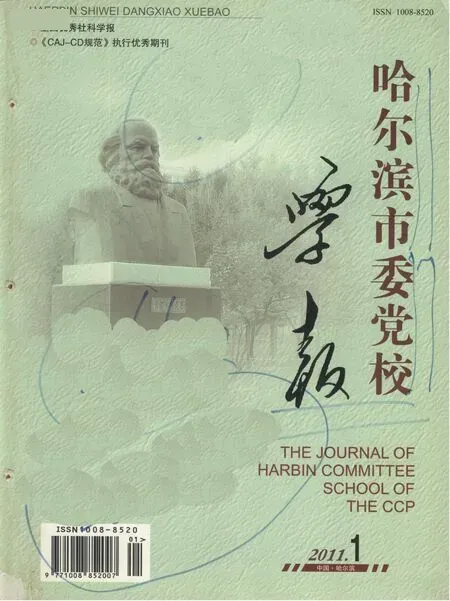从古代社会主要矛盾看专制政体的民意基础——基于公共选择学说视角
王 浩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经济研究所,武汉 430223)
·科社新探 ·
从古代社会主要矛盾看专制政体的民意基础
——基于公共选择学说视角
王 浩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经济研究所,武汉 430223)
“民主治理与国家建设”是这个时代的重大话题,国家政权是否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具有民意基础就能治理好国家吗?通过公共选择学说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主要矛盾的分析,可以勾勒出一副“君权民授”的景象。然而主要矛盾下多方博弈最后的结论则是:官僚集团是导致专制政体最后摧毁这个民意基础的罪魁祸首。
古代社会;公共选择学说;社会主要矛盾;专制政体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实质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政治体制的修正。如果说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三十年,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三十年则是全国人民得以表达自身利益需求及理性偏好的三十年。两个三十年之后,中国是不是要面对一个新的三十年的抉择,而在这个抉择的关口我们又可以从历史经验、从西方的理论中获取什么?中古时代的专制体制为何经历了一次次起义浪潮仍然延续不断,历史上最底层民众是否具有某种与政权互动的潜意识?笔者认为,公共选择学说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一、公共选择学说应用于研究专制时代的路径探析
众所周知,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说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学领域,通过选民与民选政府、政府旗下的技术官僚三者互相的博弈模型来解释民主体制下的一些悖论与困境。而这一理论作为舶来品到了中国之后明显的水土不服,更多的学者愿意分析该理论在普选背景下的运用,其中之一的原因是虽然我们也有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议制选举机构,但有时政府官员由领导指派,选举往往流于形式。其次,我国的选举权与西方的普选不同,即在于“功能组别”限制,以“单位”为基础的选举组织,提高选举人进行投票的成本,限制了他们表达偏好的机会。这两个原因导致以交易经济学作为解释政治交换过程的公共选择学说在中国似乎难以将所谓的公民投票者、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之间的“交易”过程清晰地描绘出来。
(一)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观上的公共选择学说
公共选择学说的基石,即在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笔者认为,虽然直接将公共选择学说与普选挂钩的模型在现阶段的中国难以适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即“理性人”一说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很多政教合一、单极信仰国家里,人的欲望被压制,好像不存在“经济理性人”的概念,但这实际上是身份上的依附关系凌驾于制度上的契约关系 (即“公仆才是主人”),从而导致了另一种游戏规则在实际上的确立,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古代社会与公共选择学说原先需要的民主政治背景差别在于实质上的个人利益被神秘主义和伦理纲常所掣肘,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自私自利的假设,公共选择学说将经济人的概念泛化,使得现代意义的经济人概念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可以以利他主义的视角面对经济问题。当民众只是受利他主义在精神上干涉的时候 (宗教信仰与权威胁迫),他作出的决定要么是自我实现与救赎,要么因为外在的胁迫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从而使他理性受到限制无法实现预先设定的最大化目标。公共选择学说称这样的情况为“有限理性”,我们知道西欧的中古时代教会势力强大,非但左右人的思维而且掌控经济命脉、把持王权任免,使得教宗及其支持者在历史进程的分析中无可或缺;反观东方君主专制历史,皇权与礼教思想高度统一,单纯的宗教势力只是偶尔在政治经济领域出现,如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经济。所以我们在应用公共选择学说时,可以将君臣父子之道等伦理行为准则并入君主专制体制中思考,也是在实质上将其作为外在因素影响民众理性选择的剥离。
(二)历史唯物论视角下中国主要矛盾辨析
在剥离了宗教因素对民众理性干扰这一自变量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就可以运用公共选择学说解释一系列问题。当然,笔者认为要解释这些问题必须明确古代 (封建社会)国内问题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主流论断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矛盾。地主阶级控制政权,继而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在战争、灾荒等外在环境的刺激下爆发农民起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主要矛盾这一论述来自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的论断。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社会上只剩下农民阶级及其敌人地主阶级,这也对照着“非我善类”、“异己专政”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反对将欧洲的模型盲目套用在其他地区,封建社会论断在远东的修正就是现在理论界所述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封建社会”。但这一论断无法清晰地解释主要矛盾到底是中央集权与分离主义,还是封建主与邑地农民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中央集权制度是一种权力构建,而封建社会则是这种构建的实现形式,“封建”的字面含义即为:分封建设。无论这个“建设者”与最高统治者是否具有亲缘关系,他的封邑对社会的改造必将影响统治者的施政。尽管历史上曾有君主想让两者互不干涉的和谐共存,但实际上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典型的案例就是汉初的七国之乱。所以现代的学者对“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封建社会”论断有很大程度的质疑,一些学者认为秦以后的中国不能完全称之为“封建社会”,甚至认为“将秦汉至明清称为‘封建社会’,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1]。笔者以为,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中社会形态的论断其依据是历史唯物论,其核心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说法意味着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导致了社会制度的产生,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的形成。但同时马克思也认为社会上层建筑也取决于统治者的最大利益,因为统治者掌控着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这也是中央集权与封建制度得以共存的理论基石。但即使如此,马克思本人也承认:“到蒙古人的帝国末年,所谓封建化只发生在某些区,在其他大多数区,公社的和私人的财产仍然留在土著占有者的手中,而国家公务则由中央政府所任命的官吏办理。”[2]由此可见,马克思本身反对教条式地将东西方社会经济历史混杂在一起,从而产生一条各国普遍适用的“绝对真理”。事实上,将马克思关于古中国和古印度的“东方专制主义”与关于西欧的“骑士封建制”杂糅成团,以便证明历史的必然性,本身就是某些机械唯物论者一贯信仰的“血统论”。那么将“封建主义”的古老标签从中国历史上剥除之后,中国古代的历史是否只是一代又一代君主集权的延续呢?马克思生前并未把东方制度作为他研究的重点,去世之后他的遗稿则成了政治的投笔无法供学者潜下心来研究。这需要我们借助其他理论来说明集权与封建的关系。
二、从公共选择学说角度看小农经济与君主专制的关系
中央集权与封建主义虽然并不兼容,但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实际上从微观层次来看,每一代君主上台之后都要处理这一微妙的平衡。而这一平衡与中国历史主要矛盾及社会关系的研究则要修正马克思关于西欧社会历史的论断,这也是本文运用“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说来解析中国历史若干问题的缘由。既然要用经济理论来说明社会历史问题,“经济基础”的界定也就是生产关系是什么显得极为重要。笔者认为,从西周至清末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自有土地者与土地租赁者争夺稀缺土地资源的生产关系转换中。土地私有制作为这个转换基础中的基础是不变的,无论是自有土地者还是租用他人土地者都有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力,这也是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在这里,笔者用自有土地者代替农民的说法,实际是公共选择学说从理性偏好的角度对“农民阶级”的解构,我们不应将自有土地者也就是自耕农与租用他人土地者也就是佃农划为一类,一是因为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同,这种不同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当时社会形态中所处的位置。二是因为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来看他们作为纳税人的理性偏好有很大不同。自有土地者也就是自耕农的理性偏好表现在受强制性税收的影响,从而具有强烈地支持减税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小农经济本身是自给自足的,但半干旱干旱地区的水利设施需求不是任何个人可以完成,所以自耕农对统一高效政府的渴求以及希望改变土地买卖游戏规则的愿望与专制政府治理国家时具有的扩张性一拍即合。他们被毫无联系地分散在各地,本身无法团结在一起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对治理国家这一重大问题有着一种茫然无措,即“理性的无知”。在民主社会这种无知表现为投票率低,在专制社会则表现为面对统治者时的自卑。在自耕农心中“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3]。这种自卑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在不可能望及的领域替他们作出决定,而当某些时刻他们想自己做主,却发现被其他人拥戴的专制力量为他 (她)的不合作设置了强大的障碍,成为一种巨大的交易成本,此时的理性受到专制的限制。尽管如此,自耕农作为小农经济的主体,也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和专制统治者的政治交换过程,借此来遏制地主和他们进行土地交换过程的企图。
我们可以看到,君主官僚集团与地主及自耕农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自耕农和地主向政府缴税、政府居于其间平衡两者的利益关系来实现“和谐社会”,这是否一个稳定的权利循环呢?事实上,作为一个小循环也许能达成,但当这一问题放至治理整个大帝国的语境中我们就得考虑另一个自变量——官僚集团,公共选择学说同样将官僚设定成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但这一设定有一前提,就是在民主制背景下官僚需向领导、选民双向负责,而君主制背景下,官僚秩序向君主负责,当他们可以欺骗甚至抛开君主之时,就会挤占优势社会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化,继而将这个循环中更多的人变成流民,也就是帝国的不稳定因素。
三、官僚的背叛:专制遇到的挑战及其民意基础的崩溃
在此同时,私有制背景下的自耕农与地主豪强的土地买卖则成了一条关键脉络,在人口普查水平落后的古代中国,地主会隐匿来减少赋税的边际产出,也就是说土地兼并程度越剧烈,中央政府的收入会越少。历代的专制机器存在的正当性就是它能保障农业生产与抑制土地兼并,“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4](周语上)但一方面士族地主通过科举制与行贿不断地向官僚集团渗透导致其职能丧失;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循环对体制起到不断恶化的作用,如自耕农人口向佃农、流民净流出,其原因是单个流民与地主的议价能力差距太大,导致土地私有制背景下,兼并成为市场的最优选择。这使得王朝历史的推进过程中自耕农及其赋税不断下降,王朝的危机爆发也成为一种必然。当自然灾害、异族入侵等外在因素导致第一波土地兼并潮来临的时候自耕农的数量与他们所缴纳的赋税一起减少。中央政府则需收拢那些破产的自耕农去进行恢复农业生产的建设如垦荒与兴修水利,但投资的费用则更多地摊在剩余自耕农头上,导致更多人破产;面对一部分起义的流民,政府则扩编军队予以镇压,新入伍者有一大部分是有产者,他们的脱产进一步打击了赋税基础。而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专制领导人的出现才能缓和局势的恶化。他会开垦受破坏的土地,肃清反对势力,使底层不满者叛乱的个人成本增加;整顿吏治,使税收渠道不受阻碍。但无论如何,他都得面对这样一个开局:能用的土地没有以前多了。事实上,真正导致王朝灭亡的原因就是来自这一轮专制主义的加强,在这个“圣君”之后官僚集团的掌控力大增,君主本希望利用这批人管好愈来愈强势的士族地主,但官僚权力寻租空间自然是被财力更加丰厚的地主乡绅所占据,这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可见“王权与原本是服务于自己的官僚制之间的矛盾,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乃是国家权力的一人独占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的必然产物”[5],而家长制下的君主只能继续加强专制的程度 (这个时候往往会寻求军人的支持),并由仍有正义感的官员制定税收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个节点不应是每次王朝更替,而是每次赋税改革。因为每次抑止地方势力扩张的规则变更,都是中央试图专制集权的一次努力,倘若努力失败则君主在实质上出局,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将露出它的真面目,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专制主义旗下官僚财阀与广大无政治发言权的“赋税奴隶”之间的矛盾。笔者有必要在此说明两点:其一,这里所指的财阀主要为因掌控权力而圈占土地者,“权力新贵”以协调地主与农民矛盾面目出现,实则是要大小通吃;小地主,甚至曾经可以向官僚行贿者要么已经成为其附庸,要么被完全兼并。其二,根据布坎南对地方政治的研究而得出的“俱乐部理论”:在原先成员基础上加入的新成员所带来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因此可以说,小农地主才是真正的“家天下”,因为没有人会贪污自己的钱、出卖自己的利益,这时小范围内的专制边际效益最大化,笔者认为这一分析也同样适用李光耀父子的“新加坡模式”。所以土地兼并对民众的伤害远低于官僚集团的压榨,地主的土地可以容纳更多的佃农,除非扩张到需要职业官吏来管理,不然他的平均成本是在下降。反之不然,庞大的官僚体系所消耗的远超过君主这个全国最大的“地主”;官僚体系越庞大,平摊个人赋税就越高,就会有更多的自耕农变成流民继而造反。小农经济需要强力政府保持社会形态的均衡性这也是专制政体的民意基础,而膨胀的官僚集团使“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的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6],这就是专制主义制度的命门,是它打败了自己,也正应了那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专制王朝已经被民众所抛弃,它的民意基础瓦解了。讽刺的是,之后发生的农民战争则是底层民众以自己的方式肃清这些蛀虫,建立一套与之前完全一样的专制主义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君主专制才有可能遏制底下蝇营狗苟之辈的作乱。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专制主义制度在东方如此具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众受礼教的蒙蔽,而坚信“政策虽好,贪官太多”、“上面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搞坏了”之类的谬论。所以前文所述剥去宗教外壳,还原民众理性偏好的意义正在于此。人民群众一手打造了一个荫护他们风调雨顺的专制体系,继而为维护这个体系而与其中的“文强们”进行不懈的斗争。
四、“政府失败说”:专制王朝灭亡的必然性与国家前途的转机
为什么这些贪官总是杀不绝呢?这是历代统治者与老百姓在用严刑峻法“反贪”之后的感叹,用公共选择学说的术语来说则是:为什么东方专制政府总是会出现“政府失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专制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其一,在私有化的前提下国家财富与权力被不断集中在地方利益代表者手中,专制政府只能通过加大对纳税人的压榨而维持其日益削弱的经济基础而这反过来削弱了它的社会基础,是谓杀鸡取卵。其二,中央政府加强专制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其任命的官吏对地方的掌控,但当“家天下”变成“集团天下”的时候,贪污腐败将会横行无忌,官僚集团也会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中饱私囊,君主的利益在实质上受到损害,君主专制从内部开始瓦解,演变成“君主官僚制”。其三,专制产生的根源在于民众让渡自由与平等,而换取中央集权的高效与保障,但因为广袤国土及科技限制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其无法有效地监督官僚的所作所为,使得民众在受到强烈压迫之后,收回其对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的授权揭竿而起,这是压垮专制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君主王朝灭亡了,但专制体制还在延续,古人云“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形象地道出了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轮回结束的前提与保证则是:(1)小农经济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自身瓦解,民众的分散性与封闭性被打破,也就是城市化的到来。(2)在现代城市与工业化的基础上,民众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以避免理性的无知。(3)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治,并拥有决定官僚政绩的权力,以降低“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只有满足了以上几点,权力体系才会在自下而上的授权制度下运作,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
[1]冯天瑜 .重新认识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3).
[2]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8-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8.
[4]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陈明 .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土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6][美 ]道格拉斯·C.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D691;C912.3
A
1008-8520(2011)01-0043-04
2010-10-28
王浩 (1987-),男,浙江金华人,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那青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