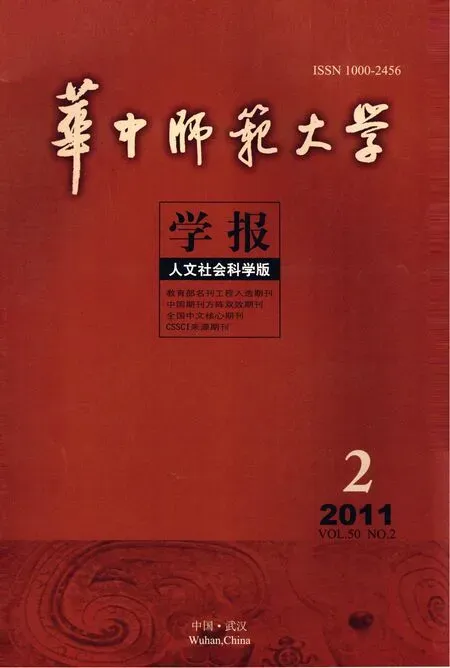民俗学的当代性建构
黄永林韩成艳
(1.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民俗学的当代性建构
黄永林1韩成艳2
(1.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传统的民俗学将向何处去?这是民俗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新时期民俗学要想走出困境,对社会和学术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必须树立新的学术品格,对社会有所担当。从“历史学”转向“当代学”,将民俗研究导入当代社会,直面当下社会的变迁;从追溯历史、重构原型、回归传统,转向关注现实、关心人生、阐释社会、服务当今社会。让以研究“古代遗留物”为开端的学问转向以研究当下现实社会习俗为主的与时俱进的学问;让以“民间文学”、“口头传承”为主体和“历史考据”、“原型重构”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俗研究传统,转向以“当代民俗”、“现代传媒”为主体,以“整体研究”、“综合研究”为主要方法的新民俗研究。民俗学的这种当代性建构需要民俗学学者们具有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民俗学;传统;现代;当代性;建构
身处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现代生活之中的每个关心民俗学发展的学者,都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传统的民俗学将向何处去?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又该有何作为?是把目光继续停留在“古老文化的遗留物”呢,还是把目光聚焦到火热的现实社会生活?是仅仅满足于对民俗文化传统的挖掘,还是直接面对并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是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口耳相传的狭小民俗范围,还是扩展到现代传媒影响下形成的鲜活的新民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门学问完全无视千百万人的现实生活,即使它有着辉煌的过去和今天,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长期兴旺发达的。民俗学只有根植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沃土之中,才会有蓬勃生机和美好前程。本文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口传与传媒的角度,研究当代社会变迁对民俗学的影响,并试图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两个维度提出构建当代发展民俗学的理论体系。
一、突破“古代遗留物”范围,直面现实生活
民俗学源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英国“古俗”(Antiquities)和“大众古俗”研究,当时一批从事古老知识与古物研究的学者,曾创办有关杂志,并出版了一批相关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伯兰德(John Brand 1744—1806)《大众古俗之观察》(伦敦1777年版)。在这部书的总序中特别强调“口头传承”(Oral Tradition)①,这个词后来经常被用作“民俗”(狭义的)或“民间文学”的同义词。民俗学国际用语为Folklore,它发端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1846年,英国的威廉·约翰·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rns,1803—1885)向《雅典娜神庙》杂志写了一封信,信中首次提出“民俗”(Folklore)这个词,他说“贵刊发表的文章常常显示出对于我们在英格兰称之为‘大众古俗’或‘大众文学’的那种东西的兴趣,(不过,我顺便提一下,与其说是一种文学,不如说它是一种知识,并且,用一个很好的撒克逊语合成词来表示它最为恰当,这个词就是Folklore——民众的知识)。”②汤姆斯第一次对民俗概念、性质、内容作了界定,将古老年代的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作为民俗研究的主要内容,把Folk-lore(民俗)当作一门学问看待和一种“古代文化遗留物”体认。汤姆斯关于民俗学科的观点,在英国得到迅速普遍的接受。1878年10月,英国民俗学会(Folk-lore Society)成立,并出版了《民俗学杂志》(The Folklore Record)。在此后近20年中,这个学科从英国及其附属国,很快影响到美、法、德、意等西方诸国。1888年美国民俗学会成立,1890年德国柏林民俗学会成立,稍后法、意等国也接受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一名称。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分别于1865年和1871年出版了《人类早期历史研究》和《原始文化》。他认为野蛮人的心智现象遗存在幼稚的游戏、信仰、谚语和故事中,而这种遗存被称为“遗留物”(Survival)。他在《原始文化》第三章“文化中的遗留物”提出“遗留物”学说,并把野蛮人的信仰和行为与现代农民的民俗联系起来看。在他们看来,各种类型的民俗都是原始文化留存在现代社会的残余。因此,每一个民俗事象的发现都可能有助于修复一点原始文化的本来面目。他的“遗留物”理论的要点是:在文明社会里有许多风俗不可理解,这是因为它属于原始文化,只有通过分析与它们同时存在的神话传说,并证之以未开化民族相应的风俗和神话传说才能解开这些风俗的文化之谜。③
“遗留物”说在民俗学界的流行,形成了民俗研究的人类学派,他们信奉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遗留物”学说,假设“原始民族”文化与欧洲农民的“遗留物”在文化史上的“同时代性”,研究对象大多是奇风异俗,即那些存在于这个时代却在本质上不属于这个时代、并常见于边缘地区的文化现象。安德鲁·兰(Andrew Lang,1844-1912)在1884年出版的《风俗和神话》第一章“民俗学的方法”中说:“有一门科学,考古学,搜集并比较古代种族遗留下来的实物,如斧子和箭簇。另有一门学问,民俗学,搜集并比较古代种族的非实体的类似遗物:遗留下来的迷信和故事,以及那些见之于我们的时代却又不具有时代性的思想观念。准确地说,民俗学致力于研究那些极少受到教育的改造、极少取得文明上的进步的民间群体、大众和若干阶级的传说、风俗和信仰。民俗的研究者立即就会发现这些在进化上落伍的阶级仍然保留着许多野蛮人的信仰和行为方式……民俗的研究者因而被吸引去审视野蛮人的习惯、神话和思想观念——欧洲的农民仍然保存着它们,并且,它们的形态不乏本来的朴野。”④在这里,民俗的“民”被定义为“那些极少受到教育的改造、极少取得文明上的进步的民群、大众和若干阶级”,他们是进化上的落伍者。并且,他特意把“欧洲的农民”作为代表列举出来了。因此,野蛮人风俗和各种奇风异俗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英国的阿尔弗雷德·纳特(Alfred Nutt,1856—1912)也属于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他在1899年出版的《田野和民俗》中认为“这些遗留物就是民俗,就是民——社会中那部分没有学问、又最落后的人——的知识。”文明“是城市生活的产物,民俗是乡村生活的产物”。⑤纳特认为民俗像庄稼一样,只能生长在乡土里,民俗是农民所特有的,而把其他职业和阶层的人排除在“民”之外。这种观点在民俗学界根深蒂固,支撑着研究奇风异俗的历史主义学术信念。
英国民俗学家夏洛特·班尼(Charlotte Sophia Burne)在1914年出版的《民俗学手册》中写道:
(民俗)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普通术语,它把流行于落后民族或保留于较先进民族无文字阶段中的传统信仰、习俗、故事、歌谣和俗语都概括在内。
研究这些传承的知识,第一步就是观察存在于现代欧洲各国低等文明居民中的大量奇异的信仰、习俗和故事,它们由一代一代的人们口头相传而来,本质上是社会集团中无文化落后人们的属物。
接着,应该注意现在流行于蒙昧和野蛮民族中的与上述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信仰、习俗和故事。⑥
综上所述,英国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初创期就具有“文化遗留物”之学的性质,英国人类学家假设民俗是古代文化(原始文化)的遗留物,他们进行民俗研究旨在通过遗留物复现它们所代表的古代文化(原始文化),并透过古代文化(原始文化)理解在当时难以理解的那些民俗。因此,他们将民俗局限于文明社会中古文化的遗留物——古老年代的礼仪、风俗习惯、典礼仪式、迷信、歌谣、寓言等方面,并把奇风异俗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英国“古文化遗留物派”的观点,一度在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影响极大。1923年北大风俗调查会筹备时征求会员启事中说“风俗(民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之良好材料。”⑦如杨成志教授的《民俗学问题格》(1928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民俗学会从书”出版)、林惠祥先生的《民俗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方纪生先生的《民俗学概论》(1934讲述,《民俗学资料丛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资料定印,1980年),都是以夏洛特·班尼《民俗手册》作为理论基础和分类依据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认识到把民俗认定为静止的、僵滞的“古老文化遗留物”的传统观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上世纪80年代,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为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所作序言时写道:“班尼女士的那种范围比较狭隘的观点,在我们过去学界中占着相当位置。一提到民俗学的对象,大家就只想到传统、故事、歌谣、婚丧仪礼、年节风俗及宗教迷信等。其实,这种看待民俗学的范围以及它所包括的项目的见解是比较陈旧的……今日世界关于民俗学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差不多已发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⑧钟敬文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他强调民俗学研究“不能固守英国民俗学早期的旧框框”,要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活世态”,“拿一般民众的‘生活相’作为直接研究的资料”⑨和对象。而且越是到80年代后期,钟敬文的这个想法越是强烈。1994年1月钟敬文先生在为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间生活》一书所作的序中更是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
在最近几年里,我在一些理论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心血,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关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来说。民俗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如果说它初期在收集和研究的范围上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有些国家里,它已经扩展到全部的社会生活、文化领域了。具体地说,如过去各种劳动的组织、操作的表现形式、技术特点和所附着的信仰;又如过去社会中,有各类团体活动像宗教的庙会,有村落和宗族的各种习惯、规例等,这些都是民俗现象。至于各地年节风俗,每人自出生到老死所奉行的诞辰、成年式、结婚、丧葬等仪礼,以及各种民间赛会、民间文学艺术活动,它们从来就被算在风俗、习尚里面,这自不必细说了。
从内涵上说,社会民俗现象虽然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既涉及生产劳动、社会组织,又涉及岁时活动、人生仪礼等等,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它们有内在的共同特点。它们首先是社会的、集体的,决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即使有些本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或发起的,但是也必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风俗)。其次,跟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大都是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扩布的。在这种特点上,它们与那些一般文化史上个人的、特定的、一时或短时的文化产物和现象(例如时尚)有显著的不同。
至于这门科学对象的时间取向,从根本上说,民俗学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拿其他学科来类比,它是像人类学、社会学那样,以现在人类、社会的活动事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跟古人类学、原始或古代社会史等学问是不一样的。自然,民俗研究中也要从今溯古,或以古证今,这些都是学术活动的自然现象,也是合理现象。但这不等于说民俗学所处理的事象,主要是历史的,它的研究资料只依靠文献,或主要依靠文献。应该说,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主要对象的。过去有些学者往往从古文献上去抄辑材料,或热衷于到历史民俗现象中去找寻研究题目。这只是文献民俗的整理或研究,是属于历史民俗学或民俗史研究的范围,跟民俗学当然也有关系,但基本上却不是一回事。⑩
钟敬文先生关于民俗学是“现在的”学问的观点和发展当代中国民俗文化学的建议,正在学术界形成共识。
对于当代民俗学来说,民俗决不仅仅只是一种具有文物价值的“古老文化遗留物”,它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国家的传统与习惯,它早已渗透在国人的血液之中,并镌铸着国人深层的心理积淀,与今日和未来都是息息相通的。正如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过的:“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也。”(11)足见民俗文化与民族精神之改造关系极为密切。民俗文化既源自传承,又在现实社会中变异,它纵向连接古今,横向又沟通内外;它既蕴藏着民族的主体精神,又包含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当代民俗学的特征,一是表现在时代上的当代性,应充分反映当代风俗文化的新风貌;二是表现在内容上的生活性,它应当是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升华为学科高度的系统理论,三是形式上的传播性,应体现文化是一个大系统,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信息传播的体系。将民俗视为文化,不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意识在世代流传,而且更表现为具体、物化了的“生活相”在不断扩布。因此,现代民俗学者应以发展的、动态的观点来看待和研究民俗事象,把目光转移到沸腾的社会生活,关注和研究当下生活中异彩纷呈的民俗,以科学的主人翁精神,去探求民俗文化中人的主体意识,并探寻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传承变异中的发展踪迹,高扬民族精神之优长,辨析民族精神之缺失,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只有这样,这门学问的意义才难以估量,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二、突破“古老传统”观念,面向现代社会
随着民俗研究日益深入,这门学科越来越重视民俗与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爱德文·西德厄·哈特兰德(Edwin Sidney Hartland 1848-1927)在他1899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什么是民俗及其功用?》中说:“民俗学就是关于传统的科学”,“作为一科学对象的传统指未受学校教育的那些人的知识整体”。(12)法国民俗学家山狄夫(Pierre Saintyves 1870-1953)在1936年发表的《民俗概论》中明确地说,“民俗学是文明国家内民间文化传承的科学”。他们都强调了民俗的传统性与传承性的特征。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根据他在墨西哥农村小社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乡民(Folk)和市民(Urban)处于对立的两极。他认为,传统的乡民社会是由不与外人交流的人群构成的,他们居住在半封闭的社区里,在文化上属于小传统而与都市文明的大传统相对立:“小传统——小规模、单一性、神圣化;大传统——大规模、多元性、世俗化。”(13)他在1947年发表的《乡民社会》中指出:
对一般社会、特别是对我们自身的现代城市化社会的理解,可以通过考虑与我们自己的社会最不相似的社会即原始社会或乡民社会来获得。一切社会在某些方面都是相似的,每个社会在另一些方面与其他社会又有所不同;这里做出的进一步假定是,乡民社会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使我们把它们看做一个类型——一个与现代城市社会形成对比的类型。
这个类型是一个理想的精神建构(mental construction)。已知的社会没有与之恰好对应的,但是人类学家主要感兴趣的那些社会最接近这一类型。实际上,对这一类型的建构要依靠有关部落族群和农民群体的特殊知识。这种理想的乡民社会可以通过在想像中把那
些在逻辑上与现代城市中发现的特征相反的
那些特点组合起来而获得界定,我们只有首先
对非城市民众有了一些知识之后,才能裁定现
代城市生活特有的属性是什么。
他在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来界说文化的存在形态时,用民间对应他的小传统,与少数上层精英分子所编造的大传统不同,小传统是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逐渐发展而成的。(14)在这里“乡民社会”在与现代城市的对比中获得了建构和界定。他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界有较大影响。
从以上理论及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欧美学者关于民俗研究对象“民”及其“传统性”特征的认识是他们从直观经验中逐步构造出来的。事实上,在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e1ville J.Herskovits 1895—1963)就指出,民俗学家应该从研究“过去僵死的遗俗”——作为遗留物的风俗——转向“关心生活现实”,而且“民”可以被看成“作为展示出可辨认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群体的任何社会的任何民众或任何阶层”(15)。尽管赫斯科维茨的观点非常有见地,然而,在相当长时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城市化步伐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急遽变化,这也促使美国学者对民俗的深入思考。印第安那大学的理查德·多尔逊教授(Richard M.Dorson 1916-1981)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民俗学家之一。1973年8月28至30日,来自31个国家的民俗学家会聚在印第安纳大学,研讨“现代世界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问题。多尔逊在会上做了同题发言,他从“城市”、“工业与技术”、“大众媒体”、“民族主义、政治与意识形态”四个方面论述了民俗的当代性。(16)他认为传统民俗学对“民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中心而做出的,并在分析这种定义内涵因素时,按照雷德菲尔德所用的二元模式列出了它们的对立因素。他说:“有些外人把民俗看作博古家溺爱的无聊玩意儿(这种态度经常可见),并把民俗学想象成关于过去的学问,想象成研究特别有趣但落后、衰败的亚文化的学科。虽然我不能接受这种价值判断,但是我承认,民俗研究从一开始确实是与古俗和‘原始的’乡下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另一方面,有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民俗研究,使民俗研究呈现为当代性的,使他们面对‘此地’和‘现在’,面对城市中心,面对工业革命,面对时代问题和思潮。根据这种观念,民俗存在于活动发生的地方,而根本不是死水中的一堆沉沙。……然而,这两种观点并非不可调和。‘Folk’不必仅指乡下人(country folk),最好意味着趋向传统的匿名大众(anonymous masses)。即使乡下人搬进城里(在过去几十年里,乡土人口的流入使世界大都市人口剧增),民俗学家并不丧失对他们的兴趣。出生在城市里的后代也并不必然失去作为民间群体(folk groups)的属性,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服饰、烹调、语汇和世界观也可能由传统力量来塑造。”(17)在1973年出版的《传说中的美国》(America in Legend)一书中,他从理论上提出民俗的当代性(the contemporaneity)问题,并以此与民俗学的古老性(the antiquity)形成对比。他认为,“民”不必单指乡民,而是指传统取向的匿名大众(anonymous masses of tradition-oriented people)。因此,他把民俗之“俗”界定为民间文化、口头文化、传统文化、非官方文化。多尔逊认为民俗文化是活生生的传统,属于它所处的时代的观点是很精辟的,然而,他仍然把民俗限制在民间宗教等传统的民俗观所认定的领域里,他的所谓的传统依然还是历史传统、乡土文化的传统。
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 1934-)在1965年出版的《民俗研究》(The Study of Folklore)将民俗从有限的传统文化转而面向文化传统这一整体。他说:
“民众”这个词,可以指“任何民众中的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中的人,至少都有某种共同的因素。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连结因素,或许是一种共同的职务、语言或宗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个不管因何种原因组成的集团,都有一些它们自己的传统。在理论上,一个集团必须至少由两个人以上组成,但一般来说,大多数集团是由许多人组成的。集团中的某一个成员,不一定认识所有其他成员,但是他会懂得属于这一集团的共同核心传统,这些传统使该集团有一种集体一致的感觉。(18)
邓迪斯从传统的共时性角度强调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指出了传统是群体现在共同享有和传承的。
在《民俗、神话与传说标准辞典》(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Mythology,and Legend)关于民俗学的多项界说中,最基本的定义是:“民俗的内容是人民——包括原始的和文明的——传统创造。它们是运用声音、文字以韵文和散文形式构成的,同时它还包括民间信仰或迷信、习俗和表演、舞蹈和游戏。进而,民俗学不是有关某一族群的科学,而是传统的民间科学和民间诗学。”(19)《大英百科全书》“民俗”条目说,“民俗,是普通民众始终保存的、未受当代知识和宗教影响的、以片段的、变动的或较为稳固的形式继续存在至今的传统、信仰、迷信、生活方式、习惯及仪式的总称。”(20)
上述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他们认为民俗学是关于传统的科学,民俗是代表某些范围内的文化传统,是指与较高阶层的文化相对照下的俗民的全部文化传统,是在民间口头讲述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将民俗学定位为关于俗民的文化传统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当前正面临着的变化迅速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传统的现代意义和内涵。
通常人们习惯于把“传统”与古老的事物等同起来,即将传统作为一个“过去”的时间概念来理解。事实上,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它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传统是现代过去的凝聚,现代将是未来的传统。以探讨现代性及现代社会变迁著称的英国社会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把我们当今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表述为“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他指出:“现代性,总是被定义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现代社会不一直就是‘后传统’的吗”?他认为,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重建了传统。(21)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然而现代性未能(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或者说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延续着并按其原有逻辑生长着,而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即进入所谓后现代以来,社会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断裂的特性,从而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大量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更无从控制的现象和过程;同时也使我们的行为陷入无常规可循的境地。这种情形或许是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称为“后传统”社会的主要原因。
民俗是群体的生活文化,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民俗,有群体的地方就有民俗存在。民俗对人们生活和群体存在如此重要,是因为民俗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包含着人生最基本的行为方式。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民俗具有的传统性和传承性,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注重它的演化和流变。作为民俗的“传统”,常常在变化的压力下,通过新发展以重建维持之。旧时代的民俗,有的已被淘汰,有的正在演化,新的民俗也在不断产生。尤其是当一个民族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经济、文化、政治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的急剧变化,新旧民俗作为新旧文化意识的一种表现,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如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层面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网络语言、虚拟空间、白领生活、小资品味、新好男人、人造美女……带来的震惊和刺激让人应接不暇,而与这些相关联的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体现为种种可以称为“新民俗”的现象。因此,民俗传统不仅是一种文化承继,更是一种文化建构。
传统民俗研究由于受“古老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将民俗事象割裂于鲜活的现实日常生活之外,使得民俗学的当代性和现实取向难以实现。作为后现代民俗,其中的传统是新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应将民俗研究的社会领域扩展和延伸至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中,一方面,扩展包含超越地区、时代、阶级差异的相关领域中;另一方面,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成员的视野中,随着持续的变异,这种扩展又凸现出不同的意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民俗学关于传统的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前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文明新传统、市场经济对传统改造或重构的现代传统,这几个维度同时构成了中国民俗研究的独特性和学术灵感的来源。因此,民俗学要在当代社会立足,必须从历史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注重历史传统转向面向现实社会。
三、突破“口头传承”局限,注重现代传媒
从世界民俗学早期的实践和学科界定中,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它的主要特点:一是口述性,二是传统性。前者是其主要的存在和表达形式,后者则旨在强调其历史传承特性。在人类学的用法中,“民俗”这一术语常指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谜语、歌谣和其他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艺术表现形式。因而,民俗可以被界定在语言艺术范围内。(22)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的人类学教授威廉·巴斯科姆(William R Bascom)有一句名言:“所有民俗都是口头流传的,但不是所有口头流传下来的都是民俗”。“在无文字的社会里(人类学家传统上对这类社会有很大兴趣),一切结构制度、传统、习俗、信仰、态度和手工艺都是以言词教导和示范作用口头传下来,当人类学家同意将民俗定义为口头传承时,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口头传承这个特点,才把民俗与文化的其他事项区别开来”。(23)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弗朗西斯·李·阿特利(Francis Lee Utley)在1916年发表的《民间文学:一个实用定义》一文中认为,为了使民俗的定义与实际民俗研究相适应,有必要采取“实用定义”,他说:
为了我自己实用便利,我采取一种非常简单的表述,即:民间文学无论在哪里被发现,与世隔绝的原始社会也好,接近文明边缘的社会也好,都市社会或村落社会也好,上层统治者与下层阶级也好,他们都是一种口头传承的文学,“口头传承”这个关键词的应用价值是很大的。(24)
在传统社会里,民众一般被限制在某个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群体或村落里,生产和交往的人数、规模都十分有限,环境范围并不很大,也并不是很复杂。这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更多的是建立在“第一手信息”的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主要是通过口头来进行,人们对事物和生活的认识总是和特定的地域或地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民俗文化多属于口传的文化,人们通过直接的对话与交流使得本民族的民俗生活和文化传承一次次积淀在活形态的民俗活动中。
由于传统民俗学强调民俗的口头性特征,因此,十分注重口述史和口述传统的研究。口述史(oral history)与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虽然都是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呈现,但前者受到个人生命周期的限制,主要是对个人亲历的生活事件及感受的叙述,一般关注较近之过去的经验,而不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记忆,它通常表现为老百姓记忆与叙述自身经历的个人生活史、家庭史、宗族史、村落史。后者则是世代相承的口述证词,主要指比较定型的、程式化的、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文艺形式: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民谣、谚语等文艺样式。口述历史最为突出的功用在于收集口述凭证,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而作为集体传承的程式化了的口述传统则是唤起民族历史记忆,激发其自我意识,进而建构族群认同边界的主要依据。简而言之,口述史与口述传统,前者是经历,是个人叙事,而后者则是记忆,是集体记忆和表述。
然而,随着对民俗认识的深入,民俗被认为是或者是应该是“口头传承”的观点,受到到学者们的质疑。阿兰·邓迪斯在《什么是民俗》一文中指出:
首先,无文字的文化(人类学家称之为“无文献文化”)几乎全靠口头传承,例如语言、狩猎技术、婚姻习俗等,都是口头传承的,但很少民俗学家将这类文化资料看作民俗。而且,即使在有文字的文化中,一些口传信息,如怎样开拖拉机,怎样刷牙等,一般也不看作是民俗。由于口传的东西并非全是民俗资料,所以仅凭“口头传承”本身,并不足以区分民俗与非民俗。
第二,某些形式的民俗与口传形式相反,几乎完全是以书面方式存在和流传的。例如签名册上题的诗句、书籍眉批、墓志铭和传统信件(如连锁信)。实际上,一个职业民俗学家,决不会仅仅因为某个民间故事或民歌,在其生活史上的某个时期,曾被书写过或印刷过,就说它不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围。当然,一个民间故事或一首民歌,如果从来未经口头流传,他必定会声明它不属于民俗。它可能属于在民间形式基础上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它本身却不是民间形式。自然,上述书面形式也是极少以口头形式传承的。
以口头传承为定义原则的第三个困难,是以身体动作为主的民俗形式,如民间舞蹈、游戏、姿势等,是否经过口头传承还是个问题。一个孩子可以通过观察和参加活动来学会这些动作,而不需要用语言来传授。在民间美术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传统的象征符号,如“卐”字符,就不是口头传承的。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说来,民俗的传承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语言和动作直接进行的。但有时也有间接性的,例如,当一位民间艺术家,模仿其他艺术家作品上的传统设计时,他可能与那位艺术家很少个人联系,或者甚至毫无联系。(25)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以日新月异的惊人速度发展,充当了社会变革的先导,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剧变,它不仅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对社会风俗,亦即我们所说的民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工具不断出现,当代社会已成为一个以“媒介环境”为基础的社会,现代传媒(如因特网、电视、广播、报纸、图书、录像录音等)大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面临着和传统截然不同的信息环境,现代传媒将人们投入到一个更大的开放性的民俗生活环境中,人们运用现代传媒改变和制约着自我。在这样的民俗生活背景下,人们应对日常生活挑战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现代传媒在影响着大众生活的同时,也以现代形式反映现代民俗生活。(26)德国民俗学家保·辛格尔对现代传媒技术与民俗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现代技术世界的发达表面上造成了许多不利于民间文化生存的条件,但在现实上现代技术世界的时间感及交通、大众传媒造成的跨越式的空间,以及社会分化的强化,促使民俗活动的节奏加快,为民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涵盖面,使之可以通过互联网的通讯技术传递到超地方的领域中,并为不同社群的认同和联谊提供机会。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现代传播媒介反映、影响乃至包容民俗生活及其变迁,它首先发挥其最基本的文化表述工具的功能,不断塑造民俗主体,在民俗传播中发挥特定的能动作用。现代发达的多媒体技术将不同的民俗跨时空转移传播、发展,人们可以更快捷地接触到更多民俗文化,各地区之间的民俗也互相交融,并可能产生新的民俗。现代传媒介入人们的民俗生活中,这时人们在活动中接受到的文化信息,已经不再是原初的自然形态的信息,而是经过加工过滤的信息。现代传媒经常与某种民俗文化绞合在一起,形成流行文化,形成新民俗。一个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诞生的现代化大众媒体,一个是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人间风情,两者的结缘完全取决于它们本质特征的趋同性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性。(27)
有学者指出:“民俗是一种社会力量,具体而言,民俗是个人社会化的一种推动力和制约力,每个社会成员个体无时不在这种力量的动态过程中力图建立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其中,对符号以及符号创作和控制的形式及常规的掌握,也就是个体获取在这个社会动态中把握自己的技能和工具,这里的符号形式及常规、工具等指的也就是传播媒介,这样,传播媒介必然要和民俗及民俗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接触和使用传媒成为个人与社会交往或者说人们民俗生活的重要方式,接触和使用传媒的方式成为民俗生活的表现和再生的方式,规范接触和使用传媒的程式和常规就成为民俗生活生存和变迁的重要社会基础。”(28)传播媒介和民俗生活变迁,其实质也就是传播媒介和文化变迁的问题。在“媒介环境”之下,不同地区具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借助媒介来“共享”同样的文化。因此,民俗学应从孤立事象的研究转向面向“生活世界”的研究,从注重“口头传统”转向注重现代传媒,立足于当今文化和民俗生活所处的时代背景,即当今一切文化均处于“媒介环境”中,并且传媒日益成为社会和民俗生活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主题进行具体阐述。同时,我们还应该在全球信息传播技术更新和全球媒介市场条件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已经变化了的民俗事象,关注民俗学的未来,将我国民俗研究引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四、突破“考据重构”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一样,经历了一个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开始是对原始蒙昧人进行研究,主要涉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崇拜仪典等;后来是对本民族民俗进行研究,有的侧重于民间文学的发掘、研究和利用,有的侧重于环境地理与生态的研究;再后是对民俗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内容进行研究,主要是解析各种心理状态下人的行为方式。从而形成了“民俗三大学派”——人类学派、人文学派、精神分析学派。早期人文学派主要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开拓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其理论背景是企图找出一个流动传播的学说,在各民族风俗中比较异同,追溯源流;相继而出现的人类学派,则是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检验民俗学的材料,通过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的分析,着重探寻人类整体行为及其与各种民俗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原因,其基本理论构成了今日文化人类学的基石;此后,精神分析学派不像人类学派那样强调功能,它强调的重点是心理因素支配下的行为模式,更加重视从人的主观方面去解析各种心理状态下民俗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内容。当然,新的研究方法一个接着一个兴起,并不意味着旧方法的寿终正寝,相反,诸种学说蜂起,形成学派林立的局面,不同学派的相互攻难,各具分歧的观点、旨趣和准则,在民俗学的发生和发展史上,相互交叉、渗透、融会,对于民俗学的发展、繁荣和学科自身理论建设是有利的。
影响中国民俗学的西学大致可以分为人文学科传统和早期人类学的民俗研究传统,当代的各种民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以上述人文学科的传统和早期人类学的遗留物研究范式为主导,民俗学的人文学科的传统以澄清研究对象的传播路线和演化历史为目标,而成其为学术传统的主要是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这一研究法经过神话学派、流传学派的探索,最后在芬兰学派的研究中得以定型。另一个遗留物研究传统则以回溯研究对象的原型和本义为目标,他们认为民俗是种族在古老的过去创造的,现代人并不创造民俗,现代人生活中的民俗是处于野蛮时代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民俗在现代人中的保留程度并不相同,保留得最显著的是那些极少受教育的群体和阶级,例如农民,保留得相对最少的是受过教育的人们。正是这种观点孕育了中国民俗学界一条主要的学术思路:首先通过采风或文献检索发现某种奇风异俗,然后探讨它是哪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留物并推测它的原型和本义,或者推断它有怎样的传播路线和演化历史。这种重考据的历史主义取向对于研究书面文化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研究作为生活文化的民俗自然很勉强。民俗学的理论范式以古典的单线进化论为前提,可是,这个前提在世界学术界早已被证明不能成立,因此,通过研究奇风异俗而重构民族原始文化的学术信念必然彻底崩溃。
当代科学的发展,已日益趋向一种完整的和系统的综合研究,整体化过程已愈来愈成为它的主要趋势。晚近以来,这种整体化的综合性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指向一切传统科学的领域。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用他自制的术语对西方科技发展的整体趋势作出了这样的描绘:“第二次浪潮文化强调孤立地研究事物,而第三次浪潮文化则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整体。”(29)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结构复杂的大系统。过去,民俗被狭隘地分解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等部门,那不是事物的本质,不是民俗文化的本质。实际上,民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逻辑系统必须体现那一时代的全部知识体系,外来民俗和文化的冲击或者说输入,常常是促使传统文化和知识结构发生变化,或按基本的知识格局作总体的转换,或对框架作若干必要的调整和创制。
民俗学是涉及到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一个连续链条。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民俗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就不难发现,19世纪的民俗学从研究古老风俗学问中脱颖而出,日益分化,从而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了20世纪,特别在当代,则表现为一种“回归”到其他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交融、汇合,显示出一种整体化和结合化的趋势。20世纪上半叶,民俗学向社会科学所寻求的主要是新的认知能力。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借鉴则从寻求社会科学的一般概念转变为方法论问题,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都将民俗文化作为重要的概念和课题,其研究成果都从不同角度推进了民俗文化学的发展。此外,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及“旧三论”、“新三论”等综合科学也都为民俗文化学提出了新的视角和概念工具。民俗学与其他科学交叉的边缘性学科也越来越多,民俗学走向民俗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及项目也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研究一个村落的民居问题,就涉及到当时社会的经济、交通、人口、生态环境、地理环境学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哪一个学科能单独完成的,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需要运用交叉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更大范围的科学的综合。如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为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打破彼此隔阂开了先河。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没有拘泥于异民族,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而且,这一研究还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自然结果。民俗学这种交叉和综合研究冲破了传统民俗学的自我封闭的体系,在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的融合、渗透和交叉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产生,这种新产生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不仅没有阻塞民俗学走向新的综合,恰恰丰富和完善了民俗学的各个侧面,从而也为民俗学中重大课题的综合研究创造了条件。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俗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特别需要用综合的眼光来进行宏观的观照。综合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创造。如果说创新是发展民俗学术思想的突破口,那么兼收并蓄,善于综合各家之长,则是打开突破口向纵深发展的正确途径。我们认为,民俗学要走向新的综合,必须站在宏观的高度,透视、剖析事物整体效应的内在联系,从而突破“思维定势”的束缚,不断诱发新见解、新观点的提出。民俗学要走向新的综合,还应当从当代社会科学最新学科和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开展跨学科研究,运用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冲破原先的民俗学格局,使陈旧的民俗学焕发青春。民俗学要走向新的综合,除了更加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思维和方法外,尤其还要注意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民俗学长期以来使用的以近代经验科学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仅仅靠搜集材料,对既有事物分别孤立地加以考察的方法,以搜集材料对民俗事象作分门别类的描述,即所谓定性方法。但由于民俗学研究对象存在于人类全部社会之中,尤其是当代知识容量不断增大,前后几代学人搜集民俗事象所积累的材料,这些对进行系统分类、保存和利用并进行新的综合研究等,都提出了复杂的难题。旧有的思维方式与认识工具便有了相当大的局限性,仅仅是搜集材料,对既存事物分门别类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够了,还需要引进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工具。如运用计量统计方法研究民俗则是一个创新。上述提到的民俗定性研究法注意点偏于事物对象之质的规定,而统计方法则偏于事物对象之数的规定。量的统计是质的基础,对质的规定提供辅佐性的论据。虽然是辅佐性的,但却往往很有力,它可以使我们对民俗事象质的分析和判断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在现代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在民俗学建设中,计量分析是民俗学走向新的综合的重要方法之一,适度地运用这个方法,可以使民俗学从封闭体系中进一步走出痛苦徘徊的“沼泽地”。
民俗学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学问,随着科学知识的扩展与学术的进步,民俗学必将得到不断丰富,传统学科的更新与新兴学科的创立、崛起,不可逆转,民俗学不仅要继承发展民俗学的合理内核,还要吸收当代其他学科的“养料”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使自己日益饱满和丰富起来。民俗文化学要发展,必须伸出两手,一手要伸向社会科学,从中汲取社会科学的模式和优点;一手要伸向自然科学,引进与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民俗学走向综合是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合与交融。学科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是当今学术发展的重要策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既要排除影响沟通与合作的非学术性障碍,又要创造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促进多样性的学术风格和多元的研究方法,鼓励学科间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借鉴、相互融会贯通。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对民俗学进行更大程度的综合的任务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每一位有志于这门学科的学者面前。
综上所述,新时期民俗学要想走出困境,对社会和学术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必须树立新的学术品格,在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民俗学研究者应该有所担当,从“历史学”转向“当代学”,将民俗研究导入当代社会,直面当下社会的变迁,从追溯原型、虚构历史,转向关心人,关心人生,关心生活,阐释社会、理解现实生活的意义。让以研究“古代遗留物”为开端的学问转向以研究当下现实社会习俗为主的与时俱进学问;让以“民间文学”、“口头传承”为主体、以“历史考据”、“原型重构”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俗研究传统,转向以“当代民俗”、“现代传媒”为主体,以“整体研究”、“综合研究”为主要方法的新民俗研究。我们深知,这种转型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敢于超越原有的学科架构和知识体系,在不断的反思中进行学术视野的拓展和理论创新。近年来,中国民俗研究开始从沉寂走向活跃,展现了学科振兴的喜人前景,这表明我国的民俗学科正处于新的重要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并预示着必将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注释
①④⑤(12)参见多尔逊编:《农民风俗和野蛮人神话》(Richard M Dorson.Peasant Customs and Savage Myths:Selections from the British Folklorists.The Un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英文版,第1-6页、第219页、第257页、第233页;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间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第14页、第17页、第5页。
②登在《雅典娜之坛》周刊第982期上,1846年8月22日出版,被收入阿兰·邓迪斯主编的《民俗研究》(The Study of Folklore)和理查德·多尔逊编的《农民风俗和野蛮人神话》(Richard M Dorson.Peasant Customs and Savage Myths)。
③参见泰勒的《原始文化》第二章“文化遗留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⑥夏洛特·班尼(Charlotte Sophia Burne):《民俗学手册》,程德祺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⑦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15-16、17-18期。
⑧⑨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载《话说民间文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6页,第9页。
⑩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间生活·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1)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文选》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
(13)(14)参见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乡民社会》(The Folk Society)载《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7年,第52期。
(15)转引自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年版,第51页。另见《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观》,蓝天出版社(纽约),1972年。
(16)(17)理查德· 多尔逊:《现代世界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载《民俗和仿俗》(Folklore and Fakelo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第33-73页,第 45-46页,
(18)(23)(24)(25)阿兰·邓 迪 斯编:《世界 民 俗 学》,陈 建 宪、彭海斌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第42页,第20页,第1-2页。
(19)(22)《民俗、神话与传说标准大辞典》(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Mythology,and Legend),纽约,1971年,第398页,第398页。
(20)李扬译著:《西方民俗学译论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1)Anthony,Giddens.“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U.Beck,A.Giddens,S.Lash,eflexive(http://www.tecn.cn).
(26)参见黄永林:《大众传播与当代大众世界——论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27)参见仲富兰:《民俗传播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447-469页。
(28)孙信茹:《传媒与民俗生活变迁——甘庄的个案分析》,传媒观察网,http://www.chuanmei.net,2002年7月4日。
(29)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371页。
责任编辑邓宏炎
2011-01-16
国家教育部、发改委211项目“中华民族文化保护、创意与数字化工程”;国家社会科学
“乡村文化建设与社区认同研究”(08BSH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