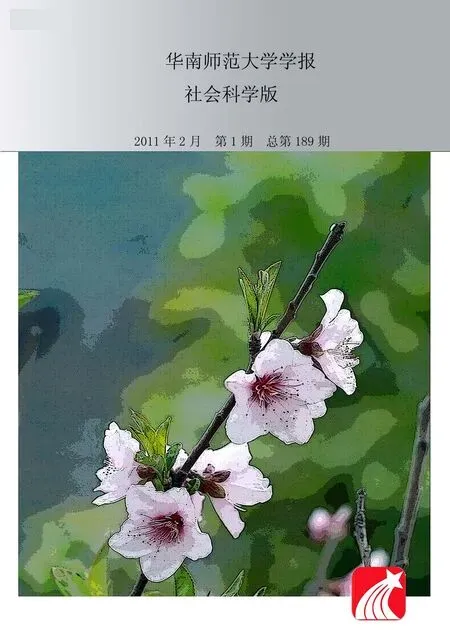宋太祖朝翰林学士述论
陈 元 锋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即帝位,定国号,改元建隆。正月,后周学士承旨陶谷迁礼部尚书,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窦俨迁礼部侍郎,学士王著、李昉迁中书舍人,皆“依前充职”。其后扈蒙、窦仪、欧阳迥、卢多逊、张澹先后入院。太祖在位十七年间(960-976), 共任用八位学士,权直院一人。他们成为由五代向宋初过渡时期的翰苑词臣。太祖创业垂统,翰林学士则为中朝文化的重建润色礼乐,草创制度。
一、重北轻南的人员结构及制度因革
太祖朝翰林学士及在院时间依次为:陶谷,建隆元年至开宝三年(960-970);窦俨,建隆元年正月至六月;王著,建隆元年至乾德元年(960-963)、乾德六年至开宝二年(968-969);李昉,建隆元年至三年(960-962)、开宝二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69-983);扈蒙,建隆三年至乾德元年(962-963)、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至雍熙二年(977-985);窦仪,乾德元年至四年(963-966);欧阳迥(亦作“炯”,下同),乾德三年至开宝四年(965-971);卢多逊,开宝二年至六年(969-973);张澹,开宝六年至七年(973-974)。其中李昉在太祖朝两入翰苑凡十年,其初拜仅三年,开宝二年至五年为直院达四年,其后在太宗朝继任学士及承旨达八年。扈蒙在太祖朝任学士仅一年余,而在太宗朝再拜学士及承旨达九年。二人政治与文学地位都是在太宗朝奠定的,因此上述二人在太祖朝学士群体中不予详论。
太祖朝学士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学士承旨陶谷,凡十一年;其次是欧阳迥,凡七年。其他人任职时间都不够长,最短者如窦俨,在职仅六月。造成任期较短的原因之一是年寿不永或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人卒于学士任上,分别是窦氏兄弟:窦仪年五十三,窦俨年仅四十二;王著开宝二年暴卒,年四十二;张澹开宝七年疽发背卒,年五十六。陶谷开宝三年卒,年六十八。欧阳迥开宝四年罢学士,亦于此年卒,年七十六。陶、欧二人是上述几人中享年较高者,亦卒于太祖朝。李昉(996-925)、扈蒙(986-915)享年亦较高,均为七十二岁,但已进入太宗朝。由此也造成太祖朝翰林学士员数较少的状况,最多时仅四员(建隆元年、三年、乾德元年),却非卒即罢。常见的为二三员,最少时为独员,如开宝六年卢多逊除参知政事出院,至开宝九年,除张澹短期权直院外,学士院均以李昉独直。
太祖朝翰林学士人员构成的突出特点是以旧朝词臣为主。陶谷、王著、李昉、窦俨、窦仪为后周学士,扈蒙为后周知制诰;欧阳迥为后蜀学士。张澹、卢多逊也分别系后晋、后周进士。其次,在地域分布上,除欧阳迥外,全为北方人。宋王朝在由北而南的统一进程中,一开始就确立了重北轻南的地域观念。这种偏见在文武大臣以及词臣的选用和科举取士中都有鲜明体现。《道山清话》详载:“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注]王日韦:《道山清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至真宗朝,河北人王旦还曾反对用江西人王钦若为相:“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注]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954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虽然太祖曾对南唐著名文士徐铉、汤悦、张洎表示欣赏[注]田况:《儒林公议》:“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铉、汤悦、张洎辈,谓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辈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但三人于开宝八年(975)方随后主入宋。即使在开宝八年、九年李昉独直学士院的情况下,三人也未曾入院任职。事实上,以中原文士为翰林学士主体的结构在太宗朝仍未被根本打破。由于翰林学士皆为文词才学之士,他们的学术、文学趣味,便会因为这一结构性的优势地位,在较长时间内对北宋前期学风、文风保持主导性的影响。
太祖朝学士院制度大体因袭五代之旧,少有更革。最值得注意的一项措置是设直院和权直院代行学士职务。《两朝国史志》载:“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阙,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注]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六引,第2519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梦溪笔谈》卷二载:“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如许敬宗为直记室是也。国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复置直舍人、学士院,但以资浅者为之,其实正官也。”[注]沈括:《梦溪笔谈》卷二,第1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宋代这一制度正始于太祖朝。《续资冶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十“开宝二年十一月戊辰”条:“诏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分直学士院。直学士院自昉及多逊始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十“开宝二年十一月戊辰”条,第23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学士年表》载:开宝六年四月张澹以左补阙、知制诰权直院[注]洪遵:《翰苑群书》卷十《学士年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后,卢多逊、李昉分别于开宝四年、五年真拜学士,张澹则于开宝七年六月卒于官。学士院直官、权直官的设置反映了王朝初期文教方兴、文学人材匮乏的客观现实。
第二项措置是建直庐。沈该《翰苑题名》序说:“艺祖受命,首建直庐。”[注]《翰苑群书》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直庐本为官署宿直之处,学士院直庐乃学士寓直待诏之所。《翰苑新书》前集卷十引《金坡遗事》云:“太祖鼎新大壮,敞金马之直庐。”[注]《翰苑新书》卷十,《四库类书丛刊》本,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云“敞”而非“首建”。按学士院机构为唐玄宗开元末设立,但在唐代似乎一直没有固定的寓直处所。周必大《奏翰苑名称札子》曰:“臣窃见唐有集贤殿书院,盖集贤殿之书院也。其后置学士院,往往因所御宫殿而寓直焉,若驾在大内即置院于明福门,驾在兴庆宫则置院于金明门,德宗尝召学士对浴堂,则又移院于金銮殿。”[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9册,第6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按此说源出李肇《续翰林志》,苏易简《续翰林志》转述之,参见《翰苑群书》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后徽宗时又曾增广直庐,程大昌《演繁录续集》卷二:“强渊明宣政间为翰林学士承旨,上为增广直庐,书‘摛文堂’榜以宠之。”[注]程大昌:《演繁录续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直庐的增设其实与制度损益关系不大,不过“直庐”一词从此频频出现在锁院、寓直的唱和诗篇中,有时也成了“翰苑”的代名词。
二 “文章无用”与翰林学士的尴尬地位
宋太祖作为创业垂统的开国皇帝,号为“艺祖”,史家也往往将宋代礻右文崇儒的局面溯源于太祖。《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云:“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木无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注]《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第12997页。但武人出身的太祖与太宗、真宗、仁宗三位“好文之主”还是有较大差异的。这从他对“读书人”以及翰林学士的态度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由武到文的转化轨迹。
关于太祖对“读书”与“书生”态度的记载颇有矛盾之处:
艺祖时新丹凤门,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对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职,国家有所兴建,即为歌颂。”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即掷于地。[注]龚鼎臣:《东原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太祖皇帝将展殿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画,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注]文莹:《湘山野录》卷中,第3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以上两条材料以生动的口吻表现了太祖鄙薄文章的武人习气,但他显然不是一介缺乏政治头脑的庸常武夫,《涑水记闻》卷一的记载耐人寻味:
太祖尝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第2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务读经书”与“不学文章”的实用主义读书观在他对武臣所使用的语境里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载:“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不过,起初“太祖与群臣未尝文谈,盖欲激厉将士之气,若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注]马永卿:《元城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但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即建隆二年),太祖就明确提出武臣读书的要求:“上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对。”[注]《宋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1页。这一转变显然使武臣无法适应,故“不知所对”。《涑水记闻》卷一亦载:“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人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注]《涑水记闻》卷一,第15页。将以上数条材料合观,太祖提倡读书的政治用意就非常明了了,即知治乱,通治道,而只有“经书”或“经史”才能提供这种效用,“文章”则是无助实用的浮文虚词。
至于太祖自身开始读书以及劝赵普读书,史籍记载颇多,从中亦可体会其良苦用心。范祖禹《帝学》卷三载:“帝自开宝以后好读书,尝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赵普为相,帝尝劝以读书。”[注]范祖禹:《帝学》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上哲宗论学本于正心》曰:“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创业垂统,日不暇给,然而晚年尤好读书。尝曰:‘宰相须用读书人。’”[注]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五,第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晩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注]《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第8940页。宋太宗撰《太师魏国公尚书令真定王赵普神道碑》载:“王性本俊迈,幼不好学,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既博达于今古,尤雅善于谈谐。”[注]《全宋文》第4册,第418页。《玉壶清话》卷二:“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注]文莹:《玉壶清话》卷二,第1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太祖与赵普的读书行为原本都不自觉,及至立国、执政以后方切身体会到读书的重要性,而其所读之书仍为“经史”。说太祖晚年或开宝以后始“好读书”,比一些典籍夸大粉饰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更符合太祖由武人到帝王身份的转变。
关于太祖“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祖训,其由来则与翰林学士有关。《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戌条”:“上初命宰相撰前世所无年号以改今元。既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阅其奁具,得旧鉴,鉴背字有‘乾德四年铸’。上大惊,出鉴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铸乎?’皆不能答,乃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仪曰:‘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上乃悟,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注]《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戌条”,第171页。孔平仲《谈苑》卷四记载了“宰相须用读书人”出处的另一个版本:“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学之士未甚进用。及卜郊乘大辂,翰林学士卢多逊执绥备顾问,占对详敏。他日,上曰:‘作宰相当用儒者。’卢果大用。”[注]孔平仲:《谈苑》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考虑到太祖尤重经史礼制以及卢多逊的博学和善于应对,这一记载也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然而一旦脱离了“经史”治国的语境,太祖对以“文章”进用的翰林学士及一般“书生”的态度就远不如对“儒臣”那么尊重了。对陶谷的使用就显示了他对文词之士的某些偏见。陶谷历仕晋、汉、周、宋,自称“七朝掌诰”[注]《篆书千字文序》,《全宋文》第1册,第18页。,但其人品不足道。《东轩笔录》卷一载:“陶谷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自汉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祸,由是缙绅莫不畏而忌之。太祖虽不喜,然藉其词章足用,故尚置于翰苑。谷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谷下。谷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注]魏泰:《东轩笔录》卷一,第5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太祖用其词章,却又毫不掩饰对这位老词臣的揶揄调侃。与陶谷共事翰苑的西蜀词臣欧阳迥则曾被太祖君臣引为鉴戒,《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八月辛酉”条载:“炯性坦率,无检束,雅喜长笛。上闻,召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刘温叟闻之,叩殿门求见,谏曰:‘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顷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相尚习此伎,故为我擒,所以召炯,欲验言者之不诬耳。’温叟谢曰:‘臣愚不识陛下鉴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复召炯矣。”[注]《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八月辛酉”条,第157页。不论太祖对刘温叟说的话是否为了掩饰尴尬的托词,但他对孟昶、欧阳迥沉溺声乐的嘲讽态度,与后来对南唐后主李煜“不能修霸业,但嘲风咏月”[注]曾慥:《类说》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而奚落其为“好一个翰林学士”[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第60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毫无二致。西蜀、南唐君臣的声色浮华确实为太祖鄙薄文学提供了口实,花间词人欧阳迥也就难以抹去其文学侍臣的痕迹。而当太祖发现吴越王钱俶以瓜子金贿赂赵普时,也大方地笑称:“但受之无害,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注]《长编》卷十二“开宝四年十一月癸巳条“,第273页。对“书生”的贬抑同样溢于言表。
总之,太祖好读书并提倡读书以及确立“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观念,乃是因政治需要而逐渐做出的改变和调整。太祖朝首辟三馆、搜求图书、开科取士等举措,也开辟了宋王朝崇尚文治的新局面,这一转变过程毕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远见。但在太祖的观念里,仍然重“经史”而轻“文章”,对翰林学士及读书人的态度轻视多于尊重。正如邓小南所说:“原本军阀习气相当浓厚的赵匡胤等人,也在‘变家为国’的过程调整着个人的意识与作风。但无庸讳言的是,如前所述,太祖对于文臣的宽和,在某种程度上恰是源于他对于控御‘书生’的自信,源于他相对于‘书生’们的居高临下的感觉。”“事实上,职业军人出身的皇帝赵匡胤与读书业儒的文臣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感。”[注]邓小南:《祖宗之法》,第167、168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因此在太祖朝,翰林学士的地位总体上说是比较尴尬的,远无在以后各朝所享有的那般荣宠清贵地位,也少有机会进入两府。
三、翰林学士之道德、文章
宋太祖对翰林学士的鄙薄倨傲,固然出于武人的偏狭,但客观地说,也与当时学士本身的道德状况有关。唐末五代之际,干戈扰攘,士大夫名节罔顾,士风颓靡,斯文扫地。太祖朝翰林学士皆系由后周或后蜀入宋的前朝文士,因此他们身上都带有五代士风的特点。《宋史》卷二六九《陶谷、扈蒙、王著、张澹等传论》概括说:“自唐以来,翰林直学士(按:应为“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对掌训辞,颂宣功德,箴谏阙失,不专为文墨之职也。宋兴,亦采词藻以备斯选,若谷之才隽,著之敏达,澹之治迹,……咸有可观。然豫成禅代之诏,见薄时君,终身不获大用(按:指陶谷)。及夫险诐忌前,酣醟少检(按:指王著);附势希荣,构谗谋己(按:指张澹),皆无取焉。蒙博洽长厚,继窦仪裁定仪制,惜乎南郊之议,请去太祖以宣祖配天,为识者所非。”[注]《宋史》卷二六九《陶谷传》,第9251-9235、9238、9238页。概要地指出了他们各自的优长与瑕疵。
综合考察太祖朝翰林学士的任用情况,仍以文学为主要条件,而其道德水平颇不一致。
太祖朝学士中文学最优者应为陶谷。他在后晋高祖时曾兼掌内外制,“词目繁委,谷言多委惬,为当时最”。“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多蓄法书名画,善隶书。为人隽辨宏博。”[注]《宋史》卷二六九《陶谷传》,第9251-9235、9238、9238页。“博记美词翰。”[注]《隆平集》卷十三《陶谷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前引《东轩笔录》卷一说“陶谷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续湘山野录》也说:“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注]《续湘山野录》,第7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他是文学、学术均有深厚造诣的学者和文人,显然并非太祖嘲讽的只会“依样画葫芦”之辈。他屡知贡举,宋初法物制度,多其所定。但他又是太祖朝操守最差的学士,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在陈桥兵变中,预拟太祖受禅文,“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在旁,出诸怀中进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注]《涑水记闻》卷一,第3页。。其次,他“奔竞务进”,“多忌好名”,“倾险巧诋,为时论所薄”。[注]《宋史》卷二六九《陶谷传》,第9251-9235、9238、9238页。。在翰苑时,与高锡、赵逢等结党,依附赵普,排挤窦仪;李昉建隆三年自学士院贬为彰武行军司马,亦系陶谷所诬。他在翰苑任职时间长达十一年而未得大用,太祖鄙薄其人品是主要原因。
王著幼能属文,有俊才,“善与人交,好延誉后进,当世士大夫称之”[注]《宋史》卷二六九《王著传》,第9241页。。但他嗜酒无度,行为放纵不检。《续翰林志》下载:“著以周世宗代邸旧僚,倍有眷注,暨世宗即大位,亦尝于曲宴扬袂起舞,上优容之,或夜召,访以时政,屡沈湎不能言。”[注]《续翰林志》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入宋后作风仍旧,乾德元年“宿直禁中,被酒,发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门求见,帝怒,发其醉宿倡家之过,黜为比部员外郎”[注]《宋史》卷二六九《王著传》,第9241页。。
张澹幼而好学,有才藻,但却被张去华指为“词学荒浅”,以校艺所对不应策问而降职。《玉壶清话》卷三载:“张去华登甲科,直馆,喜激昂,急进取,越职上言:‘知制诰张澹、卢多逊、殿院师颃,词学荒浅,深玷台阁,愿较优劣。’太祖立召澹辈临轩重试,委陶谷考之,止选多逊入格,余并黜之。时谚谓澹为‘落第紫微’,……士论短之。”[注]《玉壶清话》卷三,第31页。但太宗淳化中论及文士时曾为他鸣不平:“澹典书命而试以策,非其所长,此盖陶谷、高锡党张去华以阻澹尔。”另外,他长于吏事,“历官釐务,所至皆治”,晚年依附卢多逊而再获用[注]《宋史》卷二六九《张澹传》,第9249页。。
卢多逊是太祖朝翰林学士中唯一大拜者。这一方面缘于他的博学和文才:“博涉经史,聪明强力,文辞敏给。”[注]⑨ 《宋史》卷二六四《卢多逊传》,第9118页。他曾参与修纂《旧五代史》、《开宝通礼》等重要文献,为宋代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玉海》卷四十六:“开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注]《玉海》卷四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石林燕语》卷一:“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注]《石林燕语》卷一,第8页。据《玉海》卷六十九:“开宝四年五月,命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知制诰卢多逊、扈蒙、詹事杨昭俭、补阙贾黄中、司勋郎和岘、中舍陈鄂,以本朝沿革制度,损益《开元礼》为之。其年六月丙子书成上之,凡二百卷。《目录》二卷,号曰《开宝通礼》,藏于书府。六年四月十八日,翰林学士卢多逊又上《新修开宝通礼义纂》百卷。”则非《石林燕语》所记三人。另一方面,卢多逊的谋略也可称道:“好任数,有谋略,发多奇中。”⑨《儒林公议》 载:“卢多逊,权谋之士也。太祖尝患耶律氏据幽蓟,未有策以下之,多逊进说,愿权都镇州经画攻取,俟恢复汉土则还跸于汴,闻者异之。”[注]《儒林公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开宝四年,多逊与扈蒙修天下图经未成;开宝六年四月,多逊奉使南唐,求江表诸州图经以备修书,于是十九州岛形势尽得之[注]《玉海》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些都证明卢多逊的政治才干和智谋,但他的政治品格却不够磊落,“善伺人主意,太祖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多逊伺知即通夕阅视,诘朝问书中事,多逊应答无滞,太祖宠异之”[注]《东都事略》卷三十一《卢多逊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山诗话》载:“太祖夜幸后池,对新月置酒,问:‘当直学士为谁?’曰:‘卢多逊。’召使赋诗。请韵,曰:‘些子儿。’其诗云:‘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新开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太祖大喜,尽以坐间饮食器赐之。”[注]《后山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本,第31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是太祖朝不多见的侍从应制场景。政事能力、学术与文章水平加上善于逢迎的性格,使卢多逊极受太祖赏识,终于开宝六年由学士迁拜参知政事,太宗太平兴国初拜相,位极人臣。但他贪固权位,谗害同列,素与李昉相善,背后却在太宗面前诋毁其“不直一钱”[注]《东都事略》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与赵普不协,“在翰林日,每召对,多攻普之短”。终因赵普发其交通秦王廷美事,被追削官爵,流配崖州而卒。
与上述人物不同,窦氏昆仲则是五代至宋初以道义自守、文行兼重的儒士。《宋史》本传载:其父窦禹钧以词学名,窦氏兄弟仪、俨、侃、偁、僖后晋中相继登科,冯道赠禹钧诗有“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当时号为“窦氏五龙”。窦仪“学问优博,风度峻整”,后周广顺中为翰林学士。乾德元年,翰林学士王著以酒失贬官,扈蒙亦罢。陶谷独直,需补充学士,“太祖谓宰相曰:‘深严之地,当得宿儒处之。’范质等对曰:‘窦仪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迁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处禁中,卿当谕以朕意,勉令就职。’即日再入翰林为学士”。对其极为尊重,并屡对大臣言其有执守,欲用为相,因赵普忌其刚直,又为陶谷、髙锡党所排挤而罢。窦仪卒后,太祖闵然谓左右曰:“天何夺我窦仪之速耶!”惋惜其未能大用[注]《宋史》卷二六三《窦仪传》,第9093、9097页。。
窦俨后周广顺元年与窦仪同日拜命,分居两制,时人荣之。俨“博物洽闻,通音律历数”[注]《东都事略》卷三十《窦俨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史》本传载:“性夷旷,好贤乐善,优游策府凡十余年。所撰《周正乐》成一百二十卷,诏藏于史阁。其《通礼》未及编纂而卒。”宋初“祀事乐章,宗庙谥号,多俨撰定,议者服其该博”。有文集七十卷。就文学而言,“俨于仪尤为才俊,对景览古,皆形讽咏,更迭倡和至三百篇,多以道义相敦厉,并著集”[注]《宋史》卷二六三《窦仪传》,第9093、9097页。。可知其诗作颇多,尤长于怀古咏史,多蕴含道德主题,但今仅存《北海题渚宫》诗一首[注]《全宋诗》第1册,第157、54页。,为“对景览古”之作。窦仪亦仅存《贺李昉》、《过邠州留题》诗二首[注]《全宋诗》第1册,第157、54页。。由于现存诗歌较少,难以了解其昆仲之间或与当代诗坛唱和情况。窦仪、窦俨昆仲保持了儒学传家、道德自持的良好门风,故甚得太祖尊重,可惜均英年早卒。《宋史》卷二六三《窦仪、窦俨、窦偁等传论》将其作为宋初士风的楷模给予高度赞扬:“窦氏弟昆以儒学进,并驰时望。仪之刚方清介,有应务之材,将试大用而遽沦亡。俨优游文艺,修起礼乐。太宗尹京,偁实元僚,冲淡回翔,晚著忠谠。若其门族宦业之盛,世或以为阴德之报,其亦义方之効也。……数贤(按:本卷尚有张昭、吕余庆、刘熙古 、石熙载、李穆等人)虽当创业之始,而进退之际蔼然,承平多士之风焉。宜宋治之日进于盛也。”[注]《宋史》卷二六三《窦仪、窦俨、窦偁等传论》,第9108页。
欧阳迥是前蜀与后蜀两制词臣及学士承旨,官至宰相。乾德三年正月随后蜀孟昶入宋,八月即以左散骑常侍拜学士,时已年届七十岁,是太祖朝中原之外唯一由后蜀入宋的翰林学士。他是著名的“花间词人”,作有《花间集叙》,为中朝带来了西蜀的文采风流。欧阳迥其人,性格与王著颇为接近。《续翰林志》下载:“学士放诞,则有王著、欧阳炳。”[注]按此则见李一氓《花间集校》附录《明正德覆晁本王国维题记——录自庚辛之间读书记》,不见于四库全书本《翰苑群书》。《花间集校》,第225页。“炳以伪蜀顺化,旋召入院,尝不巾不袜,见客于玉堂之上。尤善长笛,太祖尝置酒令奏数弄,后以右貂终于西洛。”[注]《续翰林志》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欧阳炳与欧阳炯实为一人。另据《宋史》卷四七九《欧阳迥传》载:“(迥)尝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以献,昶手诏嘉美,赍以银器、锦彩。”又载:“迥好为歌诗,虽多而不工,掌诰命亦非所长。但在蜀日,卿相以奢靡相尚,迥犹能守俭素,此其可称也。”[注]《宋史》卷四七九《西蜀孟氏世家》,第13894页。可知他并非一位仅仅沉湎于花间月下、声色歌舞的御用词人,而是有一定政治责任心且能自奉“俭素”的大臣。从写作角度上说,他并不擅长制诰体文章,不是一位合格的翰林学士,但他曾模拟唐代翰林学士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讽谏时政,这组作品虽已不存,但这一现象颇值得注意。事实上,五代十国时期,西蜀与南唐、后周地区已是诗人“宗白”风尚的中心[注]本文主要关注五代至宋初之际后周、西蜀、南唐几大区域翰林学士群体之宗白现象。关于五代十国时期追踪白居易之著名诗人之多,覆盖地域之广,及其承唐启宋之流变,可参看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不妨各举一例。如陶谷后周广顺时曾作《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推尊“白傅文行”与“才美”[注]《全宋文》第2册,第19-20页。;张洎在南唐时作《张司业诗集序》,称许张籍及元、白之古风乐府[注]《全宋文》第3册,第366页。;欧阳迥在西蜀则效仿白氏讽谏诗。随着西蜀、南唐两个文学重镇相继纳入北宋王朝版图[注]西蜀、南唐亡国归宋的时间分别为乾德三年(965)、开宝八年(975),吴越钱氏政权则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朝。,江南与中原文人学士陆续汇聚于中朝,并进入太祖、太宗两朝馆阁翰苑,文学风格的整合亦成自然之势。至太宗朝,白体遂率先确立了其在由唐转宋诗史进程中的典范地位。
太祖对翰林学士的选任并未提出明确的标准,只是说“深严之地,当得宿儒处之”。经史兼通、道义与文学兼备的“宿儒”窦氏昆仲因而最受尊重,词章学术甚优而缺少气节的陶谷则颇遭鄙薄,同样品格卑劣的卢多逊因希旨善谋而获宠异,嗜酒放诞的王著被周世宗优容却遭太祖贬黜,擅长声乐词彩的欧阳迥被视为“优人”词客。总之,从太祖对诸学士的态度大体可以了解他重儒学、首德行、轻文学的用人观念。从人物代谢的自然规律看,上述翰苑学士入宋后大多已至生命的中岁和晚年,其中六人卒于建隆元年至开宝七年以前,他们对于政治与文学,已难以保持足够的热情和活力,也缺乏自觉的词臣意识和独立品格,严格地说他们尚不能称为宋代作家;而只是在五代的废墟上,为海内一统后新秩序的建立修缀礼乐仪制、连接不同区域文化的过渡性人物。新一代道德与文学兼备的高素质的词臣尚未及培养出来,人才的接替还未完成。文学的革新除弊和全面复兴,都有待于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崇文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