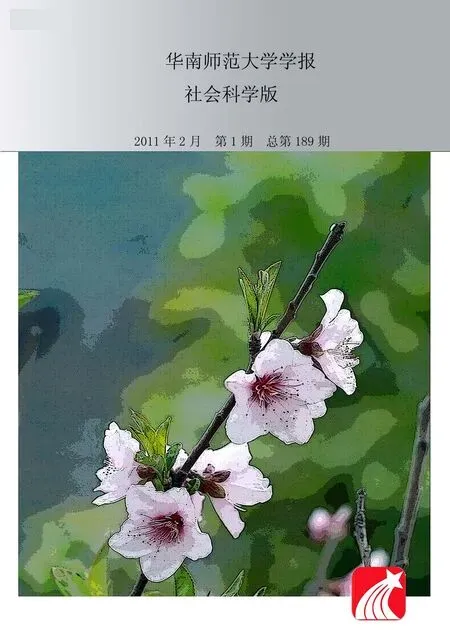“坎陷”概念起于何时?
——关于牟宗三“坎陷”概念提出过程的考察
杨 泽 波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近代以来在如何向西方学习、发展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上,很多人都提出自己的方案。牟宗三也不例外,他提出的方案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坎陷论——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但“坎陷”这一概念最早起于何时,学界则有不同说法。其中一个较有影响的说法来自傅成纶。傅成纶是牟宗三的早年弟子,在1992年山东大学举办的“牟宗三当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有一个专题发言。其中提到,1947年四五月间,他同牟宗三住在一起。牟宗三此时为思考问题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一天早上,忽然惊喜若狂,高声惊呼,“我终于把问题想通了”。据傅成纶说,这个“想通了”的问题就是“良知自我坎陷”。[注]颜炳罡:《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第87、87、8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根据这个说法,牟宗三的“坎陷”概念是在1947年上半年形成的。
傅成纶提供的这个史料有很高的价值,但学界对其可信性却常持怀疑态度。颜炳罡指出:“这个发言无疑是傅先生亲身经历的事实。不过,这个事实至今尚未发现文字材料作为佐证。因而我们断言,牟先生这时虽已出现了‘良知自我坎陷’说这一思想,但他并未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注]颜炳罡:《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第87、87、8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随后又写道:“五十年代中期,牟先生在《理性的运用表现和架构表现》一文中,正式使用道德理性自我坎陷来解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他认为,从内圣、道德理性的运用表现中直接推不出民主与科学来,因而道德理性只有通过自我坎陷,即自我否定才能成为观解理性(理论理性),从而才能成就民主与科学。由此以后,‘自我坎陷’才在牟先生的著作中盛行和通用起来。”[注]颜炳罡:《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第87、87、8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这就是说,虽然“坎陷”的说法可以追溯得更远,但作为一个概念正式提出来,特别是与科学和民主联系在一起,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郑家栋也认为,关于“道德良知自我坎陷”的理论,牟宗三首先是“在五十年代初写作的《王阳明致良知教》中提出”的[注]郑家栋:《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第31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坎陷”概念确实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而不是50年代初、中期提出来的。这可引下列材料为证。
头一则材料是《王阳明致良知教》。该书第三章名为“致知疑难”[注]后来,在写作《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时,牟宗三将这一部分作为该书第三章第一节的一个附录,同时宣称“该小册子可作废”。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卷,序言第3页,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其中明确讲到了“坎陷”问题。在该文中,牟宗三详细分析了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认为心外无物之物当然首先是指道德行为,但这并不能否认桌子椅子等同样是一种物,那么应该如何将这种物统摄到良知教当中呢?他这样写道:“吾人有行为之宇宙,有知识之宇宙。全宇宙可摄于吾之行为宇宙中,故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参天地赞化育,则天地亦不外吾心之良知。一念蔽塞,则天地闭,贤人隐。一念灵明,则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固吾之行为宇宙之盖天盖地。然而吾人亦复有知识之宇宙。全宇宙亦可摄入吾之知识宇宙中。然此必待学问而外知的万物之何所是,非良知之断制行为者之所能断制也。良知能断制‘用桌子’之行为,而不能断制‘桌子’之何所是。然则桌子之何所是,亦将何以摄入致良知中有以解之而予以安置耶?”[注]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卷,第205、206-207、208、3页。这即是说,有两个宇宙,一是行为之宇宙,一是知识之宇宙。行为之宇宙无法涵盖知识之宇宙。恰如良知能断制用桌子的行为,而不能断制桌子之何所是。如此说来,人不能仅限于行为之宇宙,而不关心知识之宇宙。客观知识不是良知天理所能给予的,要保证客观知识之形成,必须有一个渠道,否则知识之宇宙是不可能形成的。
由此牟宗三讲到“坎陷”问题:“吾心之良知决定此行为之当否,在实现此行为中,固须一面致此良知,但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此种转化是良知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此亦是其天理中之一环。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从物始能知物,知物始能宰物。及其可以宰也,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复会物以归己,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如是它无不自足,它自足而欣悦其自己。此入虎穴得虎子之本领也。此方是融摄知识之真实义。”[注]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卷,第205、206-207、208、3页。在牟宗三看来,有两种不同的知,一是良知(天心),二是认知(了别心),良知要转化为认知,其途径即是“坎陷”,即所谓“此种转化是良知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牟宗三甚至将这种“坎陷”形象地比喻为“入虎穴得虎子之本领”,意思是说,不入此虎穴,不经此“坎陷”,就得不到虎子,得不到知识。
牟宗三举“事亲”为例加以具体说明:“吾甚至且可说:即在成就‘事亲’这件行为中,同时亦必有致良知而决定去成就‘知事亲’这件知识行为。即‘事亲’固为一行为物,而同时亦为一‘知识物’。既为一‘知识物’,吾良知天心在决定事亲中亦须决定坎陷其自己而了解此知识物。此即是知什么是事亲,如何去事亲也。‘知事亲’为一知识行为,亦是良知天心之所决。而在此知识行为中,实实知道什么是事亲,则天心即须转化为了别心。是以每一致良知行为中不但有一副套之致良知行为而去了别知识物,且每一致良知行为自身即可转化为一知识物因而发出一致良知之行为而去知道这个知识物。”[注]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卷,第205、206-207、208、3页。牟宗三认为,“事亲”固是一行为物,同时也是一“知识物”。人们在成就“事亲”这一行为的过程中,同时也能成就“知事亲”这一知识行为。因为人们如果真的要将“事亲”做好,就必须了解与“事亲”相关的知识,这样一来,“事亲”同时也就成了一个知识系统。牟宗三将这种由“事亲”而成的知识系统称为“事亲”行为之“副套”。这种“副套”之形成,是由良知自我“坎陷”而成的。据牟宗三自己说,《王阳明致良知教》“写于民国四十一年”[注]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卷,第205、206-207、208、3页。。但需要注意的是,该书正式出版前,其正文曾分两部分先后分别刊载于《历史与文化》第3期(1947年8月)和《理想历史文化》第1期(1948年3月)。[注]参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卷编校说明。郑家栋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只知《王阳明致良知教》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认为牟宗三坎陷思想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此可知,至少在1947年和1948年,牟宗三已经有了“坎陷”的思想。
另一则材料是《认识心之批判》。1940年,牟宗三撰成《逻辑典范》后,开始构思《认识心之批判》,于1949年完成,1956年正式出版。该书第三卷第三章“二用格度之所函摄”也讲到了“坎陷”问题。在这一章中牟宗三指出,肯定否定之二用,本发见于纯理之自见。这一纯理之自见处即是二用之唯一出生地,所以二用才有其先验的根据。但纯理之自见必落实于现实理解活动中才能成为知识,而不能空挂。这种落实于现实理解活动中的作用,即是辩证的作用。“格度之成立是自理解之陷于辨解中而言之。理解陷于辨解中始能成知识,而陷于辨解中必有成就其辨解之格度。是以格度之立全就理解之坎陷一相而言之。此一坎陷是吾人全部知识之形成之关键,是以论知识者皆集中于此而立言,寝假遂视此为全部理解相状之所在,而不复知其只为一坎陷之相状。”[注]牟宗三:《认识心之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9卷,第610-611页。这就是说,人类知识的构成其实是理解之自我“坎陷”的过程。这个过程具体可分为四个步骤。其一是理解“坎陷”其自身形成时空相;其二是“坎陷”涌现一个因故格度,承因故格度而立范畴之运用;其三是“坎陷”涌现一曲全格度,顺此格度,运用范畴而成定然命题;其四“坎陷”涌现二用格度,二用格度只内处于四种定然命题中而连贯之使其成为一有机之发展。质言之,只有经过“坎陷”,才能形成知识。
牟宗三随后又指出:“以上所言之辩证是在认识心范围内,就认识心而言之。(坎陷之辩解与跃起之寂照俱是认识心。)尚有一种辩证,则为超越形上学中之辩证,乃顺承本心之呈露及习气执著之破除而表现,此为道德实践中之辩证。此不在本书范围内,将不论及。”[注]牟宗三:《认识心之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9卷,第612页。这一段不长,但非常要紧,因为它告诉读者,上面所说只是“坎陷”的一种含义,“坎陷”还有另外一种含义。这种新的含义的“坎陷”专就超越形上学而言,是顺承道德本心之呈露及习气执著之破除而表现的,是一种“道德实践中的辩证”。这里“道德实践中的辩证”的说法特别值得关注。它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这种“坎陷”是与道德相关的,特指道德本心的呈露以及“习气执著的破除”而言。从这一论述不难猜测出,牟宗三此时讲“坎陷”虽然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范围,但其内心其实有更为宏大的想法,直接同道德本心与“习气执著的破除”联系在一起,已经包含了后来将“坎陷”运用于科学和民主问题的端倪。尽管牟宗三此处明言,这层意思“不在本书范围内,将不论及”,但它却可以使我们明了,至少在1949年《认识心之批判》完成之前,牟宗三关于“坎陷”的思想已经较为明确,其含义也不再局限于认识论范围之内了。
“坎陷”概念地位的上升,明确运用于科学和民主问题,是在“外王三书”当中。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牟宗三开始关注历史与政治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分别收入《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之中。这三部著作学界统称为“外王三书”。《道德的理想主义》中有一篇文章名为《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在这篇文章中牟宗三这样写道:“两汉四百年,为后世历史之定型时期。一经成型,则礼俗传统,于焉形成。魏晋南北朝为混乱时期。学人思想无复儒家宗趣。此儒学之在思想方面之最[注]全集本此处“为混乱时期。学人思想无复儒家宗趣。此儒学之在思想方面之最”等字样缺失,据单行本补——引者注。暗者也。隋唐武功政略匹秦汉,而儒家思想无光彩。王通渐露端倪,韩愈粗能辟佛,李习之稍进精微。此皆以自觉之向往,而其归宗于儒术。……唐人生命原极健旺,故致力诗文,崇尚华藻,而文物制度,亦极灿烂而可观也。形上之思想无可取,而形下之文物则足以极人间之盛事。此则天资之美,生命之旺,所谓气盛言宜,有足以近道者。然气不终盛,往而不返。降至残唐五代,则规模尽丧,无复人趣。坎陷至极,觉悟乃切。宋初诸大儒,始确为儒学思想方面之复生。”[注]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第1-2页。此段中“坎陷至极,觉悟乃切”这一表述值得关注。牟宗三在这里回顾了儒学发展的过程。在他看来,儒学经过孔子、孟子、荀子、《中庸》、《易传》、《大学》以及董仲舒之后,两汉四百年已成为一种定型。其后魏晋隋唐,无甚光彩。唐人生命健旺,致力诗文,崇尚华藻,于文物制度方面灿烂可观,但形上思想无甚可取。至唐末气不终盛,规模尽失,无复人趣。“坎陷至极,觉悟乃切”,终于有宋人出来,高扬儒学,儒学才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从行文看,这里的“坎陷”乃堕落、下沉之义,特指唐人思想无力,只是尽气而行,终生乱象,乱至一定程度,迫使人们觉悟,才有了儒学新二期的大发展。这里“坎陷”的运用明显不同于《王阳明致良知教》和《认识心之批判》,内涵更为丰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出版前后有较大变化。其前身名为《理性的理想主义》,1950年元月由香港人文出版社出版。该书除“序言”外,共收入《理性的理想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与人性论》、《理想主义的实践之函义》、《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历史必然中的未来》五篇文章。其后,又增加了《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矛盾论>》、《关于共产主义者的<实践论>》、《论无人性与人无定义》等十篇文章,删去了《历史必然中的未来》一文,同时将书名改为《道德的理想主义》,1959年11月由东海大学出版。《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一文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第一版中的文章,始发于1949年。这种情况表明,至少到1949年,“坎陷”的含义已经超出了认识论的范围。
牟宗三关于“坎陷”的思想在这段时间中日渐明确。在该书《辟共产主义者的<实践论>》一文(该文最初发表于1952年9月的《民主评论》)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由希腊的审美精神转到中世纪的宗教精神,这都是向上的,其本身俱不足以形成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必须是在哥白尼、葛利略、盖伯勒、牛顿这一传统所代表的精神下完成。而这一传统所代表的精神就是以前向上浸润或向上昂扬的精神之冷静下来。这一步冷静,我们依精神之辩证的发展说,也可以叫它是一步坎陷,坎陷于‘实然’中而实事求是。所以这一步坎陷是有成果的,与堕落的物化不同。这一步坎陷,从心灵方面说,不是向上求清净解脱,而是转为冷静的理智向下落于实然中以成对于外物的理解。从其所理解的外物方面说,必须把属于质的完全抽掉,而只剩下量的。这就是科学的化质归量。因此,这一步成科学的坎陷精神,就是一步量化的精神;其成就科学的主要原理就是:数学与经验的合一。”[注]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第120-121页。牟宗三认为,西方科学精神并不来自其审美精神和宗教精神向上之浸润或向上之昂扬,而来自于这种精神自身之冷静。只有从审美精神和宗教精神中冷静下来,才能转出理智之精神,转出自然科学,而这种通过“冷静下来”转出科学的方式就是“坎陷”。
在1953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当中,“坎陷”概念的内涵更为清晰了。牟宗三这样写道:“其为一曲折,当观其精神是否向上,抑向下。……精神不能一味守其孤明,不能不落实而外用。惟在落实而外用中,始能转现实而构造之。然此必有仁义悃诚之本,即所以提撕之者,而后始可谓为精神之外用。此种外用,名曰精神之冷静,亦曰精神之自觉的坎陷,即转为理解。然本无此本,则只是外驰而下落,亦即是堕落。精神在此种堕落下,遂不见其为精神,而只见其为物化。是以其所有之措施与成就,亦可转语谓之为在物化中而带出。如此而带出,俨若为构造的,实非为真正的构造也。其精神之本已失(故流于薄),故其智之外用(所谓堕落物化),所投映之号召曰富强、曰功利、曰耕战。……秦之富强以此,其大败天下之民亦以此。”[注]牟宗三:《历史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第156-157页。此段出自《历史哲学》第二部第三章,该章是由在1953年3月1日《民主评论》发表的《秦之发展与申韩》改写而成的。在这里,牟宗三讲到精神发展的过程。在他看来,精神不能一味守其孤明,同时也必须落实而外用。精神的这种外用,就是一种曲折,而“此种外用,名曰精神之冷静,亦曰精神之自觉的坎陷”。这里由精神发展的曲折讲坎陷,讲精神之外用,精神之冷静,这些都是“坎陷”这一概念最为重要的内涵,说明此时“坎陷”已经成为一个专用概念了。
《理性之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一文正式发表于1955年10月(后来该文收在《政道与治道》之中)。该文讲“坎陷”的意思更为明确:“它所要求的东西必须由其自己之否定转而为逆其自性之反对物(即成为观解理性)始成立。它要求一个与其本性相违反的东西。这表面或平列地观之,是矛盾;但若内在贯通地观之,则若必须在此一逆中始能满足其要求,实现其要求,则此表面之矛盾即在一实现或满足中得消融。而此实现是一‘客观的实现’,如是则即在一客观实现中得消融。由此一消融而成一客观实现,即表示曲而能通。即要达到此种通,必须先曲一下。此即为由逆而成的转折上的突变。如果我们的德性只停在作用表现中,则只有主观的实现或绝对的实现。如要达成客观的实现,则必须在此曲通形态下完成。如只是主观实现,则可表之以逻辑推理;而如果是曲通由之以至客观实现,便非逻辑推理所能尽。此处可以使吾人了解辩证发展的必然性。辩证的表明,在此处非出现不可。”[注]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卷,第63页。道德是主观的,民主是客观的。要由道德之主观转为民主之客观,必须对道德有一种转变,有一个“逆”的过程、“曲”的过程。这种“逆”和“曲”,就是要求一个与其本性完全相反的东西,达成一种“客观的实现”。这种“逆”和“曲”有其“辩证发展”的必然性,在这个地方非要出现不可。此段所说的“逆”、“曲”、“辩证发展”,都是“坎陷”概念最为重要的含义。此处牟宗三通过“坎陷”解决开出科学和民主问题的意图已经非常清楚了,而“坎陷”概念此时也已完全成熟。
通过上面的分析,“坎陷”概念的提出过程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王阳明致良知教》和《认识心之批判》,至少从《认识心之批判》看,这一概念已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了。在1949年发表的《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一文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而在1952年至1953年发表《辟共产主义者的<实践论>》、《秦之发展与申韩》,以及1955年10月发表的《理性之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等文章中,这一概念的内涵已完全成熟,直到晚年用之不辍。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傅成纶关于牟宗三“坎陷”思想产生于1947年上半年的说法是基本可信的,而学界一般将其归为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做法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