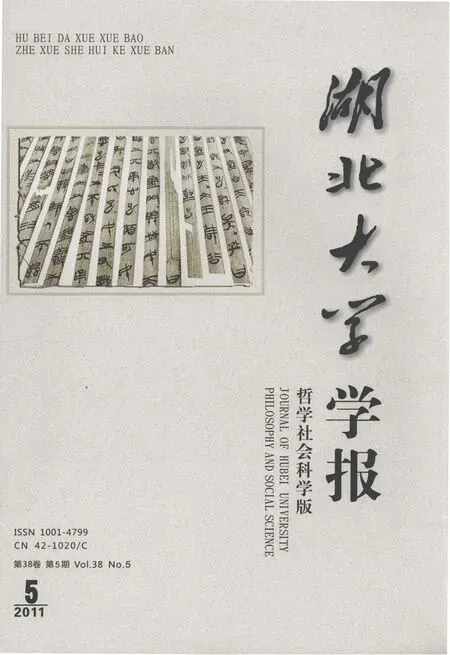新道统论法哲学与现代中国法学的兴起
魏敦友
(广西大学法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新道统论法哲学与现代中国法学的兴起
魏敦友
(广西大学法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现代中国的知识场域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其深刻性之根本要义在于,我们正在迎来一个以法学为新的知识轴心时代。从中国思想的长程历史视角来看,这个法学时代将是继子学时代(先秦)、经学时代(秦汉至两宋)、理学时代(两宋至晚清)之后的第四个知识轴心时代。现代中国法学知识的创建,虽然当下在很大程度上要以西方为借镜,但是从根本上说,又必将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为依归。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道论的基本观念之上的,因此现代中国法学的建构必然在充分吸收西方法学的营养的同时回归到道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展示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创造力。新道论法哲学正是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法学知识时代的到来进行奠基的思想系统。
新道统论;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理学时代;法学时代
一、问题意识:一个法学的时代正在到来
当代中国,法学已经成为时代的“显学”,如果说80年代文史哲还是时代的中心话题,那么今天,文史哲在当代中国正在退居幕后,法学则逐步进到前台,成为当代中国知识的重心或中心。这一点当然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法治转折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令我十分讶异的是,中国法学知识出奇地浅薄,在当代中国法学场域,似乎很少有人对中国法学本身作反思性的思考,只是满足于将西方的法学移入中国,因为在人们看来,西方的法学是具有普遍性的品格的,中国要实现法治,只有移植西方的法治,别无他途。当下中国在知识论上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个知识论的“轴心时代”的典型特征是以法学为中心而建构起来的学术或思想体系。对中国学术而言,法学时代之所以能被命名为一个全新的知识时代,乃是因为它完全有资格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理学时代相并立。
我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看法,在学术资源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我综合了并改造了冯友兰、钱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冯友兰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将中国哲学史分成两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为子学时代,第二个时代为经学时代。我从这里得到启发,但我同时认为,仅仅将近3000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区分为两个阶段是有问题的,因为很明显,宋明理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类型是不同于经学这种知识类型的,它强调的是“事物之理”,而不再是“文本之经”,所以论说的权威性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理学从经学中区分出来,把理学看成是一种有别于经学的一种全新的知识类型。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想到,我们当下的知识状况如何呢?很显然,我们要深入地勘测我们的知识状况,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我们的当下知识构成与理学知识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一般地把我们的知识归结到理学这种知识类型上去,因为很有可能,我们正处在理学知识的末端,却在一个新的知识类型的起点处。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之下,结合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变革,我终于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从长程的知识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正在终结它的理学阶段,而进到它的法学阶段。这样一来,我认为中国学术思想实际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理学时代及法学时代。子学时代的意义在于形成中国思想的基本范型,我认为就是中国延续久远的道论思想,它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如古希腊的理念论思想、印度的出世论思想等。而经学时代、理学时代及法学时代可以看成是道之三种形式,在历史上则表现为三个阶段。这就是我所悟到的中国3000年道之三变的基本理路。作为知识人和学术人,作为思想者,我们的使命就是彻底终结理学的知识时代,而自觉地进到一个全新的知识轴心时代,即法学时代。
其二,我之所谓知识轴心时代的看法显然来自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启发,同时也参考了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著述。雅斯贝尔斯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从比较文明史的视角对人类不同的文明起源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核心观点。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500年前后看成是人类的一个轴心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不同的民族如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14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文明轴心的观点极富启发性,它为我们平等地看待不同的文明类型提供了极好的思维框架。但我同时认为,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为我们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观念出发,很有可能看不到同一类型的文明在不同时期的重大变化,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雅斯贝尔斯的文明轴心观进行了重大改造,我认为不仅不同的文明类型在最初的起源上有重大的不同,而且同一的文明类型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在性质上有重大的不同,因此会形成新的轴心时代。另一方面,我将雅斯贝尔斯的文明轴心观转化成一种知识轴心观,用以观察中国学术知识演化的内在逻辑。通过雅斯贝尔斯的文明轴心观及我自己对它的改进,我认为中国学术思想实际上存在着四个轴心时代。所谓的子学时代,可以看成是中国思想主体性形成的时代,道论的基本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的本质性之规定。经学时代、理学时代及法学时代,都可以看成是在道论思想的延长线上之思,但它们同时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在问题意识、思想方法、概念范畴及学术体系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可视为不同阶段上的知识论意义上的“轴心时代”。
经由上述认识,那么我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长程历史的视角来看,对中国来说,从本体论上讲,一个法治的时代正在到来;而另一方面,从知识论上讲,一个法学的时代正在到来。可以预料的是,正如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与理学时代都曾经支配了千年的中国学术思想一样,当下中国正在建构的法学时代,作为一个新的知识轴心时代也将会支配千年的中国学术思想。
作为知识人、作为学术人、作为思想者,我们要自觉地投身到作为一个知识轴心时代的法学知识的建设之中去,从而使得这个法学时代真正成为中国知识史上的一个名符其实的知识轴心时代,真正有资格与中国知识史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理学时代相并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法学知识时代的到来,可以视之为中国文化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复兴或重构。
二、知识脉络:重建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
然而,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知识轴心时代的法学时代的深度开启并不是一件轻松之事,如前所述,百年来的中国法学,作为当下中国思想界思考中国法治转型的主要力量,却因为满足于移植西方的法治与法学而缺乏对自身知识状况的自我意识,因此而无法引领中国法治的进程,更无法完成开启法学时代的重大使命。这很使我想起庄子的话。庄子有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法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2005年,时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邓正来先生发表著名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对中国法学的“不思”状况进行了彻底的发人深思的批判,他深刻指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而无力引领中国法制/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实是因为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我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由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中国法学总体性的‘范式’危机。正是根据这一结论,我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2]13
可以说,邓正来教授的上述论述为当代中国思想家指明了思想的道路。其基本的精髓就是从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强支配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品格。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无原则地回到中国古典思想,以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儒家或道家思想自娱,无视当下中国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结合自己对当代学人邓晓芒与邓正来思想的研究,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两邓律令”,其一是邓晓芒律令,它要求人们从一种对中国古典思想的迷恋中走出来,其中心主题为“离母”;其二是邓正来律令,它要求人们从一种对西方思想的依赖中走出来,其中心主题为“弑父”。因此,我认为,“邓晓芒律令挡住了一切试图无条件回归中华古老传统文化的可能性,而邓正来律令则挡住了自五四以来一切唯西人马首是瞻的可能性”[3]3。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基本原则即“弑父离母”。
当然,所谓“弑父离母”只不过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转换成现象学的说法,则可以说是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将中国古典文化以及当代西方文化统统放置到括号之中去,进而发现最基本的剩余,即不可能再还原的东西。不可再还原的东西是什么呢?可能人见人殊。不过对我来说,那不可还原的剩余就是作为中国文化本源的道,如前所述,这个道是子学时代最伟大的创造,它所表征的乃是人参与其中的整体世界的生存秩序之建构,它强调人的创造性、能动性与主动性,同时强调这个世界的历史性、人间性、圜道性(循环往复性)与整体性[3]199~204。正是如此,我明确提出重建道统的主张,即将当下中国的法学知识纳入到道论的框架之中去解读,去阐发、去创生。唯其如此,法学知识的建构一方面可面向当下中国现实的一个理论建构,而另一方面又获得了中国文化的内在魂魄,因此法学则一如此前的子学、经学与理学一样,能成为中国文化新的道统。这就是我讲的所谓新道统论的基本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之所谓新道统论正是在为现代中国法学奠基,而现代中国法学的真正形成,则是中国文化之新道统形成的真正标志[4]。必须承认,我之所谓新道统论还有待进一步发挥与展开,但是它的基本思维取向则是十分明确的。首先,它将对中国思想内在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形成现代中国思想的自我意识。如金观涛指出:“至今人们对中国式现代观念本向仍是盲目的,缺乏反思意识的;对中国文化深层思维模式如何重构现代观念,缺乏应有的研究和清理。”[5]22的确,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深层思维模式的建构并对现代观念的深度研究,新道统论是提不出来的;其次,它必须明确自己的思想境域。在中国现代思想包括法学思想的出场的背景方面,可以说,经过100多年的思想沉淀之后,中国思想界已获得基本共识。如老一辈学者王太庆指出:“如果不了解印度佛学,就无法设想宋明理学和道学的出现,如果不了解西方哲学,也就无法设想中国今天出现什么样的新哲学。”[6]778如孙国东博士指出:“考虑到中国文化最终征服佛教花了上千年时间,中国文化容纳西方文化的时间恐怕要更长。佛教传入如果从东汉初年(约公元1世纪)算起,到宋明理学成熟并获得官方认可(以朱熹获得嘉定谥号的1209年算起),其实经历了1100多年。西方文化的传入如果从利玛窦进入中国(1582年进入澳门)算起,迄今不过400年时间。也许再过几百年之后,中国会出一个像朱熹那样的大思想家,但至少目前,我们恐怕更应当保有宽容、谦卑的心态多向西方学习。”[7]最后,新道统论呼唤法学时代的知识英雄。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位特大思想家:孔子、董仲舒、朱熹。”[8]3他们正好对应我所讲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与理学时代,因此是各自时代的知识英雄。人们常常感叹近世以还,中国没有产生世界性的思想家,从新道统论看来,这是因为中国还处在理学的末端之故,西方的思想借理学的名义进入中国,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就是西学进入中国思想的表现,从而成为理学的最后的余波,或最后一抹晚霞,在这个时代是产生不了世界性的思想家的,只有当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真正进行法学知识的创造的时代,中国才可能出现世界性的思想家。如李泽厚所说,“当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的时候,正如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笛卡尔、帕斯噶、巴尔扎克,德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思、海德格尔,俄国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中国也将有它的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巨人出现。”[9]341不过,和孙国东博士比较起来,我要乐观得多,我不认为中国出现朱熹那样的大思想家要再等几百年的时间,今天资讯的发达,以及专业化的发展,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消化要远比当年中国人消化佛教来得迅速,因此在我看来,近百年的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我之所谓的第四位特大思想家,而我们当下的学术工作则正是为这第四位特大思想家的出现作准备。
三、为学方法:走出概念规范主义泥淖
新道统论之建构,不仅需要明确的问题意思与清晰的知识脉络,而且还需要有细致的为学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倡一种新研究方法,我称之为答案-问题反溯式的研究方法,以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盛行的概念-现实向下式的研究方法相对。
当下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盛行的研究方法是概念-现实向下式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根本特点是概念规范主义,其基本表现是从概念出发,却并不对概念进行反思批判,就用概念来规范现实,而当现实反抗概念的规范时,人们就对现实肆意加以指责。这里所说的概念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对西方思想的翻译,另一方面是从中国古典思想那里获得的,但却是对西方思想的比附,可以看成是对西方思想介入中国现实的一个补充。所以从总的思想格局看,以前者为主导。这一研究方法支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形成过程中之一种独特的现象,我将它看成是中国现代思想形成的一个必要的阶段,但是现在是到了走出这一阶段的时候了,不走出这一阶段,中国思想就露不出它的头角。
但是要真正走出概念规范主义的泥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我们沉潜反复,慎思明辨。正是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之下,我提出了有别于概念规范主义研究方法的另一种研究方法,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答案-问题反溯式的研究方法。如果说概念规范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独断论的话,那么我现在倡导的这种研究方法的根本之处在于它的反思性,即它能充分意识到概念的有限性,从而在批判中敞开思想的空间并建构新的学术知识体系。
答案—问题反溯式的研究方法由一个基本假定和三个前后相联系的具体操作环节所组成。一个基本假定指的是,在它看来,任何知识/概念都是有限度的,它既展示同时也遮蔽。我们不仅要看到知识/概念展示事物的一面,我们更应该看到事物被遮蔽的另一面。因为只有揭示事物被遮蔽的另一面,我们才能深入认识概念的有限性。对知识、概念的遮蔽性,我国古人是有清晰的意识的,如庄子所讲:“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庄子·逍遥游》)邓正来说:“范式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思考什么,而更在于引导人们不去思考什么。”[2]55充分意识到知识/概念的有限性,就能使我们从一种知识的独断立场中解放出来。
答案—问题反溯式的研究方法还包括三个前后相联系的具体操作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正当性祛魅。这一观点我是从邓正来对正当性的批判中获得灵感的。邓正来这样说:“那些研究西方问题的西方现代知识,不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运动中具有着某种支配性的力量,而且在特定情势中还具有了一种赋予它所解释、认识甚或描述的对象以某种‘正当性’的力量,而不论这种力量是扭曲性质的,还是固化性质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那些所谓‘正当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其本身也许并不具有比其他性质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正当的品格,而完全有可能是透过权力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更有可能是通过我们不断运用某种‘知识系统’对之进行诠释或描述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2]100我受到韦伯的启发,把邓正来所认识到的将某种正当性视之为唯一正当性的知识批判概括为正当性祛魅,其基本要义乃是一种态度或观念的变化,从而使思想从一种板结的僵硬状态过渡到一种可反思可争辩状态。比如说,象科学、民主与法治这样一些概念,作为关乎当今人类生存甚至命运的知识承诺,在概念规范主义研究方法那里,是不对它们进行置疑的,也不可能进行置疑,然而,在答案-问题反溯式的研究方法这里,它们却必然是可疑的,并没有自然的正当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第二个环节是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因为光有正当性祛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追问,这就过渡到问题化的理论处理阶段。“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这个观念我取自于邓正来,但我比邓正来更具体,因此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其根本要义是将每一个概念都看成是一个答案,既然是一个答案,那么必有一个问题隐藏其后,于是将这个隐藏其后的问题揭示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将这个隐藏其后的问题揭示出来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会发现已有的这个答案不过是许多答案中的一个,它并不是唯一的答案,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思想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最后,第三步,我们可以就所开放出来的各种答案进行比较,从而根据当下的现实进行选择。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民主,人们并不将它视为某一个问题的答案,只限于独断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10],或,“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11](蔡定剑),这就不是将民主看成是一个答案了,而仅仅看成是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了。问题在这种独断的思维方法中消失了。问题化的处理方式反是,它将民主视为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通过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考究,我们发现,其背后的问题是:谁统治?核心在于统治权在谁之手。显然,这个问题其实有不同的回答,而民主只是其中之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民主之外,还有许多的方式,如君主统治,如贵族统治,等等。更进一步,谁统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超验的非历史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具体历史场境的问题,因此谁统治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中是有不同的答案的。这意味着,如果不对像民主这类从西方传来的概念进行问题化的理论处理,我们无法使我们的思想获致思想性的品格。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思想形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西方知识的全面引进,我认为,这一个持续百年的知识引进运动应该终结了,然而要彻底终结中国思想对西方思想的盲目引进,就必须对经由翻译而产生的许多西方式概念,如民主,如科学,如法治,如人权,如正义,如平等,等等,分门别类地进行问题化的理论处理,将中西思想对接,并由此融合产生一系列新的基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中国思想。
第三个环节是“大而化之”的思想建构。这个观念我取之于孟子。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中一个伟大的思想,为西方思想所无,它可以用来帮助我们今天如何具体地对待西方思想。中国思想今天面临西方思想的强有力冲击,其实这是中国思想之福。因为中国社会面临重大转折,中国思想负有提供转折之路向的历史使命。而中国思想之所以为中国思想,有两个根本的特征,其一是化,其二是大。别人的思想只有经过了我的消化与吸收,才能成为我的思想,从而进一步滋养我,丰富我,提升我。但另一方面,我之有能力消化并吸收他人的思想,则在于我之大,唯其大,别人的思想才有进入我之可能性。更进一步说,中国思想其化其大的根据则在于其道论的内在规定性。因为道,所以必然有路。如钱穆先生说:“我们中国人最普通最重要是讲一道字。道是一条路。我们人生应该跑的那条路,就叫道。那条道不该只求知,更贵在行。”[12]406据此我有信心认为,在中国思想的大道上,我们曾经跑出了子学之路,经学之路,也跑出了理学之路,那么在今天,我们一定能跑出法学之路。
四、结语
以上我对我之所谓新道统论的问题意识、知识脉络及为学方法三个方面作了一个简要阐明,试图从总体上展示新道统论作为一种现代中国法哲学思想所内蕴的时代背景及理论纵深开拓的力度。
从总体上讲,新道统论作为对理学知识形态的克服,它将扬弃新旧理学所认肯的必然性、客观性、历史规律性等等范畴,而通过法律世界的建构,让人从必然性、客观性与历史规律性种种桎梏之下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世界,让人们重新看到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能动性。我们知道,“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钱穆先生解释说:“若没有人的活动与行为,即就没有道。既如此,道何能来宏大人,只是人在宏大道。浅言之,道路是由人开辟修造的,人能开辟修造一条便利人的道,故说人能宏道。但纵使有了这条道,若人不在此道上行,则乃等于没有这条道,而这条道也终必荒灭了。所以说非道宏人。惟其如此,所以既说宏道,又说行道、明道、善道。总之,道脱离不了人事,脱离不了人的行为与活动。没有道,可以辟一条。道太小,可以放宽使之成大道。道之主动在人。”[13]9这段解释真是精辟之至!
[1]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4]魏敦友.新道统论为现代中国法学奠基[N].检察日报,2011-01-16.
[5]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6]王太庆.柏拉图对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孙国东.文化认同与道统重建——一种基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历史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8]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0]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N].学习时报,2007-01-05.
[11]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N].南方周末,2010-11-22.
[12]钱穆.晚学盲言: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3]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北京:三联书店,2002.
D90-05;B21
A
1001-4799(2011)05-0127-05
2011-06-05
魏敦友(1965-),男,湖北仙桃人,曾任教于湖北大学,现为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法哲学研究。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