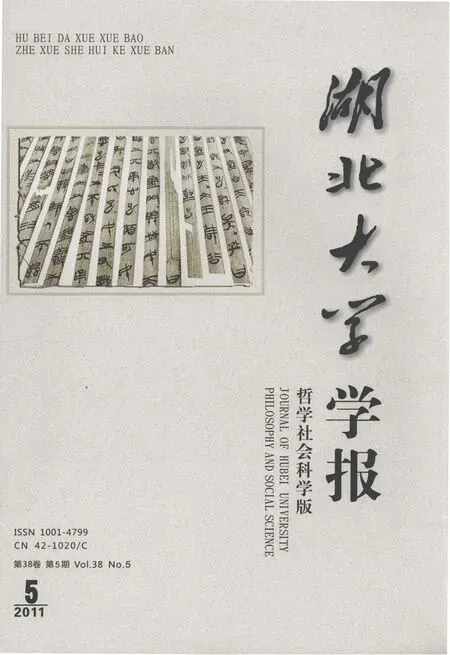辛亥首义:第一枪与第一功
陈家琪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
辛亥首义:第一枪与第一功
陈家琪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
围绕辛亥首义第一枪、第一功的荣誉争夺看似清楚,实则迷离。这种状况,印证了孙中山1912年辞去大总统后在武昌这个首义之地所说的一番话:“其真理约分二宗,首曰政治,次即言论。言论者,发自团体,以补助政治者也。”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为什么革命来革命去,社会生活的“内骨子是依旧的”呢?无非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革命者心中,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而已,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
辛亥首义;第一枪;第一功
冯天瑜、张笃勤合著的《辛亥首义史》(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是一本巨著,将近85万字的篇幅,上百幅图片、照片,构成了对辛亥首义从远到近、从粗到细的全景描画。书好读,场面逼真,人物如生,笔端流淌着激情,叙事投射出慎思,说是只讲辛亥首义,其实百年历史的走向脉络、端倪气象尽在其中;一口气读下来,冯先生近年来对于有关“封建”一说传统谬误的辩正(见其《“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关现代汉语之文化内涵的来由(见其《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早已化为这本书的内涵骨架。
1978年我参加“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面试,走出考场,就直奔“红楼”(湖北咨议局——湖北军政府旧址),就是为了看看辛亥首义的地方。当时尚不知能否被录取,觉得哪怕不被录取,看了“红楼”,也不枉武汉之行。以后在武汉生活了18年,每有来客,大多也是陪游“红楼”,前前后后少说也去了十多次,差不多每去一次在感觉上必有所触动。后来与冯先生同在湖北大学共事,知道他对中华元典精神多有独到见解,其中也包括对辛亥革命史迹的收集整理,出了几本关于“武昌首义”的书。看了这本书,才知自童年起,作者就生活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旧址旁,上初中时必过“黄克强塑像”,读高中又需行走于彭刘杨路、阅马场一带。他家有一位老邻居谢家家,曾在黎元洪府上帮佣,言语间多称“都督家”或“副总统家”,而家对面的“李太太”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汉俊的夫人,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乃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创始人之一,阳夏战争期间任黄兴的参谋长。而另一位耿伯钊更是民国孙中山总统府的军事秘书长兼大总统顾问。1957年,这位“耿秘书长”因建议中共应加强法制建设而被打成“极右派”,受到猛烈批判,再不见过去印象中挺拔的身板、执手杖和黑色氅篷。作者说:“如果说,少时的我只看到耿氏风仪整竣的外观,那么,时下阅读耿氏辞世前几个月的谈话记录,方得见民主共和精神在一位辛亥老人心中闪耀。”[1]649
关于辛亥首义,可说的事太多,最让我不能释怀的倒还是作者对首义中“第一枪”和“第一功”的考证、梳理、论述。
一、辛亥首义第一枪
“第一枪”可以笼统地讲,比如“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满清统治的第一枪”,也可以具体为“1911年10月10日的第一枪”,更可以再具体为“是夜,城内工程第八营率先打响第一枪”。但具体到人,这“第一枪”到底是谁打的,打向了谁,今天还说得清楚吗?这不仅只是一个史实的考证问题,它会让我们想到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比如“历史1”(历史上真正发生了的事)与“历史2”(史书上的有关记载,没记载的自然也就无法进入历史)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本书对“第一枪”、“第一功”的考据,也不得不纠缠于历史真实与文字记载之间,而且,它本身就可视为“历史3”,是我截止目前所相信或所愿意相信的“实史”。再比如“长时段”与“短时段”的关系,就“长时段”而言,涉及我们对整个中国在未来走向的整体设想:是不是“革命”就只有“枪杆子”这一条出路?枪响处人头落地,有了这“第一枪”,以后又会有多少“第一枪”?就“短时段”而言,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有关“民族国家”的意识(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在当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这一诉求,在开始时并不一定非要开枪。再比如“猝发”(第一枪)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比如人死不能言,而活人又会受到各种名利诱惑,以为世人皆浑浑噩噩,不会探一究竟,于是便以讹传讹,造成既有事实,如此等等。
有关“第一枪”的考据在第四章“武昌起义”,第三章写的是“革命时机成熟”。而就“成熟”论,先要说“清朝预备立宪及立宪派的活动”。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革命往往爆发在“清朝已经开始了立宪活动”的前夜。
清末的立宪运动是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之后的第三波改革进程。一方面是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江苏的张骞、四川的蒲殿俊、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等等,另一面就是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奏请十二年后君主立宪,行宪政,非如此不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于是,1905年10月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美欧考察政治;1907年清廷诏令各省筹设作为省议会雏形的咨议局;1910年1月中旬,各省咨议局代表32人聚集北京,成立“国会情愿同志会”,呼吁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获得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等人赞同;清政府在各方压力下最后同意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国会未开之前,先厘定官制,设立内阁;1911年5月8日,清廷终于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任协理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内阁大臣13人中,满族贵族占9人,而其中皇族又占5人,于是引起咨议局议长议员四十余人的更大不满,认为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之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1911年6月,立宪党人组成宪友会,汤化龙、谭延闿等发布“宣告全国书”,认为“希望绝矣”,“救亡之策穷矣”,表示只有另寻出路。
这也表明清朝末期,正是一种种族上的特殊的利益集团(满族贵族)才使得民族国家的诉求具有了某种特殊的难度(当然,任何一种利益集团的构成与维护都会有其特殊理由,于是也就有了相应的不得不的难度,这里面真正需要的就是那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想象),最后终于走到不得不打出“第一枪”的地步。
这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它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三点启示,一是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反复说过的,尽管路易十六是旧王朝中最繁荣的时期,但这种繁荣恰恰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丧失了民心(政权合法性)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发生在它已经开始改革而且使改革取得成就的时刻;其二,就是全社会悄悄弥漫着的不满现状、不耐等待而又丧失前途的情绪与气氛;其三,就是文化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往往会迫使文化人不得不走向企望国家保护或强权支撑的不归之路,于是文化上的“希望绝矣”也就与政治上的“救亡之策穷矣”混搅在了一起。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第一枪”的话题。
据冯、张二位先生考证,真正率先开枪击毙清方军官的是一个名叫程正瀛的兵士。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0月10日傍晚,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带护兵二人查铺至六棚,忽见六棚正目金兆龙荷枪实弹,大惊,直前欲夺金兆龙枪,金大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湖北鄂州人程正瀛率先开枪,击中排长陶启胜,接着又开枪击毙军官多名(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工程第八营营长阮荣发),全营震动。
关于这件事的原始记录见工程第八营共进会代表熊秉坤事后交湖北革命实录馆的四篇文字,其中《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详尽记录了起义前后的经过,表明当清方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与二排正目金兆龙发生正面冲突时,共进会员程正瀛率先开枪击中排长陶启胜,然后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此即“首义枪声”。总之,熊秉坤于辛亥首义一年间,应湖北革命实录馆征集文献的要求,先后提供了四份书写认真、内容详实的材料,所有叙事均完全一致,即10月10日晚打响“第一枪”的是一位名叫程正瀛的兵士。枪响后,熊秉坤方下楼吹哨集合,率队抵达楚望台军械库。
然而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辛亥武昌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的意义越来越重大,熊秉坤关于工程第八营起事的经过在表述上也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1914年7月,熊秉坤在日本东京加入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当即指着熊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再在上海《晨报》上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至此,“熊一枪”之说由此鹊起,以后居正等人也力倡“熊秉坤第一枪”说。
请注意:这里的前提是熊秉坤加入了孙中山在同盟会外重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也许这在许多人看来并不重要,因为同盟会之外毕竟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但也许在某种情况下又很重要,很有意义,因为它涉及到“第一枪”在不同组织间的归属,是一种荣耀与资本。
这里面明显有着对“第一枪”的荣耀与资本的争夺。
再以后,熊秉坤本人也改口,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50年代发表的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章中,也与他1912—1913、1918年的记述大相径庭,说打响“首义第一枪”的就是他熊秉坤:他在楼上巡查,见二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即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这就是“熊一枪”的由来。
而真正打响第一枪的程正瀛则于1916年在党人内争中被贾正魁处死,沉入长江。
熊秉坤身为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但“第一枪”却非由其打出,这一事实订正,至少告诉我们:时间距离越远、当事人越多不测,后来者越为名利所累,事实真相也就越为模糊,距离“实事”也就可能越来越远。
特别是程正瀛之死,实乃党人内争(原因不详),他之沉没长江,在象征的意义上,至少具有一种让人们永远忘记或者再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打响了“辛亥第一枪”的意味,这更免不了使人唏嘘怅然。
二、辛亥首义第一功
“第一功”一说出自黄兴的一首诗。
1911年10月初,四川保路风潮达到高峰,盛传成都为革命党人所得,黄兴十分振奋,写了一首喝和谭人凤(号石屏)的七律,诗称:
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趁拜敢称雄。
第二年,也就是1912年10月,黄兴又以此诗中“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之句题赠武昌首义参加者吴醒汉,以此表明他在武昌首义前就对武汉起事的期许。
这里面透漏出的问题就更多了,与前面提到的对“第一枪”的归属争夺一样,这里也涉及到在有关武装起义部署上,以内地,特别是两湖为代表的一帮革命党人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帮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或不同思路。
就到底应该在哪里打响“第一枪”的谋划而言,黄兴其实一直追随着孙中山。但他作为湖南人,又明确知道两湖一带的革命党人想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起事的意图,所以当武昌打响了“第一枪”后,他就以自己当初的诗句(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来印证自己的“预见”。
打响“第一枪”的人是谁(哪个组织)的人,荣耀也就归于谁(那个组织);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在哪里,此谋划的“第一功”在理论上也就应该属于谁(哪个组织)。
这种“预见”,同时也就表明了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概括而言,这种矛盾或思路的不同至少涉及到如下10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1907年3月,孙中山与黄兴在关于同盟会的旗式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此次争论几乎导致二人就此决裂。孙中山坚持同盟会应沿用兴中会、也就是第一次广州起义时的青天白日旗,以此确立兴中会在同盟会中的正统地位,也就借此巩固提高了孙在同盟会中的领袖地位。而在黄看来,孙的坚持实在大可不必,因为他既不争名,也不谋利,“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他认为同盟会的旗式应该是井字旗,以远古中国的井田制来表示同盟会的平均地权之意。在这场争论中,不仅黄兴的湖南同乡宋教仁站在黄兴一边,就是一直紧跟孙中山的胡汉民也认可黄兴的宽厚揖让之风。
第二,同年3月4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南洋,他随身携带了日本股票商赠送的8000元(共10000元,其中2000元留给主办《民报》的章炳麟等人,他们办报经费困难,自然嫌少),后又得日本政府赠送的5000元路费。所有这一切都使章炳麟、谭人凤、张继等人大怒;到1908年9月,陶成章更是因在孙中山、胡汉民等处筹款不着,觉得他们心不在同盟会而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此要求遭到主持同盟会总会会务的黄兴、谭人凤拒绝后,章炳麟、陶成章更是向海内外同盟会各分支寄发信函,对孙进行攻击;就连远在巴黎的张继也要求孙退隐深山,辞退总理。而这一切,都使得孙决意在同盟会外另开局面。
第三,于是,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就先在新加坡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说是“支部”,但在章程中却只字不提与东京总部的隶属关系,更不呈报东京总部批准。
第四,就是中华革命党的成立。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再次失败后,东京同盟会业已处于瘫痪状态;6月10日,孙中山秘密来到东京,宋教仁、陶成章、谭人凤等均对孙不理会务及处理财务不公表示不满,孙索性于24日再离东京,秘密筹建中华革命党,改变同盟会的誓词,并使得檀香山、纽约等地的同盟会均按中华革命党的章程行事。至此,孙与东京同盟会一批同道的分歧已昭然若揭。
第五,孙中山长期将革命目光聚集于两广及华南地区,在他本人自述的十次武装起义中,大多发生在两广地区,因为他觉得两广地区临海,购运武器方便,华侨众多,便于筹款。另外,就是孙的最为得力的几位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均为广东人。在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中,除张继(河北人)外,其余均为南方人,这也就影响了他们的目光所及。在南方人中,两湖的人尤为不满,认为孙、黄等人只在广东招募会党起义,正如谭人凤所言,“吾当日谓‘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盖轻视其人,而因轻视其地也”。
第六,1907年4月至8月,在同盟会之外,长江流域(特别是湖北)的人就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主要人物有湖北的居正、孙武、刘公等,他们对孙中山为总理的东京同盟会组织涣散、行动迟缓不满,而且对同盟会长期将革命战略中心放在华南及沿海地区不以为然。谭人凤更是认为孙中山“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恶劣”。1908年后,共进会发起人分头回国,随后在川、鄂、湘、赣等省相继成立分会;而孙武等人设立的湖北共进会果然成为领导武昌起义的两大革命团体之一;而真正打响了“第一枪”的程正瀛即为共进会会员。
第七,继共进会之后,在同盟会之外又成立了由章太炎为会长的光复会,起因也是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分歧太大,觉得难以共事。
第八,在东京同盟会总部涣散的情况下,宋教仁、谭人凤等主持中部同盟会把武装起义的战略重点转移为长江领域;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已经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共识。1911年2月23日,谭人凤奉黄兴之令由香港经上海抵达汉口。对于武汉地区的革命组织,孙中山几乎一无所知,黄兴等人尽管曾在两湖书院读书,也安排过许多人前往日本留学,但对武汉各革命组织的派系及领导成员也不清楚;此番谭人凤来,就以为居正为湖北共进会的领导人,这导致了真正的领导人孙武在辛亥革命后更愿意附和黎元洪而长期与孙、黄不合。谭人凤乃湖南人,但就当时革命人士在海外的活动而言,湖南人要比湖北人更为活跃,也更见过大世面,以致谭人凤初见湖北革命人士,觉得他们“土头土脑,或如老学究,腐气熏天,或如贵公子,纨绔未脱”。但恰就是这样一批毫不引人注意的革命党人成就了武昌首义的壮举;相比于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而言,孙中山就更是大感意外了。
第九,广州黄花岗起义乃同盟会投入人力、财力最多,也是决心最大的一次起义,起义失败后,湖北共进会于1911年5月3日在胭脂巷24号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两湖革命志士决心把起义重点确立在两湖,约定若湖北首先起义,湖南则率先响应;若湖南起义在先,湖北则呼应之。大家均对孙中山、黄兴一味经营华南不满,决心把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为一体,共谋大计,其中就包括领导人员分布、往迎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汉、军政府一旦成立后的人事安排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绕过了孙中山,革命的领导权正悄悄转移到了两湖人士手中,而经费筹措一事,主要靠清末襄阳三大富室之一的刘公(号称刘百万)慷慨解囊(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两万两银票),有了这笔钱,才有了收购、制造枪弹、炸弹、印制中华银行钞票、赶制旗帜文告,分遣同志四出联络之类的筹备工作。
第十,也是最后一项,即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总部在上海,推举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为总务干事,对此前孙中山、黄兴等人利用华侨捐款,在东南沿海一带冒然起义进行了批评,特别批评了对黄花岗善后事宜的处理方式;最后,宋教仁为中部同盟会制定了具体计划,要者有四:
以湖北为中国之中,宜首倡义;
一俟湖北举事,即令湘、蜀同时相应;
武昌既举之后,即派兵驻守武胜关,使敌兵不得南下;
拟长江下游,同时于南京举事,并即封长江海口,使敌军海军舰队孤立,而乘利应便以取之。
从这里已经看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已使武昌首义具有了一个完整雏形;但同时也说明,革命党人的分裂、内部党争也已发展到相互不通信息、各自独立行事的地步。
当然,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冯、张二人的这本书也只是一种说法,或可称之为“历史3”,我们也相信还存在着更多的“历史3”,如胡汉民、汪精卫等就很可能对这一段历史另有解释。但无论怎么解释,无论是孙氏,还是黄氏,或者宋教仁、谭人凤等重要人物毕竟在“辛亥首义”时一个也不在现场,其直接后果就是起义后建立的湖北军政府未能由革命党人直接掌握。在同盟会领导人中,黄兴是最重视两湖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状况的,但他对湖北新军的情况毕竟缺乏了解,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火速自香港经上海(偕同宋教仁、陈果夫等,其中最著名、也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由番禺人张竹君所率领的由中外人士所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到武汉,但也已经是10月28日了。
阳夏之战的惨烈就不必多说了。这段时间,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一到武汉,黎元洪就令人制一大旗,上书“黄兴到”,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汉口跑了一圈,使前线将士士气高涨,军心大振。这也说明,值此战况危难之际,所有内在矛盾、特别是争权夺利之事也就压在了下面,大家一心一意抗击清军。黄兴当然甚孚众望,但他此行此举,其实也含有为他、为两湖谋划此事的众首领争邀“神州第一功”的意味。
但黄兴毕竟未获“两湖大都督”的要职(这与他举事时不在现场密切相关),而是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党人本欲与黎元洪分权,“总司令”不必经由黎元洪委任,但湖北革命党人的实际领袖孙武却自负首义之功,自黄兴来后身价锐减,于是坚持由都督黎元洪授予黄兴总司令称号,这就是我们后来都看到的武昌“拜将台”,而黎是“主公”,黄为麾下元帅,类似于刘邦与韩信的关系,此种格局自然也就为日后的党人大权旁落埋下伏笔。究其根本,一是与孙、黄革命爆发时均不在现场有关,与党人内部的心术之争也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战局的发展与“枪杆子”到底掌握在谁人手中。
这样想来,后来发生的真正打响起义第一枪的程正瀛于1916年在党人内争中被贾正魁处死,沉入长江也就不足为怪了。
按冯、张二人的分析,阳夏之役失败,原因有四,第一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指挥不统一,内部不团结”(宋教仁谓之“事权军令之不一”),黎元洪黄兴貌合神离,军务部长孙武、参谋部长吴兆麟亦意见不一,新到的湘军与起义的鄂军也有种种相互指责之处,加上毕竟是新募的民军,军纪涣散,号令不一,这一切都使得起义部队远不是久经训练的北洋军队的对手。冯国璋不顾百姓死活和外国驻汉口领事馆的抗议,汉口纵火,大火三日三夜不熄,天为之变赤,使整个汉口繁盛区成为一片焦土,此种行径,也使民军不得不撤出汉口,后又于11月27日撤离汉阳,与北洋军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洋军或战或和,行动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手中;而无论是黎元洪还是黄兴,也都不得不把革命的前景寄托在袁世凯身上。黄兴在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直接把他比喻为拿破仑、华盛顿,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黎元洪更是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说:“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1]520~521
黄兴在这里所说的“兴等”,包括不包括孙中山?而当黎元洪提及“民国总统选举时的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时,又是如何设想他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的?
下一步,“第一功”的“先着”未得,汉口、汉阳先后失守,黄兴等人(包括李书城等十余位要员)只好离开武昌东下,企图在沪宁再起革命;如他所说,“以武昌之众顺流而下攻南京,南京克,虽失武昌,不为大害”;但背后,也有着赵凤昌、张骞、汤寿潜等江浙人士认为趁孙中山尚未归国(孙中山要到12月25日方才回国),如能让黄兴统帅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就仍不失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功”的想法。黄兴要走,黎元洪也要走,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固守武昌首义之“第一功”的将士们准备与袁军做殊死一战了。但在湖北守军中,主持军务的孙武又与负责维持全局的刘公不合;而江对面的袁世凯又只与黎元洪为谈判对手,这一切都使得重掌武昌军政府大权的实权人物非黎元洪莫属。那么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中华共和大总统与“神州第一功”之间的关系就只能在黎元洪(后面站着袁世凯)与黄兴(后面站着孙中山)中产生了。这本书的第八章名为“汉沪宁京角力”,唯独没有了粤,可见孙中山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确实只能是“临时”而已。
后来的局面就不必细说了,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中湘军援鄂,准备合力战胜袁军,攻克北京,无疑还是想延续“第一功”的荣耀(其中也包括谭人凤就任武昌防御使,准备与袁军最后决战之类的事情,但湖北军政府派系之争亦使得他不得不乘舟东下,改为鄂省议和代表),然今非昔比,就是鄂省都督黎元洪也无意北伐,只是希望南北议和,实现共和。就人格特征而言,黄兴素有宽厚揖让之风,甘当孙氏副手;黎元洪爱兵知兵,长厚逊和,遇事多有优柔,自然也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如是看来,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氏立即兴兵,谓“此后之战,皆为项城,非为满洲”;尽管副总统兼陆海军大元帅黎元洪多次发布北伐、讨袁通电,但武昌、上海两方面的主要希望还是不得不寄托在同袁世凯的和谈上,所谓“项城赞成共和,则兵弥而中国可以不亡;项城若效忠清廷,则祸结而中国必无幸存”[1]546。于是,共和之第一功的果实,自然就会落入至少在口头上表示拥护共和的袁氏以及唯一代表武昌方面的黎氏囊中。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均在对临时政府的人选考虑上绕过了武昌首义的直接领导者,这也不能不让武昌方面的人心中不平;而武昌方面的“首义代表”,无形中就成了黎元洪一人,黎与孙、黄暗中较劲,对袁却一味逢迎,这尤其表现在定都之争上。最后的结果,当武昌方面在黎的暗中支持下也表示应该建都武昌时,革命派内部的纷争,已使得南京方面和武昌方面都不得不最终顺从袁世凯的意愿,定都北京;而孙中山,则在辞去大总统后再三表示中国应定都武昌。
辛亥首义,第一枪、第一功的事看似清楚明白,实则又扑朔迷离,至少在结果上看是这样。
这种看似清楚,实则迷离的状况,恰好说明了孙中山1912年辞去大总统后在武昌这个首义之地所说的一番话:“其真理约分二宗,首曰政治,次即言论。言论者,发自团体,以补助政治者也。”[2]260~261当然,说得更好的还是鲁迅先生:为什么革命来革命去,社会生活的“内骨子是依旧的”[3]68呢?无非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革命者心中,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而已,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2]581。这也是我在读完这本书,特别是想到“第一枪”与“第一功”时所深深感受到的一种悲哀。
[1]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2]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3]鲁迅.朝花夕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K257
A
1001-4799(2011)05-0015-06
2011-05-20
陈家琪(1947-),男,北京人,曾任教于湖北大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启蒙思潮中的政治哲学及现代性问题研究。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