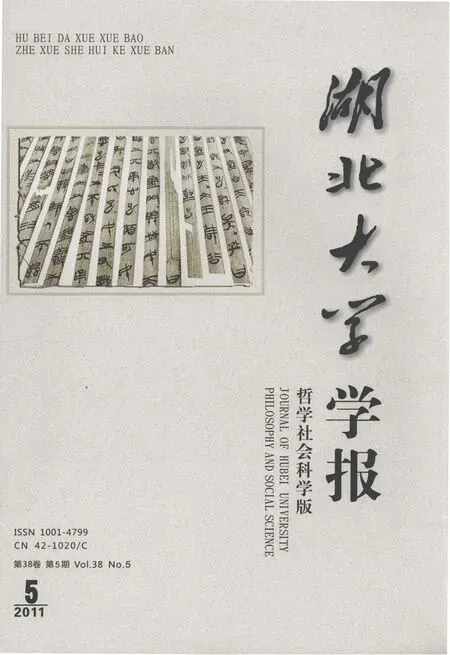论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
邓安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论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
邓安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在现代启蒙伦理的发展史上具有一种明显的过渡性质,他试图通过理性的形而上学重建伦理的最终基础,但是在思想中又留下许多经院哲学的痕迹;他与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英国经验哲学不同,在伦理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伦理学的许多论题,但又不是从德性论而是从法则和义务的概念出发,甚至把所有伦理的东西归结到作为最高立法者的神圣意志上。他的伦理思想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康德所继承,而他的旧形而上学却被康德所摧毁和改造,但无论如何,“前康德哲学的最重要努力在他的思想中找到了核心”。
快乐主义;幸福;德性;正义
莱布尼茨作为宫廷的法律顾问、外交家和政治哲学家,对其时代的欧洲伦理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目前面临着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如何解决这种状态呢?他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完善西方人最擅长的形而上学智慧,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向中国人学习实用的道德智慧,取中国文化所长,补西方文化所短。他说:“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中国—引者注)远胜于我们”[1]1~2,“他们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相互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1]2,“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1]6。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莱布尼茨对于用启示神学的方法来解决现代伦理问题的失望,而他所采取的方式,如我曾撰文①在这篇论文之前,我已发表了《第一哲学与伦理学——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实践哲学解读》,初次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9年第7期和《中国哲学年鉴》2010年转载。所指明的那样,实际上已经通过实践的形而上学解构了神学的基本语境和含义,完全以启蒙理性的立场使实践的形而上学接近于中国的“自然神学”②莱布尼茨所谓“自然神学”实际上就是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形而上学。关于这个概念的具体分析请参阅李文潮:《“自然神学”问题—莱布尼茨与沃尔夫》,载于李文潮、Hans Poser编:《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80~291 页。该书的德文版: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2000,S.320~331.。他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既然建立在天启神学基础上的欧洲伦理文明遭受到了空前的危机,而在“自然神学”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伦理却那么“完美”,那么,至少可以在实用的层面设想,良好的伦理生活秩序是可以与基督教神学伦理保持距离而由人类的理性来治理的。通过理性的治理才能把“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理性的生活”[1]4。尽管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不懂得基督教的崇高教义,不能获得上帝的恩宠国王,所以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合乎道德的生活,但通过儒学(理学)的实践理性毕竟可以控制从罪恶特性中生长出的萌芽,减轻人类罪恶带来的苦果,建成彬彬有礼、谦恭礼貌的伦理乐园。
尽管如此,我们在此必须说,尽管莱布尼茨的哲学具有实践哲学的意向,但他却没有系统的伦理学思想,他的哲学除了形而上学比较系统之外,其具体的伦理思想都是零散地表达在他的不同著作及其通信中的。为了不给人以凌乱之感,我们把它聚焦在快乐主义、德性论和正义论三方面加以具体分析。
一、莱布尼茨快乐主义的幸福论思想
德意志民族由于近代的封闭、专制、落后和挨打,一直具有冷峻、悲戚和郁郁寡欢的性格,特别是在莱布尼茨所生活的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岁月,这个民族鉴于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崛起,更是增添了一种奋起直追的焦虑。因此,莱布尼茨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非常清楚自己作为学者的使命:“克服欧洲的内在混乱,意义,整体的意义已经丧失的一个真空”,“要找到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赋予这个表面上残酷无意义的世界现实一种意义”[2]9。为了给这个时代和德意志民族甚至欧洲赋予一种意义,莱布尼茨作为早期启蒙哲学家,提出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让世界理性化,通过理性的论证为德意志民族培植一种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
乐观主义的简要口号是“存在于最好者当中”(Sein im Optimum),但作为一种“主义”,它不仅是一种情绪和希冀,而且必然要获得一种理性的证明。在莱布尼茨看来“道德学是一门推证的科学”[3]55,“推证”就是理性证明,因此,他的乐观主义必须要证明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这个论题首先承认了存在着无数个“可能的世界”,即不只是有一个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还有许多其他世界存在着。所谓“可能的”,就是事物当其不自相矛盾时,这是逻辑意义上的,即不违反“矛盾律”,就是可能的;而他所称的“世界”既不是指笛卡尔意义上的广延的物质实体的集合,也不单指我们所生活的地球,而是指无限的宇宙。但是,这种简单地界定,实际上掩盖了莱布尼茨自己所欲表达的含义,因为所谓的“最好”如果不是指“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而是逻辑上可能的宇宙空间中的某个与我们无关的“世界”,那么它怎能让我们“乐观”起来呢?所以,所谓的最好世界的理论,不能单纯是逻辑意义上的,而且必须是道德意义上的,即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是与我们的“此在”生存相关的“世界”。
但道德意义上的证明,不能止于不矛盾,而且要回答这个世界之“最好”或“最佳”在实践上是“如何可能的”(wie möglich)?莱布尼茨采取的论证策略是,首先强调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现实”,即不能把“最好”看作是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点”,而要看它的“未来”是否在朝向“更好”的方向变化和增长,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所以,乐观主义总是依赖于对未来的一种许诺,依赖于进步主义的信念:“假如幸福不在进步中,它就是令人诧异的”。1715年8月5日,莱布尼茨给Bourguet写信时这样说:“你说得有理,我们的地球应该是天堂的一种类型,而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它恐怕只能在未来变成天堂,尽管中间确实要经历反反复复的前进和倒退”。可见,用一种推向未来的信念取代一种现实的信念,只是把问题在时间上转移了,而不是在理论上解决了。所以,作为逻辑学家的莱布尼茨还要采取别的论证策略,这就是关于“不可区别者的同一性”的证明。
这种证明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涉及到对单子的存在方式的证明。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是由不可区别者——“单子”构成的,我们每个人作为单子,作为个体性是独立的真正的存在者,因而是自由的存在者,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之所在。但所有这些独立自由的单子之间是可共存的,可能世界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规律,都追求“最好”。因为每个单子内部都有“隐德莱希”这个原始的行动能力。而在地球上,人是最高级的单子,精神是其本性,这样的单子有一种类似于几何学的必然性在追求“最好”。这样一种证明正如罗素所说,是把假设的“偶然性”前提当作必然性的结论了[4]78~80,人们当然是不会满意的。但莱布尼茨借助于这种证明是想说明,这个单子构成的世界,既容许了最大的差异性、个体性、独立性和自由,同时因为它们的可共存性,又存在着令人向往的和谐与秩序,怎能说不是最好的世界呢?但莱布尼茨忘记了,即便有他所说的上帝的“预定和谐”作保证,即便人作为精神的存在者,能够把自身提升到“精灵”或“天使”的高度,但道德意义上追求“最好”的必然性,是以意志永远选择“至善”为行为原则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即便在上帝那里也是偶然的,因为上帝也要容许恶的存在。
可见,对这种乐观主义的证明是不成功的,也不会取得成功。所以,莱布尼茨乐观主义的特征比较适合于这一诗句:“在上帝面前毕竟万物都荣耀,只因牠是最好,如今众鸟要入睡,大大小小有归巢”,即不管好赖,漂亮的骏马和丑陋的河马,毕竟都是上帝所造,在上帝面前都是荣耀的,都是最好的,都有存在的充足理由。现实世界最终是否真的是最好的世界,不全靠人为的努力,而依赖神的恩典,所以道德世界最终是一个恩典的世界。这就从他的理性主义退回到经院神学的废话中去了,因此他的“最好世界理论”后来遭到伏尔泰《老实人》极其辛辣的讽刺就不令人意外了。
但是,要说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是全无意义的蒙昧主义,是为现实政治辩护的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客观的评价。从历史的角度看,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把追求快乐,追求现世的幸福作为了人的“自然权利”,这正是那个时代代表进步的启蒙思潮的基本诉求。尽管莱布尼茨理论的核心一直是以神的眼光来俯视大地,但毕竟还是把那可望不可及的“最好”确立为现实的目标了,因此,他的伦理学更多地还是像他喜爱的柏拉图等古典伦理学那样,不是以行为的义务(应该)为原则,尽管单子的内在行动原则具有了这种萌芽,而是以好生活(幸福)为目标。
“幸福论”作为西方伦理学的第一主题,是亚里士多德确立的伦理学的第一形态①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首先得到系统的探讨,但他的伦理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是幸福理论。参阅Ernst Tugendhat:Vorlesungen über Ethik,4.Aufl.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1997.S.239f.。但这一目标在经历了1000多年禁欲主义的中世纪之后,在启蒙时代重新确立,尽管从当下太过世俗化的现实看来,根本不值一提,但我们只要想一想,贫穷的苦难带给生活多大的罪恶,就会明白,对追求世俗快乐的肯定,对于走出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哲学家的思考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在提倡虔敬主义而反对世俗娱乐的弗里德里希大帝身边,莱布尼茨采取的策略只能是把人类本性具有的对快乐和幸福的追求,不单是看作自然的本能,而是看作是“天赋原则”。他在与洛克争论人的心中是否有“天赋的实践原则”时,洛克派的辩手认为,既然道德原则是需要“证明”、“推证”的,那就没有所谓的天赋的实践原则,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现在是非常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但莱布尼茨显然是改变了“天赋”的含义,把逻辑上的“必然真理”、依靠“自然之光”和“本能”所认识到的东西等等都看作是“天赋的”,所以,他认为对“快乐”、“幸福”的追求就应该是“天赋的”,即“自然在一切人心中放置了对幸福的渴望和对苦难的强烈厌恶”[3]56。我们在这里不应该也不愿意被卷入到有没有“天赋观念”这个似乎迂腐的论辩中去,因为无论是经验论的“拒绝”还是唯理论的“坚持”,结果都是一致的:为了证明有一些“自然法则”、“自然人权”(所谓的“天赋人权”)是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这在“现代”发轫之初都具有反封建、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进步”意义是无容置疑的,列奥·施特劳斯甚至认为,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工具理性都要“使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完完全全的家园感的努力,结果却使人们完完全全地无家可归了”,这就是拒斥了“自然权利”所造成的灾难后果[5]19。我们这里关注的是,莱布尼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可把“趋乐避苦”作为一种道德原则,以此为前提,他如何在伦理学意义上解决基督教“天启”的“神圣价值”(绝对价值)和基于自然人权的世俗价值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张力中,他将为“现代人”确立怎样的一种“道德原则”?
既然对幸福的渴望是大自然赋予人的“天赋权利”,莱布尼茨自然认为快乐是应该追求的:“真正的幸福应该永远是我们欲望的目标”[3]195,而幸福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持续的快乐而已。但是,对于是否把它作为一种道德原则,他是不同意的。对此的论证是:(1)既然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一种自然本能,但本能不能作为道德原则:道德科学超乎那些趋乐避苦的本能之上;(2)虽然德性的观念是“天赋的”,但是德性却不是,“德性是一种以理性来抑制情欲的习性,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遵照理性行事的习性”[3]66,因此必然推导出,道德的原则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本能基础上;(3)快乐是一种感觉,是不可定义的,最多能给出的定义是一种对完善性(或圆满性)的感觉,所以,除非欲望受理性的引导,否则它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当前的短暂的快乐,而不会把我们引导到持久的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只能由理性和意志来引导。莱布尼茨得出的结论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虽然是首要的和得到实践的原则,但是,它是以内心经验或混乱的认识为根据的,不是靠理性认识得到的一条真理。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对享乐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即使在此生之外,什么也没有,也不该以为只有吃喝玩乐才是可取的价值,灵魂的安宁,身体的健康也比这些更为可取。
在这些推证中,有三点是有意义的。第一,确认了追求幸福、快乐的合理性,并把此作为“天赋观念”,虽然这不是莱布尼茨首先提出来的,但却是他从理性的立场上重新确认的一个现代价值;第二,把理性作为德性的基础,突破了正统神学把信仰作为道德基础的藩篱;第三,他承认了在某些情况下,理性“并没有办法来证明最正直的就是最有用的。因此只有对上帝和灵魂不朽的考虑,才使得德性和正义的义务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3]197。后两点不仅为康德的道德论证提供了思路,而且似乎也合乎施特劳斯回归苏格拉底智慧的愿望,因为“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学无需更多的东西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哲学就是对于人的无知的知识”[5]34。但莱布尼茨令人厌烦之处就在于,他一方面认为人的理性无法证明诸如正义等道德原则的适用性,但另一方面却总是满怀信心地以为理性知道上帝是什么,知道人能像上帝一样达到完善。因此,他的德性论就以“完善”为核心。
二、莱布尼茨的德性论
幸福论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所赋予它的形式是德性论的。而幸福与德性的关系则是,幸福是人的所有行为的最高目的,而德性是实现幸福的最可靠的保证。莱布尼茨把德性视为一种“存在原则”就是在此意义上提出来的:“由于可能性是本质的原则,因而完善性或本质的等级是存在的原则”[6]129。所以,在分析了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的乐观主义之后,我们要分析现实世界的“存在原则”。这个原则之所以和他的德性论联系起来,就是因为“存在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单子的内在行为原则—按内在的“隐德莱希”追求目的由潜在到实现的最大完善性原则,而“完善性就是德性”[7]31。
所以,莱布尼茨的德性论完全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因为“隐德莱希”这种内在的活动力(生命力)就是一种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动力,不过,莱布尼茨更直接地把完善行动的“目的因”看作是作为最高级单子的上帝,明确宣布他的《形而上学论》是从“真正的上帝概念”出发的。上帝在他看来“是一个无条件完善的存在者(Wesen)”,“上帝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和无限的智慧,以无限完善的方式产生作用—不仅在形而上学的,而且在道德的意义上”[8]26~27。在《神义论》中,莱布尼茨进一步论证了正是由于人类“知道”上帝是一个最完美的存在者,所以我们人类才爱上帝,相反,如果人们不知道上帝之完美便不可能爱他。但爱上帝,实质上无非就是爱完美。尽管人的完美与上帝的完美不可同日而语,但就他们都是单子而言,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只有程度上(等级)的不同。这种对上帝的爱于是就不单是一种感性的情感,而是一种理智的情感。理智上的爱完美,必然促成意志上追求完美,所以他在《理性基础上自然的和恩典的原则》中,强调人的灵魂的使命“在于持续地向着新的要求和新的完善性迈进”,而在《新系统及其说明》中则这样说:“心灵应该永远以一种最适宜于对由一切心灵所构成的社会的圆满性有所贡献的方式,在宇宙中尽其本分职责,这种心灵社会在上帝之城中构成了心灵在道德上的联系。”[9]11
这段话之所以令我们感兴趣,是因为在莱布尼茨的伦理话语中终于出现了“社会”的概念。在古希腊,德性是人的灵魂的秩序,而在中世纪,伦理是在人、神和上帝之国的关系上展开,而现在,德性终于有了一个新的领域:社会。尽管“社会”这个概念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还没有得到明确地界定,尽管他还是依照单子的精神本性,谈论“心灵社会”,但毕竟在人的心灵(德性)和上帝之国之间出现了“社会”这个中间领域,这是现代伦理的真正舞台。这个舞台,尽管在莱布尼茨这里还没有明确地搭建起来,但毕竟已经露出了端倪。这在莱布尼茨思想中是有意义的,因为虽然在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中充满着保罗式的爱心和奥古斯丁式的向善意志,但他并没有在单纯的基督教神学视野上来阐释这种爱和善,而是把这种爱和善紧紧地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学框架中的德性论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框架中,如同爱上帝也就是爱完善一样,而对他人的“爱的情感,就是在所爱者的完美性上能找到令我们喜悦的东西”[10]158。所以,不仅追求完美是德性,而且由于完美是爱的对象,爱也就是一种德性了。这种德性表现为通过献身于被爱者的生活而使之完美。在此意义上,爱是一种参与完美之生成的活动。
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对莱布尼茨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人的个体完善的品质上,而且更在于这种德性论在爱的社会参与行动中表现出的伦理—政治特性上,即把城邦正义作为总的德性,作为一切公民个体之德性完善的社会条件。他说:“一个善良的人就是一个在理性容许的范围内爱一切的人。因此,正义是支配心灵倾向的德行,希腊人称这种倾向为人类的爱。”[11]141由于正义是支配心灵倾向的德行,所以,它比个人身上诸如勇敢和节制更有基础性,抓住了这一点,莱布尼茨就抓住了社会之圆满性的基石。
三、莱布尼茨的正义论
遗憾的是,莱布尼茨并没有从社会圆满性的基石这一点出发来建构他的正义论,更多的却是在“神义论”的框架中讨论的。之所以如此,倒不是由于他依然固守基督教的老教条不放,而在于他不满意于现代政治哲学从法权出发探讨正义的这一出发点。作为法学家,他深知法律与正义的关系,但他更清楚的是,法律并不等于正义,因此法权也不可能就是正义的出发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及其保障的权利是否基于普遍的法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就不会有真正的正义性。因此,对于喜好几何学公理之清楚明白的普遍必然性的莱布尼茨而言,对正义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普遍法理的探寻。
但哪里存在着这种普遍的法理呢?莱布尼茨与其说依赖于基督教神学,不如说还是依赖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因为他深知一切科学之所以依赖于形而上学作为一般(普遍)的科学,就是要从它当中借取它们的普遍原则,伦理学和政治学同样也不例外。对于伦理学、形而上学和自然神学的关系,莱布尼茨说:“真正的道德学对于形而上学的关系,就是实践对于理论的关系,因为关于共同的实体的理论,是关于精神特别是关于上帝和灵魂的知识所依赖的,这种知识给正义和德性以恰当的意义。”在另一处还说:“其实形而上学就是自然神学,同一个上帝,既是一切善的源泉,又是一切知识的原则。”[12]506所以,把实体论上的上帝作为普遍法理的源泉,实质上就是把作为最高级单子的行动原则:绝对的正义作为行动原则。之所以说上帝以绝对正义为行动原则,是因为上帝的行动不是出自其私己的意志,而是永远都符合普遍的意志:“我们可以断定,上帝做任何事情都是符合其普遍意志的,这种意志适应于牠所选定的最完善的秩序。”[13]32所以,与其说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完善是上帝的“前定和谐”预先定好了的,不如说是靠这种以普遍意志为行动原则决定的。
但是,对于一个坚持个体性自由的人来说,以普遍意志为行动原则不是违反其个体自由吗?这涉及到莱布尼茨和洛克在自由观上的两个不同。第一,莱布尼茨的重心不在法权上的自由,因为照法权上的自由,一个奴隶是毫无自由的,而一个臣民也是不完全自由的,就是说这种自由不是普遍的;第二,就事实上的自由而言,不是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做他想做的事,而是他的意志本身是否有足够的独立性。就意志的独立性而言,他一方面把自由看作是心灵的自由,只有当心灵是完善的时,它能够驾驭情感就是自由的,另一方面把自由看作是活动的自由,当理智能够引导自发性(本性的自发倾向),就是自由的[3]164~171。所以,他一直与洛克在不同的层面上讨论自由,原因在于他不想只是限于事实的层面讨论人是否自由,而是讨论自由的形而上学原则。就他把自由限于心灵(灵魂)的自由时,他确实无法真正解决伦理政治自由的根基,他过于强调了人的心灵和理智的局限,所以,他只能把普遍法理寄托于上帝的全能的理智,只有这种理智才能真正以普遍的原则(或意志)行事,只有这样行事才能有普遍的正义。所以,以普遍原则行事不仅不违反个体自由,相反却是个体自由得以可能的条件。
但这种形而上学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普遍的法理尽管非常重要,尽管要尽量超越人的有限的理智来为之寻求基础,但是,普遍法理毕竟还是要通过人的理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实行的,所以,只要是把它推到“上帝”,尽管这个上帝只是一个最完美者的理想,但是,如果人无论如何达不到这一理想的话,它再完美也是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的。为了克服这一困境,莱布尼茨一方面坚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和人,从这个最完美的存在者的最高理智和智慧确立普遍法理,即普遍的正义原则,但另一方面他认为神的正义和人的正义是遵循同一规律的:“不管是道德规范自身还是正义的本质,皆不依靠上帝的自由裁定,而是依赖永恒真理,这是神圣的智性的认识对象。正义依赖许多有关平等与相称的规律,这些规律既可在事物不可改变的天性中被发现,也存在于神圣的理念之中,一如几何学和算学中的原理一样。神的正义和人的正义拥有共同的规律,而这些可以简化为系统;它们必将在普遍法理中得到应用与传授。”①莱布尼茨:《论普芬多夫(Pufendorf)的法学原理》,转引自李文潮、Hans Poser编:《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尽管这种诉诸“永恒真理”的“神智学”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它作为对普遍法理的神圣信念的奠基,决不会像单纯相信人类制度立法的自由主义者那样,最终导致虚无主义的盛行。这套带着强烈时代烙印的形而上学虽然在现代令人讨厌,但他通过这种形而上学的奠基,坚持把普遍正义作为“总的德性”②莱布尼茨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普遍的正义不仅仅是一种德性,它甚至就是全部道德上的德性。”(《人类理智新论》下册,陈修斋译,第507页)因此在他这里,不是自由,而是普遍的正义才是普遍的法理。而确立了“自然法”的基础地位。他的“自然法”中的“自然”既非自然而然的“自然”,也非“人的本性”,相反乃是“神的本性”,但莱布尼茨所谓的“神的本性”也并非完全等同于基督教上帝的本性,而是自然的单子的本性,这种单子一方面追求完美,完善和圆满,一方面是出自本性,即按照其自发自由的倾向来追求,这样就使自发性得到理念的引导和规约,从而具有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更深基础就是上帝的最高智慧,正是这种最高智慧才是普遍正义的最终基础。把普遍正义作为普遍的法理应用于人类的社会政治伦理实践中,才可能把一个个体、民族和社会带往莱布尼茨所向往的“完满性”,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世界成为和谐完善的道德世界的原则,而且是个体的自由和利益得到保障和实现的前提:“我们必须注意到,像一个组织得十分完好的国家,对每个个人的利益都给予尽可能的关心,同样,除非对每个个体的利益得到照顾,宇宙将不会充分地完善,而只有在这个时候,宇宙的和谐才得到保持。对于这个,再没有比那个公正的规律能够作为更好的标准被树立起来:这个规律宣称每个个体都应该按照他自己的德行和他对于共同幸福的善良意志的程度的比例,共享宇宙的完善性和他自己的幸福”①莱布尼茨:《论事物的最终根源》。转引自陈乐民编著:《莱布尼茨读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这样,莱布尼茨就从普遍正义这一所谓的普遍法理探究了“社会圆满性”的形而上学基础,有了这一社会性概念,之后的德国古典伦理学,都不再单纯地从个体心灵、意志方面谈伦理问题,但社会概念在莱布尼茨这里才刚刚露出一点萌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具有一种明显地过渡性质,他试图通过理性的形而上学重建伦理的最终基础,但是在思想中又留下许多经院哲学的痕迹;他与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英国经验哲学不同,在伦理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伦理学的许多论题,但又不是从德性论而是从法则和义务的概念出发,甚至把所有伦理的东西归结到作为最高立法者的神圣意志上,从而主张伦理规范作为上帝本身的永恒本质的必然表达,具有永恒性和不变性;他看出了只有对上帝和灵魂不朽的考虑,才使得德性和正义的义务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这促成了康德定言命令的伦理范式,但他却没有像康德那样,从实践理性的希望和先天要求来言说上帝和不朽,而是继续沿用实体论的旧形而上学,作出令科学理性无法接受的论证。他的伦理思想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康德所继承,而他的旧形而上学却被康德所摧毁和改造,因此,正如新康德主义的伦理史家Friedrich Jodl所言:“莱布尼茨在近代思辨哲学发展中占有中心地位,这是早已得到承认的”,“前康德哲学的最重要努力在他的思想中找到了核心。”[14]
[1]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M].梅谦立,杨保筠,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2]Friedrich Heer:Leibniz.Fischer Bücherei KG,Frankfurt[M].am Main und Hamburg,1958.
[3]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卷[M].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罗素.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M].段德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6]陈乐民.莱布尼茨读本[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7]Leibniz.Metaphysische Abhandlung(§5)[M].Leibniz:Die Hauptwerke,1967.
[8]Leibniz:Metaphysische Abhandlung(§1)[M].Leibniz:Die Hauptwerke,Zusammengefaβt und übertragen von Gerhard Krüger,Alfred Kröner Verlag Stuttgart,1967.
[9]莱布尼茨.新系统及其说明[M].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Leibniz.Theodizee[M].Leibniz:Die Hauptwerke,a.a.O.S.158.
[11]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M].祖庆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2]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下册[M].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3]Leibniz.Metaphysische Abhandlung(§6)[M].Leibniz:Die Hauptwerke,1967.
[14]Friedrich Jodl.Geschichte der Ethik,Band 1[M].Essen:Phaidon Verlag,1967.
B82-0
A
1001-4799(2011)05-0132-06
2011-06-1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4 B Z X 052;教育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资助项目:EYH3155071
邓安庆(1962-),男,江西瑞昌人,曾就读于湖北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西方伦理学研究。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