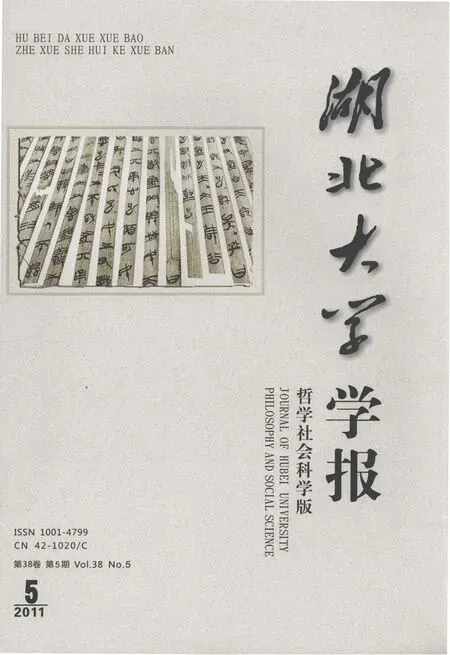传播与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
陈桐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传播与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
陈桐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先秦时期,有两个阶段文学语言进步最大:一是在西周,另一是在战国。西周文学语言的进步取决于作品的不同用途,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则得力于传播。战国很多文学作品都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由此保留了口语化特色,大大地缩短了书面语与民众口语的距离。孔子师徒开创了先生讲、弟子记的散文创作方式,弟子们出于对孔子的由衷崇拜,原汁原味地记录了孔子说话的声情口吻,这使《论语》成为口语化特色最为鲜明的战国散文作品。此后《墨子》、《孟子》等散文著作沿袭了孔子师徒的创作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论语》的口语化成果。战国文学语言取得巨大进展的另一原因,是诸子百家为了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力求在游说和写作中运用最为生动浅显的语言来表述观点,这使文学语言进一步接近民众口语。通过孔子师徒和战国诸子百家的努力,战国文学语言形成了生动形象、平易畅达的特色,此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文学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就是战国文学语言。
传播;战国;文学语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进步最大:一是在先秦时期,文学语言从殷商古奥晦涩的公文典诰用语演变为战国平易畅达的语言,此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文学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就是战国文学语言;一是在近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替代文言。近现代文学语言革命已经广为人知,而先秦文学语言的巨大进步却很少有人论及。先秦文学语言的进步不是渐进的,而是呈现出阶段性的飞跃。它有两个时段最为重要:一个是西周时期;另一个是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西周文学语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学作品用途不同:用于神圣庄严场合的作品继续沿用殷商典诰用语,而用于普通政治文化场合的作品运用当时的普通书面语。战国文学语言的进步则得力于传播:战国很多作品都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由此保留了口语化特色,缩短了书面语与民众口语的距离。在战国文学语言发展中,孔子师徒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此后战国诸子百家出于传播目的而刻意追求语言的生动优美和通俗易懂,推动战国文学语言向着平易畅达方向迅速发展。
一、战国以前文学语言的发展状况
在讨论战国文学语言发展之前,需要先确定战国文学语言的起点,这就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战国以前文学语言的发展状况。传说中的黄帝、唐尧、虞舜、夏朝都还没有考古文献依据,中国的信史是从殷商算起,因此中国文学的起点只能定在殷商。传世的殷商文学作品约有四类:一是《尚书·商书》,二是《诗经·商颂》,三是殷商铭文,四是殷墟甲骨卜辞。这些作品不仅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汉语文字载体和语法结构,而且也凝练成殷商文学语言古奥、艰深、晦涩、简略的特点。传世殷商作品几乎是一无例外的难懂,我们今天读殷商文学作品,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难关,它的佶屈聱牙,是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体会到的。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已经深感《尚书》难读,《孔丛子·居卫》载宋大夫乐朔对子思说:“《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乐朔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不过他认为《尚书》中的商、周文章是效法虞、夏,则未必尽然。进入西周以后,周人在祭祀、公诰、册封、燕飨、纪勋、占卜等重要礼仪场合继续沿用殷商典诰语言,如《尚书·周书》沿袭《尚书·商书》的语言,《诗经·周颂》沿用《诗经·商颂》的语言,西周铭文运用殷商铭文的语言,西周卜辞学习殷墟卜辞的语言。当然,周人在沿用殷商典诰用语的同时也有丰富和发展:我们将《尚书·商书》与《尚书·周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周书》的词汇比《商书》要丰富得多;西周的铭文不仅在篇幅上比殷商铭文要长得多,而且出现了许多新词语。令人庆幸的是,周人在继承前代语言的同时有所创新,他们在普通政治文化生活中(诸如史官日常记言记事,王室和各诸侯国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等),并不是运用古奥的殷商典诰语言,而是采用当时的相对平易的普通书面语。《国语》中有11篇作于西周的散文(见于《周语上》和《郑语》),《诗经》中有写于西周的部分风诗作品,这些西周诗文都没有运用殷商的典诰语言。西周作家或许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运用普通书面语进行写作时,是实实在在地掀起了一场文学语言革命——从古奥晦涩的典诰语言到普通书面语的革命。我们将《国语》中西周散文及《诗经》中西周风诗的语言与殷商作品进行对照,那种语感真是有天壤之别。西周这些用普通书面语写成的诗文,其语言与后世中国封建社会的文章已经相差无几了。文学作品是写给人看的,它必须让人看懂,读者无法看懂的作品是很难让人学习、仿效的。西周以后,除了在极少数神圣庄严的场合(如册命、封赐)有意识地仿照古奥的殷商典诰语言之外,一般情况下作家都乐于运用《国语》西周散文和《诗经》西周风诗语言,这一点,我们读《国语》中的春秋散文、《诗经》中的春秋风诗和《春秋》,就可以知道。战国文学语言的起点就是春秋末年的文学语言,具体地说,就是《国语》中的春秋散文、《诗经》中的春秋风诗和《春秋》的语言,相对于殷商的典诰语言和西周的仿古语言而言,这些作品的语言已经平易浅显得多。就是在春秋文学语言的基础之上,战国的文学语言进一步走向口语化、形象化、流畅化。
二、孔子师徒的文学传播特点
春秋末年,中国出现了三大散文作家:一个是道家祖师老聃,其生活年代比孔子稍前,著有五千言《老子》(又称《道德经》);二是兵家孙武,生活年代约与孔子同时,著有《孙子》十三篇;三是儒家创始人孔丘,其言论被弟子编为《论语》,此外还有一大批礼学文章,后来被收入大小戴《礼记》之中。这三位散文大家的著述方式是不同的,老子、孙子都是自著,而孔子则采用先生讲、弟子记的散文创作方式。①《论语·卫灵公》中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在孔门弟子中,像这种随时记载孔子言论的情况,肯定不是子张一人所独有,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子张是临时性的请益,事先未能备好简帛,所以他急中生智,将老师言论记在衣带之上。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孔门弟子应该事先为记载准备了笔墨简帛。笼统地说,《老子》、《孙子》、《论语》都可以算是散文作品,但如果仔细区分,就可以发现三者的体裁其实并不完全一样,《老子》和《孙子》是广义的散文,《老子》一书是采用商周史官迟任、仲虺、史佚、周任等人所开创的史官格言体,《孙子》是采用上古《军志》的兵书格言体,两者都是用浓缩精练的格言形式来讲述哲学、政治、人生、军事理论,唯独《论语》是地道的散文体。从文学语言角度看,《老子》和《孙子》这两部散文集分别是商周以来史官格言和兵家格言的集大成者。《老子》以后,史官格言体散文因后继无人而走向衰微,而在《孙子》之后,兵家格言体散文虽然不乏作品(如《司马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鬼谷子》、《六韬》等),但这些兵书都不像《孙子》十三篇那样运用纯正精粹的兵书格言进行创作。《老子》和《孙子》的语言特点是高度精练,言约意丰,这是一种在书面语基础之上反复提炼、浓缩而成的文学语言。有人说《老子》是哲理诗,这是就《老子》语言精练形式整齐而言的。《论语》部分语录也有格言倾向,在《论语》四百八十六章语录中,大约有五六十章语录可以作为格言来读。但《论语》更多语录的语言则大体上是倾向散体化和口语化。在先秦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老子》、《孙子》、《论语》这三部散文作品的影响走向是不同的:《老子》、《孙子》的影响走向是向前代的,它们是商周以来史官格言、兵家格言的一个总结,是商周以来格言体散文的一个发展高峰,同时也是顶峰,它们对后来散文语言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论语》的语言影响走向则是向后的,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散文语言时代。所以,老子、孙子对战国文学语言发展的贡献并不大,对战国文学语言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孔子师徒。
孔子师徒对文学语言发展的贡献与他们的传播方式有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创办私学的人士之一,要办学,就要解决最基本的教材问题,而当时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还没有统编教材。孔子是如何解决教材问题的呢?他的教材装在他的脑子里,靠他的嘴说出来,靠弟子记下来,这些记录手稿就是孔门的教材。孔子教学的主干内容是周礼,而当时还没有一部成文礼,这些礼仪要靠孔子口头传授给弟子。仅仅传授礼仪是不够的,孔子还要给弟子讲述礼仪之后的伦理政治意义。为了提高弟子服膺周礼的自觉性,孔子用毕生的精力对弟子进行道德教诲。这些教学内容全部都是通过孔子口授、弟子笔录的方式保存下来。孔子说出来,弟子载之简帛,这在当时就是出版。七十子不仅用这些记录手稿教育自己,而且用这些记录稿教育自己身后的弟子,弟子后学在传习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记录稿进行增删。用传播术语来说,就是先用口头传播,再进入书面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可以在商周史官文化中找到源头。在七十子之前,商周史官有执笔记载的传统,王侯卿相发表思想言论,史官随时将这些“治国之善语”记载下来,《尚书》、《国语》中的王侯卿相言论,就是由当时史官记录整理的。七十子受到商周史官的启示,他们像史官记言记事一样,一丝不苟地记载孔子的一言一行。不过,我们将《尚书》、《国语》与《论语》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论语》的口语化倾向特别明显。为什么同是记言散文,《论语》会有如此突出的口语特色呢?这其中的奥秘存在于记录者的心理之中。商周史官们记载王侯卿相言论,是在忠实地履行王事职责,他们与王侯卿相仅仅是职务上的关系,感情态度相对要淡薄一些,他们的着眼点主要是从资治、垂鉴的角度准确地记录王侯卿相的思想观点,至于如何传达王侯卿相说话的声情口吻,如何寄寓记录者本人的景仰崇拜之情,这些都不在史官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七十子对孔子的心理就不同了,他们对恩师有一种由衷的仰慕、崇拜之情,《论语·子罕》载颜渊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1]《论语·子张》载子贡曰:“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颜渊、子贡是以高山仰止的心情看待孔子,他们的话说出了七十子的共同心声。在他们眼中,孔子的一言一行,都如金如玉,为律为度。唯其如此,七十子才以那样虔诚的态度、钦敬的情感,执简记载孔子的一言一行。七十子笔录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时是孔子某一句名言,有时是孔子与门生弟子的闲居交谈,有时是个别弟子的请益,有时是孔子与诸侯贵族及时人的谈话,有时是孔子生平经历的各种事件,有时是孔子传授的礼仪,有时是孔子阐述的礼义,有时是孔子讲述的历史旧闻,甚至孔子的起居嗜好、一颦一笑也成为七十子的记录内容。他们逼真地描摹孔子的声情口吻,细致地记载孔子的饮食起居等行事,孔子微笑是什么样子,孔子生气又是何种情态,孔子喜欢什么,孔子厌恶什么,孔子如何待人接物,孔子如何评价弟子、时人暨历史人物,所有这些都被七十子摄影般地详细地记录下来。七十子手中,人人都有一批这样的记录手稿。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想起恩师当年对他们的教诲,想起恩师的音容笑貌,那一幕幕情景如在昨天,真是不胜思念之情。当时没有录像、摄影设备,画家可能也很少,怎样才能为历史存照,怎样才能保留恩师的音容笑貌呢?七十子所能采用的手段就是语言,他们要用语言把恩师的形象保存下来。他们所编的《论语》,除了记载孔子的道德教诲之外,还有一个为历史存照的重要功能,而为历史存照,则是通过收录那些记载孔子声情口吻的原始记录材料实现的。①《论语》记载了曾参临死之前的言论,以此推测,《论语》的编辑成书应该是在战国前期。孔子当年是用口语教学,七十子是原汁原味地记录孔子的口语,编《论语》时又保留了孔子的口语原貌——《论语》的口语化就是这样来的。
《论语》中孔子师徒的语言是春秋末年的口语。不少对话体语录通俗浅显,明白如话,甚至比明清时代的古文还要好懂得多。例如,《公冶长》载:“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雍也》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先进》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些对话几乎不用注释,就能读懂它的文意。《论语》语录在描摹孔子声情口吻方面尤其传神。例如,《八佾》:“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这是孔子高兴时的声情。《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是孔子急于洗清辨白时的情景。《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是孔子大悲大痛时的语调。《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这是孔子生气时的口吻。《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是孔子无奈时的语气。《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是孔子逗乐时的口气。《微子》:“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孔子失意时的情形。《论语》有时用重复句来表达孔子对某一思想的强调。例如,《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至牖执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处的重复表达了孔子对高足身染沉疴的痛惜和无奈。又如《子罕》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聪明的子贡通过巧设譬喻来询问老师志向,而孔子心有灵犀,他的两个“沽之哉”传达出孔子急于用世的迫切心情。运用丰富的语气词是表达声情口吻的重要手段。孔子对尊者态度恭敬,因此他在与诸侯贵族对话时运用语气词较少。他在教诲弟子时运用语气词最多。例如,《学而》载孔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本来用一个“矣”就可以了,但加上一个“已”,传达出加重、延缓、慎重的意味。《论语》某些语录甚至连用三个语气词,这在先秦其他典籍中是很少见的。例如,《雍也》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焉”、“尔”、“乎”三个疑问语气词连用,不仅加重了疑问语气,而且起到舒缓的作用,衬托出孔子作为长者迂徐含蓄的情态。又如《泰伯》载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也”表示判断,“已”表示肯定,再用“矣”收束,三个语气词连用,表达了肯定无疑的意思。《论语》对话体语录还运用了其他语气词,诸如“也已”、“也夫”、“也哉”、“也与”、“也者”、“矣夫”、“乎哉”、“而已”、“矣夫”、“矣哉”、“云尔”、“也与哉”、“云乎哉”等等,这些语气词在摹写声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战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论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散文语言由普通书面语进一步向民众生活口语方向发展。《论语》的语言不仅与殷商典诰语言有天壤之别,而且比《国语》语言要浅显、平易得多。需要说明的是,《论语》的浅易并不意味着平淡,恰恰相反,它是以浅易的语言形式表述深刻的思想,而这,正是文学语言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三、战国诸子的文学传播促进语言浅显化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围绕着如何重建一统天下的主题,战国诸子百家各开户牖,各种思想学说蜂出并作。与此相应的是,思想传播事业进入了如火如荼的时代。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诸子百家朝夕奔走,攘臂游说于世。由于当时游说者太多,而各国诸侯贵族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也缺乏很好的耐性,因此,如何抓住万分宝贵的游说机会,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诸侯贵族轻松愉快地听懂并接受自己的观点,就成为每一个游士说客都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如果游说之辞成功地打动了人主,那么不仅游说者本人可以实现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人生梦想,而且可以坐在廊庙之内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平治天下。传播言辞既然如此重要,那么诸子百家就必然会绞尽脑汁地钻研语言艺术,力求运用最浅显、最生动、最易懂的语言来传播深刻的思想观点。诸子百家的游说之辞,有的是由游说者门人弟子当场记录下来,有的则是在事后由弟子或本人补记。无论是现场实录还是事后补记,都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这样,诸子口头传播的某些特点,诸如口语化、浅显化、形象化等等,就会如实地反映到书面传播之中。当然,战国也有一些不屑于、不善于或不需要游说的诸子学者(如庄周、韩非、稷下学者以及吕不韦门客等等),他们更乐意采用纯粹书面传播的方式。这种书面传播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力把文章写得很艰深,因为作者同样要考虑如何让读者轻松接受自己观点的问题。因此,那些伏案写作的诸子也像那些游说之士一样追求语言的生动浅显。口头传播讲究把话说得形象易懂,书面传播力求做到语言的平易生动,这样就蔚成一种时代风气,一种把深刻的思想往浅易里说的时代文风。我们注意到,战国确有少数诸子试图写语言深奥的文章,但这些文章的传播效果都不够理想。例如,墨家后学创作了精练简古的《墨经》,从字面上看似乎《墨经》应该比墨子其他散文更为重要,实际上墨家真正有广泛影响的是墨子那些讲述“兼爱”、“非攻”等十大纲领的文章,而绝不是高深难懂的《墨经》。名家的文章也比较难读,这限制了他们的学说在战国的传播,《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名家文献,仅有五家二十九篇。这些名家作品后来相继失传,像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公孙龙的学说,我们仅能从《庄子·天下》中见到只言片语。我们完全可以说,语言的深浅难易,是决定战国诸子散文传播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诸子在进行口头传播时是怎样浅化语言的呢?首先,他们多用日常口语进行交流。如《墨子·公输》载墨子止楚攻宋:“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2]295墨子是出于“兼爱”、“非攻”的思想而止楚攻宋的,但他并没有对楚王、公输盘讲一番深刻的“非攻”道理,而是在轻松的口语交流中折服对方。其次,在需要正面地讲述道理时,诸子们尽量避免运用难字,而是化深为浅,化繁为简。如《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对是否变法犹豫不决,商鞅劝秦孝公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惊于民。语曰: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3]1商鞅首先指出,要想成就大事,必须打消顾虑。然后说某些高明的谋略在一开始必然不为民众所理解。这一节没有任何生僻文字,也没用什么典故,说理透彻而语言简明。第三,为了使自己的传播明白易懂,诸子说客往往从诸侯贵族的身边琐事说起,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阴阳五行家驺衍“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4]2344。《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对齐宣王传播王道学说,而齐宣王却醉心于霸道,怎样才能唤起齐宣王对王道的兴趣呢?孟子先讲了一个齐宣王本人“以羊易牛”的小故事,以此说明齐宣王富有仁心,而仁心就是实施王道仁政的前提条件。《战国策·楚策》载庄辛劝谏顷襄王疏远奸臣,从蜻蛉、黄雀、黄鹄一直说到蔡灵侯,再说到顷襄王本人,直说得顷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慄”。这样的口头传播,基本上不存在任何语言理解上的障碍。第四,通过设譬取象进行传播,这是战国诸子用得最为娴熟也最为成功的传播技巧,也是浅化语言的最有效手段。诸子设譬取象的方式方法很多,有时是随手拈来的比喻,有时是以古讽今,有时是运用寓言故事。《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游说梁惠王,梁惠王询问孟子,为什么自己尽心治国,却看不见魏国人口增长。孟子回答说:“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何如?”[5]31孟子没有正面剖析魏国为何人口没有增长的原因,而是随机以战场上五十步笑百步为喻,说明相对于其他诸侯,梁惠王之所谓尽心治国,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孟子的比喻于直白浅易之中寄寓了丰富的批评、讽刺意义,给贪婪而又虚荣的梁惠王注入了一针清醒剂。以古讽今是诸子传播的常用方法。《战国策·秦策》载秦武王使甘茂为将,甘茂担心朝中奸臣进谗,便给秦武王讲了一个历史故事:“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踰墙而走。”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甘茂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为臣之投杼也。”[6]150甘茂通过以古讽今,成功地与秦武王盟誓,从而解除了后顾之忧。战国诸子善于用通俗的寓言来讲述深刻的道理。《战国策·燕策》载赵国试图讨伐燕国,策士苏代给赵惠文王讲了一个鹬蚌相争、渔父得利的寓言故事,然后指出:“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6]1115这些用做譬喻的事物大都通俗浅显、生动形象,用于口头传播之中,可以化理性为感性、化艰深为平易、化抽象为形象,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功效。
战国诸子的书面传播也有向口头传播靠拢的倾向。在能够运用平易词语的情况下,他们决不会采用艰深的词语;在能够使用日常词语的情况下,他们决不会选择生僻的词语;在能够把道理往浅显里说的情况下,他们决不会往深奥里说。他们不屑于故作高深,不会卖弄学问,不会写那种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如,《邓析子·无厚》云:“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惟亲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亲疏,三累。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一责;居大位而不治,二责;理官而不平,三责;御军阵而奔北,四责。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以安国。”[7]1这是名家的论述文字。《慎子·内篇》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8]2这是法家的说理文字。《鶡冠子·博选》云:“故北面而事之,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十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指挥而使,则厮役者至;乐嗟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故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主与徒处。”[9]2这是兵家的说理文字。《吕氏春秋·爱士》说:“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于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10]82这是杂家的政论文章。说天下大事,道平常之语,思想上往深处发掘,语言上往浅处努力,是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为了让读者明白易懂,诸子们在摆事实讲道理时往往从百姓身边生活取材。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11]204~205韩非认为人性都是利己的,君臣之间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君主不能指望以伦理道德来要求人臣忠于自己,而必须用利益来引诱人臣为自己服务。他以雇人耕种为例,如果主人给的工钱多,伙食好,那么雇工们干起农活就会卖劲,这就将“利之所在,民归之”的道理讲清楚了。诸子的书面传播多如此类。
为了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战国诸子百家在语言方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由此巩固并发展了由《论语》开启的口语化、浅显化、形象化成果,使战国文学语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浅易、生动、形象为特色的阶段。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文学语言虽有骈散之分,但大体上沿袭了战国文学语言的特点。
与近现代文学语言革命相比,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似乎是自然而然,它没有学术领袖人物的提倡,没有语言革命的口号与纲领,没有任何人为的安排,一切都似乎是大雪无痕。其实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取决于传播:是孔门先生讲、弟子记的特定传播方式奠定了《论语》的口语化特色,是口头传播的浅显、生动、形象、易懂的要求决定了某些战国诸子散文的浅易语言风格,是传播的需要决定了某些战国书面传播向口头传播靠拢。传播像一只无形的手,决定了战国文学语言的发展方向。在此前的文学研究中,传播因素较少受到学者关注,人们都知道战国文学语言通俗易懂,但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本文从传播角度讨论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揭示传播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意在引起学者对传播在文学发展中地位的关注。
[1]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孙诒让.墨子闲诂[M]//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3]商鞅.商君书[M]//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6] 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 邓析.邓析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 慎到.慎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鹖冠子.鹖冠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吕不韦.吕氏春秋[M]//诸子集成本.高诱,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
[1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I206.2
A
1001-4799(2011)05-0047-06
2011-05-08
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GD10CZ05
陈桐生(1955-),男,安徽桐城人,曾任教于湖北大学,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熊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