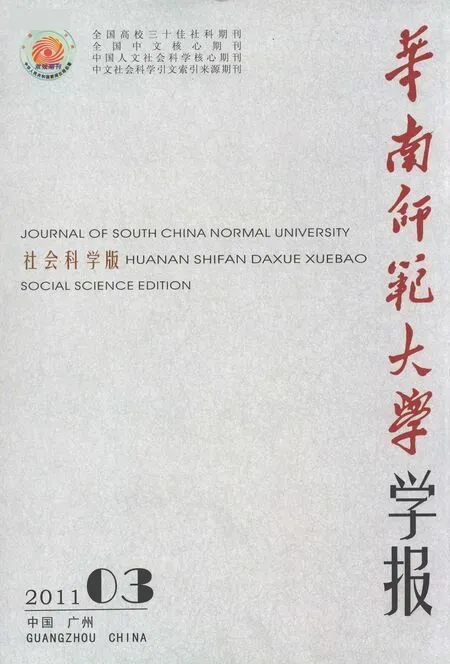陈白沙传道的语言困境与出路
卓进,王建军
(1.内江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内江 641000;2.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陈白沙传道的语言困境与出路
卓进1,王建军2
(1.内江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内江 641000;2.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在陈白沙的哲学思想中,“道”是一自身合目的性的至上存在,修道成圣是他教育理念的核心追求。然而,这种至上的道却又是无法言说描状的,圣贤的典籍也无益于道的修证。白沙认为“道”在心中,教育的任务不在于言说描状道,而是设置环境从而形成一特定心境,让心中固有的道自然活泼地呈现,这丰富了语言与教育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陈白沙 传道 语言困境 境语 诗语
陈白沙(1428-1500年),名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人,明代心学家。在儒学思想史的序列上,陈白沙作为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学术转型过渡性人物,为学者关注。但陈白沙的心学体系还是有其独特性,他提出了关于修道的内圣价值取向,并实践非语言教育传道方式,丰富了中国的教育传统。
一、修道的意义与传道的语言困境
陈白沙在传道问题上会出现“语言困境”,主要是由于他对“道”的独特体悟而导致。在中国传统语境中,“道”是万物存在的根由,是最抽象而又难以言传的存在,得道成为圣人也成为宋明理学家的终极追求。遵循修道成圣的理学传统,白沙赋予了“道”以形而上的极高地位。但由于白沙的隐逸主义价值取向,在内圣与外王的取舍上,白沙与朱熹、陆九渊,以及后来的王阳明、湛若水都不同,他赋予了得道本身的至乐意义,突出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消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赋予了得道本身的自足性。按照现代术语表达,即教育不是为了政治、经济等社会功能服务,而是为了人本身。陈白沙体悟道的这一特征与当时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理学家注重通过“内圣”,达到清整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外王”;而明代以来程朱理学作为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存在,知识分子对政治伦理问题的言说批评空间被压缩,“外王”功夫已淡出知识分子的关注视野之外,反是明初以来士大夫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成为理学思考与解决的新问题。在此背景下,陈白沙在思考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对原始儒家的精神和人生价值进行冷静的反思,成就其“自得之学”,凸现得道的“乐境”意义,赋予了修道以自足性,赋予得道以“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超越价值。①《陈献章集》卷二,第21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一)修道的意义在于体悟“至乐”
得道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这是白沙心学的核心。白沙赋予“得道”以超越得失的“至乐”意义:“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增损于我矣。天下之物尽在我而不以增损我,故卒然遇之而不惊,无故失之而不介。”②《陈献章集》卷一,第54-5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在白沙看来,得道者能够超越富贵、贫贱、死生、祸福,达到与天地同一的境界,由此也就达到了自得的至乐境界。自得在此既是一种治学方法,也是一种超脱于功名利禄、天地万物之外的自足自洽的高妙精神境界,获得者也就拥有了至上的快乐而无需外求。“得道”的意义在于“把握操持万化枢机”,在于“道乐”的至上境界;白沙通过“得道”者的“自得”或“洒落”或“至乐”的存在,为“得道”赋予了无需凭依挂靠的自身合目的性。诚如陈来先生所言:“陈白沙为明代心学的先驱,不仅在于他把讲习著述一齐塞断,断然转向彻底的反求内心的路线,还在于他所开启的明代心学特别表现出一种对于超道德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精神境界的主要特点是‘乐’或‘洒落’或‘自然’。”①陈来:《宋明理学》,第19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白沙心学体系中,得道的目的是至乐,通过至乐又可以有助于领悟道境,“乐”既是得道的目的,也是得道的路径,“以道为乐”、“寻乐得道”是相互达致的,“道”与“乐”共同构成白沙心学的核心。
(二)“道”无法言状,当求诸心
由于白沙不尚著书立说,我们只能在《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等极少数文献中看到他对“道”的阐述。白沙认为道至高至上,囊括并超越了天地万物,“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相侔亦。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侔哉?”延续古来“道”不可言的传统,白沙认为超越性的“道”,是无法用具体语言描述来形状的:“或问:‘道可状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于可言则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试言之,则已非我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言状,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于形,道通于物,有目者不得见也。何以言之?“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物不足状也。”②《陈献章集》卷一,第56、68、20页。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白沙的“道”存在于天地之间,而又超越天地之外;任何言语物状都无法描摹道的存在,只能通过一种妙不可言的洞彻天地万物的心理体验来感受和体悟,这种体验只能靠人心自去感悟体会,而不能用言语来描述传承。
“道”不可言状和心中自有的特点,决定了“道”不可求之典籍,而要求之吾心,从而形成与朱学迥异的修道路径。朱子认为“理”是普遍蕴涵在万事万物中的终极道理,通过对各种分殊之“理”的体认和把握可以彻底领悟终极的“理”,而具体路径则是通过读书格物,“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最后达到理的豁然贯通。与朱子相反,白沙认为今日格一物,明日明一理的方式无法得道,“道”是无法积累达致的,白沙说:“夫学有由积累而至者,有不由积累而至者;有可以言传者,有不可以言传者。夫道至无而动,至近而神,故藏而后发,形而斯存。大抵由积累而至者,可以言传也;不由积累而至者,不可以言传者。”③《陈献章集》卷二,第131、131-132、192页。没有主体觉悟的书籍填塞教育,不仅不能帮助悟道,而且还会成为主体悟道的障碍。白沙看到,当时教育注重背诵圣贤典籍,虽然六经背得烂熟,却领悟不到其中的奥妙,针灸时弊,白沙遂塞断著述,反对读书悟道的传统,如白沙弟子张诩说,“先生尝以道之显晦在人而不在语言也,遂绝意著述。”白沙赋诗说:“他年傥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又说:“莫笑老庸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④《陈献章集》附录三,第88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白沙在大量的诗句、书信表达了“道”不可言说描状,无法由读书达致的观点。对此,陈白沙发出呐喊的声音:“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辞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乱人也,君子奚取焉?”⑤《陈献章集》卷二,第131、131-132、192页。
陈白沙一反朱子学读书穷理的求道路径,提出“为学当求诸心”的求道新路径。“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⑥《陈献章集》卷一,第56、68、20页。。由此,白沙提出不要求诸书,而要求诸吾心,遂倡自得之学。“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⑦《陈献章集》卷一,第56、68、20页。
二、自然为宗的得“道”方法
既然得道由吾心,如何让本心中的“道”活泼流畅、无所窒碍的流出,成为白沙功夫论和涵养论的重要命题。白沙认为只有此心活泼自在,没有外在的牵缠,心中的“道”才能自然流出。白沙非常看重“自然”境界,他对湛甘泉说,“此学以自然为宗者也”,“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⑧《陈献章集》卷二,第131、131-132、192页。黄宗羲称白沙“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⑨(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白沙的“自然”在形上意义上是指“心灵的自由,不受牵连制累,也就是无滞”①陈来:《宋明理学》,第194页。。陈来还指出了“自然”在白沙心学中既是追求的精神境界,也是达到此种境界的功夫。
白沙通过老庄的内外两忘方式,来让此心得以自然无滞,他说:“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此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②(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 89、89、2、92、104页。白沙绝意科举功名,在春阳台中静坐几年,斩断各种外在缠绕,终于有了第一次悟道的飞跃。“于是舍彼之烦,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③《陈献章集》卷二,第145页。白沙后来又拓展悟道的路径,由静坐而至于优游自然之中,弟子张东所说:“(白沙)自见聘君归后,静坐一室,虽家人罕见其面,数年未之有得。于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盖主静而见大矣。由斯致力,迟迟至二十余年之久,乃大悟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一真万事,本自圆成,不假人力。无动静,无内外,大小精粗,一以贯之。”④(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 89、89、2、92、104页。白沙由“静坐”以及“弄艇投竿”的动静结合,捐耳目,去心智,修习着道家式的修行方式,悟得了自己的“道”。
白沙在修道的过程中,在博览经籍而无所得后,后来又采用静坐体悟,再到动静结合的悟道过程中,白沙总结出以静为门户,以自然为宗的心学修炼法门。经过长期的沉潜研修,白沙感受到了“道”体的存在。但是,由于道的无法言说描状性,如何接引学者悟“道”就成为陈白沙教育传“道”的语言困境。
三、“境语”、“诗语”的传道途径
白沙的“道”不可言状,也不可给予,只能靠学者的自我修证体道,方能“自得”自成。黄宗羲称白沙之学,“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⑤(清)黄宗 羲:《明 儒学 案》 ,第 89、89、2、92、104页。湖北嘉鱼的李承箕不远千里来江门师从陈白沙,“白沙与之登临吊古,赋诗染翰,投壶饮酒,凡天地间耳目所闻见,古今上下载籍所存,无所不语。所未语者,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见闻承当也”⑥(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 89、89、2、92、104页。。白沙如何将这种“不可言状”的道,通过“言说”启导接引学者,存在一个内在的逻辑困境。语言不能描述模状道,所以,诵读典籍无益于道。佛学特别是禅学早已认识到了“道”的语言学的困难,语言在传递意义的同时,又遮蔽了意义。但人总是要靠语言来传递这份超越“语言”的道,所以禅宗就通过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艺术语言,如诗偈的形式,或者语势兼用的传释智慧,来解决语言与实在之间的紧张关系。语言本身并非道,但通过语言的指引,能够指出一条见道之路,引导学者自证、自悟或自得。陈白沙在潜泳暗收禅宗的传道方式的同时又有所摈弃,他没有走上禅宗的离奇语言的建构或棒打雷喝式的语势并用,他说,“得山莫杖,临济莫喝。万化自然,太虚何说?”虽然太虚是无言的,但陈白沙还是吸取了禅宗的诗性语言的“言说”方式,辅助对体道之“境”的选择和设置来实现“不可言说”的道的传导启迪。简言之,白沙是通过“境语”和“诗语”两种智慧的传道方式来完成传道的教育任务。
白沙注重“境语”,特别注意去除外在的功名利禄对心的缠绕牵缠。因此,凡入白沙之门的弟子也多厌弃科举官场,形成了一种隐逸主义的团体。这种弃绝人事、专心体道的传统始自吴与弼,至于白沙则有坐小庐山十年,足迹不出于阈外,谢弃朝廷征召举荐。正如黄宗羲言“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白沙弟子多不入仕,如贺钦、张诩、湛若水、陈庸辈皆然。因弟子林光做官入仕,白沙责其“因斗升之禄以求便养,无难处者,特于语默进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决,遂贻此悔,胸中不皎洁磊落也”⑦(清)黄 宗羲:《明儒 学案》 ,第 89、89、2、92、104页。。王乐用以御史退居二十余年,后来起用为广东佥事,不满一年就被考察去官。陈白沙送给他的一首蕴涵批评与安慰的诗,标明了白沙对入仕和入道的取舍,诗曰:“可可可,左左左,费尽多少精神,惹得一场笑唾。百年不满一瞬,烦劳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辈人,达塞一齐觑破。归来乎青山,还我白云满座。莫思量,但高卧。”⑧《陈献章集》附录一,第70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毋庸置疑,白沙及其群体的退而不仕并非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而是其对“道乐”价值体系追求的选择。
要进入白沙设定的“道”中,就必须弃绝外在世俗纷扰对此心的牵缠。只有弃绝功名,塞断讲习著述,“无令半点芥蒂于胸中,然后善端可养,静可能也。”①(清)邓淳:《粤东名儒言行录》卷五,第13、13页,道光辛卯年养拙山房藏版白沙正是通过这种外在环境的设置来形设体道的心境,通过各种自然的“境语”来释放心中自有的真道,达到接引学者入道的教育启迪。早期的白沙注重通过“静坐”来设置“境语”。陈白沙在阳春台静坐数年,悟出“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的求道之方,涣然自信“作圣之功”在于静坐,白沙说:“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非务为高虚以误人也。”②《陈献章集》卷二,第 145、156、133、162、155 -156、190 页。陈白沙自言,“老拙每日饱食之后,辄瞑目坐竟日,甚稳便也。”③《陈献章集》卷二,第 145、156、133、162、155 -156、190 页。由于白沙注重静坐,教授生徒多用静坐,黄宗羲称白沙之学是“以静为门户”。④(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9、98页。如弟子林光说,“先生教人其初必令静坐以养其善端”。⑤(清)邓淳:《粤东名儒言行录》卷五,第13、13页,道光辛卯年养拙山房藏版又如白沙对林友说,“学劳扰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⑥(明)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三,第269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在给贺钦的信中,白沙称,“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端倪来,方有商量处……但只依此下工,不至相误,未可便靠书策也。”⑦《陈献章集》卷二,第 145、156、133、162、155 -156、190 页。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9、98页。贺钦遵循白沙的教导,构小楼读书其中,随事体验,未得其要,潜心玩味,杜门不出者十余年,悟出“实理充塞无间,化机显行,莫非道体。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实理,吾人之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寻其所谓本然者而已”⑧《陈献章集》附录一,第70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为了有一个好的静坐环境,白沙弟子多专门构筑小屋,避开家庭人事的缠绕,得以专门静坐养圣。在张诩求静而不可得时,白沙就建议其构小屋别居以求静,“承喻。求静之意,反复图之,未见其可,若遂行之,祈益动耳,恶在其能静耶?必不得已,如来喻构所居旁小屋处之,庶几少静耳”⑨《陈 献章集 》卷二 ,第 145、156、133、162、155 -156、190 页。。弟子伍光宇,就在居所背面的岩亭中静坐修道,“岩亭,高不盈一丈,其中阒寂,视之窈如也。而君以夙疾未除,齿发日耗,其为学也,盖不能无日暮途远之忧,便杜门息交,不择远近为趋舍,凡平居一切与往还者,皆抗颜谢焉。入处于亭,焚香正襟,迭坐竟日,闻者异之。”伍光宇还在白沙居所旁边筑草屋三间,号寻乐斋,专门用来习静养圣,并戒嘱家人“吾不可去白沙。吾其斋戒有事于家庙,吾疾作须扶持,吾乃归一日二日,小健吾当返,慎无以家事累我”⑩《陈献章集》卷一,第103-104、87页。。
除了静坐,白沙还依靠在自然中静居观物、悠游大自然、寻乐等其它途径来设置“境语”,来接引学者悟得“无法言说”的道。
陈白沙过着接近自然的隐居自适的生活,他学陶渊明种田采菊,游目高原,披怀深林,与禽鸟作伴,与鹿豕相游。他在给一个处士的墓志铭中论说了这种静居的优处,“无声色嗜好以乱其耳目,无形势奔走以渎其交际,无是非毁誉以干其喜寂”⑪《陈献章集》卷一,第103-104、87页。。白沙在大量诗文里,流露出对自然隐居生活的向往,在《东圃诗序》中更具体而细致地摹画了一幅隐士的行乐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氏隐居生活,正是“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的悟道最佳清境。
除了静居观物的体道,白沙与其弟子优游于大自然中,通过自然中的放浪俯仰之间,达到内外两忘的悟道之机。白沙讲学江门,常与诸弟子优游山水,“江门洗足上庐山,放脚一踏云霞穿。大行不加穷亦全,尧舜与我都自然。”⑫《陈献章集》卷四,第325、27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白沙弟子经常访游于名山大川之间,如左廷弼游罗浮山,白沙致书曰:“秋且尽矣,拉何山人驾扁舟出扶胥口,东望罗浮铁桥之胜,遂登飞云,访朱明洞天,此其时乎!因想足下能飘然自适,益觉某之匏击于病为可厌也。近稿十数首录在别纸,早晚东游,则此纸或可随行。有至飞云顶,且令从者歌之,为我通一语于山灵也。”⑬《陈献章集》卷二,第 145、156、133、162、155 -156、190 页。白沙自己也念念于罗浮、衡山之行,而终未能如愿,只好在想象之中神游名山,他在给湛若水的信中称,“飞云之高几千仞,未若立本于空中,与此山平。置足其颠,若履平地,四顾脱然,尤为奇绝。此其人内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气浩然,物莫能干,神游八极,未足言也”⑭《陈献章集》卷二,第 145、156、133、162、155 -156、190 页。。置身于大自然中,“内忘其心、外忘其形”的内外两忘正是白沙所追求的“自然”境界,在《湖山雅趣赋》中,白沙再次提到“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的湖山优游中,“当其境与心容,时与意会,悠然而适,泰然而安,物我于是乎两忘,死生焉得而相干,亦一时壮游也”⑮《陈献章集》卷四,第325、27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白沙正是通过弟子们在大自然中的内外两忘来实现“道”的体悟。
陈白沙最心醉于“勿忘勿助,鸢飞鱼跃”的自然境界,而这一境界承继自曾点到孟子的自然“乐”境。如果说周敦颐从“以道为乐”的层面解读颜渊之学,陈白沙则在“以道为乐”的层面之外,还多出“以乐得道”的层面来解读曾点之学。白沙以为心学最难处即在达致此心“何思何虑”的自然状态,他说,“治心之学,不可把捉太紧,失了元初体段,愈认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漫,漫则流于泛滥而无所归。”①(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第881页。要使此心达到“何思何虑”的自然之境,白沙以为除了静坐养睨、居游自然,最直截有效的法子就是寻得曾点的“浴沂舞雩”之乐。
在陈白沙与诸弟子的交往中,多有曾点“浴沂舞雩”式的乐事,他与李承箕的“登临吊古,赋诗染翰,投壶饮酒”即是例证,而白沙与弟子伍光宇的交往更充满了对“曾点之乐”的寻觅。伍光宇师从陈白沙,在白沙居所旁筑草屋三间,号曰寻乐斋,常与白沙弄艇投竿于江中,寻“曾点之乐”。白沙在《伍光宇行状》中记:“南山之南有大江,君以意为钓艇,置琴一张,诸供具其中,题曰:(光风艇)。遇良夜,皓魄当空,水天一色,君乘艇独钓,或设茗招予共啜。君悠然在艇尾赋诗,傲睨八极,予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啸,飘飘乎任情去来,不知天壤之大也”②《陈献章集》卷一,第103、11-12、16页。。
据白沙自言,会从这种“曾点之乐”中悟出大道,“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安事推乎?”白沙的“道”之所以能从这种“乐”中来寻,关键在于“此理包罗上下,贯彻终始,滚作一片,都无分别,无尽藏故也”③《陈献章集》卷二,第217、172页。。这种浑沦无分解的“道”是无法通过意识的条分缕析而获得,只能通过“勿忘勿助,鸢飞鱼跃”的自然境界中体得,而“曾点之乐”既是达到此种境界的路径,又是达到此种境界的表征。
虽然“道”不可言,但白沙还是保留了诗的语言对道的领证觉悟作用,在白沙教学中,大量使用“诗语”。湛若水称“白沙先生无著作也,著作之意寓于诗也。是故道德之精必于诗焉发之”④《陈献章集》附录一,第699、700页。。陈炎宗说白沙“不著述,独好诗。诗即先生之心法也,即先生之所以为教也”⑤《陈献章集》卷二,第217、172页。。白沙尝试着用“诗语”的形式来描绘传神玄妙难言的“道”,自他以《此日不再得》名震京师,到他辞世,白沙留下的诗文不下万余首,在他辞世前还做诗曰:“托仙终被谤,托佛乃多修。弄艇江溟月,闻歌碧玉楼”。⑥《陈献章集》卷一,第103、11-12、16页。 《陈献章集》附录一,第699、700页。
陈白沙通过诗来自由地抒发人的真性情,要通过自然日常之事的吟咏见得自然真道。言为心声,通过“诗语”就得以自由地流露此心的真性情。诗从此心之中流发而出,就可达到“动天地、感鬼神”的“天人合一”境界,白沙就把诗的妙用与“道”的体认紧密相契起来,“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会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枢机造化,开阖万象,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⑦《陈献章集》卷一,第103、11-12、16页。
陈白沙援诗学入儒学,通过“诗语”呈现“鸢飞鱼跃”之机,以诗运思,以诗呈心,以诗证道,形成了自成一格的传道方式。他常同学生一道游山览水,触景生情,因情为诗,一唱一和。如陈白沙与李承箕诗酒唱和,“时时呼酒与世卿投壶共饮,必期于醉。醉则赋诗,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积凡百余篇。其言皆本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赞毁”⑧。陈白沙经常把自己即兴所得之诗寄与朋友、弟子,冀其讽咏体道,通过书信与诸弟子探讨诗文,启迪弟子“以诗证道”的悟道之径。白沙要走诗教的传道途径,所以,也就有许多白沙与弟子论如何做诗的道理。陈白沙随意施教,不立课程;但为了“诗教”,白沙还是花了不少精力“教诗”。白沙与其弟子论如何做诗的书信很多,仅他通过书信对张诩的诗进行细致的批答,往来往往达数十次之多,可见,他非常重视诗的悟道路径。
结语
对明代以来背诵圣贤典籍,鹜于科举辞章的学风,白沙心学具有风气为之一变的时代意义。搁下书本,放下名利,与天地自然对话融合,体悟天人合一的大道,无疑有其永恒的意义。当然,白沙提出的塞断读书著述,但求诸心,以静为门户,以自然为宗等修道主张,则是离不开白沙前期的博学于文积淀。在白沙门下弟子中,多是学业已有根基或小成,又困于不能更上一层楼的修学之士;白沙的先觉先悟启迪引导了这群特殊的学生群体。
陈白沙通过静坐涵育,养其澄明虚静之心,在日常万物生生化化的自然流行中体悟心中大道,用诗歌讽咏的“诗语”来表达传递这种难以言传的对“道”的感悟,通过“境语”和“诗语”来传递玄冥难言的“道”,丰富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实践。
Languag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for the Education of CHEN Baisha
(by ZHUO Jin,WANG Jian-jun)
In CHEN Baisha's philosophy,the aim of the“Dao”is itself,and it is the supreme being.The core of his education concept is being a saint by preach.However,such supreme“Dao”couldn't be described by the language.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of saints couldn't help the cultiv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Dao”.CHEN Baisha considered“Dao”as being in the heart,and the task of education is not to describe“Dao”by language but to set the environment for special feel of our heart.And then,“Dao”in the heart expresses naturally.It enriche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CHEN Baisha;preach;language predicament;language of surrounding;language of poetics
卓进(1979—),男,湖南慈利人,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2011-01-10
E40-09
A
1000-5455(2011)03-0056-05
【责任编辑: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