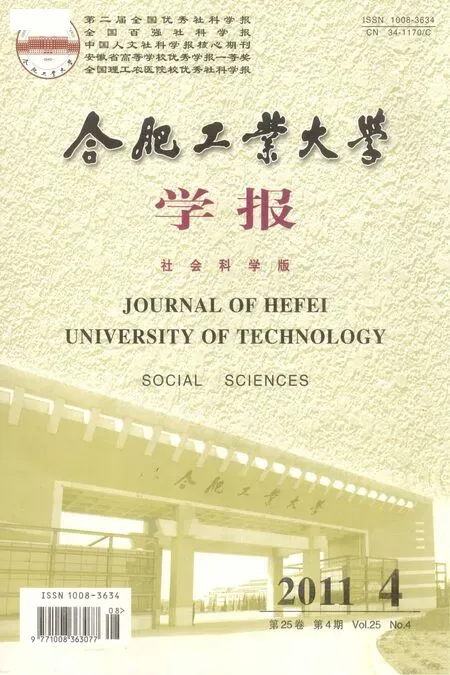文明变革图景中的技术理性重构
熊小青
(赣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文明变革图景中的技术理性重构
熊小青
(赣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农业技术体系建立以后,文明不仅是人类优秀成果的凝结,更是一种创建,是基于人的生存现实的反思和超越。当工业文明以反生态的方式显现为对人的反动时,文明变革就有了必然性。在这种文明变革之中,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文明的表现,必然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这一改变表现为技术理性真正地为人化和属人化。
文明变革;技术理性;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环境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人类主体性黄昏的关注与现代性反思,技术及其技术理性必定是一个中心话语。这显然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以至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技术理性僭越成为社会主导思维方式和实践原则有关,也与现代技术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文化现象有关。温纳指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文化体系又构成了整个社会。”[1]当技术成为一种主导的文化乃至一种价值标准之时,技术及其技术理性就被人们理解为解决社会发展的主要乃至唯一手段,也成为了物质财富创造乃至“富民强国”的根本路途,随着技术被异化,人也置于危机之中。于是,人们以“人的被遮敝”或者“人的技术生成”等问题,从技术自身及其人性等诸多方面反思技术和技术理性,并提出了不同的技术控制图景。但是,技术理性在现有文明样式之中的深刻必然性和正当性,揭示了技术理性的反思不仅仅是技术自身的反思,也不仅是现有文明图景中的修补或“用”之纠偏,更多地是应该从文明高度即现有文明的正当性的视角加以探讨。
一、技术理性是时代的文明表现
“理性”(Reasou)一词源自于拉丁文Ration,是计算、帐目、理由之意,它是指依据一定法则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也指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理由和根据。笼统地说,理性意味着比较、判断和推理,是人运用先在的知识和经验而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因此,理性更多的是求真范畴。“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式的正确’……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2]因此,如果说科学更多地关注“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那么技术更多的是“做什么”(do what)和“如何做”(how to do)。正如邦格所说,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也就是说,技术理性就是在一种求效和求用的思维之下对物质世界的为人化。
“当人类有意识地打制出第一把石器,并通过它来获得并加工野生食物时,意味着原始技术开发活动的开始。陶器被发明和制作,人类技术史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开始了。”[3]技术和技术理性成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在技术理性的不断启蒙和训练之下不断显现出来。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使人类社会进入铁器时代——农业技术体系建立以后,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即农业文明出现之后,人的主体性开始了显意识状态出现。人类在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之后,在关注“天”(自然)的同时开始了关注人自身,也由此建构了以对人自身生存的意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文化体系。如果说在这之前,技术仅仅是人类经验的积累和潜意识的表现,是人类出于人本能地超越动物的无意识的简单表现,那么在这之后,技术及其体现出来的技术理性就与人对自身生存的认识包括自身生存意义紧紧结合在一起,并且服从于人的生存,也就是说,无论是技术及技术理性还是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体系都完全服从于已经建构起来了的社会文化体系即一种文明内涵和样式。如果说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技术的进化推动人类的进化”是从早期技术对人类影响而言,那么“人类的进化推动了技术的进化”无疑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反映。
以工程建筑为例。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有限,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是技术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技术仅仅是人实现生存的基本手段。建筑,这一体现着肉体存在之安身之所与灵魂之安宁之处的地方,在农业文明这一天人一体、灵肉相融的时代,建筑技术充分体现了实用特征而被推向了辉煌,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同样,水作为农业社会的命脉,在农业社会的地位决定了技术的发展。与水有关的,如中国民间的大禹治水、都江堰的江水分流、灵渠修建、江河之上的桥梁建造等等,极大地推进了水利技术的发展。无论是治水和建筑技术,它们立足于所具有的物质条件以更有效地为人使用的样式呈现出来,因而古代农业社会的建造技术主要体现为坚固、实用的特征,体现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巧妙构思的建筑原则,表现出与生活直接相关的为人性和与人亲近和善的人文情结。古代城区和街道在实用的同时体现出充分的人文传统也是极好的例证。“自古希腊和古罗马以来,街道和城市街区就一起是城市生活的基础。街道向来有综合的功能:生活空间、运动场、剧场、生产车间、商品市场、交通运输联结点。”[4]这在今天的技术理性之下的城市空间规划或功能规划来看,显然是无法想象和理解的。但恰恰是这样的设计,体现着技术的手段、功能在那个时代的为人性。
工业文明时代,文明被技术和技术理性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所诠释,技术和技术理性在其物质形态上表现为被“制造”的“人工物”、“大机器”等。农业文明时代直接来自于自然之中的“石块、木头、手工制作的砖瓦建筑材料,被水泥、钢筋、玻璃等工业材料所代替,制造经验被结构力学所代替,钢筋混凝土结构、悬索结构等现代结构代替了传统建筑的砖木砖石结构,以采用大量预制件、现场组装和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施工替代传统的手工营造……”[5]这种建筑及其技术上的变化的根源,在于工业文明所确立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在于“人是目的”的价值设定。随着持续地作用于自然界,人自身在经验的基础上确立起了主体性,从而也确立起了自然为人化和自然是死的质料的自然观。人对自然的任何改造、征服获得了正当性,也使人获得了任意按人的需要或意愿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组装、剪裁的思维模式。随着这种组装、剪裁的应用,技术作为一种“机械力”(牛顿把自然界的一切变化归结为力)获得了巨大的彰显并深刻地影响着技术的进程。一是人对物质世界的人化力度大增,表现在对物质世界征服的广度和深度的认识和改造上,如各种大型的水电设施、原子能、基因工程、深海勘探等;二是激发了人对物质世界的更加强烈的占有欲,使人直接确立起了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体现着现代文明的深刻本质的核心话语如征服欲、占有欲以及自然的为人性等观念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此时,技术在其发展道路上原有的各种人伦禁忌、价值理念或者是技术环境中的次要因素统统被作为干扰因素清除出去了。技术拒绝人文,技术也不要情感,技术只有能不能的问题,没有应不应该的问题。于是,技术高歌猛进,宏观上如空间技术对太空的人为扰动,微观上如分子生物技术对微观世界的干预;深海中,深潜水技术对海底世界的人类印记,等等。技术在获得巨大作用和进步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影响人的自我发展意识以至于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沉迷于对技术的膜拜,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着技术的发展:建筑高楼,并非为着人的居住,而是为着建筑技术的展示;城市交通设计定位,不是从市民出行方便着手,而是为着技术上的需要,等等。现代技术理性要求人们适合技术系统的内在逻辑要求而不是相反。正如马尔库塞认为的那样,技术规则即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权威的东西,规范着人们日常活动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自我发展意识。通俗地说,机器供养着人们,现实中的每一个体的血肉乃至灵魂都需要按照机器设备来制造。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6]这一切反人性的技术理性非但未引发人们对它的反对,相反,人们却接受技术对人的异化,拥抱异化人和对人反动的技术。人们对技术的盲从和追捧,使得技术理性成为当今社会意识形态,也成为技术高速发展的价值基础。
在工业文明引发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而遭到人们质疑的当今世界,人们从人与自然的本体意义和实践意义上深切感悟二者的关联。于是技术理性也出现了某些具有生态文明内涵的萌芽式转向,比如技术设计的人性化、技术理性的伦理意蕴、技术的价值引导等。然而,如果对技术的反思仅仅表现为进行一种对技术负面作用的纠正或修补,这显然只能是一种被动的、补救式的方式,其技术应用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工业文明的一种展示而已。
二、工业文明变革引发对技术理性合理性的质疑
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成为当今时代鲜明的思想特征,“现代性批判”就是其中的核心话语,究其根源就在于工业文明的反生态逻辑及其技术异化和技术理性扩张所形成的对人的反动。之所以说是反生态的,就是工业文明把自然当成是被动的存在物,是为人的存在物,从而人必然对其进行为人化的无限制改造,其结果必然破坏自然已有的规律。这是工业文明主客分离思维的必然结果。文艺复兴运动以降,随着人的发现,人与自然统一的世界被二分为人与人之外的自然界,人取代了上帝成为了主人、主体,成为了宇宙中的最高存在,自然界成了为人的存在、属人的存在。因而,在“我思故我在”的追问之下必然有了“人为自然立法”,从而自然这一被动的质料只是依赖于主体(人)才获得规定、理由及其价值。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工业文明表现为“制造文明”、“资本文明”和“机器文明”,也演变为“科学技术文明”、“贪欲文明”和“征服文明”。它们之间具有着内在逻辑性。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自然成为为人的客体,人的天然本性使人也成为了疯狂主体、野蛮主体,进而就有了征服、制造等。
工业文明之下的制造区别于农业文明下的制造,在于这种制造已经改变了农业文明以模仿自然、取于自然(非人工之物,自然之物形态而非内在结构改变)的方式,它是通过改变自然物的结构和性质而创造出新东西。刘福森教授指出:“首先把自然界整体联系割碎,从中选择部分有用的材料,再按照人的目的重新‘组装’,最后形成一个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人工物’”[7]。在这里,制造遵循着“有用”和“有效”原则,“有用”就是满足人的当下需要,这种需要包括生存性和奢侈性的需要。为着“有用”,“有效”问题就自然而然出现了。有效就在于使自然物快速地成为有用物,因而祛除一切无用因素成为了这一过程的基本逻辑。为此,就必须对自然物进行分解、破碎、筛选、祛除等,从中提炼出被人认为有用的东西,而同时把所谓的“无用”之物抛弃。这种“有用”之物通过各种去粗取精成为了“精美制品”,“无用”之物成为了“废物”。这种文化逻辑或技术逻辑之下所进行的“有用”提炼过程是非自然逻辑过程,无论是“有用”物还是“无用”物都是非自然物,其结果是,比如杀虫剂、塑料等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必然无法很快地融入自然循环(因其难以降解),“无用”之物如各种工业垃圾、废料,由于与原有系统割离,失去了内在的制衡因素而成为有害之物,最终它们都成为整个自然系统物质能量循环的障碍,成为了自然系统的垃圾。
工业文明下,“科学技术”必然强化成被培根认为的是拷打自然的有效工具,并拓展至社会所有领域被无限度运用。在资本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之下,掠夺资源和大量消费成为资本获利的基本支点,技术理性进一步彰显,技术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同时各种奢侈性消费、虚假消费、异化消费滋生,为着不断消化由技术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远超过生存所需的产品而大行其道。这些消费从本质上说就是浪费。
工业文明客观上推进了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为人们更好地适应自然奠定了基础。然而,工业文明的反生态逻辑——一种文化逻辑和资本逻辑而非自然逻辑地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如比尔·麦克基本在《自然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的,“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终极了自然,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欲求、习惯和期待”[8]。他认为今天的自然“不再是古典工业社会的概念”,而是“被文化整合了的自然”,因而不再是人类存在于其中的自然而然的自然。这种文化了的自然,打破了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系统的能量平衡、物质循环平衡和生态链平衡关系,人在长期与自然交往和对象化中所定格化了的人的生理结构与文化,已无法适应这一变化了的生态系统而使人类生存陷入危机之中。这一切都与技术理性的扩展有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奴隶,而奴役者就是现代技术。”[9]哈贝马斯认为,人依附于机器生成为物,科技是一切社会异化问题的罪魁祸首,甚至“技术已成了组织一切生命活动的方式”[10]。为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必须超越工业文明,必须反思工业文明。文明的转型即提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并在现实中建构之,在人的生存危机之中成为了必然。
因此,文明的变革和转型根源于人类的生存危机,是当下人们为摆脱生存危机而超越已有生存方式的集体意义上的生存自觉。针对人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拯救,在于工业文明之下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实践的超越。因此,修复和重建人的生存环境所引发的人们生存价值和生存实践即一种文明形态的变革,就成为一种人类生存智慧的必然结果。它表现在以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为最高准则,也就是说要维持一种与人类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生理结构相适应的自然系统。这种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文明建构元点、思维基点,从根基上决定了这一文明将更加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与工业文明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凸显的理论基点和最终反人类走向形成了根本区别。“对人的生存的肯定,对自然界在人之生存和发展意义的肯定,这不仅仅是对人是否有利或利有多少的考量,而且更是从人之安身、人之本性的自然回归等人之根本上的主观认识,是突破了仅仅从人之社会性实践性去肯定人之根本的思维模式,从而实现人自身全面解放的结果。人的生态生存,意味人并不是高于自然之物。”[11]实践准则的确立及生存价值的转向,必须把人的活动包括技术的应用或经济的发展限定在这一“边界约束”中,它要求技术及技术理性在属人上予以展示,属人意义的基点就是人的生态存在。这就强调了技术永远是人的主体性明晰和展示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压制人、折磨人和异化人的工具。
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充分彰显着人的主体性并且在人对之膜拜之后,展现为技术自主性从而导致了人的异化。它是一种仅仅把自然当作人化对象或征服对象的思维方式,一种反自然的技术逻辑的思维取向,最终推翻了人的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工业文明与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共同演绎了这一切。技术理性作为文明的一种表现方式,技术理性是“流”,只有“文明”是“源”,在工业文明之下技术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如此,也只有如此。因此,当人类为着生存和延续下去而进行反省之时,人的生态生存“边界”这一最高法则的确立,预示着工业文明变革和技术理性的重构成为了必然。
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技术理性重构
新的文明就其发生学而言,它不可能从工业文明内部合乎逻辑地发生,它不是工业文明的内生物。恰恰相反,它是人类在对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生存危机进行深刻反思之后的理性自觉,是人类拯救自我的理性建构,是人类的集体理性之自觉。正因为如此,这一理性建构被人们所期待、所理解。我们将这种新的文明称为生态文明。这是在经历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生存的唯一选择。“所谓生态文明,就是把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作为最高原则的文明形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始终是人类及其它生物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不仅成为人类生存的根本利益,而且是实现人类及其它一切生物可持续生存的最高利益。”[7]人类行为从其类本质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从人类自身利益出发。人的生态生存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人与自然之间尽管存在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是人类生存之必须,但是更应有适应和共生共荣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应该存有对自然养育之恩的感激感恩、敬畏甚至膜拜的情感。这一切无疑为生态文明之中的技术理性展现确立了基本点及方向,表现为技术理性应该遵循人的生态生存及其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基本原则。技术理性这一根本原则的确立,其合理性体现在技术无论如何是造福于人类、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工具。技术理性在追求技术的效益从而实现技术更强大的实用性、操作性和工具性的同时,应该深刻地把握住这些实用性、操作性和工具性的最终目的在于为着人自身的更好生存而并非对人的异化,甚至否定和反动。为此,生态文明中的技术理性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技术理性必须被自然存在论和自然秩序所统摄。工业文明中的技术理性立足点在于主体性,即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主客二分和人是绝对主体的本体论,简言之体现为属人性。但是这种属人性是建立在人类没有明天、不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因而其本质是反人类的、虚假的。工业文明之中的技术理性遵循的是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大量生产和大量浪费,效率越高,生产产品也多,同时为着资本增殖需要的异化消费也越多,最终浪费也越大。生态文明立足于人的生态生存即一种被环境所塑造、所规定的人的生存,因而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在这当中,人们不是用“人文秩序”代替“自然秩序”、用“文化选择”代替“自然选择”,而是在“自然秩序”和“自然选择”的统领和决定之下天然性地存在,因而是生态性存在这一物质前提决定下的实践存在物。
人的生态生存意味着人与自然在存在意义上的平等性和互惠性。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作为生态链上的一环,与其它存在物一样占据着生态位,发挥在这一生态位上应有的作用。这与工业文明的主体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及由此展示出来的征服文明所主张的“人为自然立法”迥然不同。生态文明要求技术理性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之下回归到本体论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平等关系,也就是说,终止近代工业生产中技术承担的“人工物”的制造——一种把“有用”物从自然界整体联系中割裂、抽象出来并进行组装的思维惯性。
然而,技术存在的合理性正是在创造“有用”的“人工物”当中体现出更高的效率,当“人工物”制造被停止,这是否意味着人需要返回到原始蒙昧的状况?答案是否定的。生态文明并非是渔猎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简单重复或回归,同样,生态文明下的技术理性也并非是要回到自然对人的奴役和人对自然的膜拜之中,不是通过牺牲人的主体性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恰恰相反,生态文明是以一种全面的、符合人的生态生存的技术理性来建构技术体系。这种技术所体现的理性始终是在自然存在论和人的生态存在基础上的展示,是在实现自然界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维护的前提下对自然实行人化或对象化。具体地说,当人需要从自然中获得“有用之物”时,应注重整个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并不因为“有用之物”的剥离而使生态系统表现为对人的反动性。因此生态文明中的技术理性即一种对自然的人文秩序、技术逻辑的建构是一种受限的建构,是立足于自然已有秩序上的人化建构。
其次,在实践意义上,人的生态生存的满足是技术理性的边界约束。当技术把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了自由的主体性存在物之时,技术理性这一文化系统便获得了价值上的肯定。然而,工业文明所体现出来的“制造”必然引发技术理性扩张,技术逻辑必然逾越自然生态逻辑。为着满足人的异化存在或人的主体性的极度张扬,满足人的欲求即一种逾越了生理需要的心理意愿,一种想要的满足(或为欲求),成为了技术及技术理性的存在依据。随着人对自然超越于其生态限度的对象化,人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系统被打破,自然生态系统成为了对人的反动从而出现了人的生存危机。因此,“制造”所体现出来的是征服,最终是人的生存危机。当我们倡导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文明,即人充分意识到人的生态存在之文明时,技术理性在实践意义上的合理性,就表现为是否维护人存在所需要的生态条件。也就是说,与我们生理肉体结构相适应的生态系统的存在和稳定,而并非人的心理意义上“想要”的满足。生理的需要是维持人的身体正常消耗之必须,而心理的“想要”是超越维持身体之必须的贪欲意念,永远没有止境。当技术理性立足于人的“想要”这一心理满足,技术创造物这一非自然之物对于人的既定的生理机体的有益性就必然转化为对它的伤害和反动。当人希望口感更好的贪欲转化为技术,粗糙的大米在技术作用下被打磨得越来越精细时,人的机体所需要的的维生素只能从专门制造的维生素片中获得;当人类利用技术不断减轻人的辛劳(汽车代足、洗衣机代洗、除草剂代人工除草等等),人的机体活力和敏捷、人天然地对疾病的抵抗只能通过专门的活动和药物来解决;当人类不断用科学来分析人的机体的奥秘,并用技术制造营养来解决机体的健康之时,人就成为了被试验的小白鼠而失去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类科学技术似乎不断把人置于尴尬地步,人在技术之下获取轻松、快乐的心理满足的同时,人又在不断地自讨苦吃。这一状况的深层根源就是主体性缺失。人类为着自身的解放(身体的自然束缚及精神压抑)和自我独立的主体性满足不断表现出对技术的需要,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是,这种技术需要是基于人的主体性获得和明晰的视野,是人的主体性更加全面而并非更加偏执。工业文明把人的主体性解读为征服、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这在克服农业文明的不足之时,又把人推向了另一极端。人的主体性的更加全面,“应该是高度发展了的主体性,即全面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对外部自然界的整体规律有清楚的认识,对活动的限度有清醒的认识,对自身活动的后果有预见性意识,对自身解放能力有规范性意识”[12],应该是充分明晰“人自身的自然”和“利于自然整体系统的稳定平衡”的主体性展示。在其现实上,就是人充分意识到人与自然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对于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实践准则。这种生态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的”、“绿色的”。“一个现存的生物结构,或者已知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按照常识似乎是‘最好的’,因为这是对有伤害的成分做过筛选的。”[13]因此,“善”的技术理性就是维持这一“自然的”结构,也就是技术的应用仍然维持着系统中的能量、物质循环和生态链之间的平衡,使得这三者的内在关联性和平衡性不会被打破,这一平衡之中仍然是遵循“物”之规律的“自然”之存在物。工业文明之技术理性已经超越了这一边界(它们之间的平衡状态)所形成的“人工物”或“人工自然”,从其本质上成为“自在自然”的对立物,以至与其生态系统对立,从而对人形成反动。塑料的发明、滴滴畏农药的使用、氟里昂的使用等就是这样。因此,“自然的”不是拒绝“人工的”,而是要求在制造“人工物”时遵循“人的生态生存”和“人的自身自然”为边界原则。这一自然应该是“按美的规律”来构造或者说“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马克思语)的自然。
最后,技术理性有了更多的伦理润泽。技术理性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就在于把效率置于绝对的地位,因而技术理性的展示过程总是以排除各种影响、干预因素以保障技术的效率最大化地实现,当然也包括排除伦理的人文价值因素。甚至当伽利略创立了数学-实验方法以至最终形成科学理性之时,事物内在的复杂性结构和关系被高度抽象为数学符号和数学结构,技术理性对事物内在规律的把握从丰富性的物质转向了数量关系的认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存在物存在仅仅被理解为是实现效率的工具或手段所需的数量关系。在此同时,技术的理性通过技术的物化不断否定人、控制人,从而使人成为了技术的“奴隶”。科技这种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和奴役人的异己性力量。
生态文明之中的技术理性,昭示着为人之目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14]赫费针对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给出了一条可通约的标准,即科学技术“不可以伤害人本身”。生态文明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生活样式,技术理性之善无疑体现在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技术是人实现价值的手段,“这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技术的标准。”[15]因此,技术理性作为人的充分发展了的主体性的展示,始终受到为人这一目的对技术逻辑规则和技术体系结构所构成的技术评判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决定性作用,始终围绕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展开。概言之,一切技术理性的能够行为必须受到价值理性的应当性约束,这种应当性来源于人的真实需要而非虚假需要,来源于人类终极意义上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追求。所谓真实的需要,就是根源于人作为类存在的需要。类意义上的人,是一个体现“正义”的人际关系和种际意义上的人,包括各种国与国环境正义、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环境正义。就是说,立足于“生态生存”的每个人,包括当代和后代人,都应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能通过牺牲他人(别国的人或后代人)的环境生态权来满足其超越基本生存之外的发展利益;种际意义的人,就是人与自然界中各种存在物在其存在意义上即生存意义上都是平等的,任何存在物在整个生态链中都有存在的理由。尽管人必须以人为中心,但是生态意义上人与其它存在物之间的互相规定决定了人在实施中心意义的作为之时,必须以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为前提。在一种“正义”、“公正”意义上人的需要就呈现为真实需要。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真实存在的属人存在。
现代文明是一种创建,是基于人的生存现实的深刻反思的一种对人的当下生存超越的指引。任何一种技术理性,固然存在“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和“技术通过内部固有的力量而增长”[16],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技术必须通过人来完成和实现。随着文明的变革,即一种人对人与自然关系更加理性认识的人类生存图景的构建,人所呈现出的主体性将不断克服其狭隘性而呈现为全面性,技术理性的展示必然呈现出新文明的印记,并在新文明对人的生存范式和人的范式之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工业文明中的技术理性在今天的革命中就成为了必然。
[1]Winner.Autonomous Technology[M].Cambridge Mass:MII.pree,1977.
[2]李醒民.科学与技术异同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1):1-9.
[3]熊小青.技术的边界及其伦理重构[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8,(5):449-552.
[4]艾尔伯特·鲍尔格曼.全球化与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0.
[5]李宏伟.现代技术的社会文化后果[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4):1-5.
[6]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82.
[7]刘福森.与时代同行:生态文明的呼唤一场哲学革命[J].人文杂志,2010,(5):6-11.
[8]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2.
[9]陈翠芳.科技异化与科学发展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
[10]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74.
[11]熊小青.环境道德引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135.
[12]熊小青.浅谈生态伦理中人的主体性[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1):11-14.
[13]巴里·康芝纳.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出版社,1997:33.
[1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出版社,2003:1.
[15]高亮华.希望的革命:弗洛姆论技术的人道化[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2):12-16,37.
[16]百度百科.埃吕尔[EB/OL].(2010-07-19)[2010-12-20].http://baoke.baidu.com/view/3976129.htm.
Re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Ra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Revolution
XIONG Xiao-q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 341000,Chin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grotechnique system,the civilization has not just been seen as the crystalization of human excellent achievements,but as a creation,a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based on the living reality of human being.The civilization revolution is of necessity as long as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displays as anti-ecology as well as anti-human.As an expression of civilization,the technology rationality would inevitably change in a way of revolution,showing that it is really for man and belongs to man.
civilization revolution;technology rationality;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B152
A
1008-3634(2011)04-0001-07
2010-12-23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ZX02)
熊小青(1964-),男,江西于都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硕士。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