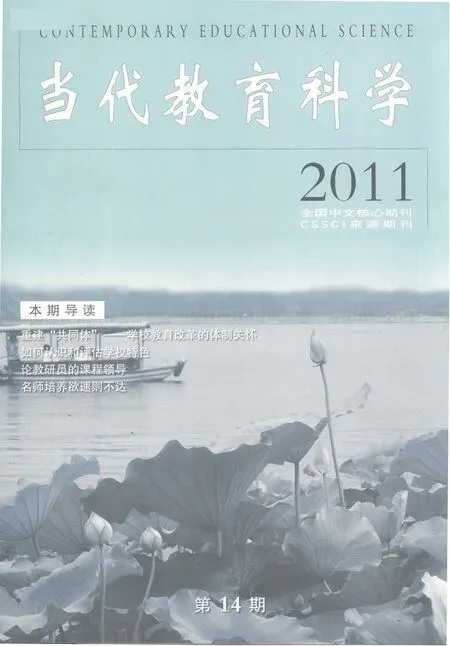追寻创造性和谐:人本教育的文化价值使命
●焦 伟
追寻创造性和谐:人本教育的文化价值使命
●焦 伟
高科技丰富了物质世界也挤压了精神世界,因此,怎样把网络时代的创新教育与人的理性追寻智慧融合实现人类精神的丰腴是集体教学时代人们面临的又一智慧难题。教育应该何为呢?
一、先贤倡导的人文主义是创新教育理性的原生态
“人文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却是在现代汉语中作为英文“humamism”一词的中文翻译才出现的。humamism原始意义是指人文学科的教育,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和训练。“humamism”成熟于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指以人为中心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体现人性与人文精神。但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humanism这个词。1808年,德国教育家尼特哈迈尔首次使用这一术语。1859年,近代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乔治·沃伊格特(George Voigt)在《古代经典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世纪》中,第一次将humanism运用于文艺复兴。这一时期的humanism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以人自身为中心,提出有关人的最终本性问题,并试图在自身的范围内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发展来丰富人的本性。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构建了“人本学”。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他所指的人不是抽象理性的人,而是具有感性、欲望的人,人的自然性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核心。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注重叔本华、尼采的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哲学目的是个人自由,方法是反传统的,又企图超越传统。现代人对科技理性的怀疑以及战争对人类理性的灾难性毁灭,显示了人的存在的自由性而不是人的存在的自然性。弗洛伊德倡导的精神分析学派冲破对人性中阴暗面的集体无意识,关爱完整的人性。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认为,人性是后天生成而非预先预定的,近来演化为后现代主义对人的差异性的尊重,对多元的欣赏。以上人本主义关于人的自然性、超越性、社会性的不同侧重,代表了人的问题研究上的不同方面。人本主义发展的新契机是人类存在的自然方面(生态环境)、个人方面(生存意义)、社会方面(自由解放)的有机结合,才能为社会提供发展的现实可能。
二、人文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创新教育的理论基石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哲学进入现代阶段,humanism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反对传统的本体主义——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人们偏颇地认为物质丰富是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正如弗卢姆所说:“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它具有关于物质世界的全部认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的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都茫无所知。”人类对自然界无节制的掠夺性开发,而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资源日趋匮乏,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存在及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现当代哲学家们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反思,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他们强调要改善伦理道德的传统观念,伦理道德不仅是人类所特有的,伦理道德应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人类无节制的掠夺资源,不仅是违法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当今时代兴起的生态伦理学。也许人们可以改善生存空间,一旦大气层污染达到一定的度,人类赖以依存的生存家园将彻底毁灭,整个人类也许会幻化成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海德格尔在著作《林中路》中论述了人的处境问题,提出在技术完全统治地球的今天,如果让人的主体性一味膨胀,作为客体的世界将被主体所吞没,理性以反理性实现所谓的理性,结果人毁灭了世界客体,同时也毁灭了人自身。所以,人的本质应该是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守护者,人是存在于自然中或在自然中存在的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亲在”,人与世界应该建立和谐的关系。赫舍尔进一步强调:我们从人出发来研究、思考人,就应该从人的处境去研究人,“人是谁”这个难题是人处境的产物。他说:奥斯威辛事件和广岛事件之后,哲学再不能依然故我,某些关于人性的断言被证明是虚有其表,被打得粉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合理的,到头来是乌托邦主义和生命虚无。哲学要想与时俱进,就必须给我们提供生存的智慧和具有道德正义的伦理命题——它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反对,来自对科技、启蒙、工具理性的“后现代”批判。人类不仅应该在学术报告厅里,而且应该在看到死亡集中营的囚徒时、在看到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时思考人的问题。社会纯以理性和契约来约束维持,并未见得完美无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nsm)对启蒙一代以来崇尚的理性原则正进行挑战和改进,如何为人类未来寻找一条比较理性支持的社会架构和秩序更为圆满幸福的道路焦灼的开放在人们面前。
教育的人文性是教育本质属性的要旨。创新学习关心人的和谐生存和科学发展,但是传统的教育理论在探讨教育目的时候,往往偏重确立教育目的所依据的社会本位,偏离了人之为人的本然诉求。教育实践论者只认识到教育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把教育看作是传递社会生活经验的工具,由此淡忘甚至牺牲了教育的本质属性——人文属性,造成本应该协调发展的个性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潮流之中变得支离破碎。集体创新时代的学习嬗变为人类追寻理性和谐的工具化、利益化的代名词。
三、创新与理性和谐发展
创新是理性的创新,创新融于理性之中才富有生命力,无理性的创新是一种粗制滥造或简单模仿。理性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与时俱进,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文化教育始终是型构人类价值理性的强大力量,当代教育理性的价值诉求是日益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以教育本体意蕴发生,教育本体意义的人文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不再只是经济、政治以及其他社会发展因素的附属物,不再把教育自身及教育对象——人仅仅作为辅助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当代教育可以真正关注自身及教育对象——人的生存和发展。教育使人超越了动物的物性,善待人的情感并合理地运用自身的理性,使人“人”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存在于世界之中与世界万物和谐地生活。夸美纽斯把人看成是等同一切自然体,把教育拟自然化。卢梭提倡遵循自然、顺应人性的自然教育。钟启泉呼吁:当代的教育应该关注个体生命意义的存在,而这些不只是一种理想,应该成为事实,也能够成为事实。教育回归理性以追求人文价值,是创新教育发展的归宿。
传统的教育目的观,其依据是“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无论是“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当今社会人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人必须改变自己的主体性立场,把自身的利益与自然紧密相连,放弃孤立地、主观地看待人类权利的态度。人虽贵为万物之灵长,但人终究存在自然界之中,这正如弗洛姆所说:“在整个自然中,人的生存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他离弃可自然,但似乎仍然在它之中;他部分是神,部分是动物;部分无限,部分有限”。当人类反思自己的行为给自然带来的灾难时,才终于明白人在不停地毁灭自然的同时,也在毁灭着自身。当人类开始觉醒的时候,必将引起一场价值观的革命,即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代替人统治自然的价值观。以往的价值观中,只重视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探索,强调人对自然界的超越性,而把自然这个重要的范畴丢在一边。现今的事实使我们懂得了,人应当与自然万物形成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人应该尊重它们存在的权利,对它们施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这既是人类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为了保证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教育的生态价值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教育的生态价值的基本含义是,通过教育帮助人类建立起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和谐共处的关系,教育的目的不应只盯着人、社会,而应关注自然、个人的整体和谐发展,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式的发展。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使人从难以抗拒的自然法则中寻求自身生存方式,既能够有别于其它生物体被动适应自然的生存方式,又能够保证以不侵害自然的根本利益为前提,最终实现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代替统治自然的价值观,使人类在向自然的回归中获得人性的回归与自我的回归。
教育,应该体现教育本真的、本性的价值——即人文价值,不能因为一味强调教育附属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和功能消解的人文价值。人文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人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前设,人是文化存在、社会存在、历史存在、传统存在的统一,人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追寻与世界的和谐。
焦 伟/山东省枣庄市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陈培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