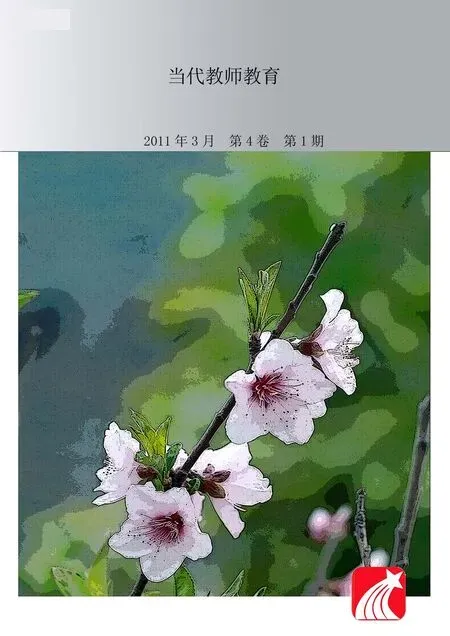教学实践家的品质及其成长
王 天 平
(西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所,重庆 400715)
一、提出教学实践家的原因
在教师专业化的进程中,中小学出现了一批从教学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名师,如斯霞、段力佩、霍懋征、于漪、钱梦龙、李吉林、邱学华、魏书生、李镇西等。他们多数是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实质上也具有“反思性实践家”和“专家型教师”的品质,对不同时期的教师专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但是在新世纪,这样的名师显得较为稀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特级教师”、“反思性实践家”、“专家型教师”等在内涵和意义上的现实变迁中发现一些原因。
1978年,为了表彰“有特殊贡献的优秀教师”,尤其是德艺双馨的优秀教师,我国建立了特级教师制度。特级教师并非是一种专业职称,而是一种荣誉称号。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特级教师的“专业身份”与“荣誉称号”之间的边界相当模糊,过于强调“学术标准”而淡化“师德标准”导致特级教师的原意缺失,作为教师的“终身成就奖”而淡化了特级教师制度的激励和导向功能。[1]而且事实上在中小学,特级教师制度已约定俗成成为高级职称之后的一级职称,类似于最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中小学的正高级职称。这些使得特级教师制度遭遇现实困境,在教师的崇高荣誉与专业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错位,极大地影响了特级教师的专业发展。“特级教师是否还姓特”、“特级教师制度还能走多远”等问题常有耳闻。
90年代末,基于对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技术熟练者”的反思,“反思性实践者”的概念应运而生。教育界引入这一概念,倡导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家”,希冀他们对教学活动进行反思,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教学情境,有效地解决复杂的教学问题。虽然作为反思性实践家的教师既是教学实践者,又是自身教学行为的反思者、研究者,但是教师把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活动作为教学研究的主要形式,就容易受到自身经验的局限,限制自己的研究视野。而且教学反思通常发生在教学活动之后,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时刻与教学实践相伴随。更进一步来看,反思也只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一种途径,因为尽管“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具有反思性的特征”,[2]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善于反思。由此看来,教师通过教学反思不能完全深刻地研究教学实践,有效地从理论上引导实践,进而从整体上提升自我。
新世纪之初,我国为了全面提高教师素质,支持和培养在教育界有重大影响的教育专家和名师,“专家型教师”成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又一个标志性口号。专家型教师是指在教育教学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有专长的教师,不仅具有教学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技巧,同时还具有对教学问题进行探索和处理的能力。但是,“专家型教师”对教学问题往往缺乏长期、系统和自觉的探索,从而不利于构建起自己的教学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到学科化知识体系的影响,“专家型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教学专家”或者“学科课程专家”。[3]他们通常主要掌握和运用“学科教育学”、“学科教学法”,过于倾向从“如何教”的层面来把握教学实践,不能很好地从普通教育教学理论的高度有效地统一学科的逻辑结构和学生的心理结构,这有可能导致他们的教学研究流于教学问题的表面。
从前述看来,“特级教师”侧重赋予教师荣誉和对教师成就的认可,但是没有提出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反思性实践家”侧重教师成长的途径,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专家型教师”侧重教师拥有在教育教学上的专长,其教学研究则多囿于学科的范围之内。因此无论是“特级教师”,还是“反思性实践家”,或是“专家型教师”,都不足以描述层次更高、成就更大的教师的品质。因此,由于教师的生命起点在于教学实践,为了和教学思想家和教学理论家相区别,我们尝试提出“教学实践家”这一概念,以此描述从教学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教育家,进而通过分析他们的成长规律,促进“特级教师”、“反思性实践家”、“专家型教师”的进一步转变。
二、教学实践家的品质
教学实践家作为教师队伍中的杰出人物,自然在教书育人两个方面都能够做出表率。在育人方面,教学实践家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对学生和其他教师能够产生不可估量的榜样示范作用。在教学方面,教学实践家是教学专家。专家有两种解释:一是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二是擅长某项技术的人。[4]随着专业化色彩的加强,专家的内涵趋于两者统一,不但具有实践品质,擅长所在领域的实践,还具有理论品质,能够比较深刻地研究自己的实践,从而保障实践的理性。从这一点来看,教学实践家是指擅长教学实践、系统地研究教学实践、职业道德高尚的教师。而在教师专业化的背景下,教学实践家通常不断追求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投身教学实践,积极对教学实践进行理性思考,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达到教学技能丰富、教学风格鲜明、教学理论独树一帜的专业状态。
(一)擅长教学实践,深度解读和改善教学实践
擅长教学实践是教学实践家存在的根本所在。教学实践家能够精熟地运用各种教学技能技巧,激发自己的教学智慧,运用个体的实践性知识,达到“自动化”地操控教学实践的水平。在不断高效地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学实践家逐渐以自己特有的教学方式将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教学活动“烙上”自己的个性,进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这正如于漪所言,“教出自己个性的时候,才是学生收获最大的时候。”[5]一般而言,教学论研究者是站在教学实践之外的,他们所谈的教学实践“被符号化、客观化和对象化”,[6]已经不是教学实践本身。而教学实践家作为教学实践的优秀的创造者,能够更加接近教学实践的本真,深刻地理解教学实践的活动方式,尤其是深谙教学实践的逻辑,如教学行为易于受到哪些教学传统的规约,受到哪些个人背景的潜在影响,受到教学情境怎样的控制,受到教学活动时空的何种限制,等等。教学实践家深度解读教学实践可以为教学理论的发展奠定深厚的事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更好地改善教学实践。一方面,教学实践家能够较为完整地把握教学实践的逻辑,掌握教学实践的确定性,尽量规避教学实践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在教学情境中,教学实践家能够发挥自身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更为有效地根据教学实践的不确定性,从整体上艺术地把握教学实践。如曾被周总理称为“国宝”的教师霍懋征,在教学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语文教学中娴熟地做到“引其言,激其情,启其疑,导其思,倡其辩,点其晴,明其理,活其用。教其知,授其法;显其情,正其本。”
(二)自觉开展教学研究,构建个性鲜明的实践教学论
自觉开展教学研究是教学实践家专业发展的关键。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教学活动受到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影响,教师对教学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容易处于一种自在自发的状态。教学实践家能够超越这种自在自发的状态,将教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内在需要,长期有目的、有意识、创造性研究某些教学问题,使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相得益彰。“教育不是理论,但理论是最高的教育实践”。[7]因而,在自觉开展教学研究的过程中,教学实践家立足教学实践,梳理教学事实,反思教学活动,总结教学经验,形成经验教学论。在此基础上,教学实践家借助科学教学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不断发掘自己的实践性知识,建构个性化的实践教学论。如李吉林始终从培养全人的角度出发,从情境教学论到情境教育论,再到情境课程,构建了情境教育教学的操作体系和理论框架,并出版了洋洋洒洒八卷本的《李吉林文集》。她由此叹言“教育科研也开发了我潜在的智慧,教育科研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获得充实而丰富的人生”。[8]
(三)投入教学感情,与学生一起成长
在一定程度上,师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教师及其所教学科的认可度,以及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发展水平。教学实践家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视教学生活不是为了生计和职业之需,而是师生共同成长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教学实践家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知识世界,而且要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与学生在心灵上建立起联系,将自身的成人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有机地融为一体,将自身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完美的人格特质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使教学过程真正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师生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共同实现教学目标,自然而然地展开成长的历程。正如李吉林所言“我是在儿童的世界中,在爱孩子中渐渐长大。我把这个爱升华为自己的理念,把这个爱细化为自己的行为”。[9]同样,即使在教师最不受学生尊重的“文革”时期,于漪还是以一颗真心真诚地对待学生,做到了“教心必须知心”,感动了她的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四)秉持教学理想,积极投身和引领教学改革
教学实践家始终秉持促进学生和谐自主发展的教学理想,几十年如一日,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积极投身教学改革、更新教学观念和变革教学方式,使自己的专业发展始终保持良好的态势。如魏书生原本只有初中学历,抱着对教师这个职业极其羡慕的心情,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经过多达150次申请才当上了教师,通过勤奋自学,深深扎根于教学实践,努力探索如何教好学生,形成了有名的“六步教学法”,从一个农村中学教师成长为一名闻名全国的教育改革家。更为重要的是,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容易“作为有价值的知识的维护者而拒绝变革”,[10]面对复杂的教学实践容易产生一种抗拒教学改革的心态,习惯性地维护自己熟悉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而教学实践家作为教学改革的“尖兵”,为教学改革树立了一面面旗帜,在广大教师队伍中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如邱学华一生只为了“尝试教学”而努力,从1980年开始尝试教学实验以来,跑遍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为中小学教师作报告和上现场课六百多场次,建立尝试教学实验基地有近2000个,参与实验的老师有六七十万人,参与实验的学生达三千多万人。[11]这不仅促进了自身的成长,丰富和充实的“尝试教学”的理论,而且带动了许多师生积极参与教学改革。
三、教学实践家成长的动力、环境及方式
教师要成为教学实践家,需要经过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历程。在特定的外在环境支持下,教师要善于采取适当的方式,在如火如荼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始终追求卓越。
(一)教学实践家成长的内在动力
在人生道路上,由外在要求的驱动和自主发展的需要转化而来的内在动力,往往对人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讲,一定的内在动力体现出一定的精神品质。在教学实践家成长的过程中,强大的内在动力通常表现为以创新为核心的精神品质。
1.勇气
教学实践家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跨越无数障碍,经历一次次痛苦的自我否定,最终才能获得“新生”。正是内在动力的强大支持,教学实践家才能知难而进,超越自我,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曾任上海育才中学校长的段力佩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适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模式,从开展教法改革到推进学校全面改革,推出了若干改革举措,形成了全国著名的“育才”经验。被誉为“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李镇西为了大张旗鼓地反对应试教育,曾经以非凡的勇气在四川乐山一中打着为未来培养人才的旗号,开办“未来班”,大胆地进行教学改革实验。
2.奉献
为了追求教学实践的精深境界,教学实践家将教学生活内化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产生强烈的敬业精神,把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都奉献给自己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于漪追求卓越的个性品质引领她挑战常规教学、挑战已有认识、挑战能力极限。[12]如果没有强烈的奉献精神作为支撑,她是无法50年如一日地行走于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之间的。同样,李吉林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一是她对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二是她有不断学习、永远进取的精神;三是她爱孩子、爱事业、爱祖国、爱人民的一片深情。[13]这表明李吉林挚爱教学生活,愿意为教学生活奉献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与孩子打成一片,这叫有童心;要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这就叫对学生的母爱。”[14]斯霞的这条教育格言展示了教育的大爱,是需要以忘我的奉献为依托的。
3.创新
无论是根据教学实践的发展变化而改善教学实践,还是构建个性化的经验教学论和实践教学论,都需要教学实践家在成长过程中时刻以拓荒者的心态和勇气打破常规、推陈出新,在一次次的教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获得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如斯霞在五十年代创造出“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小学语文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法,大面积、高效率地提高了识字教学的质量。60年代,她的“以语文教学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话三者结合起来”的小学语文教学法,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于漪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这说明教学实践家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永不满足、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提出“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的钱梦龙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他在上课之前先消化课文,在课堂上将自己的理解与老师的讲解相互印证和比较,并仔细揣摩老师讲解课文的思路与方法。这使他体味到“自主学习”对于学生学习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作为他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所追求的目标。
(二)教学实践家成长的外在环境
内在动力是教学实践家成长的主观条件,外在环境则是教学实践家成长的客观条件。外在环境指教学实践家工作和生活的大环境,大致可以分为物质经济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在当代中国,物质经济环境一般能够满足教学实践家成长的基本需要,精神文化环境对于教学实践家的成长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1.社会背景是教学实践家成长的土壤
特定的时代需求造就出反映时代特征的教学实践家。建国以来,在民富国强和实现现代化的时代呼唤下,我国出现了两代教学实践家。从建国初到文革之前,在教育复兴、百废待举的时代要求之下,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当务之急,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就是主要的实然教学目标,这造就了一批知识系统、功底扎实的名师,如斯霞、段力佩、霍懋征等。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教育改革自然成为了时代的标志之一,这又造就了一批致力于革新传统教学、将教学研究与教学实际相结合的名师,如魏书生、李镇西等。
2.制度环境是教学实践家成长的保障
人在合理的制度框架内可以自由发展。如果制度尊重人的主体性,人的发展就会积极有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不断激发人的主体性。这使得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断变革教育的机制和体制,关于教师的评价制度、科研制度、培训制度等越来越人性化,从而为教学实践家成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在“研究型教育”理念指导下,形成了一个“学校处处搞科研,教师人人做课题”的良好氛围,规定教师做到“科研领先,教有特点”,实现科研与教学密切联系,人人都成为“研究型教师”。正是在这种“科研兴校”的制度规范下,该校孕育出了刘定一、张思中等全国知名的名师,构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研究型教师”队伍。[15]
3.文化氛围是教学实践家成长的助推器
文化是一种内在于人心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以无形的力量深刻地规约人的行为和引导人的发展。团结和谐、积极向上、宽容大度的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及教学文化能够鼓励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创新,有利于创新能力强的教师脱颖而出。如在1979年,钱梦龙在偶然的情形下以“指导学生自学”为指导思想上了两次现场公开课,让人耳目一新,在上海市中小学崭露头角,接着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上海市首批五位特级教师之一。正是在当时改革开放、求实创新的文化氛围之中,钱梦龙独创的教学方式方法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无疑增加了他实施教学改革、探索教学规律的信心和勇气,加快了他成长的节奏,促使他总结提炼出“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的操作程序和理论体系。
(三)教学实践家成长的方式
教学实践家成长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个人主义的成长方式和社会取向的成长方式。教师“从自己出发”的立场孕育和滋生了教学的个人主义倾向,[16]因而教学实践家的成长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当然,这种倾向是必要的,因为在教学创新的过程中,教学实践家往往需要个人不断突破自我。个人主义的成长方式使得教师按照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教学实践,从而形成个性特征鲜明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教学风格等。事实上,许多教学实践家主要是在教学实践中经过自己不懈的独立探索逐渐脱颖而出的。虽然个人主义的成长方式有利于教学实践家形成自我负责的观念,但是社会取向的成长方式能够使教学实践家在成长过程中借力而行,改变独善其身的倾向,走出自己的专业领地,与教学理论研究者、同伴、学生、家长、社会人士等一起面对教学实践,共同成长。尤其是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教师要以开放的、合作的心态与教学理论研究者、同伴等结成学术共同体,与学生做到“教学相长”、共同发展,与家长和社会人士共同承担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从而更加愉悦地成长为教学实践家。
[参考文献]
[1] 韩淑萍.身份·标准·价值·功能——我国特级教师制度的现实困境[J].教育学报,2009(4):56-61.
[2]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2.
[3] 陈桂生.“专家型教师”辨析[J].江西教育科研,2003(4):6-7.
[4]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17.
[5] 董蓓菲,陈江月,郭琛晖.言说名师的专业历程[J].全球教育展望,2008(4):30-33.
[6] 石中英.论教育实践的逻辑[J].教育研究,2006(1):3-9.
[7] 王卫华.论教育的实践性——来自亚里斯多德实践哲学的视角[J].教育学报,2007(4):20-23.
[8] 李吉林.李吉林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2006:47.
[9] 王亦晴整理.李吉林:从小学教师里走出来的教育家[J].课程·教材·教法,2006(11):3-10.
[10] [英]B.霍尔姆斯,M.麦克莱恩.比较课程论[M].张文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4.
[11] 王敏勤.人生只做一件事——读《邱学华与尝试教育人生》[J].人民教育,2006(22):43.
[12] 朱晓民.专家知能发展的原型经验——以于漪为例[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39-142.
[13] 王亦晴整理.李吉林:从小学教师里走出来的教育家[J].课程·教材·教法,2006(11):3-10.
[14] 贾书建.“童心母爱”,洒向人间都是爱——为斯霞老师诞辰100周年而作[EB/OL].http:∥blog.xxt.cn/showSingleArticle.action?artld=2715337.http:∥baike.baidu.com/view/111337.htm.
[15] 陶小青.在科研氛围中孕育名师[J].上海教育,2003(7B):14-15.
[16] 徐继存.个人主义教学及其批判[J].课程·教材·教法,2007(8):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