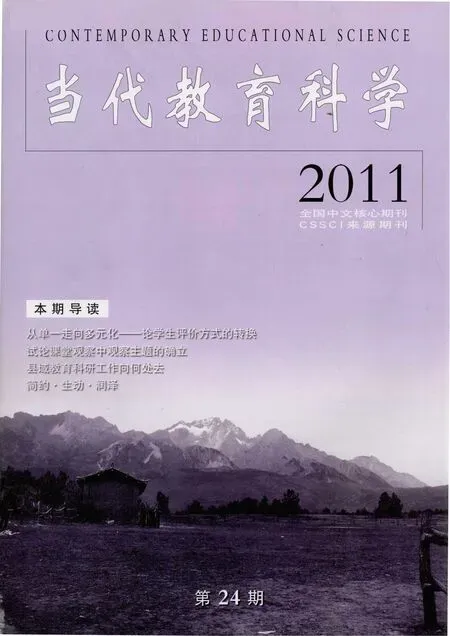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表现与实质*
● 李茂森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表现与实质*
● 李茂森
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教师个人语言的丧失或殖民、方向感的模糊或偏离、教师教学个性与创造性的缺乏、日常教学实践的去意义化等方面。其实质是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观意义建构没有得到彰显,以及教师对课程改革的不适应性表征,造成了教师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的丧失。
新课程改革;身份认同;认同危机
教师的身份认同与认同危机是两个相互关联的论题。认同危机的出现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关注与重视教师的身份认同问题,而对身份认同的重新建构则有助于澄清与化解教师自我的认同危机问题。所以,在新课程改革的特定情境脉络中,我们需要认清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基本表现及其实质所在。
一、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基本表现
在我国新世纪开展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性质上是一种“深度变革”或“适应性变革”,这种变革是对当下教育实践的一种“否定行为”,从根本上要求教师对课程改革作出适应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给教师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情感态度、利益需求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严峻挑战和现实冲击,教师在重新界定自身的身份时陷入了“认同危机”之中。具体来说,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师个人语言的丧失或殖民
在海德格尔(Heidegger,M.)那里,“语言是存在的家”。通过语言的思想性表达,存在者的此在意义得以澄明和显现。为了克服与逃避“作为自己”的独特个性的异化,寻找这种“在家”的感觉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然而“随着自我感的丧失,与之俱来的是我们丧失了用来彼此交流深邃的个人意见的语言”[1]。可以说,教师自我感的丧失,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教师个人话语的丧失或殖民。
新课程改革为教师的自主、创新创设了广阔的可能空间。教师要在改革中“成为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需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在课程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之景象,中小学教师也不断陷入理论话语所织就的“无形之网”中难以自拔。不管是在日常实践中谈论一些教育教学问题,还是通过叙事、反思等方式构建自我的专业身份,教师们总是习惯于“借用”一些自己不甚清楚的理论话语来解释,似乎不用这些概念名词就显得自己思考地不深入、不透彻;或者是担心说得不当而在众人面前显现自己的“不足”,毕竟衡量自己是否够“专业”的标准,还是由外部的专家“说了算”。这样,教师个人自己的语言不知不觉中就丧失掉了,出现了一种“缺席的在场”和“在场的缺席”的奇特现象[2]。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形孕育着教师自我的失落,致使教师陷入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
更为糟糕的是,一些教师在繁多杂乱的专家理论话语中无所适从,导致自己不知道“该听谁的”。而出现这种状况的结果就是教师个人话语的丧失,因为教师自身缺乏对教育教学问题的认识、判断与思考,总是等待着他人给予某条“金科玉律”去被动实施。可见,很多教师“不知道如何办”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他们为了逃避“无家可归”的状态,就将自己消融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这一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之中,宁愿放弃“成为自己”的本真存在方式,以获得安身立命之所。
(二)方向感的模糊或偏离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任何教师的日常教学实践总是需要采取一定的价值立场和观念,依据价值观的基本框架来决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定的价值立场能够给予教师明确的方向感,知道“我”站在何处,将要走向何处。没有方向或偏离方向的行动是盲目的,它会使我们失去前行的基本动力,陷入一种无所依靠的困境,“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认同危机’的处境,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3]。
“旧身份的丧失”和“新身份的建构”这一动态、复杂的过程,已经成为我们审视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及其重构的焦点所在。在当前课程改革中,教师以往熟悉的做法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常教育实践的原有价值基础受到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原来明确的方向感变得模糊不清了,这些都使教师的专业身份面临着认同危机的处境。“信念的变革是实现持久变革的基础”[4],它触及到了个人持有的、潜藏在深处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上,在改革实践中同时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念,一种是改革倡导的教育价值观,另一种是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而教师则在两种教育价值观的夹缝中艰难地、尴尬地生存,甚至是在混乱、无序中“无所适从”。
也就是说,在课程改革场域中存在着一些不同性质的改革话语,它们在共时的意义上“共存”,彼此之间相互“角力”。正是这些话语表达的不同声音,不断地型塑与撕扯着每个教师的身份认同。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念在实践中表征为两种不同的话语形态:“进步的话语”与“传统的话语”。前者与改革倡导的价值观相关联,强调教师专业身份的重构以及对教师变革性行动的指导与规范,例如 “个性”、“自主”、“改进”、“有效”等等;后者与传统的价值观相关联,强调深深扎根于教育实践的“考试文化”的边际效应,例如“升学”、“统考”、“排名”等等。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进步的话语”明显居于绝对的支配性地位,大多数教师都努力按照改革设定的方向进行着艰辛而又复杂的“朝圣之旅”,尝试建构一种新的专业身份,追寻自我在改革中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然而,“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魔咒”仍然在牢牢地宰制着教师的教育实践,因为强烈的“考试文化”似乎在“决定着一切”,教师对改革理想中自我的专业身份认同产生了现实的困惑,并在旧有身份与理想身份之间不断地痛苦挣扎与徘徊,出现了一种“不确定”的、“碎片化”的身份认同。可见,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两种当前依然严重对立与冲突的价值观念之间的行为抉择,很好地表征了一部分教师在实践中的“无奈”与“难为”,造成对自己“路在何方”的不知所措。方向感的迷失,导致了教师自我价值定位的“摇摆”与“错乱”,陷入一种深深的“认同危机”之中。
(三)教师教学个性与创造性的缺乏
教师的教学活动需要与自己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乃至整个生命有机交融在一起。然而长期以来,教师的自我与教学个性都淹没在固有的程序性规则之中,没有形成一种理性的自觉,“教师主体性的缺乏,造成教师对国家课程文本的‘职业依赖症’”[5]。同时,一些教师甚至为了避免承担可能出现的教学风险,有意地进行“防御性教学”。这一切,都造成了教师的教学与自我的身份认同相分离了。帕克·帕尔默(Palmer,P.)曾极力强调要进行 “超越技术的教学”,“要按照我们是谁而施教”。她说,“在我不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不能了解我的学科——不能从体现个人意义的最深的层次上来了解。我只不过是远距离地看到一堆远离世界的抽象概念,如同我自己远离真实的我一样”。而且“好的教学不能归结为技术,好的教学来自教师的个性和整体性”。[6]
在课程改革过程中,一些教师认为自己是改革的忠实执行者,改革怎么要求他就怎么照着做,在行为上表现得十分顺从,至于如何改似乎与他没有关系。在实践中,他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到底有没有用”、“怎么操作”。很显然,这种类型的教师只是他的行为发出者,以教学行为的顺从代替了自我的教学思考,行为本身变成了控制他自己的消极力量。他根本感受不到自己的教学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结果只是一味地“趋同”,原本丰富的自我在机械地行为操作中“异化”了。其实,任何一种教育改革的理论,都会给我们带来思想和行为上的冲击,我们需要找到、接纳并内化符合自身“最近发展区”的理论与做法,简单地顺从固然能够找到“家”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但在行为趋同中却会掩盖甚至丧失属于自己的思想与个性。”我们太多地沉浸在热潮中,一种热潮来了,往往就是思想的缺席,因为只有一个声音、一种话语、一种热情,从众固然不孤独,但是没有了自己,没有了思想。我们都在流行的时尚的思潮中淹没了个性”[7]。可以说,在课程改革中能否认识“我是谁”以及应该“如何行动”,往往将教师推入到身份认同危机的漩涡之中。
(四)日常教学实践的去意义化
日常教学实践作为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专业生存方式,是教师自我不断追寻生活意义以及生命价值的现实基础。但是,日常教学实践的重复性特征,以及教师在改革实践中的消极被动应付,往往造成教师陷入一种 “无意义感”、“无力感”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在改革实践中,一些教师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动原则,在公开课、表演课等场合,他们会下功夫按照课改精神来精心“打造”课堂教学,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改革期待的形象,但在所谓的“日常课”中又退回到原有的“套路”之中。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自我“表演”,教师在日常教学实践中难以确证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意义感。同时,频繁的改革方案,繁杂多样的新概念、新理念“新鲜出炉”,在“新”工具理性的钳制下,学校与教师总是需要不断地采用新技术,导致“方法与技术折旧得太快,然而这些方法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并未真正被理解或适切运用”[8]。由于变化与调整的速度太快和频次太多,致使很多教师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在政策的变动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无根的浮萍”。于是,“应接不暇”的教师干脆就采取“不予理睬”、“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认为改革是“换汤不换药”,在消极等待中应付改革。可见,改革的被动应付将会带来日常教学实践的去意义化。
二、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实质分析
以上分析了新课程改革中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基本表现。从根本上来说,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观意义建构没有得到彰显,以及教师对课程改革的不适应性表征,造成了教师自我身份感、或者自我价值感与意义感的丧失。
(一)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观意义建构问题
改革的实施总是以某种方式被调整,因为政策层面的理想改革与教师个人所理解的改革之间、外在的改革期待与教师个人的价值信念与经验之间可能都存在着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对教师的身份认同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外在的角色期待与要求在何种程度上转化为内在的自觉则是至为重要的一环,这牵涉到教育改革中教师个人的主观意义问题。赫舍尔指出,“人甚至在未认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人的存在要么获得意义,要么叛离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9]。对个人主观意义的关注,是教师作为“人”的一种创造性存在,能够促使教师对自己的生活保持一种积极自觉的投入状态。个人意义的形成,总是一个反思性理解与行动的持续发生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地获取某种相对稳定的个体心理结构。如果教师在价值信念上难以达成共识,在情绪态度上表现出消极保守的立场与倾向,也就是说,在理性与非理性层面都不能形成合理的专业身份认同,没有形成一种自觉主动的意义建构,那么在这种“处境”中,教师对“我是谁”、“我要成为谁”的困惑就会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
在变革性实践中,富兰(Fullan,M.)也强调,意义问题是理解教育变革的关键所在。[10]当前的课程改革,在教育理念、教材内容、教学方式与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全面、系统的革新,如此激烈、复杂的改革要让教师还像以往一样简单地听从行政命令,单纯强调改革本身的客观意义似乎难以奏效。“对改革的实施和采纳过程的日益重视使得直接卷入教育改革的人——特别是教师、家长和学生等——在改革实施上享有真实参与权和分享更多的信息成为可能。由于改革已经从强令式向能力构建方面转变,领导人将会更多关注‘第一线’人士的意见,因为改革最终还是要通过他们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11]。所以,为了成功地实施改革,就更应该充分考虑到在实践中改革的教师个人意见,重视教师个人对教育改革的主观意义建构,重视教师已有的经验、价值、能力、信念、情绪和态度对改革方案本身的调适作用。
改革的意义建构过程是教师个人“抓住”变革现实的一种经历,而这种经历具有着冲突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它可能带来积极的、成功的情感体验,也可能产生严重的自我焦虑感。当前的课程改革已经成为每个教师沉浸于其中的“生活事实”,教师该如何行动,在改革中能否成为真正的主体以及成为自己,都离不开教师自我的反思性筹划,以及赋予改革本身的主观意义。改革的实施不仅需要教师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执行者”,更期望着教师自我的意识觉醒。当改革仅仅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没有得到教师个人的意义建构并转化为主观的事实,没有形成一种“我化”的改革实践,也就是说,如果教师感受不到改革所带来的可能意义,那么他难以作出积极主动的思考和行动,从而表现出应付、不合作、抵制等消极行为。日常教学实践的去意义化,以及教学个性与创造性的匮乏,正是由于教师没有意识到改革给自我发展带来的契机,没有形成教师个人的主观事实,而依然习惯性地沉湎于以重复、操作为特征的日常生活实践,不愿意自觉地去改变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正因为对课程改革中教师个人的主观意义建构的忽视,导致教师自我对“我是谁”、“我将要走向何处”等存在论问题的困惑,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可以说,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恰恰是教师个人在课程改革中的主观意义建构没有得到适当地、有效地彰显。
(二)课程改革中教师的适应性问题
教师的适应性并不是被动地适应课程改革这一外部环境的变化需求,而是在自己主观意义建构的基础上凸显自我的存在性价值,或者说要在课程改革的外部特定情境要求与教师自己具备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等先在背景之间发生有效的“对接”。在课程改革中教师适应性的形成,有助于其专业身份认同的合理塑造;与此相应,教师的不适应性则孕育并表征了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教师的不适应性意味着自我同一性遭到解构,它打破了自我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动态平衡,自我身份感、归属感与意义感的缺失也随之发生。对于教师自我的身份认同,不仅要在外在行为方式上与改革环境的要求保持一致,更要在心理与精神层面上的价值信念、情感、态度、动机等保持内在的一致性;不仅要在理性认知维度上实现教师自我的改变,更要在非理性层面上切实促进教师的改变。这种对内在同一性的自觉追求,正反映了人是一种超越性存在的特征。
作为一种超越性存在,“人”从来都不安于既有的生存现状,而是始终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与期望,并不断追寻自己的“家园”[12]。也正是在不断朝着理想的、可能的教学生活迈进过程中,教师获得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可以说,新课程改革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理想的生存家园,在改革中许多老师都已经踏上了(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自己的朝圣之途。然而,改革始终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13]离开了自己原来熟悉的家园,周围立即变得陌生起来,问题、冲突与矛盾也逐渐复杂起来,原本清晰的改革目标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因应外界改革要求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声音,而为了与外界的改革环境保持一致,教师个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态度等方面都要发生根本性改变,重新营造自己倍感熟悉、拥有安全感和控制感的专业生存场景。可是改革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被迫放弃传统的习惯性做法的同时,亦引起了许多教师的“不适应性”或者说存在性焦虑。
显然,对于已经熟悉既有教学实践“套路”的教师来说,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有实践秩序和意义的“破坏”,使教师在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中难以适从。教师的适应性并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去替代另一种“旧的”行为模式;并不是实践行为上发生变化就一定表明价值观念的觉醒与更新,而是受到多个因素的整体作用。从文化—个人视角出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适应性包括四个关键因素:思想上的认同、能力上的胜任、情感上的关注以及文化上的融入。[14]这四个因素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师适应性分析框架。反过来说,如果教师在价值信念上没有与改革期待保持一致;即使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方法与技术,在能力上也难以胜任;对教师在改革中遭受的压力缺乏积极情绪管理;学校文化、习俗等外围环境没有有效地得到改变,那么在改革实践中教师就自然会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倾向。即使在某一个因素方面出现问题,情况也会如此。这种教师的不适应性表征也正是对身份认同危机的恰当注脚。
[1]罗洛·梅.人寻找自己[M].冯川,陈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45.
[2]吴永军,徐华丽.新课改中教师主体地位的社会学审视[J].教育发展研究,2009(6).
[3][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7.
[4][10][13][加]迈克尔·富兰.教育变革新意义(第 3 版)[M].赵中建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47.29-50.54.
[5]石鸥.教育困惑中的理性追求[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17.
[6]帕克·帕尔默.教师的内心世界[A].阿伦·C.奥恩斯坦,琳达·S.贝阿尔—霍伦斯坦,爱德华·F.帕荣克.当代课程问题(第3版)[C].余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96-98.
[7]邓友超.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56.
[8]周淑卿.课程发展与教师专业[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25.
[9][美]赫舍尔.人是谁[M].隗仁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47.
[11]Benjamin Levin.教育改革——从启动到成果[M].项贤明,洪成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88.
[12]鲁洁.超越性的存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
[14]靳玉乐,于泽元.文化—个人视角下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适应性探讨[J].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2).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教育转型背景下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及其重构研究”(11YJC880055)的部分成果。
李茂森/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师专业发展
(责任编辑:张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