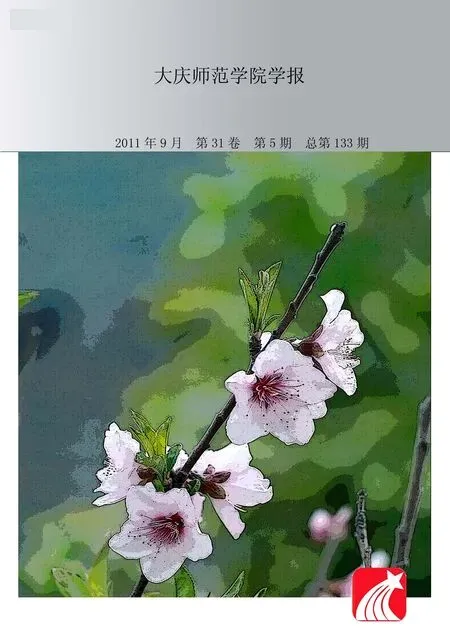论简帛文献常用词新搭配的词语演变研究价值
赵 岩,张世超,周忠兵
(1.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2.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3.吉林大学 古籍所,吉林 长春 130012)
“词的组合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词的搭配关系。”[1]搭配关系虽是表层现象,但深层次上却体现了语义与语用问题,故分析搭配关系的变化是我们认清词的语义、语用变化的重要途径,在汉语史研究中意义重大。不断出土的简帛文献中含有大量的新搭配,其中很多是常用词的新搭配,从中可以窥见汉语词汇系统的演变。以下我们从简帛文献中若干常用词的新搭配入手,讨论简帛文献对于词语演变研究的价值。
一、简帛文献常用词的新搭配与新词
(一)新词的语源
有些新词的语源在漫长的历时演变过程中隐没不见于传世文献,而简帛文献中一些常用词的新搭配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些新词的语源是什么。以“陷败”为例,它在传世文献中泛指“覆没、失败”,如:
1) 此九者,骑之死地也。明将之所以远避,闇将之所以陷败也。(《六韬·战骑》)
2) 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汉司马迁《报任安书》)
简帛文献中“陷败”与“道”相搭配,如:
3) 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青川木牍《为田律》)
4) 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247)
由此看来,初时“陷败”的主体指道路,后来才由道路扩展到人,泛指“覆没、失败”。因此,我们认为“陷败”的语源是“(道路)毁坏”。
(二)新词的产生过程
新词的产生往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流变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有一些关键触发点,这些触发点找到了,新词的产生过程也就清晰了。但由于传世文献失载,使得我们对一些词语的产生过程产生误解。以新词“颗”的产生过程为例,《说文解字·页部》:“颗,小头。”[2]段玉裁认为“颗”由此“引申为凡小物一枚之称,珠子曰颗,米粒曰颗是也”[3]。而黄德宽等则认为“果可以以粒计,故引申有颗义。……疑人之头小若果,故以果称,复派生专字颗”[4]。汉以前文献中并未见“颗”用作“小脑袋”义。出土文献中“颗”字较早见于秦印,作人名,此外未见他义。传世文献中,在汉代“颗”作名词仅有一例,即《汉书·贾山传》:“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也。”颜师古注:“颗谓土块。”这实际上是通假字,本字是“堁”,《淮南子》多见,如:“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末,譬犹扬堁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淮南子·主术》)既如此,段说可商,“颗”的量词义应另有来源。黄说认为“颗”的来源是“果”,应该是正确的,只不过其引申途径需进一步讨论。
“果”的本义为“树木所结果实”,但因为认知的关系,渐渐一些类似果实的饱满的突出的物体皆可命名为“果”,语用范围因之扩大,在战国楚简中“果”可以指“戟”突出的支干[注]整理者认为,“果”指戟有二个或三个戈头,“果”通“戈”。我们认为,从词义引申的角度可以讲通“果”在此处的用法,不必曲为说解。:
5) 一戟,三果。(曾侯乙墓简14)
或作“菓”,如:
6) 一戟,三菓。(曾侯乙墓简3)
而在先秦及汉初的量词系统中没有一个相应的量词用于指称植物的“果实”,这使得“果”在汉初保留了名词复指的用法。马王堆汉墓医简中出现了“植物名+数词+果”的搭配样式,如:
7) 取雷矢三果,冶,以猪煎膏和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48)
8) 干姜二果,十沸,抒置瓮中,埋席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249-250)
9) 疽未□□□□乌喙十四果。(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280)
10) 一曰:每朝啜蒜[注]“蒜”字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释作“柰”(《马王堆汉墓帛书(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28页),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772页)从之。周一谋、萧佐桃(《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334-335页)释作“蒜”,郭永秉(《说蒜、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12月11日)利用张家山汉简中“蒜”字字形对此字进一步阐说,认定是“蒜”字,其说可从。二三果,及服食之。(马王堆汉墓帛书《杂疗方》62)
我们认为,这种用法中的“果”仍作名词,复指“雷矢”、“姜”、“乌喙”、“蒜”等植物[注]“雷矢”主要部分是菌核,“乌喙”也主要取用其块根,“姜”、“蒜”的主要部分是其果实,故“果”可复指以上植物。,这在简帛文献中还有类似用法,如:
11) 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8-9)
12) 壶枣一木,第九十四,实九百八十六枚。(南越王墓简068)
13) 枣二十五木,梨六百二木。(虎溪山汉简)
“木”即复指桑树、枣树等。不过如前人所述,这种用法往往发展成为量词用法,很多词在秦汉时期已可明确理解为量词,如“口”[注]战国时代的“口”量词义还不明显,可理解为复指名词,如:“丁亡,盗女子也,室在东方,疵在尾口口口,其食者五口。”(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乙种256):
14)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史记·平准书》)
15) 故釜一口。(居延汉简128.1)
这里的“口”用来指“釜”,从语义上解释为名词已难讲通,故应是量词用法。另外,同时期相似位置上的多数词也是量词,如:
16) 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史记·货殖列传》)
17) 等三人,捕羌虏斩首各二级,当免为庶人,有书。(居延新简EPT22.221)
18) 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史记·田儋列传》)
这会使得人们重新分析这种常见结构,将其理解为量词,从而产生了量词“果(颗)”。又由于语用上的巨大差异,使人们另用“颗”字表示量词用法,而用“果”字表示量词外的用法。虽然马王堆医简中“果”不是“颗”,但却提示我们量词“颗”的来源应该是“果”,且这种用法体现了名词“果”发展为量词“颗”的重要一步。
(三)新词代替旧词的过程
汉语词汇系统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词语的交替性演变。所谓交替性演变,即“词汇成员的新增旧减以及新旧词语的历史交替”[5]。新词代替旧词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一些搭配格式的出现及历时交替往往是演变阶段的重要标志。以“树”代替“木”为例,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某某树”(如桃树)代替“某某木”(如桃木)。
“某某树”格式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中已经见到,如:
19) 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吕氏春秋·去宥》)
20) 南至交阯、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吕氏春秋·求人》)
21) 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鸲鹆不过济,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淮南子·原道》)
22) 昆仑山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淮南子·坠形》)
23) 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史记·燕召公世家》)
这种用例在《史记》中仅见1例。由此,汪维辉指出:
“棠树”即棠梨树,这种以小名冠大名的“某某树”格式是现代汉语最常用的称树方式。据目前所知,这种格式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去宥》……但从总体上说,在先秦西汉这种格式还是罕见的。而且汉魏以后一般也较少用“木”来构成这个格式。[6]
但在西汉未央宫简中我们却见到大量以小名冠大名的“某某树”格式,如:
24) □乐长常甘露下,府官寺中柏树(未央宫简21)
25) □榆树上,其色黄白,味甘如密。(未央宫简33)
26) ……桃树二,一树□九子□(未央宫简34)
27) ……□柏树一枚……(未央宫简35)
28) ……府柏树二枚……(未央宫简50)
29) ……□治病中柏树。(未央宫简51)
30) □府中柏、杏、李、榆树。(未央宫简55)
这说明至少在西汉口语中,以小名冠大名的“某某树”格式已经很常见,这在居延新简中也有体现,如:
31) □处田中桼树下有石,下入地中,石上与地平,取诊视三偶,大如小杯,广二寸(居延新简E.P.T40:24A)
此简出于破城子探方40号,中有元始、建平、绥和、元延、新始等年号,说明此坑中的简多属于西汉中后期,故E.P.T40:24简亦应代表西汉中后期的语料。值得注意的是周家台秦简相同格式中用的是“木”字,如:
32) 恒多取櫌桑木,燔以为炭火,而取牛肉劙之,小大如黑子,而炙之炭火,令温勿令焦,即以傅黑子,寒辄更之。(周家台秦简317-319)
因此,“某某树”的格式较早出现在战国末年,不过早期用例较少,到了汉初用例已渐多,代替“某某木”应该是在西汉中后期完成的,只不过在传世文献中由于用例不多而体现得不明显。
二、简帛文献常用词的新搭配与语义的演变
(一)新义位的产生时间
由于现存上古文献语料的局限性,很多常用词新义位的产生时间较晚,而简帛文献中常用词的新搭配使我们见到了这些义位的更早用例。
马王堆汉墓帛书载:
33) 欲产女,【取】乌雌鸡煮,令女子独食肉歠汁。(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27)
“乌雌鸡”这一搭配文献首见。西周金文中始见“乌”字,象鸟张口鸣叫气出之形[注]或认为象乌鸦张口之形,但西周时期以前未见“乌”有“乌鸦”义,故我们认为“乌”未必一定是象乌鸦之形,其形可能与“呜呼”义的关系更密切,象鸟张口鸣叫气出之形。,金文中组成“呜呼”一词,为习见叹词,如:
34) 乌虖!(何尊)
35) 乌虖哀哉!(禹鼎)
至晚在战国时已可用于指“乌鸟”,如:
36)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诗·邶风·北风》)
37) 燕雀乌鹊。(《楚辞·屈原·涉江》)
又由于乌鸟体黑(《诗经》中的辞例说明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故引申有“黑”义,但传世文献作此种意义的用例要晚到晋时,如:
38) 身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三国志》卷28)
帛书将这一意义的用例提前到了汉代[注]《汉语大词典》首见用例引宋苏轼《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穷年弄笔衫袖乌,古人有之我愿如。”过晚。。且“乌雌鸡”体现了“乌鸡”这一术语的语源,传世文献中“乌”与“鸡”相搭配要到《通典》中才能见到。
(二)新义位的衍生过程
词的语义变化会在搭配上有一定的反映,旧义位衍生新义位往往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往往会体现在一些搭配的变化上。
1.疾沸
“疾沸”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如:
39) 一,伤而痉者,以水裁煮李实,疾沸而抒,浚取其汁,寒和,以饮病者,饮以□□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34-35)
40) 取锻铁者灰三□,以鍑煮,安炊之,勿令疾沸,□不尽可一升,□□□以金□去,复再三傅其处而已。(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446-447)
未见于传世文献。从“疾”的“快速”义理解这一搭配可译为“水沸腾后水花急速翻动的状态”,从“疾”的“劲”义理解这一搭配可译为“水花有力跳动的状态”,这两种译法皆可,恰可体现“疾”义位发展的中间态。
2.熟学
“熟学”或作“孰学”,见于马王堆汉墓医书,如:
41) 氏□□□则□此□□□□□□□脉之玄,书而熟学之。(马王堆汉墓帛书《脉法》82-83)
这个搭配未见于传世文献。“熟”字本义为“成熟”,在战国、汉初文献中常置于动词前表示程度,如:
42) 值一钱,笞十;值廿钱以上,孰(熟)笞之,出其器。(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148)
43) 愿【君】之孰(熟)虑之而毋行危也。(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147)
44) 一,取雉二,孰(熟)煮余疾,鸡羽自解,堕其尾,□□□□□皆燔冶,取灰,以猪膏和【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328)
45) 一曰:必孰(熟)洒澣【胞】,又以洒澣□□□□□□小□□□□□□□□以瓦瓯,毋令虫蚁能入,而□□□□□□【见】日所,使婴儿无疕,曼理,寿□。(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15-16)
可依语境译为“反复”、“仔细”等义,此时“熟”置于动词前的用法在语义上颇为混沌,义位的分解大概还没有完全完成。
三、简帛文献常用词的新搭配与语用的演变
张志毅等指出:“义位是由义值和义域组成的。”[7]因此,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义域的变化必然引起意义的变化。但由于在析出义位时,不能根据义域的细微变化而无限析出义位,所以部分搭配上的变化从性质上看属于语用的演变。而简帛文献中一些常用词的新搭配反映了这种语用上的产生与发展。
(一)温汤
“汤”有“热水”义,“温汤”即“温的热水”,此搭配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如:
46) 一,消石置温汤中,以洒痈。(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22)
传世文献直到唐代方见类似用法,如:
47) 其法,以甲乙日用温汤向东灌之,向夜取一大盘,盘中画一直墨界,一边为己,一边为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10)
这一与语用搭配汉以后趋于固定化,直到今天的江淮官话及吴语中仍或用“温汤水”表示“不冷不热的水”[8]。
(二)阴精漏泄
“阴精漏泄”这一搭配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如:
48) 彼生有殃,必其阴精漏泄,百脉菀废,喜怒不时,不明大道,生气去之。(马王堆汉墓帛书《十问》52-53)
“漏泄”一词至晚在战国初年即已产生,较早见于《左传》,如:“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左传·襄公十四年》)战国之后的文献中屡见,如:
49) 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50) 於是石显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语,下狱掠治,减死,髡为城旦,因废。(《汉书》卷66)
但漏泄的对象多为言语,而《十问》中与“阴精”搭配,应属语用之扩展,这一语用搭配后来屡见于医学文献。
(三)宿气
“宿气”这一搭配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义为“旧有之体气”,与“新气”意义相反,用如:
51) 息必深而久,新气易守。宿气为老,新气为寿。善治气者,使宿气夜散,新气朝最,以彻九窍,而实六府。(马王堆汉墓帛书《十问》30-32)
传世文献未见用此义之“宿气”[注]明清传世文献见“宿气”,义为“旧有之怒气”,如“一则是两个人有些宿气,二则是黑地里分不得甚么高低,那个一拳,打个喜雀争巢;这个一拳,打个乌鸦扑食。那个一拳,打个满面花;这个一拳,打个萃地锦。”(明《三宝太监西洋记》)“果真如此,不但叔父宿气可消,就便侄儿冤仇也算报了。”(清《施公案》)与我们讨论的“宿气”不是一个词。。
(四)殖人
“殖人”这一搭配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义为“繁殖人”,用如:
52) 禹问幼频曰:我欲埴(殖)人产子,何如而有?(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1)
传世文献未见。
(五)垂字
“垂字”这一搭配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义为“临产”,如:
53) 字者,且垂字,先取市土濡清者,□之方三四尺,高三四寸。(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29)
“字”有“生产”义,“垂”有“临近”义,但“字”语义较古,传世文献少见,故“垂字”这一搭配未见于传世文献。
综上所述,简帛文献常用词的新搭配对于词语演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从词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新词的语源、产生过程、代替旧词的过程,从词义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新义位的产生时间及衍生过程,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词汇的语用演变。
[参考文献]
[1]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7.
[2]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36.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418.
[4]黄德宽,等.古文字谱系疏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251.
[5]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2.
[6]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82.
[7]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23.
[8]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9:6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