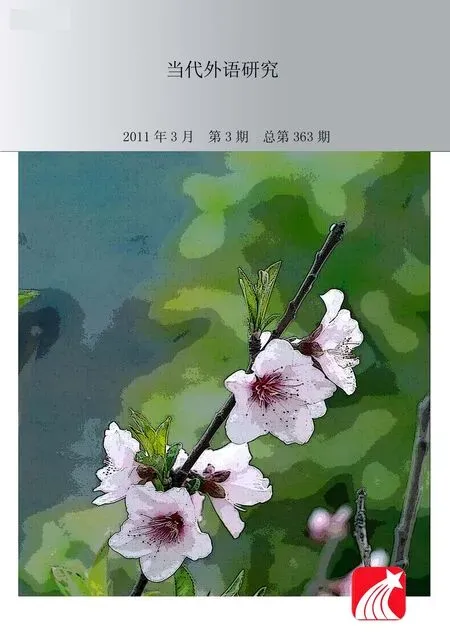中美“出行”文化情结及其在文艺中的表现
田俊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191)
1. 引言
翻开中美文艺史,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不管是中国古代李白的《蜀道难》,还是美国近代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也不管是美国现作家代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还是中国当代影视大剧《走西口》,两国文艺家们似乎都关注过“在路上”这样一个主题和结构模式:即描写主人公从一个地域的或精神的荒原出发,希求达到物质的乐园或取得精神的升华和救赎。他们的“出行”(journey)往往会受到社会邪恶环境和个人心理向度的干扰,有的人在“出行”中获得精神的成长,而有些人却走向了毁灭。表现这种主题和结构模式的文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出行”文学,它具有詹姆斯·格雷所说的“将人类状况的当代迹象与人类过去的经历结合起来”(Gary 1971:45)的史诗性文学特征,而所谓“史诗性”,不仅可以涵盖叙事文学中史诗作品的特质,也可能超越叙事文学作品的题材限制,而渗入其它文学艺术体裁,如戏剧、电影艺术中(马润生2003:53)。首先,“出行”是人类亘古以来一个宏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解决自身物质或精神困厄的主要方式。只要人类陷入物质或精神环境的困厄,他们就必然要通过一场地域的或精神的“出行”来摆脱困境。其次,就中美文艺来看,作为一个宏大的主题,“出行”可以涵盖两国文艺作品的许多亚主题,例如“善与恶冲突”、“人类的堕落与救赎”、“爱与死”、“主人公心理成长”以及“梦的寻觅与破灭”等,它们是人类在出行途中必然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2. 中美“出行”情结的历史渊源
作为一种心理情结,“出行”具有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圣经》中的《出埃及记》记述的就是人类的出行历程。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古犹太人到埃及寻觅食物,结果被困四百余年。他们的困厄惊动了上帝,他派先知摩西去解救他们。摩西率领古犹太人逃出埃及,到达圣地迦南。自此以后,“出行”作为一种史诗性主题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欧美作家的笔下。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出行”或迁徙的主题更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型。从历史上讲,1620年,一批英国清教徒为逃避本国天主教的迫害,搭乘“五月花号”轮船,出行到新大陆这个“清新的、保持着童贞、又是荒野粗狂、渺无人烟的伊甸园”(罗伯逊1990:52),成了今日美国人的祖先。1803年,杰斐逊总统从法国人手里购买了包括现在路易斯安那州在内的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拓荒者西进提供了辽阔的疆域。于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离开自己贫瘠的家园,奔向西部理想中的天堂。有首民谣形象地刻画了拓荒时代美国佬西行的风貌:
都来吧,希望改变命运的杨基佬们,
勇敢地走出你们土生土长的庄园,
离开爹娘恋爱不舍的村落,
跟我来吧,定居密执安。(罗伯逊1990:190)
今天,“出行”依然是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美国人在本性上是一个不安分的民族,加之美国道路和汽车工业发达,因此上路出行就成了美国生活的一种主要方式。美利坚民族被称为是一个“坐在车轮上的民族”,它不断地在出行。住在城市的出行到乡下,住在乡村的迁徙到城市。这种无止境的出行或迁徙成了美国的象征。他们出行或迁徙的目的概括起来讲有两个,一是为了物质生存,一是为了精神自由。
如果说美利坚民族的出行是源于宗教和个性生活方式的追求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们的出行则是为了摆脱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存的痛苦。历史上,中国人大规模的迁徙发生过四、五次。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唐朝时期“安史之乱”的爆发,使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这又一次引起了人口南迁的大潮。“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三次规模不小的移民潮,它们是“闯关东”、“下南洋”和“走西口”。其中,“走西口”是一次不大不小的人口出行,它从明朝中叶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不独山西人走西口,陕西、河北都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所谓“口”,原来指明朝隆庆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后来演变成对蒙贸易的关卡。山西商人习惯称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东口”,大同以西的右玉县杀虎口为“西口”;长城以内为“口内”,长城以外为“口外”(王俊斌2007:5)。
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出行是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并成为“民族集体心理无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荣格(1987:52)在研究无意识的时候,曾将它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个层次,“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存在的。我把这更深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我们探讨无意识心灵所能达到的最深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人不再有个体的区分,个人的心灵在这里扩展开来并融入人类的心灵。按照荣格的解释,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反映了人类在以往的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是千百万年来人类祖先经验的沉积物。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历史上的迁徙或出行,作为历史的积淀,深深地植入了两个民族的深层无意识中,并会在适当的时候以一种或隐或显的形式在文艺作品中体现出来。对于中美两个民族来说,“出行”已经不仅仅是在地域上从一个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过程,而是被视为对某种历程的经历。它可以象征性地指代个人的心理成长或者对一种信仰的追求。
3. “出行”主题在中美文艺作品中的表现
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出行”作品究竟何时出现,出于何人之手,有待考证。但是可以肯定,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霍桑的《小伙子布朗》和麦尔维尔的《白鲸》都是美国浪漫主义时代最杰出的“出行”作品。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将主人公的“自然”出行与“梦幻”出行结合在一起。为逃避田间的劳作和老婆的吵闹,瑞普向大山出行。在山上,他误饮小矮人的仙酒,在梦乡一呆便是二十年。当他醒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时,悍妻已故,庄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表层意义上,瑞普的“出行”历程实际上表达了“逃避责任和历史”(Mednick 1985:47)这样一个更深层的主题。瑞普象征着处于成长时期的幼稚、粗心、富于幻想和快活的美国人,他的悍妻象征着清教时期的清规戒律和富兰克林式的劳动哲学,小镇本身则象征着日益变化的美国。在现实主义文学中,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以及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出行”文学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再现的是少年主人公哈克的“出行”和心理的成长。哈克是密西西比河畔圣彼得堡镇上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然之子”,后被富裕的道格拉斯寡妇收养,并进行文明的教化。然而岸上文明社会的浮华、虚伪和残忍使哈克健全的儿童天性时时受到压抑和戕害,并成为他出行的精神动机。为了最终摆脱文明社会的束缚和暴虐,哈克决定乘木筏顺密西西比河而下,遁入大自然。哈克的出行意义深刻,“在意识层面上,它是一种逃避;但在无意识层面上却暗示着一种探索和追求”(Brooks 1973:1280)。这种无意识的探索即是追求自由,摆脱文明的束缚,保全健康的天性。哈克的精神追求和探索在全书第三十一章“祷告岂能扯谎”部分达到了高潮。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健全的天性和人类正义战胜了社会教化出的“良心”,哈克宁可下地狱也要救出与自己相依为命的黑人同伴。虽然最后哈克不得已又回到了“文明”社会,但他内心里还是想遁入西部印地安人居住的森林,重过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至于他是否付诸行动,马克·吐温在小说的尾声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暗示——哈克站在绝望的边缘。
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则是一个刚满16岁的纨绔少年,他短暂的流浪经历堪称一曲“出行”和探索的悲歌。考试的失利和父母的严威迫使霍尔顿逃离学校和家庭,遁入纽约这个“文明”的都市。三天自我放逐式的漫游和冷眼旁观使他发现外面的成人世界远比校内的生活虚伪和庸俗,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他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决心逃往西部的大森林,像大卫·梭罗那样,盖一间小屋,靠自己的勤奋劳动过一种宁静简朴的田园生活。然而不同于梭罗和哈克的是,在霍尔顿的时代,曾在美国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西部边疆拓荒已经结束(Smith 1950:1824),霍尔顿幻想中的纯朴的西部地区已不复存在,已经没有大自然可以作为他的精神避难所了。这是霍尔顿的无奈和悲哀,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不满于物欲横流而又无处逃遁的美国人的无奈和悲哀。所以霍尔顿的结局是彻底的人生绝望和精神崩溃。在失去自然归宿的境况下,后霍尔顿时代的美国人将通过在大路上漫无目的地出行来浪费自己的青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美国现代主义阶段最著名的“出行”文学作品。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表达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出行”与“虚无”。《在路上》真实地反映了二战后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一部分美国青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主人公狄恩·莫里亚蒂可算是“垮掉”文学中塑造得最为贴切的“反英雄”形象了,离经叛道的主题在他身上也体现得最为充分。他先后三次结婚,周旋于已婚和未婚妻子之间,并在旅途中与其他女人随意发生关系。他是个疯狂的人物,有时大喊大叫,放荡不羁,有时又以学究式的口气说话。他可以马不停蹄地飞车千里去找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又往往因一点小事与人不欢而散。
中国的“出行”略有不同。历年的战乱、仕途的坎坷,使得我国古代的诗人不断地随人民迁徙流离或独自漂泊出行。中国文人的出行,就像蜜蜂酿蜜,春蚕吐丝,使得文化散发出馥郁清新之气。旅行中沿途的风景、产生的寂寞、独立的思考、涌动的乡愁和忧国的情怀,无不成为汩汩泉眼,倾泻着文人的内心的“文化苦旅”。先秦两汉时,屈原写《离骚》,是遭忧离别之辞。唐朝、五代十国时期,表现“出行”的诗作就更多。李白的《行路难》以出行的艰难比喻世道的险阻,抒写诗人在政治道路上遭遇险阻后的愤懑之情,以及他面对险阻豪放乐观的情怀。杜甫的《兵车行》以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和连年征战为背景,揭示人民所遭受的迁徙和出行之苦。宋、金、元朝时代,李清照的《声声慢》,写于晚年流寓江南之时;马致远的《天静沙·秋思》更是以“断肠人在天涯”的千古名句,表现了出行的艰辛和孤独。到了明清时代,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出行”主题便以局部或整体的形式在小说中得到形象的表达。明朝陈仲林的《封神演义》是一部神话魔幻小说,更是一部“出行”文学作品。
《封神演义》以武王伐纣为主线,表现周武王始终不忘替天行道、救殷商臣民于水火的重大使命,挥师东进大举讨伐纣王暴政,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遭受了各种不同的灭顶之灾式的考验。但在以姜子牙为代表的众神帮助下,终于在经历各种危难后后完成了除恶安良和建立周朝的重大历史使命。在“武王伐纣”的大叙事背景下,也不乏个体英雄的出行叙事,如周文王姬昌和武成王黄飞虎的反离朝歌等,都充满了“出行”的艰险。这种个体英雄的“出行”故事也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长篇小说中以局部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和“林冲雪夜上梁山”等。《西游记》是明末出现的中国最伟大的“出行”小说。唐朝皇帝受到困厄,于是委托唐僧西天取经来解除王国的灾难。象所有的出行一样,唐僧的西行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各种妖魔鬼怪和人间的情感纠葛不断地阻止他的西行。值得庆幸的是,唐僧的西行有众多的帮助者,身边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天上和佛界还有众神予以相助,纵有八十一难,取经任务终得完成,师徒四人也修成正果。
到了现当代时期,随着影视的繁荣,以《长征》、《走西口》、《闯关东》和《下南洋》为代表的表现“出行”情结的史诗性影视剧更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在文艺中呈现出来。1930年代,乌云笼罩着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相继对中央苏区发动了5次军事围剿。以李德、博古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红军惨遭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遵义小城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党从幼年走向了成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长征》以电视剧方式再现了这段历史,而《闯关东》讲述的是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户山东人家为生活所迫而离乡背井“闯关东”的故事。它以主人公朱开山复杂、坎坷的一生为线索,其中穿插了朱家三个性格炯异、命运不同的儿子在关东路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和考验。“闯关东”这种民族行为是在中华民族特定历史背景下被迫进行的民族大迁移,关东路上,山东大汉勇猛闯荡,历经了一次次波折磨难,饱受土匪、官兵、土豪、乡霸、流氓流民等的欺诈,各种各样的困难让苦难之下的朱家父子、兄弟、夫妻最终对人生和世道产生顿悟,开始走向革命。
4. 《愤怒的葡萄》与《走西口》
中美现代文艺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出行”作品是《愤怒的葡萄》和《走西口》。为了表现“出行”这个宏大的主题,斯坦贝克采用了《圣经》式的和史诗性的结构。《圣经》的神话模式主要是“伊甸园”、“出埃及记”和“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等,《愤怒的葡萄》全书30章也可以划分为三部分,即俄克拉荷马(第1至第10章)、出行(第11至第18章)和加利福尼亚(第19至30章)。这三部分大体上和《圣经》的“伊甸园”、“出埃及记”和“死亡与复活”呈结构性对应。首先,斯坦贝克用16个插入章、长达100多页的篇幅来渲染俄克拉荷马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背景、66号公路上的逃荒实况以及季节的自然变化,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史诗般的背景,使读者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了解约德一家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美国季节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出行的必然性以及他们美国梦破灭的必然结局。例如,第一章用全景式的笔法描写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干旱及其对人们生活和心理的影响,这就为读者揭示了一个现代荒原的图景,同时也预示了以约德一家为代表的季节工人出行寻求新家园的必然性。第12章用全景式和蒙太奇的笔法记述了66号公路上季节工人的大逃难以及约德一家的实际出行,这就将一般和个别、整体性和典型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到了全书的第19章,约德一家和其他的西行家庭终于来到了梦想的加利福尼亚。然而加州并非他们所想像的迦南圣地,这块盛产葡萄的乐园早已异化为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面对这一新的困厄,他们精神上开始顿悟。汤姆与镇压工人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凯绥为救汤姆而甘愿代人受过,就像耶稣为拯救世人而上十字架一样。对于凯绥来说,监狱的日子就像耶稣在旷野度过的日子。在那里,他感悟了人生的真理,认为人性的堕落是因为贫穷所致,而摆脱贫穷的唯一办法就是组成一个群体来和压迫者抗争。因此他出狱后积极组织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不幸被农场主的走狗杀害。凯绥作为一个拯救人类的先知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他的死教育了汤姆,使其最终从个人主义的窠臼中摆脱出来,将自己的灵魂融入群体的大灵魂中,并成为一个新的先知。汤姆打死杀害凯绥的敌人后藏在一个幽暗的洞穴,这个洞穴既是旷野的象征,又是子宫的象征。他从洞穴中走出以及和母亲的告别象征着耶稣从旷野中获得启示和灵魂的新生。他对母亲说:
也许凯绥说得对,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一个大灵魂的一部分……到处都有我……不管你往哪一边望,都能看见我。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场。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场。……我们老百姓吃到了自己种的粮食,住上了自己造的房子的时候……我都会在场。(斯坦贝克1982:553)
至此,汤姆在灵魂中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他踏入了新的人生征途,投入到为人民谋利益的宏大事业中去了。汤姆的转变也深深地影响了约德妈,她从儿子身上看到了博爱,看到了人类救赎的希望。她和其余家人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后迁移到山上的一个仓棚,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行将饿死的男人。约德妈给女儿罗撒香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女儿便躺在那个挨饿的男人身边,将奶水喂给他。这一崇高的行为标志着罗撒香从一个极度自私、只关心自己腹中孩子的女人变成了伟大的人类之母,她的转变标志着约德一家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之旅。他们经过出行虽然没有抵达物质的乐园,却获得了精神的升华和救赎,进入了崇高的境界。
与《愤怒的葡萄》一样,电视剧《走西口》一开始也形象地再现了剧中人“出行”的历史语境。20世纪初年,在素有“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的山西祁县,乡民靠垦种上岭下坂活命。然而,连年的自然灾害后,天天有人成为饿殍,民不聊生。于是,男人们背起简单的行囊,听着女人们合着血泪唱出的《走西口》踏上了出行之路。在这一大背景下,电视剧将镜头聚焦到故事的主人公田青一家。由于染上了赌瘾,田父输掉了祖上的田家大院和自己漂亮的老婆淑贞。田老太太被气死,田父在无奈之下走了西口。淑贞幸得此前被她所救的革命党人、兴中会会员徐木匠挺身相救,才免于受到恶少夏三的污辱。为了养活儿子田青,淑贞被迫将九岁的女儿丹丹送给梁家当童养媳。田青长大后,大旱和匪祸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为了生计,为了收复失去的田家大院,田青决定带着姐夫梁满囤去走西口。
与约德一家的经历相似,《走西口》中的田青也在“出行”历程中获得精神的升华,亦即“崇高”。途中,田青和梁满屯先是结识了同是走西口的王南瓜,三人结伴而行,后来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包括被土匪刘一刀裹胁进了黑土崖上的土匪窝,同时被土匪劫持到黑土崖的还有年轻貌美的姑娘豆花。田青率领众人逃出匪窝,历尽艰辛到了包头,结果反被他所营救的裘老板指认为匪首,被官府判斩。豆花也被未婚夫赶出家门,共同的命运使得豆花对田青产生了爱情。在田青即将被斩首的时候,革命者徐木匠和诺颜王子及时赶到,救下了田青。秉承儒家的宽容道德,田青与裘老板冰释前嫌,并应邀到裘老板的皮货店做管家。恪守坚定的儒家道德信念和对翠翠的爱情忠贞,田青拒绝了与裘老板女儿裘巧巧的婚姻,离开裘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而面对金钱和利益的诱惑,梁满屯却抛弃了自己善良的妻子田丹丹,做起了裘老板的上门女婿和迫害田青的小人,也就是说他在“出行”的途中迷失了方向,最终导致了堕落和死亡。
在包头和恰克图创业的岁月里,虽然田青在为人处事上处处遵循儒家的美德,但灾难却不断地降临到他头上。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所处的黑暗的社会。政治的腐败和官匪的猖獗,使任何一个按儒家道德规范行事的晋商都无法正常地做生意。在革命者徐木匠和诺颜王子的帮助和教育下,田青逐渐地意识到儒家道德规范的局限性,并将旧的田家祖训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符合时代发展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大忠大爱为仁、天下一统为仁、世界大同为仁。大孝大勇为义、民族兴亡为义、祖国山河为义。修齐治平为礼、自强不息为礼、家国天下为礼。大恩大恕为智、福亏自盈为智、钢柔相兼为智。公平合理为信、以义取利为信、一诺千金为信”。这种对儒家文化核心重新的诠释与扩展,不仅延伸了这一文化的内涵,而且扩张了本剧思想层面的张力。尤其是故事的结尾,在深明大义的母亲支持下,田青变卖了作为田家基业象征的田家大院,所得钱款成为诺颜王子和革命志士参加北伐战争的经费。这表明母亲和田青都获得了灵魂的“崇高”,母亲成为了革命的母亲,田青也在妻子豆花“走西口”的歌声中,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5. 结语
提起“在路上”一词,人们就首先会想到20世纪美国作家杰凯鲁亚克创作的、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精神宣言书的《在路上》。其实,作为“出行”文艺外在表现的“在路上”不是一个突兀的现象,而是中美文化史上一个共同的民族心理情结,并在中美文艺史上有多种形式的表达。这些作品通过对人“在路上”的状态的描绘,指向人的心灵和信仰历程的追寻。当然,由于中美文化的差异,虽然同是围绕“出行”展开故事,作品表现的方式却不尽相同。美国作品中多表现个人在出行途中对宗教信仰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以及在出行途中遭遇的毁灭或救赎,中国文艺作品多表现出行途中世道的艰难、出行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以及他们通过出行获得的灵魂崇高。揭示中美文艺中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对于研究比较两国文化和文学的异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Brooks, Cleanthetal. 1973.AmericanLiterature(Vol. 2) [M]. New York: St Martain’s.
Gary, James. 1971.JohnSteinbeck[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Minnesota Press.
Mednick, Fred. 1985.AnIntroductiontoAmericanLiterature[M].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Henry Nash. 1950.VirginLand:TheAmericanWestasSymbolandMyt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卡尔·荣格.1987.心理与文学(冯川、苏克译)[M].北京:三联书店.
廖永清、张跃军.2008.美国文学中的旅行与美国梦[J].外语教学(4):62-65.
马润生.2003.论史诗性[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王俊斌.2007.近代历史上的“走西口”[J].山西档案(5):49-51.
约翰·斯坦贝克.1982.愤怒的葡萄(胡仲持等译)[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詹姆士·罗伯逊.1990.美国神话美国现实(贾秀东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