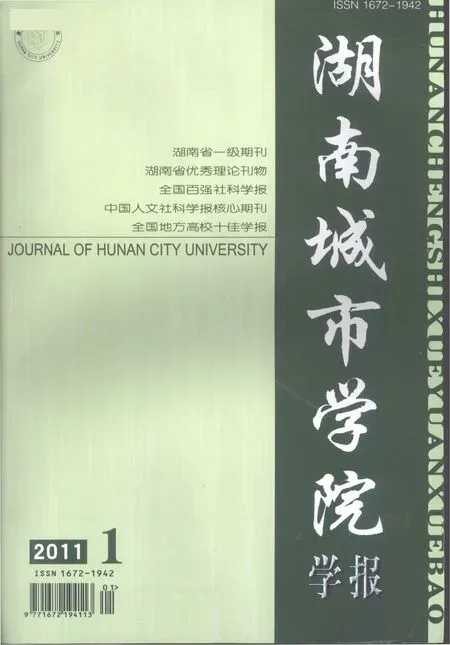梅山教是宗教信仰还是民间信仰
吴秋林
(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文化学院,贵阳 550025)
梅山教是宗教信仰还是民间信仰
吴秋林
(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文化学院,贵阳 550025)
梅山有两个意义上的概念:一是地理上的梅山,二是人文上的梅山。梅山教不是一种宗教,也就不是一种宗教信仰!梅山信仰是一种具有比较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形式。它的存在有自己的本体,与其文化地域和文化有强烈的共生性和独立的信仰文化形式意义。这种类型的信仰文化形式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是一体的,我们不能用宗教的信仰形式评价体系来评价它。
梅山教;宗教信仰;民间信仰
在信仰文化的历史上,有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即信仰文化的形式认定。取得“话语权”的是来源于西方的宗教理论,是它们认定了什么是宗教,什么不是宗教!这也许没有什么问题,用某种理论的概念和学理来辨析宗教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是,一旦话语成为一种“权力”之后,经过西方宗教理论确立的“宗教”意义,却把异样文化中的类似事物“异化”为“准宗教”、“原始宗教”、“野蛮人的宗教”、“自然宗教”等等,而把自己的宗教文化奉为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最高宗教文化阶段,并且认为由此而来的宗教才是人类文化中唯一可以称为宗教来运行的信仰文化形式……故而在这样的宗教文化中的,异族人的信仰文化形式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异族人的文化亦是微不足道的。把“梅山教是宗教信仰还是民间信仰”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出来,就涉及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文化课题。
一、梅山
梅山有两个意义上的概念:一是地理上的梅山;二是人文上的梅山。
地理上的梅山在历史上的记载最早始于宋。《宋史》:“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熙宁五年(1072年)……遂檄谕开梅山……乃筑武阳、关硖二城。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并二城隶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1]《湖南通史》中,这些区域则表述为“大致在今宁乡、邵阳、益阳和湘乡之间,中心在今安化、新化一带。新化为上梅山,安化为下梅山。”[2]
上引所述“其地”的四至即今湖南省中部雪峰山麓之中北部、资江中下游至洞庭湖平原的东起长沙、南至邵阳、西至沅陵、北至常德的广大地域。在这片地域中,今有1000多万人口,苗、瑶、土家、侗、壮等少数民族有50多万。
这样,地理上的梅山最明确的指向就是湘中,而新化、安化县则是这一区域的中心区域,“梅山地区”这样的地理区域概念则随着不同角度和不同因素的认定而变化,亦大亦小。
梅山,或者说梅山地区也不是一个因地域而确立的名称。关于梅山这一名称的来源有三种:一是因为其山产梅而得名;二是以汉代的梅鋗因助汉高祖灭秦有功受封于湘中山地,并且其在湘中山地以默林为家故得名;三是源出苗语“皋芈”,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苗语中的“芈山”是“梅山”的异写,这块地方盛产枫木,是芈姓王族子孙居住的地方。
以地域特征、物产特征、人文特征等因素来命名某个地理区域,是地名成名的基本路径,而“梅山”这一名称的出现亦莫能外,它人文因素、物产因素都有,而地域特征稍弱,故我们反而在其地理特征上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有这地方相对于湘是开发得最晚的一块地域的基本印象。“熙宁五年……遂檄谕开梅山……乃筑武阳、关硖二城。”这“熙宁五年”是1072年,而湘作为古代楚地的一部分,其许多地方的开发远远早于此地。
这是地理上的梅山,而“梅山”这一地理名词单独存在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有在“梅山峒”和“梅山峒区”这样的词汇下才有意思,但这又成为我们所说的人文意义上的“梅山”了。可为什么在1072年才会“开梅山”呢?是什么吸引了“外来者”的目光?使他们要在1072年时“开梅山”呢?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在梅山,不但地理上的开发比较晚近,且文化上的认定也比较晚近。在11世纪时,我们才在《宋史》中看到“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这样的字眼,但就是这样一句话,使这一地区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文化认定”,并成为今世人们一切“文化想象”的源头。“峒”(原为“硐”)是唐以来中央政权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建置的县以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后衍化为部分苗、瑶、侗、壮等民族聚居区地名的泛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表述?是北宋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还是本地的文化发展的内因驱动?肯定在这个时期的南方一定发生了文化上的一些重大变化,而“梅山”就是这个变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今天贵州省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比如侗族的形成。今天称为“侗族”的族群,基本上也是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峒蛮”的一部分,在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建构之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族群,并且得到历代中央政府的承认和尊重。也许“梅山峒蛮”没有这样幸运,但它在文化上也一定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和发展,要不,我们今天没有理由来如此看重人文意义上的梅山文化。所以,梅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一人文概念。
在今世,好事者把所谓的梅山文化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形成期,又称为古梅山时期”,指的是1072年《宋史》记录梅山之前的时期;二是融合期,又称为旧梅山时期,指的是1072年至1919年;三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发展期,又称为现代梅山时期。我们对于这样的分期不做评价,但这肯定是一种人文意义上梅山的一种表现。
人文意义上的梅山表述,还有空间和内容的意义。空间大致指“梅山地区是指现在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湘江与沅江二水之间的广大区域。……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3]内容指在这样一块地域中,一般意义上文化的一切表现都可以视为“梅山文化”,有巫傩的、习俗的、民间文艺的、工艺的,甚至还有武术的等等。但梅山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并引起人们的重视,应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性质的文化表现,因为如此的区域性文化表现随处可见。我以为,梅山之所以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热点,是因为其中我们今天称之为“梅山教”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是梅山文化中的“梅山教”吸引了我们的眼球。
二、梅山教
在梅山地区,“梅山、梅山教”这样的称呼是很久以前就有的说法,但是,这样的称呼并没有直接导致“梅山教”这一所谓宗教的学理认知,而基本上局限于“巫”术的一种和猎神格的认识等等。
在一本称为《上梅广阐宫傩事》的书中,其介绍了梅山教所能够举行的仪式。这是一为“梅山教”教内人士自己的著作,而不是宗教学、民族学学者们的田野采录。这为师者的秦国荣在书中描述:他们这一师门有一系列的传承系统和规矩,能够举行的诸如:“酬还都猖大愿”、“大宫和会”、“大宫和会傩戏”、“冲攘急救劝神”、“灵宝玉阳炼铁罐”、“七七罗天章蘸”等仪式。在所谓的梅山教中,也自然有许多规则,一方面约束“师者”,一方面也劝戒百姓。
这些内容与在中国南方广泛存在的“巫傩文化”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是巫傩文化在梅山地区存在的一种形式而已。
但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随着对梅山文化研究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步从学理上把原来的所谓梅山教,上升到一种宗教性质的文化来认识它。
胡起望在《论瑶传道教》一文中就说:“梅山是道教中的一支梅山教的故地。在本世纪30年代多次到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的唐兆民曾指出,大瑶山瑶民的宗教信仰,有的是‘梅山教’,有的是‘茅山教’。”[4]
在张泽洪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梅山教》一文中,他说:“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中,起源于湘中梅山的梅山教,是具有多元族群影响的宗教。”[5]
在张有隽的《瑶族与华南诸族梅山教比较研究》一文中说:“梅山教,或被称为道教梅山派、武教、法教、师公教的宗教,是华南汉、壮、瑶、仫佬、毛南、侗等民族民间信仰的一种宗教。”[6]
在宗教学界和民族学界还有许多学者涉及了梅山教的研究,故张泽洪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梅山教》一文中说:“民族学界张有隽、胡起望、宋恩常、董络、马少侨、顾有识、赵砚球等人都曾从不同层面论及梅山教。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梅山教进行探讨,以与民族学、道教学界同好共商。”[5]
在这两界的探讨中,似乎宗教学界比较倾向于其只是一种民间信仰的宗教,或者说“准宗教”,而民族学界则比较热衷于把它视为一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宗教。这是一个互相潜越的话题,但恍惚间梅山就成了一种南方宗教,而且是一种影响力巨大的宗教,并且与古代的蚩尤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如此等等。
在外界视“梅山”为一宗教时,也有人专门从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行为、宗教组织等四个方面来考虑它的存在依据,这在时下已经有许多论述,并且都可以在所谓的梅山教中寻找到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亦可以判定其作为宗教而存在的性质,但是,在人类的文化形式中,也不仅仅是宗教的信仰形式具有这样的内容。
但是,真正的被视为最权威的界定中,梅山教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宗教地位,而是一种“准宗教”。在陈子艾教授和李新吾先生的界定中,他们就说:“梅山教是指现存于古梅山峒区域民间并辐射于周边地域乃至跨省、跨境外的一种自然神和祖先英雄神相交融的多神信仰,是深受道教正一派影响的介于自然宗教与人为宗教之间的准宗教。”[7]
实际上,“准宗教”和“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引发了我的关于“‘梅山教’是宗教信仰还是民间信仰”的思考。
三、梅山信仰是民间信仰
梅山教不是一种宗教,也就不是一种宗教信仰!“梅山教”这个词汇我们在旧时称呼它时,实际上只把它看成是一种具有比较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所以说梅山信仰是一种民间性质的信仰文化,而不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宗教信仰。
其理由有三:
一是梅山信仰的基本形态与中国南方的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民间信仰一样,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地方,把它单独作为一种宗教来对待是不妥的。
二是宗教信仰中有信仰文化表现,民族民间信仰中也有自己的信仰文化表现,二者都有自己的信仰本体,也有自己的信仰表现形式,而且其信仰形式还不是一种可以对比的事物,故我们不能使用宗教信仰的形式关系来评价民族民间的信仰形式关系。
三是民族民间信仰形式是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多样性为共生的,即它的存在有自己的文化意义,而且每个文化共同体中的信仰体系都有自己的运行机制,有自己独立的信仰形式,没有必要去外部寻求一个统一的信仰形式,比如某种宗教的信仰形式。
在宗教学的学理表述中,“佛、法、僧”三宝是一组基本的词汇。“佛”也理解为上帝、主神等,即一个信仰本体,这个信仰本体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一群;亦可以是一群,但有主次之分。这个本体主要是一个观念的本体、一个精神的。法就是法度,比如说基督教中的“摩西十戒”、佛教中的“五戒”等等,这个法度在民间状态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法。僧也就是组织,即专门研习和传播前面两个内容的组织人员。这三个内容就是我们现今所说的宗教的基本构成,没有这些,你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教。这个宗教的概念是在现代宗教形态下形成的,也就形成了信仰文化的一种最高程度上的表现形式。我们的世界也是以此来判断宗教的。这可能没有任何问题,但强调宗教信仰为信仰文化的极致者,就可能在学理上出问题,因为他们可能认为,只有宗教的信仰形式才可能表达信仰,而其他的信仰形式就是有问题的,不可信的等等,比如说基督教历史上的“异教徒”一词就基本等同于敌人。其实,在世界上,每一种文化共同体都会有自己的信仰形式存在,并且是自己文化的基础性结构,而且深深地影响到其文化的基本表现,即有什么样的信仰形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而,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信仰形式下运行的。梅山信仰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特定地域中运行的信仰文化形式!
在梅山地区出现的这种信仰文化形式与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出现的包含巫、道、儒、佛,以及“万物有灵”信仰为一体的民族民间信仰形式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只不过各地的信仰主体有所不同。比如贵州等诸省出现的阳戏坛的信仰形式,其主神是“三主”(川主、药王、土主);贵州等诸省出现的傩坛的信仰形式,其主神是傩公、傩母。而梅山诸坛的主神为“巫工百匠”,并且以猎神为最,其巫意最浓,因为人类最早的巫意表达就在于狩猎,也就是说,猎神是人类巫术之神的最早神灵,也是影响最为久远的神灵。
在这些以坛为存在形式的信仰体系中,在形式上受道家的影响最大,但信仰内容上却千差万别。即民族民间的信仰以道家的“坛”的形式,结构了各自的信仰文化体系和文化,在以族群文化为重的文化共同体中,族群的原始信仰主体、或者说族群的祖先英雄人物就成了此坛的主神,比如贵州省侗族的“萨坛”信仰就是这样的民族信仰形式。再比如说土家族的傩坛,其主神傩公、傩母就已经变化为自己民族的祖先英灵的一种存在形式,而来自于梅山的神灵,反而成为傩公、傩母之下的一个称为“翻坛小三”的小神。
在民间,主要是汉族的各种坛中,民间的信仰形态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并且与“官家”的一般意义上的信仰对立。在这样的坛中,也使用的是道家的外在形式,但包含就极广了,在“官家”推行儒、佛、道诸教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就一直存在巫意的信仰形式,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
在这样的信仰形式中,历时和共时性的人们就把不同时代的有灵异的事物和人物,都会“装”到这个信仰形式的结构中去,因为这个信仰结构是开放性的。
梅山信仰形式与中国南方的民族民间的信仰形式并没有什么可以“超然”为一种宗教的地方。但实际上已经有许多人把它作为一种宗教来进行研究了,在上述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这样大量的观点。我以为这是一种称之为文化的心灵扩张主义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一篇称之为《古梅山峒区域梅山教探究——以师公的信仰为中心》表现得最为彻底。这是一篇来自于湖南师范大学宗教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提要”中有这样的文字:
通过对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行为与宗教组织四个方面的特征分析,可以发现,古梅山峒区域梅山教是历史上本土原始宗教与外来道教相结合的产物,本土与民族特征非常明显。
梅山教的信仰是一种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泛神信仰,它涵盖了天上、地下、人间的众多神灵;教义表现在其济世利人和来世成仙。人与神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和”—调停和解,这是梅山教非常特别的宗教情感。梅山教的仪式活动主要表现在替人喃神赶鬼、驱邪治病的许愿还愿,这与其济世利人的教义相符。梅山教的组织主要以家族内部自我传承为主的坛场模式,其教派整体松散,各坛场之间往往各自为阵。梅山教的早期是一种原始的巫术形式,历史由来己久;正式作为一种的教派,从自造的经书与史志资料推测,形成时间大约在元代以后。
梅山教的形成,与道教的传入与影响关系密切。道教在本土扎根、发展,完成了本土化;同时,本土宗教也完成了道教化,从而产生了一种异于本土原始宗教又异于外来道教的梅山教。梅山教与道教在古梅山峒区域作为教派互相独立,并列存在;在具体分工方面,二者又职司互补。总之,梅山教作为一种宗教,是本土原始宗教与外来道教在历史的交流与融合中形成的产物,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属性与特征。之所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符合了民众在当时历史与社会环境下生存与生活的需要;作为一种民间的宗教信仰,我们要正确看待其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见《中国知网》)
我不否认这种研究的权利,但实在是梅山信仰中“宗”的维系非常勉强,“教”的程度也极为虚弱,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形式来研究会“掩盖”更多的信仰文化意义。
在第二个问题上,我们不可否认,现代宗教的理念肯定是在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没有必要把现行的宗教信仰形式“套用”到一切信仰形式中去表现其意义,因为这不会正确地表达其他信仰形式的意义。我们前面说过,文化运行的核心是信仰文化的基本形式,有什么样的信仰文化形式就会什么样的文化表现,也就是说,信仰形式的存在是与文化式样的存在是相适应的。这样的民族民间信仰形式就是自己的文化环境中的自在系统,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如果突然有一个在外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信仰文化评价体系来评价这样的信仰文化体系,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除了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准宗教之外,还会有什么评价呢?而这样的评价会在后面存在典型的“文化阴谋”,即你是“落后”的,而文化的多样性表述中是不会“文化落后”这样的字眼的。文化是相对而言存在的,信仰文化的形式也是相对而言存在的。这就是我说的不要把梅山的信仰形式看成一种宗教的最大理由。
在类似于梅山信仰形式的诸多表现中,它们肯定不可能具有现代宗教的完备的主神和神系。也不可能具有现代宗教的“法度”,这样的东西要么在民间的习惯法中,要么在官方的司法制度中。至于“僧”这样的角色,他们更多的是“通神的人”,是神灵与人的中介,是一种如《金枝》中金枝的守护者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上的意义,而不是现代宗教学中“僧”的意义。还有,现代宗教学意义上的“教化”更不可能有所表现。在中国,儒家的“人文教化”在很早就取得了主导地位,而民族民间的信仰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表现机会。这样一来,我们有必要把梅山的信仰形式视为一种宗教吗?更不要说希望从“建构”梅山教中得到什么了。
其实,把梅山信仰作为一种民族民间的信仰形式来对待,才是真正推进深化认识梅山信仰的最好认知。虽然在叶明生的《共生文化圈之巫道文化形态探讨——福建闾山教与湖南梅山教之比较》一文中,只把梅山信仰看着是南方巫教一个“不起眼”的组成部分,但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梅山信仰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信仰文化形式,它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周边的广大地区看到,但这种影响不是宗教性质的影响,而是文化中神性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民族民间的神性文化表现来说清楚它们的之间的关系,而使用宗教学的观念来解读就未必。
在第三个问题上,我们说“民族民间信仰形式是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多样性为共生的,即它的存在有自己的文化意义,而且每个文化共同体中的信仰体系都有自己的运行机制,有自己独立的信仰形式,没有必要去外部寻求一个统一的信仰形式,比如某种宗教的信仰形式。”多少年来,在中国南方,这样的民族民间信仰形式的一直“推动”着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多样性的进程,是我们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发展的一种基本文化动力。如果我们使用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宗教理论的信仰形式来匡定它,那它的生命活力就可能丧失。存在于中国南方的民族民间的信仰文化形式,在历史上的“消化”能力是惊人的,巫的、道的、佛的、儒的、自然灵异的……它都“消化”在自己的文化框架中,并且成功地运行于民族和民间,成就了多种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可以说,没有一样外来文化不被异化,或者说“地方化”了的。甚至于在中国南方的近现代历史上,抵御外来宗教的“文化干涉”最为有力和强烈的力量,就多来之于多种多样的民族民间的信仰文化。而这样的信仰力量是可以自在运行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如果只以宗教信仰才是唯一的信仰形式,那这样的信仰形式不是落后的就是野蛮的,甚至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只是信仰某种制度化宗教的人才有灵魂,而是所有的文化运行都会有自己的信仰体系,有自己的灵魂的。
[1] 脱脱. 宋史第40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196-14197.
[2] 伍新福. 湖南通史·古代卷[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4: 394.
[3] 刘楚魁, 刘辛田. 梅山民俗与旅游[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
[4] 胡起望. 论瑶传道教[J]. 云南社会科学, 1994(1): 61-69.
[5] 张泽洪.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梅山教[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4): 36-40.
[6] 张有隽. 瑶族与华南诸族梅山教比较研究[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4): 15-21.
[7] 陈子艾, 李新吾. 古梅山峒区域是蚩尤部族世居地之一—湘中山地蚩尤信仰民俗调查[J]. 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4): 1-6.
Meishan Religion is a Religious Belief, or a Folk Belief?
WU Qiu-lin
(National Cultural Institute,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For Meishan, it is of two concepts. One is geographical Meishan, and the other is the Meishan humanities. Meishan belief is a kind of folk belief with relatively strong faith. Its existence has its own ontology, which is of a strong belief in the symbiotic and independent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forms with its cultural geography and culture. This type of belief in cultural forms and the n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s a unity. We can not use evaluation system of religious beliefs form to evaluate it.
Meishan religion; religious beliefs; folk beliefs
K 203
A
1672–1942(2011)01–0022–05
(责任编校:易永卿)
2010-12-23
吴秋林(1955-),男,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