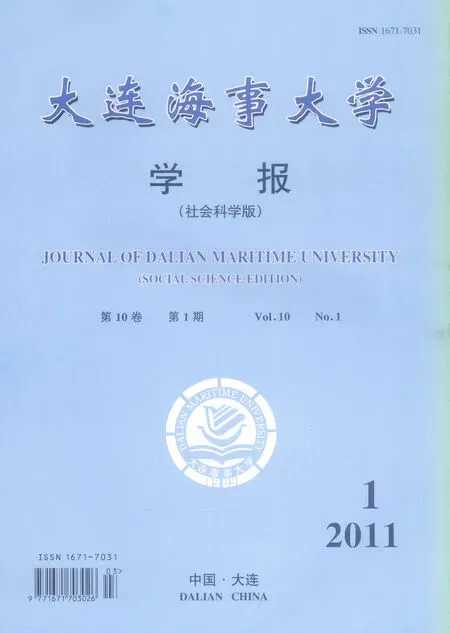中国遗失物归属制度的评析与思考
钟国才(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中国遗失物归属制度的评析与思考
钟国才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遗失物归属制度用于规范拾得人与失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物权法》通过外在的法律强制限制了拾得人取得所有权,实现了道德上的理想,然而立法者未意识到,任何道德只能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在中国现阶段,在对待遗失物的态度上,不能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相关制度设计有待完善。
遗失物;所有权;归属制度;拾得人;失主
所谓遗失物是指权利人因自身疏忽或自然原因遗忘于他处而不被任何人占有的动产。[1]遗失物归属制度属于物权领域。依据我国《物权法》第2条的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这里所谓物的归属,是指民事主体对物之所有权的享有。因此,所谓遗失物归属制度,简言之,即规范遗失物的所有权属于谁的制度。遗失物一经被他人拾得便在拾得人与失主之间就该物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此种权利义务关系往往有法律明确规定,如何配置因各国的社会道德观念及立法的价值取向而有所不同。理论上对于遗失物拾得制度的规范意旨,一直存在争议。[2]无论是中国《物权法》颁布之前还是实施之后,这一问题都激发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究其原因,因其映射出一般民事法律制度中所没有的高尚道德要求。因而,对遗失物归属规则、制度的探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剖析,更应是在新时期人们一般观念层面上的解构思考。
一、中国《物权法》遗失物归属制度的基本立法思路
《物权法》在第109条至第113条规定了遗失物制度。其中第113条、第109条规定遗失物未被转让时,当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他首先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遗失人发现拾得人并且向其主张返还遗失物,拾得人应当返还。在遗失人没有主动联系拾得人的情况下,如果拾得人能够发现遗失人,他可以通知遗失人前来领取;如果拾得人不能发现遗失人或虽然能发现但不想主动联系遗失人,遗失人应将遗失物送交公安部门。公安部门能够通知遗失人的,应当及时通知遗失人前来领取;公安部门不能通知遗失人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并妥善保管遗失物。公告期间内遗失人前来领取的,其在支付相应的保管费用后有权领走遗失物;公告期满遗失人没有前来领取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另外,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考察《物权法》关于遗失物所有权取得制度的基本思路不难看出,《物权法》并未从善意取得的路径为拾得人设定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即拾得不是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方式。据此,拾得人被排除了将来获得遗失物所有权的任何可能性。拾得人在权利人认领遗失物时如拒不返还遗失物,则构成侵占遗失物的行为;拾得人如将遗失物转让,则构成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情形,权利人对此既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亦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只是权利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是无偿的还是有偿的,取决于受让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受让人如果是通过拍卖或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虽然其不能以善意取得为由阻却权利人对遗失物予以追索的权利,因为权利人仍然有权请求善意受让人返还原物,但善意受让人有权获得权利人支付的其因购得遗失物而付出的费用;权利人尔后有权再向无处分权人追偿这笔费用。如若不然,权利人则无权请求善意受让人返还原物。显然,中国《物权法》在处理遗失物拾得关系时继受的是罗马法的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只要权利人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都可以对拾得人提起拾得物返还之诉。拾得人则应当返还原物,其只能依无因管理要求权利人赔偿费用,无权向权利人请求拾得遗失物的报酬。[3]有观点认为,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的二年期间的性质应属除斥期间,二年期间届满,权利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即归于消灭。[4]该请求权为形成权,只要权利人提出返还原物的请求,即使善意受让人未将原物交付给权利人,善意受让人的动产所有权亦因此而消灭,动产所有关系回复到权利人所有的状态。[5]《物权法》的这一规定为权利人最终保有自己不慎遗失的动产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与保障,权利人断不会因拾得人拒不返还或拒不送交抑或擅自处分遗失物而失去对遗失物的权利。当然,权利人对上述权利可以主动选择放弃,如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不向受让人提出返还原物的请求的,即属放弃请求返还原物的权利,此时善意受让人才能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
此一系列法律规则所构成的遗失物制度旨在构建一种立法者所倡导的道德理想,昭示拾得人应当像尊重他人那样去尊重遗失物,否则轻则构成民法上的侵占,重则出民入刑,构成侵占罪;从而警示拾得人应当完璧归赵,否则不仅会受到道德的责难,且应受法律的非难。可见,此种拾得人归还遗失物的规范设计,强制指引拾得人履行由法律确保的道德上的义务,亦即拾得人返还遗失物是一种法定的义务。于是,拾得人负有法定义务归还遗失物是整个遗失物法律制度的核心立法思想。这种思想的逻辑前提是,拾金不昧为中国数千年所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应得到不断的发扬和光大。然而,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与之有关的争论却很激烈。争论主要聚焦于两点:其一,物权法应否规定拾得人的法定报酬请求权;其二,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当归拾得人抑或国家。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公开发表的论文以及学者主持起草的物权法建议草案均主张:拾得人的法定报酬请求权以及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应予规定。[6-8]提出这些主张的理由可谓非常充分。*“从实际生活考虑,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甚有必要:一是报酬请求权确实能给遗失物的返还提供激励机制;二是规定报酬请求权可以减少许多纠纷,消除社会矛盾;三是纠纷发生后,为法院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四是报酬请求的规定并不会损害失主多大利益,规定报酬请求权主要对失主有利。”参见文献[9]。[9]可《物权法》最终对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未予规定,且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综观中国物权立法过程,关于拾得遗失物法律后果的设计始终存在着道德理想价值取向和承认世俗利益的价值取向之间的斗争。
二、对中国《物权法》遗失物归属制度的评析
综观以第113条为核心的遗失物所有权归属制度,没有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拾得人所有权的取得”和使用“侵占”这样的字眼等。按照立法者的逻辑推导,拾得人拾得的物肯定是遗失物,因此整个物权法条文的设计,既然如此,根据传统的道德思想,“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拾得人返还拾得物的行为,纯属一种道德上的应当。此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应当由现在法律加以确保,岂知法律乃仅仅是最低的道德水平要求。注重道德,强调理想,本无可厚非。然若空有理想与热情,不注意人的正常需求,反而以道德和理想来排斥这些需求,时间一长,难免会造成普遍的虚伪。尽管高尚的道德和理想依然被提倡和称颂,内心却不再信仰它们,剩下的,则是千方百计谋求私欲的满足。且因这些欲望没有为社会所充分认可,甚至不为法律所允许,人们还可能采用种种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手段去满足私欲。如果说,法律并不能体现各种现实利益需求的本来面目,而是将它扭曲,这不仅会降低法的重要性,而且会极大阻碍社会的发展。因为承认各种现实的利益及其冲突并加以合理解决,是任何一个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概言之,如果法律完全追求道德理想,则不仅很难对现实生活起真正的调节作用,而且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遗失物制度当然也不例外。有鉴于此,整个遗失物制度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漠视拾得人利益的立场上的,这种倾向影响了整个遗失物制度的架构。在这个基础上,拾得人所拾得之物由于是他人之物,寻找权利人就成了整个遗失物制度的重点。此点从中国遗失物制度设计上的着墨轻重即可窥豹一斑。庆幸的是,法律还明白拾得人不一定知道权利人是谁,否则法律会强行拾得人必须将遗失物交给权利人。至于拾得人本身的权利,在负有法定归还义务的情况下不复存在。由此看来,立法者依然在肩负道德教化的重任,通过外在的法律强制彻底实现了道德的理想。然而,立法者可能未意识到,任何道德只能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缺乏自己的自觉选择,一切道德律都只能是他律,因为“道德是把善的意志,作为其要求的对象的。如果这种善的意志,不但是道德,而且也成为法律所要求的对象,那么善乃至道德,就立即变得不可能”[10]。
遗失物之返还,是现代民法学中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遗失物返还之立法,不仅涉及法律问题,同时涉及中国的传统道德问题。而拾得物之返还所涉及的根本问题还是拾遗物的归属问题,即所有权问题。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确实大多数规定了遗失物必须返还,拾得人不能取得所有权。然而,需要慎重注意的是,古老的中华法系追求的是和谐的立法理念、严密的刑罚理论、完善的行政法律体系。即使在被当今民法学界所关注的私法领域,自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商鞅等人主持变法、确立土地私有之后,历代封建法典都以严格保护私人的财产不受侵犯为主导思想。*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的著作《法经》中,就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法经》现已佚失,汉代桓谭的《新论》对《法经》的内容作了如下记载:“《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魏国的《法经》和秦国的《秦律》规定“拾遗者刖”,即对于拾得遗失物不返还原主的行为处以刖刑,其目的就是防止民众有“盗心”,保护财产所有人的权利。也即是说,中国古代法典对于强调的私人拥有的土地、住宅、牲畜及其他财物,都以法律的形式给予全方位的保护。按照现代的物权法理论来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物权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物权,它剥夺了财产所有人之外他人对于动产或不动产任何形式占有的可能,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原则。恰恰是这种立法精神直接影响了封建法典对于拾得物之返还的规定,其终极目的是达到定纷止争,从而奠定高枕无忧的物权秩序。
为科学配置拾得人和失主的权利义务,有必要明确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立法目的。由于传统民法强调所有权绝对理念,作为民事权利之一的所有权具有观念性,所有人即使丧失对动产的占有,也非是丧失对动产的所有权。在非基于所有人自己的意思丧失对动产的占有非是丧失所有权的前提下,出于保护私人所有权乃整个物权法律制度建构的基础和目标之考量,各国民事立法构建的拾得遗失物制度虽其具体内容有所差异,但确有首先规定他人可拾得该物并承担返还的义务。如《德国民法典》第967条、《瑞士民法典》第720条、《日本遗失物法》第1条等。中国《民法通则》第97条第二款、《物权法》第109条亦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归还权利人。”然而,现代物权法的理念是确保物尽其用,物权制度设计的核心不再是围绕着所有权做文章,而是在制度设计时如何最大化地发挥物的效用。
三、关于遗失物所有权之归属的理想构建
《物权法》规定遗失人在公告期满仍未前来认领就丧失遗失物的所有权,殊值赞同;但却把此时遗失物的所有权赋予了国家而非拾得人,这样的规定就值得商榷了。自罗马法以来,有正反两种立法例,即罗马法的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与日耳曼法的取得所有权主义。近代以来的诸多立法,基本上继受了日耳曼法的立法例。*参见《法国民法典》第717条、《德国民法典》第973条、《瑞士民法典》第722条、《日本民法典》第240条和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07条。中国《民法通则》第79条第二项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返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秉承《民法通则》的规定,中国现行立法关于遗失物的拾得依然采用罗马法的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然中国学者大多主张中国民事立法应采用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因为如依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拾得人即使拾得价值极小之物,如一分钱的硬币,也不能取得其所有权,而应返还于遗失人。这固然有发扬中华民族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的作用,但却有所不妥。其一,脱离现实,对人们的行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仅难以达到法律的预期目的,而且使法律规定形同虚设,不被信仰。其二,不利于发挥物的效用。路不拾遗,固为人们所称道,但将财产弃之而不加利用,实为资源的浪费,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利的。[11]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堪可赞同。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中国《物权法》这个传统美德的道德性体现在哪?凭什么说,将之入法就能确保这种德性?信手拈来的词汇,除证明我们守祖宗成法外,并不能说明其经过了批判性的反思。路不拾遗,是圣人的理想。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状态,集中表现在动机上。任何“拾”的行为的产生,必将被认定为动机不纯,亦即贪图小利,置君子之风于不顾。就义舍利的德性教化,从根本上清除了人们的不纯洁想法。从理论上来讲,若能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完全置换每个人内心不可名状的行动基础,自然所有人的行为将会如出一辙,“尧舜满天下”的大治美景必将得到实现。道不拾遗的圣人理想,作为道德规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将其入法就值得商榷了。假若法律所想象的人们个个都是道德高尚的人,那法律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无用可言,甚至对任何人来说,法律都已成为无必要的制度,人们的行为光有道德指引就够了,何必由法律来提供行为模式。然而,人类几千年的惨痛历史表明,舍法律而存道德是不可行的。法律只是最低道德水平的要求,如果法律对人类行为的要求上升到高尚道德要求的高度,法律就与道德无异,亦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人们在对待遗失物的态度上,不能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对于遗失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物权法》颁布之前的几个学者的建议稿依然有可取之处。
(1)改采取得所有权主义,使拾得人得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拾得物的所有权。如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规定:遗失物于通知或公告之日起6个月无人认领的,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价值微小的遗失物,自拾得人通知或报告之日起10日无人认领的,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但是,拾得人若为国家机关,不得依拾得行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拾得人侵占遗失物或违反法定义务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拾得人不得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
(2)承认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并在其报酬请求权未获实现前得留置拾得物。当然,拾得人侵占遗失物或违反法定义务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丧失报酬请求权。关于报酬数额的确定,有的主张应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但最高不得超过遗失物价值的20%。如失主已在其发出的悬赏广告中明确了酬金,则不在此限。有的主张酬金应相当于遗失物价值的20%~3%,遗失物价值难以衡量的,为适当数额。[9][12]此外,拾得人在公共交通工具等内拾得遗失物,有的学者主张借鉴德国、瑞士民法的做法,否认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13]然亦有学者主张,仍应肯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只不过拾得遗失物的人与住户、交通工具或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各有权获得酬金的一半。[12]
同时,依近现代民法,需限定遗失物拾得的构成要件。
(1)须为遗失物。遗失物,是指所有人遗忘于某处,不为任何人占有的物。构成遗失物必须具有下列条件:遗失物须为非无主物;遗失人丧失了对物的占有;遗失人占有的丧失须非出于本意,也非因他人的夺取;须非隐藏的物;须为动产。遗失物与无主物不能判明时,推定为遗失物;凡未为所有人明确抛弃的动产,推定为遗失物。
(2)须有拾得的行为。所谓拾得,是指发现且实在占有遗失物。发现与占有构成拾得行为的两要素,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拾得并非一定以拾得人在物理上享有支配不可,依社会的一般观念,凡有占有遗失物的事实,例如雇佣看守或登报声明,均可构成拾得。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拾得人,是指最先占有遗失物的人。拾得行为是由他人指示而实施的,指示人或指使人为拾得人。在他人住宅、交通工具或者机关、学校、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应当将遗失物交给住户或管理人,此时住户或管理人为拾得人。
现行《物权法》规定的拾得人义务应当予以保留。第一,通知义务。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以后,应及时通知所有人或其他有权受领的人。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不明时,应当发出招领通知并代为妥善保存,或者交公安机关或有关单位处理。第二,保管义务。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之后,应尽如同管理自己事务一样的注意义务妥善保管拾得物。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4条的规定,拾得人因故意造成拾得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国有学者认为,因拾得人重大过失致拾得物毁损灭失的,拾得人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参见文献[14]。王利明教授、梁慧星教授分别主持起草的我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亦采此种观点。[14]第三,返还义务。拾得人拾得遗失物的,应当返还失主。如果拾得人将遗失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则视为对他人所有权的侵犯,所有人可提起侵权行为之诉。*对此理论界认识不一,主要有不当得利说、侵权行为说、公平责任说和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竞合说,参见文献[14]。中国司法实践中采侵权行为说,如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4条规定:“……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14]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按侵占罪论处。此外,拾得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适用关于遗失物的规定。
四、中国遗失物归属制度的完善
《物权法》刚刚出台不久,短时期内要想获得伤筋动骨的重大修改,或许并不现实。既然现阶段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民法关于拾得遗失物的规定采用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及罗马法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的原则,那么,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不妨借鉴中外法典关于遗失物之返还的立法经验,做一些完善性的细化工作。
其一,借鉴唐代和元代设立遗失物管理机构的经验。国家本着便民的原则,在全国各区、县、镇等基层机构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由该机构定期公示拾得物,以方便拾得人送交和失主认领,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拾得人拣到遗失物后,如何将遗失物返还给财产所有人,大致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知道失主的姓名和住址,直接将拾得物返还给失主;第二种途径是拾得人不知道失主的姓名和地址,直接将拾得物送交有关国家机关,由国家机关公示后返还给失主。这就需要在国家机关内部设立一个相应的管理部门来处理此事,否则拾遗物很可能被某些工作人员私吞,无法返还给失主。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据《新唐书》卷46《百官一》记载:“司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门关出入之籍及阑遗之物。”对于阑遗之物,“揭于门外,期年没官”。在全国各地方,由拾得物所在的州、县、乡、里等基层组织负责公示,寻找失主。据《大元通制条格》卷28记载:“诸处应有不阑奚人口头匹等,从各路府司收拾……每月申部。”在皇庆元年(1312年)5月中书省颁布的公文中,规定由地方基层官吏里正负责收养阑遗人口和头匹,“凡有不阑奚人口头匹,责付里正主守收养,立法关防,用心点检,毋致逃易隐匿瘦弱倒死。按月申报,每岁三月九月二次送纳,实为便益”。
其二,拾得物在无人认领的情况下归国家所有。为了防止拾得人、拾得物管理机关非法侵占遗失物,侵害财产所有人的利益,应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作进一步的调整,对此种犯罪行为的处罚应比照贪污国家财产罪定罪量刑。
其三,现阶段《物权法》不妨参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合理内容。为了减轻拾得人、国家机关及遗失人的负担,提高社会效率,《物权法》应参照《德国民法典》第965条第二款“物的价值不超过十欧元的,无须通知”之规定,设立最低送交和公示的数额。
其四,《物权法》不妨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半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遗失物在无人认领的情况下归国家所有,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法律不应当加重拾得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拾得人拾到遗失物后,只需立即将拾得物送交有关国家机关即可,无须再承担保管、公示等其他义务。对于拾得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如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由国家机关向财产所有人(失主)追偿。
[1]李淑梅,郜永昌.论遗失物拾得[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5):116-119.
[2]董学立.遗失物拾得制度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37-40.
[3]钱明星.物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15.
[4]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M].台北:三民书局,1995.
[5]王泽鉴.民法物权·占有[M].台北:三民书局,1996:199.
[6]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4,35.
[7]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31.
[8]王利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05.
[9]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47-248.
[10]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82.
[11]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3辑)(修订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97.
[12]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3]郭明瑞,房绍坤,唐广良,等.民商法原理(2)[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7-98.
[14]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23.
CommentsonChina'sownershipsystemoflostpropertyandthoughts
ZHONG Guo-cai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 Wuhan 430072, China)
The ownership system of lost property is designed to regulate the j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keepers and the owner of lost property. By external law enforcement,PropertyLawlimits the keepers to obtain the ownership, and realizes the dream of moral. However, the legislators do not realize that any moral can only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free will. In Chinese present stage, on people's attitude at dealing with lost property, too much of the ethical requirements couldn't be asked yet, and related system design should be improved.
lost property; ownership; ownership system; keeper; owner of lost property
D923
A*
1671-7041(2011)01-0021-05
2010-11-01
钟国才(1968-),男,广州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