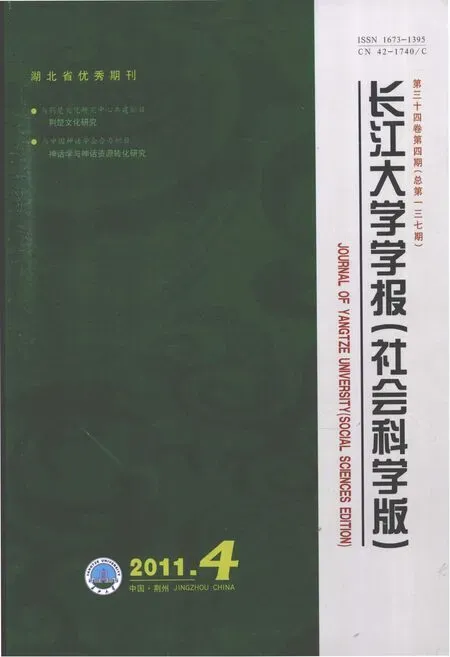《达洛维夫人》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①
李 伟 赵 娟
(宿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达洛维夫人》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①
李 伟 赵 娟
(宿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析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通过分析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战争对自然和女性造成的伤害,探索作品中女性和自然的紧密联系,可以发现伍尔芙希望构建两性平等、和谐生存的和乐世界的心理愿望。
生态女性主义;自然;女性;男权
将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的生态女性主义,为全面探究《达洛维夫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分析文本中有关自然的意象以及女性与自然对战争的控诉,可以展现这部充满生态女性主义意蕴的作品中自然与文明、女性与男性的对立。
一、自然与女性
伍尔芙在《达洛维夫人》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意境和被意象模糊了具体轮廓的物体,其中以故事中的两个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和雷西娅的意象尤其引人入胜。究其原因,在于作者将自然意象与被父权制操控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女性结合起来,通过自然意象,反映出两个女主人公真实的生活意味。
六月的一天,久病初愈的克拉丽莎·达洛维为准备晚宴,将这天的生活局限在家、花店及其间的一段街道,这有限的空间构成了鸟的囚笼。树林中愉悦的鸟儿,反衬出克拉丽莎内心的“森林”的依靠。在进入花店前的内心独白中,达洛维夫人将自己的内心比作“枝叶繁茂的森林”,而“密林深处”中掺杂着的哔剥的树枝声和践踏的马蹄声,深刻地反映出她身体和内心的苦楚与煎熬,“特别从她大病以来,这种仇恨的心情会使她皮肤破损、脊背挫伤,使她蒙受肉体的痛楚,并使一切对于美、友谊、健康、爱情和建立幸福家庭的乐趣都像临风的小树那样摇晃、颤抖、垂倒,似乎确有一个怪物在刨根挖地,似乎她的心满意足只不过是孤芳自赏!”[1]我们看到,原本轻盈活泼的达洛维夫人的精神森林被密林深处岌岌可危的意境渐渐淹没,导致她在“美、友谊、健康、爱情和建立幸福家庭的乐趣”中“变得异常苍白”。
常常被比作鸟的雷西娅尽管与克拉丽莎素不相识,却因为这一比喻存在着某些联系。在伦敦摄政公园中,雷西娅每每想到陪着赛普蒂黙斯来到伦敦而自己孤身离开家乡意大利和丈夫的古怪精神和异常行为时,便会觉得自己“好比一只小鸟,栖身在一片薄薄的树叶之下;当树叶飘拂时,鸟儿对着阳光睒眼,一根树枝的毕剥声也会使她惊吓”[1]。
二、战争、自然与女性
从古希腊文明到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明建立了强制征服、武力控制、人为改造自然的思想,确立了人在自然中的统治地位,即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不仅“为人而存在”,而且应当“成为人的奴隶”[2]。在以人类自身为中心的社会中,为了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畸形的私欲发动的战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伍尔芙在《达洛维夫人》中通过描写自然与女性受到战争的各种伤害,强烈展现了自然和女性对战争的不满与控诉。
战争摧毁了自然的美好,“欧洲大战的魔爪是如此阴狠,如此无孔不入,把一座谷物女神的石膏像砸得粉碎,在天竺葵花床里炸出个大洞”[1]。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树木的意象无疑是自然世界的象征。“树木是有生命的”,“人类不应该砍伐树木”,而在法国战场上,风景秀丽的村庄被毁坏,大量的树木被砍伐,自然遭受着战火的蹂躏。战争的黑夜夺取了黎明带给人们的宽慰。“当曙光洗净四壁的黑暗,照出每个窗户,驱散田野上的薄雾,照见那些棕红色奶牛在安详地吃草,一切事物重又整整齐齐地呈现于眼前,恢复了生存。”[1]大战结束后的平静生活则从侧面反映了战争对自然的破坏。“树木在婆娑起舞。……大地恍惚在说:美。仿佛为了证实美的存在,无论他往哪里看,无论他看的是房屋、栏杆,还是跨越栅栏的羚羊,美立即在那里呈现。……天空中,燕子翩然掠过,飞翔,旋转,尽情地飞进飞出,萦回缭绕,……到处都洋溢着美。”[1]
将取得战争的胜利看成是男人品格的实现和地位的象征的父权制社会,通过各种仪式化的符号去鼓励男人的攻击欲、占有欲,从而发动了被伍尔芙直接归咎于父权制的各种战争。英国虽然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其经济实力却被严重削弱,丧失了其“世界银行家”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战争中葬送的还有英国整整一代年轻人的美好前程。由于许多男人死于战场,使得青年女子婚姻没有着落,中年妇女也在可恶的战争中失去她们的丈夫。走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中,过着衣食无忧富足生活的达洛维夫人仍能深深感受到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与绝望。“战争已经结束,不过,还有像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那样伤心的人,她昨晚在大使馆痛不欲生,因为她的好儿子已阵亡,那所古老的庄园得让侄儿继承了。还有贝克斯巴勒夫人,人们说她主持义卖市场开幕时,手里还拿着那份电报;她最疼爱的儿子约翰牺牲了。”[1]在莎士比亚的诗句“不要再怕骄阳炎热,也不怕隆冬严寒”的鼓励下,克拉丽莎忙碌地准备着晚宴,积极地投入生活,期望自己能够走出战争带来的恐惧与困惑,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战争同样剥夺了雷西娅享有幸福生活的权利。作为一名志愿兵参加战争的赛普蒂默斯,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后,饱受在战争中死去的好友亡灵不断折磨的他患上了战后精神紊乱症。于是,赛普蒂默斯便用婚姻作为避难所,欺骗并引诱了他并不爱的雷西娅。作者借用雷西娅的感受,生动地描述了战争对女性的伤害。丈夫的疯狂使得雷西娅无法忍受,“她再也无法忍受……她宁愿他不如死掉!瞧着他那样愣愣地瞪视,连她坐在身边也视而不见,这使周围的一切变得可怕。她确实不能再和他坐在一起了。爱,使人孤独,她不能向任何人诉说。……他是自私的,男人都如此。她在经受煎熬,却无人可以诉说”[1]。雷西娅曾经满怀希望地离开自己那可爱的家乡意大利,告别亲人陪丈夫来到陌生的伦敦,她期望的仅仅是得到丈夫的点点温存,但这点可怜的愿望,在可恶的战争中也被无情地吞噬了。随着丈夫在自杀中得到解脱,雷西娅最后的救命稻草似的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为什么我该无依无靠呢?为什么不让我留在米兰?为什么我要忍受折磨?为什么?”[1]一连串的“为什么”是雷西娅内心悲惨无助的真实写照,也是可恨的罪恶的战争对女性摧残的深刻表现,是她们心灵被严重扭曲的集中体现。父权制及其发动的各种战争对自然和女性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达洛维夫人,还是作者伍尔芙都对其进行了严正的控诉。
三、结语
将战争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贯穿始终的《达洛维夫人》通过分析女性与自然意象的联系,反衬出女性与自然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体现了女性对父权制及战争的控诉,表达了作者对建立两性平等、和谐生存的和乐世界的追求。作品中,作者不断将自然意象与女性联系起来,强调它们之间的关联,这为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去进一步解读伍尔芙及其作品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英)弗吉尼亚·伍尔芙.达洛维夫人[M].孙梁,苏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胡新梅,战争:创伤与女人——从女性视角解析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6).
I106.4
A
1673-1395(2011)04-0010-02
2011-02-20
李伟(1982—),女,安徽宿州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本文系宿州学院校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09ysk25)产出论文。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