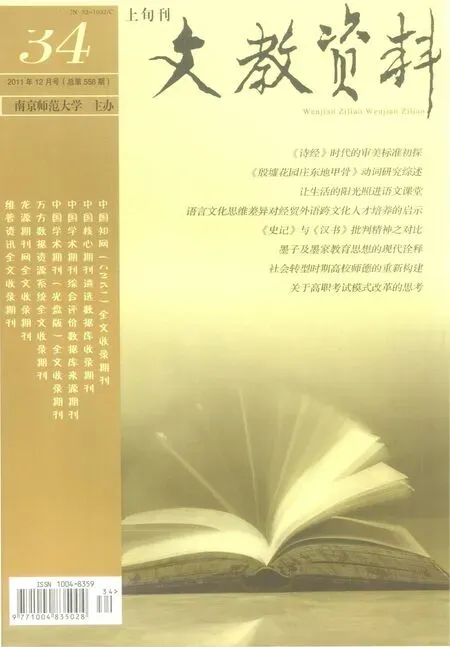康拉德非洲题材小说中欧洲“空心人”的道德救赎
岳 峰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自十八世纪英国诞生第一部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开始,冒险小说(Adventure Story)这种创作形式就与英国文学伴随《鲁宾逊漂流记》、《金银岛》等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加拿大学者库特·洛博将书写帝国殖民的作家分为三类:冒险小说家(Adventure Novelists,1832—1932),二战前的提倡良心小说家(The Novelists of conscience,prior toWorldWar II,1857—1957), 以及二战后后殖民时代的小说家 (Post World War II,The Age of Decolonization)[1]。与那些极力渲染海外风情、大肆鼓吹帝国扩张的传统冒险小说不同的是,康拉德在《黑暗的心》、《进步前哨》两部非洲题材小说中更关心蛮荒的非洲丛林之于传播文明的欧洲殖民者的意义,换言之,他更关心非洲这个“另类世界”的文化语境是如何使欧洲殖民者的文化身份发生嬗变的,白人如何“在这一新的环境中重新定位,赋予自我存在的意义”[2]。 这正像C.B.考克斯教授所指出的:“他的旅行,他讲故事的决定给我们提供了获得某种启示的希望——某种心灵或许并非全然不可知的希望。”[3]康拉德在小说中采取较为理性的审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英帝国文明传播者在非洲丛林里的罪恶,批评家往往称这种灵魂与肉体分离的这类形象为“空心人”,康拉德企盼“有野性的生气”的原始非洲丛林对身染沉疴的帝国空心人进行道德救赎。
一
冒险题材小说一直是英帝国的重要文类,无以数计的这类小说早就成为意识形态工具,一系列以英雄冒险为包装、渗透殖民意识形态的文本传递给维多利亚末期、爱德华时代初期的英国青年人的信息是:非洲、亚洲等殖民地是上帝赐给欧洲选民的“迦南”,在殖民地传播欧洲文明是帝国青年的神圣使命。在这些殖民时代流行的所谓“青少年冒险故事”里面,青年主人公往往都是通过阅读这些极具诱惑的冒险小说来到非洲和东方诸国传播欧洲文明的,他们总是被描写成“棒小子”、“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成为帝国文明的传播者。长期受殖民话语的熏染和流行冒险小说的蛊惑,英国青年人将传播欧洲文明视为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冒险小说成为宣扬并支撑大英帝国殖民扩张意识形态的有效形式,“在形成并强化不列颠是主宰世界的强国这一观念方面,是参与其中的”[4]。欧洲殖民扩张和统治往往以文明启蒙的扩展为借口,进行非洲内陆探险和传教等运动,这些文化侵略运动是以欧洲文明远胜于非洲文明、白人人种优秀于黑人人种为信念基础的,因此,欧洲殖民者传播文化的过程往往是残酷的种族征服过程。康拉德对欧洲殖民文化的揭露是走在其同时代作家前列的,其非洲题材小说相比同时代或前后出版的英语小说,在控诉殖民文化的罪恶方面,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康拉德在两部非洲题材小说中对欧洲殖民者手持利剑和火把进行文化传播的虚伪性进行了强有力的“颠覆”。《黑暗的心》中的库尔茨与《进步前哨》中的凯亦兹,作为欧洲文明传播者,均具有双重文化身份,一个是西方文化熏陶下理性的帝国青年,一个是被非洲的“黑暗”所俘获堕落的殖民者。库尔茨可谓是整个欧洲的象征:“他母亲是半个英国人,父亲是半个法国人。整个欧洲都对库尔兹先生的形成做出过贡献”(64),这样谜一样的人,康拉德刻意将库尔兹的才能和整个欧洲的联系起来,从而成为19世纪欧洲时代精神和殖民主义思想的象征,欧洲殖民者的典范。库尔兹身负欧洲殖民主义者责任感,即在非洲进行殖民经济探索与响应时代号召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带到非洲以启蒙黑暗非洲的伟大任务相结合,库尔兹的经历极具维多利亚时代“有志青年”经历的典型性。库尔茨的观点是:“我们白人,从我们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来看,‘必定会让他们——野蛮人们——看成好像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我们是带着一种类乎神灵的威力去接近他们的’,如此等等,如此等等。”(64)库尔茨,作为一个非洲贸易站的商业代理人享有极高声誉,“最好的公司代理人”(27),他正是欧洲鼓吹的高度的工作效率、先进的文明和理想的秩序的完美体现者。当然其“名声”和“成功”,都是建立在他运用欧洲科技和枪支进行残酷的象牙贸易和疯狂地掠夺非洲人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狂热的欧洲只愿意接受成功的商人,伟大的冒险者,拒绝一个草菅人命的暴徒形象,欧洲的文化体系具有一种文化过滤功能,被过滤掉的殖民者的罪恶不在欧洲人的主要视域之中。
二
在康拉德的非洲题材小说中,小说中的“空心人”话语并不多,实际意义上行动更少。《黑暗的心》的故事由马洛讲述,并被马洛有意说得断断续续,很不连贯,不断插叙其他故事,几条线索往往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在冲突中共同表现另一个主题,即极具典型性的库尔兹所涵盖的道德堕落和心灵黑暗。库尔兹的经历被马洛拆散在故事的不同阶段中进行回忆。“我即将去结识的,是一个软弱无力、装腔作势而又目光短浅的贪婪和残忍得愚蠢的魔鬼。”(503)这个欧洲人眼中的英雄,在权力和欲望的驱使下,早已抛弃了教化“野蛮愚昧”的非洲土著和播散“文明进步”的伟大使命,“光明”并没有带给“黑暗”的非洲,结果库尔兹自己却成了“黑暗”的俘虏。马洛第一次见到库尔兹时,“看见他咧开大嘴——这使他的面貌显得不可思议的贪婪,好像他要吞掉整个天空,整个大地,和所有他面前的人”。这象征着欧洲的扩张野心已经无以复加。“库尔兹先生在满足他种种欲望这方面是毫无节制的”。库尔兹人性中善的一面逐渐泯灭,恶的一面不断膨胀,在其征服非洲的同时非洲也征服了他,非洲大陆的“黑暗”神秘地“抓住了他(库尔兹),爱上了他,拥抱了他,侵入他的血管,耗尽他的肌体,还用某个魔鬼仪式上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礼节使他的灵魂永远属于荒野所有”。 (62)
欧洲“空心人”挣脱了来自文明世界社会准则的束缚后,非洲大陆的黑暗唤醒了他内心中的某些“恶”的因素,外在的蛮荒生活与内心的“蛮荒”交织在一起,空心人身心交瘁,神志不清。当文明社会所代表的法律及道德的约束力不复存在时,人性中的兽性终于复苏了——“空心人”对象牙的疯狂掠夺不再是为了重回欧洲后的个人辉煌而进行的掠夺,而是人生中原始、黑暗力量驱使下的机械的行为,对土著黑人的大肆杀戮也不再需要任何理由,是为了杀戮的杀戮[5]。赛德雷克·瓦兹称库尔兹为“现代的浮士德”(modern Faust)[6],一个与欧洲文明渐行渐远的人,其堕落并不是简单的沉沦,如同浮士德一样伴随着极端痛苦的挣扎和反思。《黑暗的心》对库尔兹无法摆脱灵魂深处善恶的缠斗以及在人性的泥沼中挣扎的描写断断续续,片断的印象、模糊的语言、奇特的场景最终达到了连续中的间断,间断中的连续,这种抛开传统的人物刻画方法,极不连贯,即康拉德的“最省力的方法”。他在1902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承认,显然我的错误是使库尔兹这个人物太象征化了,确切地说,纯粹是一个象征性人物。但小说情节主要是作为传达一些个人印象的工具,所以我就放任我懒惰的思想,采取了最省力的办法。”[7]
三
康拉德正是通过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印象感觉的交织与组合,塑造了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小说特征的“反英雄”人物——库尔兹与凯亦兹。库尔兹与凯亦兹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各种黑暗势力的包围中,他作为欧洲文明典范的身份渐渐迷失,他们不再是传统冒险小说中勇敢正直的青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一新的环境中如何重新定位,赋予自我存在的意义。在黑暗非洲的深处庞大殖民体系当中,他们位于金字塔的顶端,拥有无限的权利。库尔兹彷徨在追求权力的满足与得到无膺的权力欲望后的厌恶之间,身份的裂变转化为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他厌恶非洲土著人,叫嚣着消灭一切野蛮人,一方面又被非洲的黑暗所诱惑,库尔兹已经无法重新回到欧洲社会中去,只能拒绝马洛劝诱他回去所说的“在欧洲你的成就是毫无疑问的”。他命令非洲土著袭击那些来营救他的人,并在刚果河中打进树桩阻止营救他的船只靠近。库尔兹想方设法从白人汽船上逃回野蛮人丛林,小说对期间过程小说描写惊心动魄,以一连串象征意象的描写和神秘氛围的渲染,马洛首先听到库尔兹的喊叫声,接着见到库尔兹在黑暗中“用手脚爬行”,这场文明和野蛮的灵魂争夺战在极度紧张气氛中上演,库尔兹的意境也更加深邃。
康拉德把欧洲空心人置于各种黑暗势力包围之中,展示他和黑暗进行道德斗争。他郑重提醒马洛:“当然你必须注意正确的动机——正确的动机——永远要注意。”他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的动机是正确的,把他的罪行解释为必需的手段。在经历了所有欲望的可怕的满足和灵魂的痛苦的挣扎后,库尔兹临死前终于迸发出那句著名的谜一样的“可怕!可怕呀!”康拉德一方面让库尔兹窥见了人心灵的地狱以及西方世界道德的地狱,最终以一个道德反省者而结束生命,另一方面又留下多处遗憾暗示这种救赎的尴尬。康拉德本人对所谓的宗教救赎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康拉德在与爱德华·加耐特的对话中,对基督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真奇怪,从十四岁上起,我就开始讨厌基督教,它的教义、仪式和节日。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主教——相信它。”[8]对于库尔兹这个早已将灵魂押给魔鬼的人来说,道德前的退却是难以想象的,仅仅依靠临死前的呼喊,却从未有任何心灵的自我救赎,读者很难相信库尔兹被迫放下屠刀后会立地成佛。
库尔兹这一人物的伟大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身表现的殖民主义罪恶,而是在于其体现的处于西方传统道德危机时代白人人性的复杂性和典型性。库尔兹形象的演变,让我们看到欧洲文明的衰弱,看到殖民主义对非洲黑人和欧洲白人的戕害,看到“殖民主义的思想依据——对机械文明崇拜备至,并以之为信仰和价值标准——忽略了人的道德改善,更没有意识到科学的发展如果用于邪恶的目的,只能放纵人性中固有的向恶的倾向。殖民主义就是科学和文明发展走入歧途的产物。”[9]T.S.艾略特的名言“库尔茨先生——他死喽”,就是直接从《黑暗的心》中引用的。文学史上这类“空心人”形象不在少数,如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冯内格特笔下的弗兰克,等等,批评家不断地审视“空心人”形象灵魂的不在场状态。康拉德透过库尔兹这个“空心人”形象揭示了西方文明的深层危机,殖民者的“空心”状态证明了真正最具威胁力的黑暗不是非洲的野蛮和落后,而是西方文明最深处的黑暗。殖民帝国时期“空心人”形象有力地证明了殖民者的贪婪和虚伪,非洲丛林的黑暗更加彰显了殖民者的灵魂深处黑暗与疯狂的融合和混淆,其“空心”状态的实质是欧洲文明自身长期矛盾引发的危机爆发,这象征着欧洲人在精神危机时代的迷茫和煎熬。
[1]Kurt Loeb.A Study of Colonial Attitudes in English 29 NovelsSetin Africa[M].UniversityofToronto,1984:5.
[2]苏勇.自我的湮灭——从《黑暗的心》中的克兹说起[J].国外文学,2001,(3):121.
[3]C.B.Cox,Joseph Conrad:The Modern Imagination[M].London:.J.M.Dent&Sons LTD.1974:51.
[4]艾勒克·博埃默著.盛宁,韩敏中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5]苏勇.自我的湮灭——从《黑暗的心》中的克兹说起[J].国外文学,2001,(3):121.
[6]Watts,Cedric.“Heart of Darkness”Joseph Conrad.Ed.J.H.Stap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47.
[7]Frederick R.karl,A Reade’s Guide to Joseph Conrad,Farrar,Straux&Giroux,1989:132.
[8]Joseph Conrad,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Frederick R.Karl&Laurence Davies,ed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6:468.
[9]隋旭升.黑暗的心脏中库尔兹和马洛的象征意义[J].外国文学评论,199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