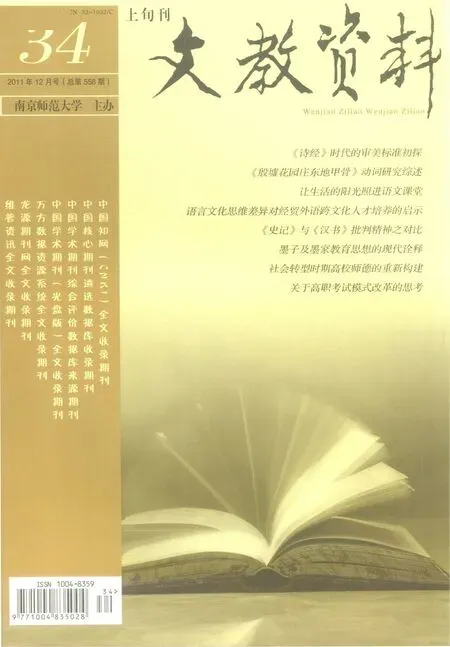《旧制度与大革命》与托克维尔的政治自由思想
徐 蕾
(北京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9)
一、旧制度下的贵族自由
托克维尔对自由情有独钟,批判旧制度。他认为旧制度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却存在某些奇特的自由——贵族自由,使得王权专制并未成为所有人民的主宰。托克维尔以略带同情的眼光分析这些自由,试图呈现出旧体制比较美好、比较值得怀念的一面。在贵族的自由下,个人可能保有很大的权利、独立性和空间活动性,包括贵族的所有上层阶级都用此防止国家权力对自身特殊权利的侵害。他认为贵族阶级虽然不复拥有权力,却仍然保持着祖先传下来的骄傲气质,“既仇视奴役,也仇视法规。他们毫不关心公民的普遍自由,对政府在公民周围加强控制心安理得;但是他们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们自己头上,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要时甘冒种种危险”①。结果,贵族在王权面前反而展现了某种崇高的精神与品质,成为旧体制下捍卫自由最坚定的一群人。我们可以想象,当大革命爆发后,贵族阶层随着封建制度走入历史,托克维尔势必认为人民少了一道防卫中央专制的机制,从而更加怀念昔日贵族制的贡献。从这一点上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对旧体制美好一面的怀念。除了贵族阶级之外,教士与法官也同样得到托克维尔的高度肯定。托克维尔认为教士由于拥有不可剥夺的土地特权,因此在世俗政权面前往往显得独立不屈,他们“同第三等级或贵族一样,仇视专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热爱政治自由”②,铲除了教士的土地特权,人民也失去了自由的一个极大成分。至于法官方面,由于法官实行终身制,且不求升迁,这两点大大有利于司法的独立,从而多少发挥了保障个人自由的作用。最后,托克维尔认为即使在资产阶级和一般人民身上也有某种自由气质是革命后的人们所欠缺的。旧体制下的资产阶级喜欢效法贵族阶级,这些“假贵族”因此无意中承袭了真贵族的骄傲与抗拒精神。他们习惯追求一个舞台,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捍卫共同的尊严与利益。托克维尔虽有美化贵族阶级之嫌,但是确实他认为贵族极能反映时代的精神——关心个人权利、社会义务、极力主张发展公共教育,并且和第三等级一样希望改革彻底、国家强盛。
托克维尔认为旧体制绝不是一个充满奴役与依附的社会,透过鬻官制、贵族、教士、法官、资产阶级,法国人民事实上享有不少政治自由。这些自由有其生命力,使人们心中“培育着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③。虽然他认为这种政治自由难以帮助法国人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但是他依然固执地认为旧体制下的人“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然而同时托克维尔也意识到这种贵族的自由毕竟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是贵族们在契约关系下所获得的特权,是非正规的、病态的、与阶级制度相关联的,实质是“特权的享受”。正是这种远比德国、英国之贵族轻微的法国贵族的特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原因在于贵族已经变成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阶级了,因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大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些令人民难以忍受的贵族及教士,取消他们的封建特权,以建立一个人人地位平等的社会。一旦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就不能奢望旧式自由继续保存于新的民主社会中。民主社会如何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兼有自由呢?托克维尔认为贵族的自由必然要让位于民主的自由,这也正是其睿智之处。
二、民主与自由的关系
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后给法国社会带来了什么?自由还是平等?
托克维尔进一步要思索的是在民主社会的前提下,如何认识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从而实现“民主的自由”。他认识到,在新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地丧失了自由。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④与之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又非常遗憾地说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⑤,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⑥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这与法国人执著平等、不尚自由的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
平等本身不会威胁自由,平等不是自由的对抗价值,平等可以与自由兼容,其关键是不要盲目服从一个权威的支配。大革命以后,民主社会的身份平等造成人们强势政府的依附心理,结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组织形式——民主专制,即平等的专制局面。常识告诉人们,民主与专制是相对立的。在欧洲的君主专制时代,民主的敌人是君主个人的独裁专政。一旦民主取胜,它还有新的敌人吗?托克维尔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敌人就隐藏在民主内部,即多数人的专制。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的不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美国民主式的民选政府,而且同样可能是高高耸立的断头台。民主作为所有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参与形式带有多数人暴政的危险,最终带来泯灭个性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自由。大革命期间,尽管人们需要在自由上的一律平等,但是当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放弃对自由的追求,选择奴役上的平等,他们宁愿忍耐贫困,也容不得贵族。这就是他对大革命前法国人政治心态的写照。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们充其量不过是心满意足的奴隶,因为民主中孕育着新专制主义,其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参与的多数专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民主加剧了自由在社会中的逐步失落。对此,托克维尔表达了强烈的遗憾,并对他心中那种真正的、发自心灵的、毫无功利目的的自由给予了高调的赞扬。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专制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追求铁血式平等的法国才会有血腥的大革命和革命后的专制复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只是自由与民主的早期争论的一个历史记录。在这场争论中,焦点是多数的专制。在这一问题上,托克维尔像其他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奋力为个人的权利免受国家的权力,哪怕是民主国家的权力的入侵加以辩护。
三、如何使自由和民主相容,实现民主的自由
托克维尔不为贵族制度的消逝而挽歌,也并不指望法国能够重建贵族制度以获取自由,同样也不认同人民主权理论。托克维尔关注的是:在一个不可避免地走向平等和民主的时代中,自由在革命后的集权国家如何重建?或者说,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和民主化过程中成为可能?这是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也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论题。如同“将巴士底狱片片拆毁,并不能使囚徒变成自由人”,摧毁旧制度不能靠大革命,追求民主,则只能沿着追求自由的路径才能得到;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则只能导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民主应该服从自由,把自由置于社会平等之上。这或许是托克维尔为全人类总结的政治教训,这也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价值日久而弥新之所在。与多数统治相比,在托克维尔眼中自由的珍爱有其独到的魅力:
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但我认为,自由制度能使他们在独立中支持一段时间,而无需他们自助。基于自立的自由是可以培养的,而对自由的真正热爱则是不可传授的,因为它来自所有伟大的人类的情欲的神秘处。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⑦
“民主”制打破了贵族制的不平等和特权,实现了平等,是符合社会正义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与“贵族自由”相比,“民主”也存在多数人专制的危险。民主不仅仅是多数人的统治,它更是人民可以撤换统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国内和平的一种有用的工具。民主不仅在于主权者的人数,更在于运用权力的方式。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自由是民主的目的。自由与民主,尽管是同为世人所追求的两个目标,却有着各自的内在逻辑。一旦这两种逻辑互不相容,两者就会发生冲突。只有自由与平等携手并进,才有机会摆脱暴政与平等相结合的“民主专制”的危机。
托克维尔从“贵族自由”转向考察“民主的自由”后,更多地关注这个理论问题本身与法国现实的结合。法国历史的进程证明,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民主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民主的思想和行动已开始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应该如何抑制民主的弊端呢?那就需要依靠自由。然而鉴于转型社会中尚无民主运作的基础,同时民主和自由仍处在相对分离状态,如何使自由在民主政治和民主化过程中成为可能?托克维尔最终把目光投向了市民社会,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他认识到,市民社会是民主化和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领域,他强调,不是公民参与政治,而是积极地参与自愿的结社,否则就难以保证政体的自由性质和公民个人的自由不致失落。市民社会自身就是社会整合和公众自由的最重要的领域,有助于限制国家政治权力。托克维尔发现法国之所以长期受害于威权传统,是因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把社会原子化为孤立的个人了,即在社会中铲除了作为中介组织的等级和结社,因而在没有市民社会的情形下使个人直接地暴露于国家的权力,这样,个人就无法形成民间的力量,也就难以对国家的权力构成有效的牵制。民主政治建立在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独立组织和社会集团的存在的基础之上。若是没有社会中介的存在,就会出现独裁或集权政权。托克维尔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⑧
托克维尔认为要挖掘社会传统中一切有助于保持自由和抵御专制的因素,而乡镇自治和结社自由这两条正是为未来重建自由制度的最重要的资源。因为他始终认为国家除了君主(无论是旧君主还是新专制者)和民众以外,还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中间政权机构和中层组织,来限制中央集权,保障公民自由,训练政治参与,促进公民精神。既然旧制度和大革命一起夷平了贵族这一天然的中间政权和社团组织,那么地方自治和结社自由就成为新的手段。“在贵族制国家,贵族社团是制止滥用职权的天然社团”,那对于没有或者铲平贵族的民主国家而言呢?“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从而形成今天我们所称的公民社会。这也是他认为政治自由能得到保证的最好制度安排。事实上,法国一直没有摆脱中央集权和独尊巴黎的事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才开始大规模的地方分权改革,包括把地方官员的任命制逐步改为选举制,同时赋予地方官员直接选举产生而使得其具备独立权力。这已经是大革命爆发两百年之后了。
托克维尔的卓越见识来源于他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亲身观察和分析,来源于他对历史材料的充分把握,来源于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实践,更来源于他对国家政治命运的深刻思考。在托克维尔身后,法国革命开启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并被添加了新的内容,比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使得制度、思想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注释:
①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09-110.
②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0.
③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6.
④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2.
⑤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2.
⑥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01.
⑦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02-203.
⑧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6.
[1]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李宏图.从贵族的自由到民主的自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3).
[3]黄艳红.“自由”的丧失和平等的起源[J].衡阳市师范学院学报,2006,(8).
——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