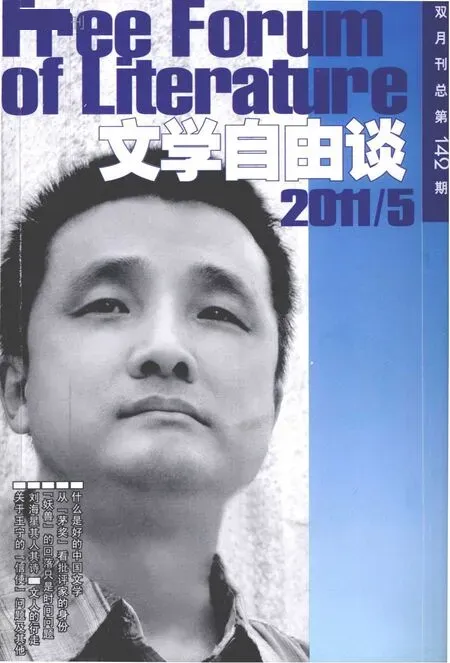我与《中国》
日前,偶然发现王增如刊于《江南》的长篇纪实《丁玲办<中国>》。
坦率说,因吾亦当事者,且随着年岁的增长早已厌倦了文坛名利场的是是与非非。所以,开始并无兴趣去阅读。更何况,当时那与我有关的流言与影响,就更是我永远不想回忆的。其中,如在《中国》数百万字的组稿中,我何以能不仅在创刊号上大出风头,还在此后的几期连载了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答案则必然是:若非丁玲一伙,又能是什么?而当时的文坛,谁靠近丁玲,谁就是老左,就再没好果子吃。
但话虽如此,后来我还是被这部作品吸引住了。而之所以如此,则因当年我虽涉足于《中国》,亦恰如雷加所说的,其实也只是个局外的“投稿人”。别说对其内幕的不可能得知,就连我又何以被看重,就更是莫名其糊涂。现在,作为丁玲前秘书的王增如,终于以其最权威的诠释,让我也顿有所悟了。
于是,与《中国》那一往事亦重现于眼前……
那是1984年夏季的一天,突然接到雷加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问我手中有什么好稿子。当他得知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藏归来,正埋头于长篇《迷魂泉·雪人》的紧张创作时,就说他和丁玲、舒群、魏巍、牛汉、刘绍棠等正创办一个大型的文学期刊。问稿成时,能否先给他们来刊用。
因此稿已早有婆家,坦率说,若是其他的某人我肯定该婉拒的。但对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以《聚鲸洋》闯入文坛就对我呵护有加的老雷加,又怎能说不呢?但是,雷加亦只来了一次电话就再无音信。于是,我就按原计划将小说作最后的润色再通知北京一家出版社来取稿。但几乎同时,雷加的人也赶到了。
记不清是几月几日了。却记得,那天上午煤店送来足有一吨过冬的煤球。于是,我也只能放下手中的笔,和现在的诗人、当时才十岁的儿子震海一筐筐往楼上的阳台倒。近中午,刚倒完煤老诗人鲁黎夫妇又领来两位北京的客人,进门就嚷饿死了,有什么好吃的?我就让震海到楼下饭馆端来一笹刚出笼的肉包子。这时,才知北京来的一位是雷加所说的刊物副主编、著名诗人牛汉,另一位是编辑部主任、冯雪峰的大公子冯夏熊。来访的目的,则是要拿走我曾应允雷加的这部长篇小说。但最后议定,三天后我将稿子寄出。半个月内,再由编辑部告知对此稿审读的意见。
就这样,我如期将稿子寄出。而且不到半个月,冯夏熊就来电话说丁玲对此稿很满意,并决定在创刊号上全文推出。为此,他希望我即刻赴京,在文字上做最后的加工。
于是,转天我就去了北京。但一见面,冯夏熊又说计划有变。即,为使创刊号有更多版面以显示更大的作者阵容,则我的长篇又改在第二期发。但为使我能在创刊号亮相,希望能再提供一部两三万字的小中篇。我说有部中篇《背尸人》,是写西藏天葬师的。但你们来之前,已给《人民文学》的崔道怡。于是,他又让我去找老崔。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才得知稿子被老崔带回家,而他本人又在外边参加一个会。为此,我也只能去老崔的家中请他夫人帮我撤回了这部小中篇。跟着,冯夏熊又以最快的速度赶回编辑部,工夫不大便电话通知我此稿不仅上创刊号,老太太还赞赏地说: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反封建。
然后,为使《背尸人》更符合编辑的要求,我与冯夏熊在恭王府后院平房单身宿舍中又将稿子连夜作了最后的修改。分手时,他说很快就要召开一个隆重的创刊招待会。届时,肯定将给我发请柬。然而,不知为什么,那空头的请柬不仅毫无综影,后来他对我也疏远了。如,一次在恭王府见他与一年轻女子走来,问那部长篇的情况,他只说了句还没定就弃我而去。为此,我自然亦多有不满。但碍于雷加的关系,也就不计较。
但是,当随着创刊招待会的召开,对我的传言又一次扑面而来时我就不能心平气和了。这当中,对我在人格上最大的侮辱是说我傻,被丁玲为首的一伙老左们所利用。根据是,除这次的投稿,再就是1982年丁玲去天津搞串连拉队伍,我还给她抬轿子。
说错了吗?没错。因为1982年丁玲来天津亦确实是我全程接待的。但我之如此,亦纯系公务。经过是,丁玲从北大荒归来,给天津作协主席孙犁写信说希望能看看天津的老朋友。当时,因孙犁的人事关系不在作协,根据他的意见凡寄到作协的信皆由我处理。所以,孙犁让作协向市委上报,并让我代表他和天津作家去北京接丁玲。到了北京,才知原计划同行者还有田间、秦兆阳、古立高。于是,又分别去邀请。不知为何,田间和秦兆阳又说身体不适而突然变卦。丁玲不高兴地说:不去就不去吧。
但就算是抬轿子,这也是罪过吗?更何况,我与丁玲的交往亦仅此一次。她给我的除送一部签名的小说集和‘你比我写得好’的鼓励,就再也未曾见过面。至于她在津的几天,因所有的活动皆由我安排,就更是心明眼亮了。如,去孙犁的家中是专为看他生活和创作的环境。而作为性情孤傲的孙犁对丁玲的接待,除必恭必敬地说他年轻时就喜欢她的《韦护》和清茶一杯、脐橙一碟,再就是将其搀扶到院门外,这也是他送客的一个例外了。再有,就是参加了一个由作协召集的文学座谈会。都讲了些什么,记不清了。却记得,会后,先是袁静请饭,后是市委书记到宾馆看望。再后来,我又陪她去总医院治牙……仅此而已。
而且,到四次作代会召开时,对我的传言就更多了。如,据说由于丁玲在大会上散发了《中国》创刊号的目录。就连认识我的人见我亦忝列其中也大惊小怪地喊:王家斌,何许人也?
尽管如此,也许是出于逆反心理,我对丁玲却更同情。尤其听说一些当红的作家在作代会上秘密串联和政客那样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向各地代表游说‘别选丁老太’时,那就更不仅是同情了。对此,记得我曾与孙犁先生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他说,丁玲也找他约稿,就是后发于创刊号的《从腊月·正月谈起》。但若说她办《中国》是跟张光年、冯牧的《中国作家》对着干,则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挑拨。他还说,作家靠作品,还是埋头写你的东西吧。
所幸,那险些胎死腹中的《中国》终于面世了。而更该庆幸的是,我的《背尸人》刊出之后就引起读者的关注。如,某电影厂一编剧很快就将其改编成电影;如,雷加告诉我,丁玲访澳途经香港有人还谈过这小说。更意外的是一天我突然接到王若望的一封信。那所谓的信竟是他在飞机上读了《背尸人》后写在烟盒纸上的评论稿。他说,很希望能在《中国》刊出。却又怕丁玲不喜欢他这个人,才请我代为转呈的。对此,我亦很为难。一者,王若望与丁玲确实不是一路人;二者,用烟盒写稿,丁玲又怎能不反感?但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据说,丁玲见稿不仅不反感还挺高兴,说王若望这个人可很少说谁的好话。于是便将此稿发在了《中国》的第5期。
但是,我最看重的那部长篇是否将发在二期又成了未知数。最使我恼火的是,几次给冯夏熊去信皆不见回。于是,便写信问雷加。他回信说:“你的长篇,对刊物来说,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可以这期发或是那期发,总的说,《中国》杂志前六期目录的编排是煞费苦心的,所以只好委屈你一下,也忍耐一下。夏熊答应你二期发,二期又没有发,所以他现在不好回你的信。”那么,到底又将何时发?我又去信,这次连雷加也不再回复了。于是,我就去信要撤稿。仍不见复,就奇怪《中国》到底怎么了?而此疑点,直到现在读王增如的《丁玲办<中国>》亦才恍然。即,“拿不到当红作家的稿子”,“在这种情势下,一批崭露头角的新秀,成为《中国》创作的主角,像山西的田东照,天津的王家斌,北京的陶正、刘恒、林青、湖南的残雪等。由于作者队伍狭窄,好稿子上不来,导致一些人的稿子多次刊用”。“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家斌,第一期发了中篇《背尸人》,紧接着,长篇《迷魂泉·雪人》在三、四、五期上连载。这两部作品以其藏族题材备受关注,但是在一年总共六期刊物中,一个作者在四期上都占据重要位置,十分少见。”所以,虽然后来雷加终于回信说:“听说你的长篇又分三期发了。理由是你的作品可读性强,可以这样作。我想编辑部也有一番安排稿件的苦心在其中。”我仍百般的不理解。而且我想,若分三期,那将是读到结尾忘开头。作为长篇,也就糟蹋了。更何况,关于《中国》随时都会散伙的传言又满天飞。
于是,又致信冯夏熊和牛汉,希望能按最初的约定一期将这部长篇全推出,却仍不见回复。最后,碍于雷加的情分,也只能听天由命,被安排在3、4、5的三期。这当中,因编辑部未给我寄样刊又弄得很不愉快。所以,当一天丁玲突然又派王中忱来津,说为缓解《中国》的财政危机,将编辑发行《中国丛书》。因我的《迷魂泉·雪人》是《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反响也很好,希望我能同意收入《中国丛书》出版单行本时,我竟断然回绝了。
我想,到此我与《中国》的缘分也算了结了。但不知为什么,望着中忱离去的背影,我又不能不懊悔自己的太绝情。因为,不管怎么说,从《中国》诞生我就与其息息相关了。更何况,虽然我与丁玲、陈明、牛汉、夏熊、桂欣、中忱、增如等接触不多,但他们对文学的执著,还是使我感佩在心的。
所以,尽管此生亦再无往来,但对《中国》的命运却更加关注。如《中国》与作协关系越来越紧张;如《中国》又改月刊并到外地去出版;如丁玲的病危和与世之长辞——皆使我萦系于怀。尤其是在电视《晚间新闻》看到丁玲去世的消息。这一夜,就在失眠中度过。想什么呢?首先浮上心头的是:《中国》,完了。
然后,就回忆那所谓的“曾给丁玲抬轿子”。我记得,那是1982年5月的一天。天还没亮我乘火车赴京接丁玲。到丁玲家时,才知她和小孙女打羽毛球扭了腰。另外,过几天河北的女作家刘真要来,因此只能将行期后延到19日。为此,我亦决定找全国作协开介绍信去买高干才能享受的预售软席票。结果,却因丁玲的阻拦而买了硬板凳的慢车票。接站时,市委和作协的有关领导都去了。当领导们发现丁玲是被陈明和古立高搀扶着从拥挤的硬席车厢下来时,我也就成众矢之的了。而这当中,最不给面子的则是时任天津作协党组负责人的作家鲍昌。他说:你呀你,真不是个办事的衙役。
想到孙犁不看电视,转天一早我去孙犁家。当时他正在卫生间,久久的未出声。我在门外问是否发唁电?他说,唁电由《天津日报》文艺部的邹明发;你,写篇悼念的文章给《天津日报》;他也写,给《人民日报》。于是,我就将丁玲来津访问的起因与经过,写了篇《硬席客车》发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见报后,且不说反响如何,但对丁玲来津种种传言,则多有澄清了。
后来,亦恰如我所忧虑的。不久,就听说群龙无首的《中国》已陷入绝境。于是,作协就要收《中国》的刊号。再后来,到1986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本不知谁寄的《中国》终刊号。
我记得,我是以极其复杂的心态勉强读完那篇终刊号致读者的《中国》备忘录的。我记得,读最后那“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时,我竟落泪了。然后,就陷入此生最大的困扰中。而且,直到25年后的今天,仍在想:当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的,丁玲办《中国》无罪。但作为文坛一大事件,谁又能为丁玲和她的《中国》做出客观而权威的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