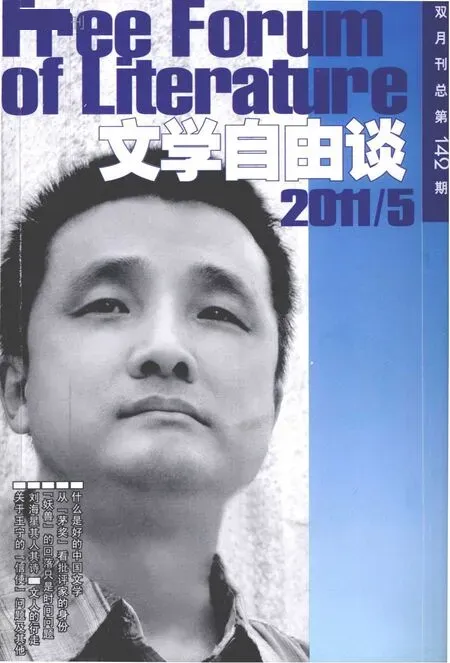待诌的后记,没用的书名
●文 高 为
孔子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礼记·中庸》)用白话翻译就是:任何事情,有准备就能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我现在才认识到:自己之所以至今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就是因为对所有事情都一直没有准备好。《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单之蔷,在《中国景色》自序中强调著作与文集的区别:文集无系统,著作有中心。对照这种标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书只能算是文集,不敢说是著作——没有中心思想,没有预设框架,甚至连书名都是临时由别人代起的,怎么能与著作沾边呢?这也是没有准备的一种表现吧?
《书缘与人缘》是我的第二本随笔集,书名是《书声!书声!》文丛主编王春瑜先生给起的。我原先报给王先生的书名是《准盛世微言》,王先生认为太俗太滥,类似的书名太多,所以从我的书稿目录中选了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我绞尽脑汁准备的就被搁置了,成了没用的书名。
“没用的”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没处用的,没用过的(not used,unused)二、没用处的,没价值的(nouse,useless)。我那没用的书名属于哪一种呢?
有时我想,假如本人拟定的书名被采用了,总得有篇后记吧?序或者前言都显得太正式了,忒正经了。后记则没那么多规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愿写几句就写几句,怎么着也得感谢感谢师友亲朋吧?如果用了《准盛世微言》作书名,后记我可能会这么写:
《准盛世微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来自两部书名:《盛世危言》和《准风月谈》。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提出了对清朝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在《自序》中指出洋务派以为购入坚船利炮就可以使国家富强的想法和做法是“逐末而忘本”。
《盛世危言》问世时,朝野争阅,光绪皇帝命令总理衙门印发2000部,让大臣们人手一册。《盛世危言》的思想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前进了一大步,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郑观应(1842—1922)出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已经进入了晚期或者说末期,积贫积弱,危机四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国侵略羞辱,被迫割地赔款。他的《盛世危言》出版于1893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又一次大败,再过了十八年(1912),清朝覆亡。明明是末世、乱世,郑观应却偏偏说成是盛世,讽刺乎?修辞乎?害怕文字狱而心有余悸乎?
时间过去了近一个世纪,又一部类似著作横空出世——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作者用十八章、三十多万字描述了当时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经济、交通、工业、农业、人口压力、生态危机、资源枯竭、教育、第三产业、知识分子人心、科学技术、干部素质、环境污染、未来的挑战、信息化前景等等。在《编者心声》中,责任编辑许医农女士说此书:“是为不甘落伍沉沦的炎黄子孙书写的并非危言耸听的 《盛世危言》。”
《山坳上的中国》于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后,一时洛阳纸贵。单是1989年6月的第二版,印数就达二十五万五千册。上世纪80年代,是历史上最活跃的十年。人们有理想,有希望,有道德,有信仰,有激情,所以,《山坳上的中国》生逢其时。二十多年过去了,书中列举的困境依然如故,预言的危机依次应验。类似的著作却难再现。现在不断出现的是“说不”“不高兴”,自高自大、自吹自擂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人们还是欢迎报喜的喜鹊,不容忍预警的乌鸦,忘记了孟老夫子的告诫——“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章句下》只有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应有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现代化——人的思想现代化。剪掉脑袋上的辫子容易,去除脑袋里的辫子就没那么容易了。人虽然早进入了21世纪,还是满脑子的“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我们的硬件(摩天大厦、名车、别墅、高铁、计算机、核武器、坚船利炮、各种名牌奢侈品)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大,而软件呢(制度建设、财务公开、舆论监督、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打破垄断、公平竞争、平等互助、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国民意识、慈善传统、捐赠精神、文化水平、道德素质、遵纪守法自觉性等等等等),不说也罢。
罗素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更可悲的是,连过去都不敢承认它是事实,千方百计地选择性失忆,处心积虑地造成民族遗忘,只许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能提走麦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逝者讳,无真情,无真话,无真相,不认账,不认错,不认罪,结果是不断地重复制造过去的悲剧。
如同《准风月谈》,《准盛世微言》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准,盛世微言;二、准盛世,微言。按照第一种解释,准是准许、允许的意思(allow,grant);按照第二种解释,准是接近、很像、疑似的意思(quasi-,para-),如准将、准新娘。如果是准盛世,那就还需继续努力,因为“准”在这里是没准儿的事情,如准新娘不抓紧逼婚、诱婚,准新郎可能会见异思迁背信弃义娶了别人,或突发奇病突遭横祸暴亡夭折,自己就无法转正守了望门寡;准将一蹉跎,可能就直到退休仍然是准将,一辈子当不上正式的将军。如果已经是盛世,就应当有盛世的大度与风采,准许“微言”存在,而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一种腔调。一元的价值观是很危险的。最近极端的例子就是挪威32岁的青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7月22日先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制造爆炸案,然后又在于特岛向人群扫射,共杀害了七十多人,炸伤打伤二百多人。他的目标就是在欧洲实行像日本或韩国那样的“单一文化”,反对移民和多元文化。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单一文化论或纯洁文化论,都是违背天理,有害又危险的。
“沉默的大多数”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死人。“自有人类以来,迄于今日,已有850亿人先后死在这个星球上。”(李书崇《与死亡言和》,亦名《死亡简史》)与此相比,活着的60亿人只是“喧嚣的一小撮”。二、活人中被剥夺了或没有说话机会的弱势群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这也就是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其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有人白吃白喝,就有人没吃没喝或少吃少喝却付出双倍的代价——总得有人为白吃们埋单哪!于是就会产生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少数强势群体垄断了话语权,自然就没有多数弱势群体说话的地方,这既不符合天理,也不符合天意。
契诃夫说:“自从莫泊桑以自己的才能给创作定下了那么高的要求之后,写作就不容易了。不过还是应该写,特别是我们俄罗斯人;而且在写作中还应该大胆。有大狗,也有小狗;可是小狗不应该因为有大狗的存在而慌乱不安。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不光是有权力的人才有资格说话,人人都有权利发言,哪怕只是“微言”。
《现代汉语词典》只有“微言大义”这一词条:“精微的语言和深奥的道理。”没有那么邪乎,我还没有自大自夸到这种地步。这里没有“大义”,只有“微言”,而且也不是“精微的语言”,我的微言就是“人微言轻”的缩略,是小百姓的闲言碎语,小老儿的家长里短。
书分四辑:书评集萃、书人书事、书生意气、书外闲话。除了真话,就是实话。其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求。
感谢老师的提携,感谢老友的帮助,感谢老婆的支持——必须的。
以上就是我虚拟的后记。按照我现在一年写半打千字文的速度,再凑够一本集子怎么着也得在十年之后。俗话说只有错放的财富,没有无用的物资。如果你认为“没用的”的书名是没处用的、没用过的,拿去用就是了,我连这篇序也无偿奉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文章是一家。什么你的我的,乐和乐和得了。如果你认为“没用的”的书名是没用处的、没价值的,那就你我都省事了,就让它在那儿搁着吧,十年后也许我还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