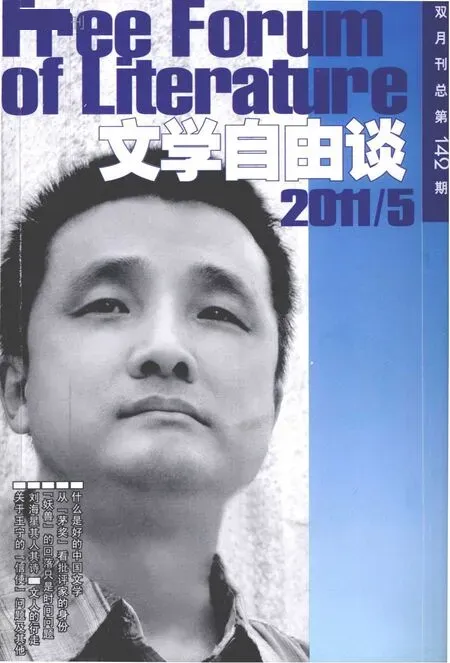明朗真诚的周旋
●文朱晶
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影歌两栖明星周旋的,皆赞叹她有个“金嗓子”。可她的“脑子”也不俗,这似乎知者不多。在周旋遗留的有限文字资讯里,人们会感受到一个昔日当红明星出奇的冷静与涵养,与当今浮躁的娱乐界恰成某种对照。
据说,当年上海电影圈只推举过两个“影后”。一个是胡蝶,由当时《大晶报》报人冯梦熊和小报名编陈蝶衣主持推出,在“大沪舞厅”举行过一次富丽堂皇的“影后胡蝶加冕典礼”。另一位即周旋。由《上海日报》发起1941年的“电影皇后”选举,正红遍上海滩的周旋当选。在该报公布竞选结果的翌日,周旋发表婉辞启事,称:“倾阅报载,见某报主办之1941年电影皇后选举揭晓广告内,附列贱名。周璇性情淡泊,不尚荣利,平日除为公司摄片外,业余惟以读书消遣,对于外界情形极少接触。自问学识技能均极有限,对于影后名称绝难接受,并祈勿将影后二字涉及贱名,则不胜感荷,敬希谅鉴,此启。”此文字此心态,从容淡定,毫无伪饰,令人钦佩。
翻检周旋的答记者问,同样明朗真诚,进退得体。请看,1948年12月答上海《电影杂志》问(摘录):
问:能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你的身世、籍贯及通讯处?
答:早年失怙,萱堂健在。原籍广东,年近三旬。现在上海。
问:你的歌喉是天生或者苦练而成的?怎样保护?以你的意见,“金嗓子”还能保持多久的日子?
答:既非天生,也非苦练,我也不懂怎样去保护。“金嗓子”愧不敢当;反正能唱一天就多唱一天。
问:你的人生观如何?
答: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好好地做,像一个人。
问:你的影坛生活有没有受到意外刺激?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
答:背一句古语作为答复吧,“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1944年1月《上海影坛》发了一则“周旋答二十一问”,兹摘几句:
问:对自己年龄的增长,有什么感想?
答:恐慌。
问:常常哭吗?常常生气吗?用什么方法发泄?
答:不常哭。不生气。不响。
问:每次,当你说谎以后,心里感到痛快,还是痛苦?
答:又痛苦又痛快。
问: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答:“滑稽来”。
问:给你影响最大的导演是谁?
答:导演过我演戏的各位导演先生。
问:你最感烦难的表演是什么?
答:哭里带笑,笑里带哭。
问:你以为在现时代下,观众最需要的是怎么样的影片?
答:教育片。
问:你觉得最标准的节约饭菜是几碗?你在实行吗?
答:一菜一汤,已实行。
还有些精彩答问,不能再举了。上述若干,是否可见周旋的机智与可爱?周旋的命很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凄零的女子,我不知道我的诞生之地,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她6岁被上海一户周姓广东籍人家收养,13岁加入黎锦晖的歌舞剧社,15岁参拍第一部影片《风云儿女》,主演的名片有《马路天使》《红楼梦》《天涯歌女》等;一生拍片43部,演唱歌曲300余首,其中电影插曲114首。1957年9月22日病逝于上海。
周旋没念多少书,她的知识和文化全靠在演艺实践中自学与感悟。可她不但留下了大量拍摄的影片、演唱的歌曲,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书信和访谈答问。难得她做人的真实、从艺的真诚,难得她那样淡泊名利、那样有自知之明。我相信,对于每个从文弄艺的人,周旋都会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焦祖尧与陈柏中
山西的焦祖尧与新疆的陈柏中有何关联?
他们并不相识,但都是我尊敬的兄长,都是工作在黄土莽原、天山高地半个多世纪的江浙秀士。
焦祖尧,1936年生于江苏常州,1955年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毕业,1957年开始文学创作。后入山西作协,担任多年省作协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有《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及大量小说、报告文学作品问世、获奖。我和祖尧相识较迟,1993年始,我在吉林省作协工作,每年全国作协工作会议,我总是与祖尧分到一个讨论小组,他是组长。见面多了,熟识起来,觉得他待人亲切、识见锐利,时常向他请教文学工作上的一些问题。1999年夏,我参加中国作协的三晋采风团,没想到,这个文质彬彬的山西作协主席,竟有一肚子荤素搭配的笑话,而且在黎城黄崖洞善陀同心石旁的赛歌会上,山东毕玉堂高歌《小白扬》,山西韩石山戏咏《十送红军》,他领唱山西作协“会歌”——《亲个个蛋》,那出奇的幽默与洒脱,让我不禁对祖尧刮目相看。当然,对于他的报告文学写作,我更是敬重有加。90年代中,收到他寄赠的长篇报告文学《黄河落天走山西》,我马上推荐给我省正在写高速公路报告文学的陈景河。景河看后大为感慨,觉得祖尧采写太旧公路的坚韧精神堪为榜样。而景河的《走出柳条边》出版后,竟又受到祖尧的注意,2001年8月9日,他寄信给我:“朱晶老弟:从《文艺报》读到你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柳条边》的文章,很感兴趣,因为我数月来也在采写一条纵贯全省南北的高速公路项目(667公里);了解一下吉林的高速公路建设情况有个对比,于我的工作当有裨益。能否请弄一本书给我,不胜感激。”我遵嘱寄出了书并转达了陈景河的敬意。一年后,他那本公路纪实的压卷之作《大运亨通》出版,博得多方好评。
陈柏中,1935年生于浙江绍兴新昌,1958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分配到新疆文联,历任《新疆文学》、《中国西部文学》主编,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新疆文联副主席。1982年,我与柏中同入中国作协文学所(现鲁迅文学院)第七届进修。他为人谦谨宽厚,是这个编辑评论班的班长。两年时间,我们相处融洽。他十分关心他人,我毕业论文写习读王蒙小说心得,因他是王蒙在新疆的老朋友,就带我去王蒙家登门求教。王蒙称他“老陈”,看得出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毕业后,他曾去长春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女儿晓帆,我们又得以相见,可惜我却一直未能找到机会去新疆看望他。2010年秋,柏中寄来他见证新疆多民族文学60年的评论集《融合的高地》,这30万言64篇文章,确实“凝聚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心血思考,为我们回顾与审视新疆文学和中国西部文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本”。王蒙说得好:“老陈的这些文字,对于我来说不仅是文字、文学,而且是时代是历史,是见证也是伤痛,是青春记忆,是斑斑泪痕也是老来一笑,是宝贵的经验也是此生的欣慰。”柏中10月13日来信说,这本书“很可能是同文坛的告别,该画一个句号了”。又说,“退下来10多年了,我过的是散淡的晚年生活,只是这几年也有些杂事找上门来,反而使平静的心多少有些躁动不安了,这人间也实在没有一块可以过宁静、舒心生活的净土!”其实,文坛上淡泊如柏中者鲜矣。
前面说过,焦祖尧与陈柏中并不相识。可我每想起他们,便觉得他们实在是有不少相似处:他们都是身材修长的江浙赤子,从1950年代就走上中西部高原,携妻将雏耽佳句,“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们都德高望重,都是我的良师与畏友,除了对我多有耳提面命的教诲,他们奉献青春乃至毕生于一隅的事业精神,他们所达到的崇高的文学境界,应说已成为中国文坛之地方作家中钻石般宝贵的长者与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