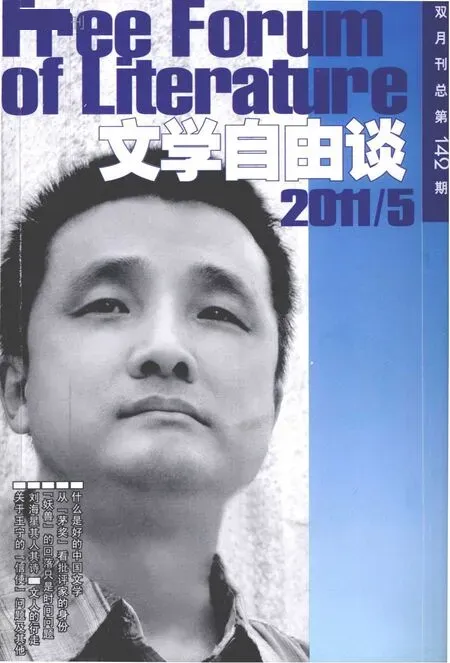刘海星其人其诗散论
●文侯军
(一)
那年,素未谋面的刘海星,夹着他的一本摄影集,敲开了我办公室的房门。没有寒暄,直奔主题:打开影集,立即一张张充满激情地讲解起来,这山,这水,这树林,这飘着大雪的早晨……
我在报海沉浮三十多年,取舍照片算是日课,对摄影作品的好赖本是一眼即可洞穿。说实在话,我起初并没有把面前这位业余摄影家的东西太当一回事。不过,大概看了不到五分钟,我就被他感染了,首先是被他镜头下的那些画面感染,接着听到他对那些画面背后故事的阐释,我又被深深地感动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当他起身向我告辞时,我们俨然已是多年的老友,而且,我已经满口答应要为这个只有一面之交的摄影家写一篇正儿八经的评论文章——尽管写摄影评论并不为我所熟悉和擅长。
送走刘海星,我翻阅了这位中年壮汉留下的简介:出生于江苏,在四川大巴山长大,大学学的是经济,毕业后在国家机关当了几年公务员,随后南下深圳下海经商,很快就创建了一份不大不小的产业,正当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却忽然迷上了摄影,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自己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跑遍了大江南北的荒山野岭,然后就把所拍的风光摄影作品挂在网页上,不料竟大受追捧,直至被一向只认专业水准的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吸纳为会员,让国内摄影界刮目相看……
这是一个多少带点传奇性的家伙,我从与他一个多小时的倾谈中,已经发现了一种极富征服性和穿透力的个性特征,他的口才,他的激情,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清晰思路,他对所有对话者内心情态的准确把握,以及他的机敏和睿智,他的见识和眼界,他对所做事情的计划性和可操作性……翻看着他的简历和摄影作品,我心里暗想:不要说办企业、玩摄影,天下任何事情,只要他认真投入去做,恐怕都能做得八九不离十——这是那种想到就要做到,想到就能做到的家伙!
(二)
果然,刘海星玩摄影迅速玩出了轰动效应。先是在珠海试水,搞了一个很专业的风光摄影展。说他很专业,是因为他把国内好几位摄影艺术的大佬都请到珠海的古元美术馆,开了个像模像样的艺术研讨会。接着又在深圳办展,还别出心裁地开了一个以诗人为主要参加者的座谈会。随后就直接进京,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大美中国”摄影展。这一系列摄影展,前言都是节选于我写的那篇评论文章《非诚勿照》,刘海星显然对这篇粗浅的文字厚爱有加,在他看来,这是第一篇专门评论其摄影艺术的文章,由此开端,他作为摄影家的江湖地位就被奠定了。
2009年10月,刘海星把“大美中国”摄影展办到了台湾的国父纪念堂,这可视为他将摄影艺术玩到极致的巅峰之举。他的摄影作品,视野开阔,题材新颖,充满激情,着力于表现大自然的苍茫雄浑万千气象。他把祖国大陆神奇而美丽的山川大地,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一度隔绝的海峡对岸的观众面前,其视觉冲击力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风光摄影”,它所唤醒的是遥远而亲近的家国之思,是触手可及却又因久违而显得陌生的故土情怀,是难以言喻的精神上的共鸣和文化上的慰藉。
这次台湾影展,使刘海星成为第一位在台湾办展的大陆摄影家,恰如台湾评论家南方朔所言:“大陆著名摄影家刘海星先生来台个展,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以来,这还是摄影艺术这个领域的首次。”这使他在两岸摄影艺术领域树立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标杆。我本以为,他会继续在这块艺术高地上勤奋耕耘,再创佳绩的,谁知,这个不安分的家伙从台湾回来之后,却出人意料地放下相机,一头钻进诗歌的海洋。当他一个“猛子”从诗海里冒出头来时,竟然是夹着一本新出的诗集,再次敲开了我的办公室房门。
(三)
刘海星喜欢写诗。我最早读到他的诗是在他的摄影集里。有些摄影作品,他特意配上几句画龙点睛的诗句,这应该就是他诗歌创作的肇始之作了。由此可见,他的诗并非刻意而为,而是信笔所至,而且从一开始就与其摄影艺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对他这种诗画合一、情景交融的创作特点,谢冕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对于刘海星来说,诗歌也许只是业余,摄影更近专业。大家知道他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家。然而,反过来说,他是摄影家,更是诗人。他行走在大地上,摄取那些山川湖海、人生万象,他的镜头保存了自然界的瞬息万变,雄奇秀美,但风景毕竟只是无声的叙说,他感到了这一手段的局限和缺憾。他要用文字来传达和扩充那画面的‘留白’——揭示画面背后的意义和暗示,于是他找到了诗,于是他成为诗人。他成功地找到绘画难以道出的、探及人的内心世界隐曲和幽微的方式。”(见谢冕为刘海星诗集《太阳的眼泪》所作的序言《一切与记忆相连的都很伟大》)
恰恰因为他的并非刻意,所以他的诗率真而质朴;恰恰因为他是信笔而为,所以他的诗“干净,透明,简约是他的底色”。“因为他是独立的,所以他意外地保持了诗歌的纯净,他的诗没有被‘污染’。”(加引号者均为谢冕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的业余性和随意性反倒成全了他,他从来不想把自己定格在一个固定的框子里,在他眼里,无论摄影还是诗歌,均是非专业的创作。在这里,“非专业”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它意味着刘海星的创作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追求,没有任何既定的行业范式的框框,也没有时下流行的媚俗时风的影响,他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的喜爱和对自己内心感受的表达需求,而去拍照,而去抒写。正如他在谈及摄影时所说的:“只有我们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倾听内心的感受,不浮不躁,我们又怎能不为自然感动,何愁没有情感的自然流露和生发呢?正所谓,待已诚,才能待人诚,做人、摄影,皆源于此。”这样的艺术创作,似乎更加接近艺术的真谛和创作的本源。当他以自己真诚的双眼去直面自然,用自己的一腔真情去直抒胸臆,那么他拿出手的作品,无论摄影还是诗歌,想不率真、想不干净、想不透明、想不简约,都难!
(四)
刘海星的诗歌,亦如他的摄影,风格上偏重于大气象大视野大境界。他的视线所及,往往不是个人的小圈子,而是宏阔的大自然,天空、大地、山川、海洋、日月、潮汐……都在他的诗歌里得到熔炼,被赋予形象而深刻的内涵和底蕴,形成独具特色的诗歌意象——
他写天空:“当我与天在一起/一切便与天齐/当所有的问题/都从云彩中发出/天,便是我的问题。”(见《背影与天空》)
他写大地:“我有鹰的视野/俯瞰/胸怀,就成了大地的胶卷。”(见《支点》)
他写日月:“月亮钻入/太阳心脏/燃烧/令人窒息的光芒/它把太阳划伤/完成自己的倔强/太阳被爱切割成/鲜红鲜红的月牙/黑黑的月亮挤进/太阳火红的炉膛。”(见《太阳的新娘》)
他写大海:“面朝大海/每个人都会张臂拥抱/因为它宽广、浩瀚/没有人会拥抱一根针/尽管它和人类相伴最久/你会走入大海/但你见过谁/曾经走出大海?”(见《大海,总在我身边》)
……
读着这样的诗句,你会想象着这个孤独的诗人,伫立在天地之间,仰望苍穹之浩淼,俯瞰大地之寥廓,念人生之须臾,发亘古之浩叹。他的思绪上下纵横,不可端倪;他的目光悠远深邃,洞穿表象。凡目之所及者,皆为他的镜头所摄取;凡思之所及而目所难及者,皆化作他那富于情感与哲思的诗行。刘海星诗歌意境的大开大合、理性思维的形象外化以及语言表现的不事雕琢,无疑成了刘海星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色。
(五)
刘海星的诗歌,不同于他的摄影,内容上往往蕴含着深刻的、缜密的、执著的人生思考。前面已经谈及,他之所以写诗,正是因为摄影的直观性无法准确而全面地表达他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万物的叩问,无法传达他对一些深邃问题的哲理性思考,他才要诉诸文字。这既是他写诗的出发点,也是他对诗歌功能的终极诉求。正如他在《太阳的眼泪》卷首语中所写到的:“我始终认为,诗歌艺术是对人类想象力的挑战,诗歌不仅仅要表达个人的情感,还要表达人类的反思和对生命的礼赞。”于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总能不经意间读到这种“反思和礼赞”——
他写道:“承载生命的飞翔/不是梦想/承载灵魂的黄土/不会荒凉……我们都陷入了时间老人编制的谜团/向后/是无尽的答案/向前/是永远的迷茫。”(节选自《一个老兵的故事》)为什么前面“是永远的迷茫”?对未来与未知的一切,我们除了“迷茫”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他写道:“想抓住风的轨迹/无奈/漫天黄沙/双眼迷离/当所有的意象/都化为绝唱/伤痛/就是离别的嫁妆。”(节选自《骄傲的飞翔》)相信所有品尝过离别之痛的读者,都会被这平白如水的诗句,重重地敲击一下心房。
他写道:“如果我已睡去/就不要叫醒我/如果我醒着/就不要让我睡去……如果我在梦里/就让我睡去/如果我醒着/就让我回到梦里!”(节选自《你不要叫醒我》)这些近似的句式重重叠叠,回环往复,看似平常,却蕴涵着深意——睡与醒,在被主观意念的选择中,凸显出残酷现实与理想梦境的二律背反——细细咀嚼,一丝无奈,三分苦涩,不禁袭上心头。
刘海星的诗集中有一辑就叫做《精神观察》,里边收集的不少短诗,恰恰是诗人思绪中那些一闪而过的吉光片羽。他思考《影子》:“太阳和大海/都没有影子/人类却喜欢/自己的影子。”他思考《陌生的风》:“想看看风的存在/应该很容易找到/它却变得陌生/我点燃了另一只烛光/它在摇曳/不敢肯定/是否就是/我熟悉的风。”他思考《名利》:“一切都是过去/一切都将要过去/一切都是过去的过去/我们站在过去的今天/走过来/那是明天/走过去/那已是逝去的记忆/你站定的那一点/那也是/今天的过去/我们都在/过来过去。”
刘海星说,他“四十二岁才开始写诗,也从未尝试发表过”,他因此而自称为“迟到的诗人”。然而,这原本的“劣势”在评论家严家炎先生眼里却成了一个“优势”:因为这“意味着个人从生活、思想到艺术都经历了较长期的准备”。(见严家炎《读诗集<太阳的眼泪>有感》)是的,我们从上面引述的这些诗行中,不难看到刘海星内心的敏感和多情,看到他在经历三十几年风霜雨雪历练之后所显露出来的丰赡与深沉,同时也看到了一个诗人永远不变的纯粹与童真。正是这种人生阅历的丰富性与诗人赤子之心的同时存在,构成了刘海星诗歌的独特风貌:深邃中蕴含着澄澈,狡黠中饱含着单纯,思考的艰涩不掩其表达的质朴,对人生复杂性的彻悟也未能妨碍其孩童般的直观阐释。
(六)
刘海星的成长乃至成功的过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一路并行。短短三十年中,中国社会大踏步走向了城市化、全球化和现代化,这对一个从大巴山走出来的诗人来说,内心的感受可谓是五味杂陈,有欣悦也有失望,有憧憬也有迷茫,有冲动也有焦虑,有振奋也有怅惘……当他在人到中年之际,转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审视眼前的一切时,他的感慨和忧虑便多了一层反思与反省的色彩。于是,我们在他的诗歌中,读到了一丝忧郁一丝困惑一丝无奈,这是一代都市人矛盾心理的折射,是现代化生存与田园化梦想无法同时兼得而产生的纠结。我以为,这是刘海星诗歌中最具认识价值的部分,也构成了他不同于一般青春诗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现代化生存与原有生活方式的疏离乃至割裂,使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与当年的出发地渐行渐远。刘海星在《重回故乡》中这样写道:“曾经的完整变得残破/曾经的洁净变得斑驳/多少次如洗的月光/划过窗棂/一寸一寸的岁月/轻轻流过。”重回故乡的诗人,见到眼前的一切已经不可复识,才意识到自己“走出大山好久好远”。如果说,当年毅然决然地走出大山,迈出的是走向现代化生存的第一步,那么,几十年后,当我们终于以一个现代都市人的身份重回故乡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心底依旧保存着对这大山的无限依恋,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叛离”。在那首《永远的大巴山》中,诗人的感情愈发浓烈,表白也更加直率:“再喝上一杯山里人酿的酒/让自己醉吧/倒在山里婆娘的怀中/让自己的梦/在大山深处神游……不管你走出大山有多远/那雄鹰盘旋的山崖上/总有一双手在挥动/那是告别,让你一路走好/那是说再见/你知道,随时可以再回首!”读着这样的诗句,相信每一个从大山或者乡村走进城市的现代人,都会心旌为之摇动。
泰戈尔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和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这是现代化大潮带给全人类的召唤,使我们不得不抛弃离开家乡的忧伤和对未来的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于是,我们跟随着“永恒的异乡人”,走出大山,走向城市,蓦然回首,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也变成了“永恒的异乡人”。我们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将注定在归家的路上漂泊——这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心灵困境,也使诗人刘海星在重回故乡之时感慨丛生。
现代化生存与人类的田园化梦想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填平的鸿沟。而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城里人的田园化情结往往就越发浓烈。这无疑是当今中国急速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悖论。刘海星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然而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的思考却超越了自身的视界,具有更深刻的思辨性和批判性。在《冷空气,一望无际地南下》中,他写道:“城市里的人/面对一望无际的寒冷/奔走相告/终于迎来了初冬第一场雪/蒸腾的暖气飘出房顶/妖娆中/城市如此地鬼迷心窍/绚烂晚霞来不及微笑/暗夜的冷/停止了兴奋不已的心跳/那一个冰洁的刻度被保持在气象台/无人理会/那个在寒冷中终止的生命/也无从知晓!”这是诗人借着冷空气在批评城市的冷漠。在《城市的桑拿天》中,他写道:“马路中央/汽车和人流/蠕动着/天际和大地/眯成了一条发白的光带/昏黄的太阳/涂抹着城市的表情/崭新的招贴画上/每一个物象/都被扭曲……每个地方都在交换/煤炭交换成电力/汽油交换成马力/氟利昂交换成冷气/碳排放也成了交易/唯有绿色/成为城市中的韭菜地!”这是诗人借着桑拿天来批评城市发展与绿色环保之间的尖锐对立;而当诗人写到其理想中的田园生活的情景时,笔下流露出的却是那么清新那么温润的诗句:“早春二月的枝头/桃花开了/那绿的苗和金灿灿的油菜花/让这四望无际的原野/充满欣喜/我在路上寻觅/可以化入梦中的仙境/让我的房前屋后/开满嫣红柳绿/让陶渊明成为我的邻居/没有喧嚣/没有交易/让每一缕晨光/羞涩地掀开眼帘/打量我的梦呓/在遥远的过去/在陶渊明的故里。”(见《早春二月》)这里表达的是诗人对“遥远的过去”那种诗意栖息的向往,是对陶渊明田园诗境的追慕,同时,也曲折地传递出诗人对现代化生存的无奈和遗憾。
(七)
这次,他的诗集《太阳的眼泪》由海峡两岸的商务印书馆同步出版,这在百年商务的出版史上尚属首次,这使他在两岸诗歌创作领域再次占据了一个不容忽略的高地。他带着大陆版的诗集回到深圳,郑重其事地签名题赠四个大字“相知行远”。我再次在一个多小时的倾谈之后,答应给他写一篇正儿八经的诗评,尽管诗歌也不是我所熟悉的领域。
我问他,你这次玩诗歌又玩出了大名堂,是不是真的可以与诗“相知行远”啦?他诡秘地笑一笑,没有回答。
我由此悟到:其实刘海星一直是在路上行走,沿途所见,信手拈来,玩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玩得到位,玩出精彩。我期待着他能接连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奇惊异和惊喜。
2011年8月8日至11日,于深圳寄荃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