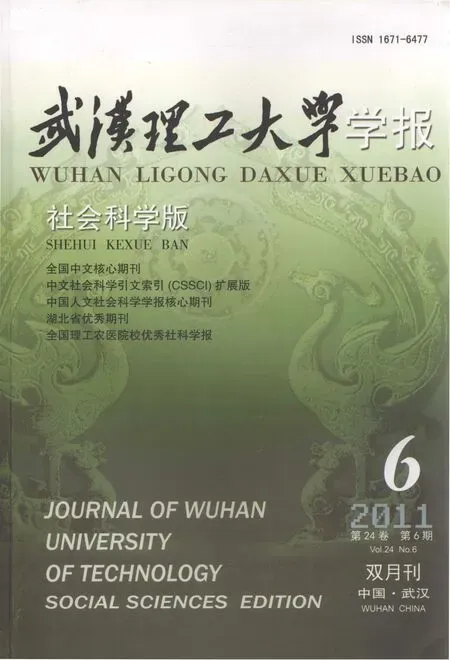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与文化世俗化的精神轨迹
张 宁
(1.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一、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国教危机
从维多利亚中期开始,英国国教面临着一系列来自教会内外的猛烈冲击。
这场宗教和教会的危机仿佛是1860年代突如其来的。19世纪30年代,随着英国政治宗教环境的宽松,英国出现了自17世纪清教运动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一时间,教派林立,教徒增多。不论教派分歧如何,各派教义总体上与维多利亚王室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相契合。以安立甘宗为核心的神学观念渗透到公共生活和公众意识中去,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宗教事务上,英国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除了天主教势力有所增强,新近冒出的诸如仪式派以及社会底层人士上教堂做礼拜人数有所减少等少数异常现象外,整个社会精神氛围是怡然平和的。然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突然出现于英国人面前的一些“异端邪说”,对神学正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打破了人们平和从容的精神生活[1]。
今天,人们很容易看到19世纪科学新发现对正统神学造成的巨大打击,如莱尔的《地理学原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上帝创世说的冲击;也很容易发现对《圣经》的不同解读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如六名英国国教牧师和一名非宗教人士共同撰写的《论文与评论》以及英国驻南非纳塔尔省主教科伦索的《摩西五经与〈约书亚记〉的批判考察》。这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宗教思想家向英国人介绍了德国《圣经》批评学,激发了英国人对《圣经》文本的正统解释的疑问,也引起了正统派神学家们的不满。
面对来自神学界内外的诘难和冲击,19世纪的教廷不可能像中世纪时那样采取断然措施。1864年和1865年,英国具有世俗法庭地位的枢密院两次干预教会,宣布对教会内部的“颠覆性行为”,不得采取制裁措施。1869年,上述《论文与评论》的撰稿人之一坦普尔竟然还当上了教区主教。19世纪60年代以后,自然主义的《圣经》解读,不带神秘色彩的人间化的耶稣向英国人稳步走来。如1863年勒南的《耶稣的生活》、赫胥黎的《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莱尔的《人类的远古时期》,直至1871年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解神秘化的作用[2]。在地理、生物和历史科学的新发现面前,正统神学节节败退。这场科学对神学的战争以科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伴随着神学败退的是整个社会全面的信仰危机。到了19世纪中后期,宗教普查表明,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已不到英国总人数的一半,让人感觉英国人普遍地不信教。
二、19世纪英国神学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世俗化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固然导致了神学的衰败,然而,维多利亚时期知识阶层对这些新学说的接受远不是一蹴而就的。像桂冠诗人丁尼逊那样狐疑过,焦虑过,但大体上保持着信仰的大有人在[3]。应该看到,维多利亚晚期的信仰危机和英国文化的世俗化与正统神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其中,神职人员职业共同体意识与维多利亚道德的矛盾张力是考察时代文化世俗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正统神学在19世纪英国的衰落过程中充斥着神学意识形态与维多利亚道德的张力运动。
在18世纪的英国,教士还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职业。乡村牧师要承担的宗教事务并不多,除了日常宗教活动,他更是一位乡绅。他有足够的时间融入地方,全面参与地方事务,如担任地方治安官;在报刊上写写散文评论,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作为一名博物学家,考察植物动物矿物;兴之所至,还可以参加体育竞技活动……而到了19世纪,尤其是福音运动兴起后,教士们被要求“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职业。宗教职责具体化并且量化了:工作日的宗教服务,每周日两场布道,扶危济困,等等。高教派中的牛津神学家们甚至明确提出教士的职业意识问题。维多利亚教士阶层对自己的职业是虔敬和专注的。他们不再像18世纪的牧师们那样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不打猎,不看戏,常年穿着黑底灰边圆领的牧师袍子,潜心于神学宗教事务。从工作态度上看,他们是可敬的;然而这种高度的职业化也意味着头脑的封闭化,意味着从广义的知识活动中退出。柯勒律治曾经生造过一个词clerisy(词根为clergy,有牧师和学问双重含义),用来包含以神职人员为主体的所有的知识阶层。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由于神职人员思想上和业务上退缩到《圣经》和帕里的《自然神学》之中,而不再与时俱进地参与任何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新发现的探讨活动,这个词显然已经失去了柯勒律治所意欲指称的意义。
与此同时,世俗的职业化趋势也在发展。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们尽管多数不是专职人士,但他们的职业共同体在逐步形成。他们是一群关注“事实”的人,时刻追寻可实证和可应用的事实。在追寻事实的过程中,他们对教会的狭隘做法,如独断论地把教义上的所谓“事实”摆在优先地位,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来源于国教正统派,国教内部的福音复兴运动声势浩大。这场宗教复兴运动对维多利亚社会生活的影响,就是造就了一个高度的道德社会。维多利亚道德与当今道德信条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对某些具体的行为的道德评判标准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今天我们习惯于对许多社会现象和观念不作道德判断,而对于一个严谨的维多利亚人来说,“悬置”本身就意味着不道德。当今的所谓“保持客观性”就是维多利亚人眼中的“不道德”。维多利亚人宗教意识的敏感性及其自我意识与反省意识是令人敬畏的,然而,这些意识与正统神学、福音新教教义却是不能相容的。
维多利亚道德观念的核心之一是关于“真”的问题。“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事实之“真”,客观之“真”;二是“真诚”,指的是人的品行之“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宗教问题上,“真”的二重含义无法取得一致。就拿《论文与评论》来说,如果作者坚持自然科学发现之“真”而质疑或否认《圣经》记载的宗教事实,他们的结论就与他们在圣职受任仪式上的宣誓相抵触。这样,对“真”的追求最后往往引起对人品的怀疑,从事实层面的争论转向人身攻击。而神职人员的专业化——同时意味着——眼界和知识的狭隘化,他们主导的精神生活无法满足人们对“真”的探求。可以说,神职人员越是专业化就越是失去了公众的信赖。当时的宽和教派牧师亚瑟·斯坦利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描绘了神职人员和教众之间的隔膜:“我相信教士职业最易犯的罪过——这种职业易于导致的——是对严格意义上的‘真’的漠视。牧师们布道时习惯于使用这样的语言:空泛、模棱两可,或套用现成的论据,或生拉硬拽,或直接抵达已然的论点……这些,导致了对布道的严重的漠视,导致了神学信仰与教众的分离,导致了教众对牧师的不信任,导致了牧师对教众的不可容忍的傲慢。”[4]35
牧师们将话题和结论限定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不涉及对“真”这样的时代敏感话题的讨论。这种做法维护了信仰,却令宗教问题的讨论失去应有的深度,也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到19世纪60年代,有思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不再愿意谋求圣职职位。大学里的年轻人在宗教事务上没有热情,成为“沉默无言”的一族。时代要求对某些问题进行解答,而宗教正统却希望那些问题“提都不要提出来”。他们告诫人们,怀疑本身就是“罪”,怀疑让人失去信仰,最终导致空虚与不幸。然而,对于这一代知识人而言,他们处于启蒙以来一个提问的时代,时代精神要他们投身于对“真”的探索,可他们却不断地撞见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他们可能永远压抑住自己的怀疑而无条件地信任左支右绌的神学信条吗?
另一个让维多利亚人感到紧张的是福音主义新教宣扬的博爱论与神学教条之间的张力。维多利亚道德高扬人文主义与博爱理想。福音派尽管在社会公众能否最终得救的问题上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宣扬友爱、慈善,在世俗事务上积极推动废奴,改善工厂环境,扶危济困等。教义方面,福音派接近加尔文宗,严格强调原罪、上帝拣选、赎罪、永罚等,这就与时代精神和情感格格不入。严格的教义教规与时代伦理相背,使更多人对宗教产生了怀疑。达尔文曾把《圣经》中的耶和华比作“复仇的暴君”。他说,一个慈爱而敏感的心灵,怎么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暴君,他将犯下微小罪行的,或不是出于人的过错而犯罪的人类大多数,罚入万劫不复的境地[5]。约维特——《论文与评论》的撰稿人之一——这样描绘维多利亚人对上帝的不满:“上帝对我们从未做过的事情大发雷霆。我们生来如此,他却要给予天罚;他的儿子替我们受难,他却心满意足……”约维特总结道:“……如此,我对于我还能否一如既往地进行布道有一种恐惧,我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宣扬基督教教义而同时不向上帝的神圣性投下一片阴影。”[4]57面对严酷的教义,伦理的自觉侵蚀了信仰。一个正直诚实善良的维多利亚人,几乎不可能同时成为正统宗教人士。人心的转变是必然的,社会的世俗化也是必然的。
三、阿诺德的救赎方案:精神祛魅的确证
面对社会日益世俗化的趋势,各宗派推出了各自的信仰主张。福音主义等高教派一味地执着于《圣经》,对来自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冲击漠然视之;广教派等新教自由主义对经文采取修辞解读,同时强调自然与神启间的联系;马修·阿诺德则转向宗教的道德教谕功能,让宗教远离教义纷争而仅仅发挥引导人们走向“甜美”与“光明”的文化作用。
维多利亚诗人、思想家马修·阿诺德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宗教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宗教问题上,其父、广教派领袖托马斯·阿诺德和恩师、牛津运动领袖纽曼是给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然而,他既未倒向广教派的新教自由主义思想,也不认可牛津的保守传统。他关注的是宗教在人的完善和国家社群整合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并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回归他心目中的正统基督教,重建国家主导的基督教会。
阿诺德在宗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圣保罗与新教》、《文学与教条》、《上帝与圣经》和《关于教会与宗教的最后几篇论文》。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圣经》解读、大众信仰、国家宗教问题等的演说。在这些著作和演说中,阿诺德用自己的神学体系回应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对正统神学的怀疑和诘难,从而成为维多利亚宗教纷争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阿诺德认为,宗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必须还原到它的原初教义上去;只有领悟并抓住了其本质精神,才能发挥指导人的言和行,达到“美好”与“光明”的作用。从《圣保罗与新教》开始,阿诺德就指出了新教在教义领悟上的偏颇:“在圣保罗那里是第二位和从属的东西,新教拿来当做首要的和根本的……”[6]300-309他指的是,加尔文主义强调的“因信得救”和“上帝拣选”的信条实际上偏离了使徒保罗的原意。其实,保罗反复强调的是人的正直与公义。新教教义看到的是基督耶稣的代人受难,而保罗的原话,却是显示一个可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榜样的精神楷模。基督的死而复生,包括肉体和精神两个层面。保罗强调的是精神层面。“死”是隐喻的说法,是精神上的死去,是浑浑噩噩地活在原罪之中。阿诺德指出,尊奉使徒保罗,不是要笃信“死而复生”的教条,而是仿效基督,对生活中的“罪”说“不”,从而获得生命的重生,达至此生的正直与公义。
阿诺德坚信,真义只有从修辞、类比的角度才能获得领悟。执着于经文的神迹记叙,不仅理解上谬误百出,而且累及整个宗教大厦。在《文学与教条》中,阿诺德宣称《圣经》是文学,圣经术语也是文学术语,即便像“上帝”这样的名词,也没有科学术语般的明确意指。正统神学家曾把“上帝”定义为“最伟大的第一因,德行与理智的最高裁判者”,而事实上,这种定义是无法验证的。阿诺德认为,不妨将“上帝”描绘成或解释为“我们自身之外的追求公义者”,“万事万物寻求完善自身的倾向原则”。阿诺德承认,诸如此类的定义是不完备的,尽管他怀疑人是否拥有完整表述上帝的能力,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存在,因为人的心灵、理性能感受到上帝的法则。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些促使他完善自身的律令。当人克服了自己天性上的弱点而抵御住瞬间冲动的诱惑时,上帝就现身了,人随之“因感激、虔敬和敬畏而战栗,产生了一种愉悦与平静的幸福感……”[6]310
阿诺德认为,正是由于未能修辞化地理解《圣经》,才导致了附加在真义上的额外的教义,导致人们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忘记了《圣经》彼时的道德教谕。相信那些额外的教义(如圣母圣灵感孕、基督死而复活)对人的行动而言虽然并无害处,但问题在于,由于无法验证,“整个宗教的确定性看上去就不可信,人们就失去了行动的基础”[6]310。宗教怀疑论就不可避免了。阿诺德明白,宗教怀疑论是时代精神的必然产物,人们不可能用新的神迹来回答科学的质疑。坚持神迹教条,只会引来更猛烈的攻击,给教会和信仰带来更大的灾难。阿诺德另辟蹊径,从经文文本出发,转向了宗教的道德教谕层面。他追本溯源,宣称“耶稣从来就不曾费心于宗教事务”[6]310,《圣经》本身没有任何教义教条,如果一定要说出其真义的话,无非就是“服从上帝”和“跟从基督”[6]320,而上帝和基督无非就是道德律令和人生楷模罢了。至于神迹,经文上记载的固然是壮观的,然而,只要我们追随真的基督精神,我们自会在心灵里感受到更为壮观的景象。
阿诺德把宗教最终归结为道德。为了避免宗教完全湮没于道德,阿诺德说宗教是“带有情感的道德”,是“人生的四分之三”[6]322。他坚信宗教的生命立足于“行动”,于是,他对宗教作了不涉教义的解释,让宗教远离教义纷争而仅仅发挥引导人们走向“甜美”与“光明”的作用。阿诺德深知,自己的神学只是对《圣经》的一种合理化的解读。《圣经》和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诗人,他认为《圣经》语言是流动的,诗性的,而非僵硬的,科学化的。为了更合理地理解它,现代人必须广采博闻。一个人如果仅仅宣称他懂得了《圣经》,他未必就真的理解了《圣经》,因为《圣经》需要我们超然无执地批判地解读,这需要广博的文化修养。
阿诺德的神学观点产生于维多利亚晚期。尽管他处处维护英国国教的地位和尊严,他的观点与国教正统派,与其父辈神学家们已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国教正统派,尽管他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坚持作为人格神的上帝的事实上的不可证实性,让“上帝”作为道德的象征而存在;相对于自由主义者,他认可民众需要情感和想象作为道德实践的支撑,但坚持认为最强烈的情感和想象力来源于《圣经》;相对于执着于教义的高教派,他尊重他们的道德感和虔敬的宗教热情,但坚信现代人应该追本溯源,看到教谕的基点在“行动”,看到国家主导的宗教是完善个人,引导个人走向“甜美”与“光明”的巨大精神力量。
阿诺德是严肃的。他一再申明自己的信仰并真诚地在不断改造的基础上维护国教权威。但他的神学理念,怎么看都与宗教无关。时人指其学说为“业余神学”。德劳拉干脆说阿诺德像拯救遇险的船只向海中抛弃货物那样,将传统神学的形而上的装备和方法论基础都扔掉了[7]122。阿诺德看似给神学做加法,实际上是做减法,他的神学只不过是从《圣经》中抽取带上宗教色彩的道德箴言罢了。
在保守的纽曼看来,唯理智论的自由主义分子托马斯·阿诺德都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马修·阿诺德这位剥离了基督教义而仅侧重其实践功能的“业余神学家”则是彻头彻尾的“伪教徒”了。德劳拉写道,阿诺德青年时代就洒脱地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而转向了不可知论,却毫无卡莱尔、罗斯金般的焦虑和痛苦[7]60。阿诺德也许不曾自觉到其宗教思想中的矛盾,其信誓旦旦的信仰表白与其道德“神学”间的矛盾,正是维多利亚社会世俗化的精神确证。
[1] Williams R.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M].London:Happer &Torchboks,1958:23.
[2] 刘 锋.《圣经》的文学性阐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7.
[4] Houghton W E.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1830—1870[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3] Stanley T W.Studie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M].New York:E.P.Dutton &Company,1923:30.
[5] White P.Ministers of Culture:Arnold,Huxley and Liberal Anglican Reform of Learning[J].History of Science,2005(2):115-138.
[6] Arnold M.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M].Ed.Colli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7] DeLaura David J.Hebrew and Hellene in Victorian England:Newman,Arnold,and Pater.Austi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