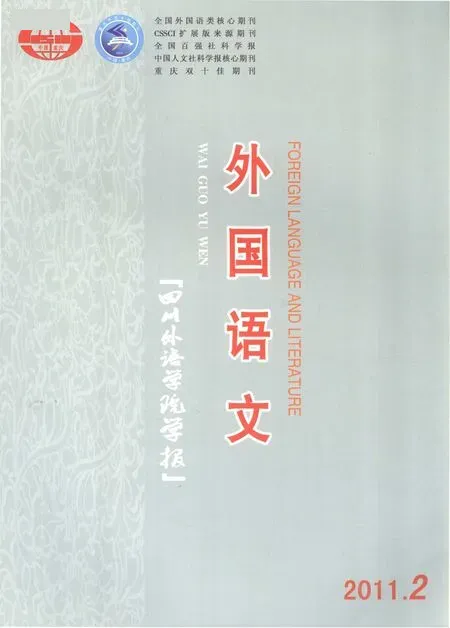约翰·斯坦贝克女性观流变探析
蔡荣寿
(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女性角色及女性观的流变
不可否认的是,斯坦贝克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男性角色和男性关系。女性角色远没有男性角色那样备受关注,她们甚至还被评论家们看做是小龙套、老套。皮特·利斯卡,研究斯坦贝克的著名学者,在《约翰·斯坦贝克的泛泛世界》一书中把其对斯坦贝克女性角色的批判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女性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只不过她们往往被迫在居家黄脸婆和卖身行业中二选一。”[1]即使如此,有很多女性角色,如《人鼠之间》中柯莱的妻子、《菊花》中的伊莉莎、《愤怒的葡萄》中的罗莎香、《甜蜜周四》中的苏西、《烦恼的冬天》中的玛丽、玛吉,虽然不像《愤怒的葡萄》中妈妈、《珍珠》中胡安娜那样可敬可佩,但研究她们,对我们了解斯坦贝克女性观很有帮助。
1.《人鼠之间》:柯莱的妻子
《人鼠之间》是斯坦贝克的第一桶金。这本书,
是描写关于兄弟情谊,关于追寻无法触及的、最终破灭的美国梦的小说。为了表现被世人排挤的孤独女人柯莱的妻子的悲剧,该书消极地向读者公然表现了斯坦贝克的反女性观。柯莱的妻子决定了小说结局,她强化了孤独寂寞这个主旨和个人理想理念这个中心思想。就男性角色和斯坦贝克的总主旨来说,她似乎作用很小。然而,对其角色的深入研究表明,她不仅仅是小说中的重要影响力量,而且是个苦心刻画的角色。书中柯莱的妻子是从农夫的角度进行描写的,而这些刻画诱使读者对其产生偏见。坎迪对乔治说道:“我认为柯莱娶了个妓女 ……你好好看看她,先生。你就会明白的。”[2]322-323斯坦贝克对柯莱最初的描写更强化了农夫的观点。她有“鲜红大嘴,眼妆极重,亮红指甲,头发卷得跟腊肠一样。她穿着棉质睡衣,红拖鞋,脚踝还粘着红色鸵鸟毛”[2]324。她明白只有用“我在找柯莱”[2]325这种借口才能被允许在简易宿舍旁边转悠。当她甚至更直白些,“我只是想找个人说会儿话”[2]325时,招来的是冷漠和不满。乔治认为她严重威胁了他们的工作保障,影响了他们的发财大计,甚至毁掉他们的土地梦。乔治狠狠地威胁雷尼,“不准看那婊子一眼。她说什么,她做什么,不关我事。我见过无数那样的祸水,但没一个比得上她”[2]326。
斯坦贝克刻意没给柯莱的妻子名字,为的是表示她只是她丈夫的一个延伸,只是一个对象。这并不意味着斯坦贝克认为她这个角色无关紧要。恰恰相反,他故意把她刻画成一个表面轻浮邋遢的女人。小说结尾处,雷尼杀死了她。斯坦贝克对于干掉个没有名字的低级角色没有半点悔意。如今,那种天真女人终身追寻着梦想,引起我们的同情,可却被社会轻视。这不是个案,那个时期无数女人有着相似的遭遇。她代表着男性在该特定时期该地域的女性观无用、麻烦的性工具。斯坦贝克的女性观要不是公然的鄙视轻蔑就是负面的。
2.《菊花》:伊莉莎
《菊花》被众人评为斯坦贝克最佳短篇小说之一。《菊花》的主旨就是其主要人物伊莉莎的挫折。很多评论家主张认为在故事中她被丈夫欺负、被修补匠背弃已经是对女权主义的抨击了。然而,深入观察下,故事中的伊莉莎有着强烈的女权精神。她的行为和感受映射出女人为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变强而进行的斗争。她在花园中很强大很骄傲,但在和丈夫一起外出吃饭的时,变得很软弱。斯坦贝克短时间内漂亮地完成了她在女子本性和男子气间的频繁换位。
故事位于发生萨利纳斯山谷的艾伦牧场。起先,伊莉莎在她的花园里剪下枯萎的菊花茎,而她丈夫在院子另一边和两个男人谈生意。对她着装的描写“压低的黑色男款帽遮住了她的眼睛,厚重的鞋,印有图案的裙子已被巨大的灯芯绒围裙完全遮盖……”[3]使其男性化。当她丈夫亨利过来夸赞她的园艺才能时,她很得意,以为她的园艺能使他们平起平坐。然而,当亨利提出出去吃饭去看打架,她女人的一面又出现了。她很兴奋并说她宁愿去看电影也不愿看打架,她“不喜欢打架”[3]。
有一天,亨利离家后,修补匠驾驶着一辆破旧的篷车来到了她门口。这个男人问伊莉莎有没有要修的锅、盆,伊莉莎像个男人似的表情严肃地拒绝了。但是当补锅匠表示很喜欢她的菊花时,伊莉莎不再恼怒,反而变得很激动并且还找了两个平底锅给补锅匠补。她对花的喜爱之情无疑是女性特征的表现。在修补匠离开后,伊莉莎似乎完全变了个人,修补匠四处谋生的求生方式引起了她的兴趣,还憧憬着“女人也能这样活着”[3]。
晚上准备和丈夫外出,她马上变成一个小女人。她洗澡并小心翼翼地打扮。丈夫看见伊莉莎洗完澡打扮得漂漂亮亮时给予了夸奖,然而丈夫的夸奖令她措手不及:“你指的漂亮是什么?”“What do you mean by‘nice’?”[3]对于这种对女性的赞美,伊莉莎似乎很不习惯。伊莉莎的外表,言谈举止描绘出 19世纪 30年代那种斯坦贝克男性世界里女性的挫败感。伊莉莎不止想和男性平起平坐,还想拥有统治权,到最后只能悲惨地发现这些她永远都做不到。
3.《愤怒的葡萄》:乔德妈妈和罗莎香
《愤怒的葡萄》一书中刻画了乔德一家的迁徙。一个植根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家庭为了改善生活,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乔德一家,共 13个家庭成员,由于他们的土地被风沙侵蚀,一无所有的农民走投无路,只能冒险朝着他们唯一的希望前进。他们中间有两个最显眼的女人:乔德妈妈和罗莎香。
当乔德家里人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妈妈总能让他们充满自信,是妈妈毫无止境的自信保证着这一大家子生活的继续继续前行。当乔德父亲变得脆弱了,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地位,她告诉他:“我们一直以我父亲的一句话自豪,那就是”谁都能倒下,只有男人不行。[4]95她总能说出些安慰人的话,比如:“汤姆,你知道为什么其他人都死了,而我们还活着吗?你知道为什么是我们活下来吗?他们是没法打败我们的。”[4]192
乔德妈妈也是个聪明人。当别人需要建议或安慰时,妈妈总是在那,总是努力着取悦他们。第一次她的出现时,“她淡褐色的眼睛似乎见证过一切悲剧,积攒了太多了的疼痛和苦难,一步步走向人类超我境界。”[4]49这暗示着她是个大家可以信任的领导者。妈妈经营着这一大家子,仁慈但也严厉。最终,乔德妈妈成为了她家的带头人。她聪明,充满智慧,坚强。和她呆在一起,总让人感到舒心,精力充沛。她明白“女人可以改变男人……女人把一切掌握在手里。男人却只会空想”[4]291。“男人,活在破烂堆里……女人,流动着,就像小溪……缓缓前行。女人看待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我看来就是为了当下而活。”[4]292乔德妈妈是本书中的精华,是无法毁灭、永不妥协、有着惊人忍耐力的突出代表。乔德妈妈直面逆境,接受挫折,为家而战,斯坦贝克高度赞扬了这个伟大母亲。
在妈妈的影响下,罗莎香从一个天真软弱的少女变成了个伟大的女人,至少在斯坦贝克的世界里,对建立女性社会权威有重大作用。罗莎香,一介新婚女子,满脑子的加州婚后幸福生活,挺着个大肚子加入了家族大迁移。她从没想过什么独立生存,还幻想着依靠丈夫。事情往往与她的想法背道而驰,丈夫在半路就离开了,抛下了所有的痛苦和责任。其后,这可怜的女子被推进痛苦的深渊,却还怀着小小的幻想,期待着丈夫的归来。那时,她没有她母亲勇敢,只能变得神经过敏,惶惶不可终日。更糟的是,由于洪水时期的灾荒,营养不良导致她生下死婴。这女人遭了太多罪,但这些却改变了她的性格。最终她终于自力更生。在本书的结尾处,这个虚弱的女子用母乳救活了一个中年男子。当她给一个陌生人,还是个快饿死的男人喂奶之后,她奇怪地笑了起来。这一行为使罗莎香代表了人类的大循环:除了她本人的需要,她还能救人一命。她充满正义感的行为使读者们联想到圣母玛利亚。她被神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是个男人得到她的母乳。这个情节的设计目的在于强化男女平等精神。结尾处暗指另一层意思,女性是男性的母亲,这是条通则,然而,却常常被忽视。但在本书中,罗莎香强化了女性角色这一观念。因此,女性作为整个社会的源头的地位和她们的权利都被很好地解释了。
4.《珍珠》:胡安娜
故事发生在 20世纪。继承祖业,奇诺成了一名落魄的潜水采珠人,从曾一度给墨西哥带来财富的海湾河床中采集。采珠是奇诺一家三口维持最基本生计的手段。意外的是,他们的幼儿小狗子被蝎子咬了。奇诺没有足够的钱请医生来医治小狗子,于是他跑去找珍珠,还意外地找到了像海鸟蛋一般大的、如满月般的珍珠。这珍珠带来了希望,舒适的前景,但这要以冲破原有制度为代价。就如米里亚姆·雷赛·戈德斯坦所说的,“如果斯坦贝克想要表达的只是物质盈利带来的只是贪心和挫败,那就没需要写个勇敢的有忍耐力的女人。”[5]49胡安娜这个角色是精心刻画的。显然,在创作这个不可毁灭的女性角色的时候,斯坦贝克在脑子里早已想好了其功能。作为这则故事中的女英雄,胡安娜代表了女性好的一面,与每个母亲一样,总是保护着她们爱着的人。斯坦贝克通过胡安娜内心的警惕揭示了这一点:“胡安娜也睁着眼。奇诺醒着时都没见过她闭眼。她黑色的眼睛就如偏离轨道的小星星。他醒着的时候,胡安娜就看着他。”[5]3这里的形象简直是上天女神的守护。当小狗子被蝎子咬了时,是胡安娜把毒液吸出来,而“奇诺徘徊着,他无助,只能碍手碍脚”[5]11。是胡安娜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才找到珍珠,才使得医生前来。胡安娜就是坚强意志的代表。
纵观全文,胡安娜是力量和献身精神的代表,当奇诺遇到那些狡猾的珍珠商,她支持着他:“他感觉身后有人在拉他,回过头去,正好直视到胡安娜的眼睛,当他把目光移开时,他的力量又回来了。”[5]70当他决心不够时,她鼓励他;处于险境时,即使他设法让她走,她绝不离开。“那时,他试图在她脸上寻找脆弱,寻找恐惧或是犹豫不决,但是找不到。她的眼睛很亮。他只有无奈地耸了耸肩,但他从她那找回了力量。”[5]106
5.《甜蜜周四》:苏西
《甜蜜周四》是《罐头工厂》(1945)的续集,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者称,《甜蜜周四》是在讨厌的周三和等待的周五的中间日。一生中,妓女苏西不只代表女性还代表被践踏的社会阶层。当朱笃看到苏西的生活现状,他大叫着,“天哪,人们也太勇敢了吧!”[6]248贯穿本书,苏西不屈不挠的特性总是被强调。她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里长大;她从一个分裂婚姻里解脱出来:她失去了她的孩子;她被朱笃侮辱拒绝;但她仍鼓起勇气,坚持着她的刚毅。当朱笃意识到他对苏西的需要和渴望时,他同情地叹着气,“我同情我自己,因为她的勇敢……我需要她来拯救我自己。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是完整的。”[6]246苏西坚强却也脆弱,聪明但也热心。虽然斯坦贝克小心翼翼地指出苏西的不可毁灭的特性明显是软弱的,但是象征性地,苏西的人性获胜了。
二、女性观流变原因
1.个人经历
斯塔贝克的的成长环境、宗教信仰以及婚姻生活影响他女性观的成形及流变。斯坦贝克生于加州萨利纳斯一个中产家庭。他父亲,大约翰·斯坦贝克,是蒙特利郡的出纳员。他母亲,奥利弗·汉米尔顿,是个老师,从母亲那他继承了写作和读书的巨大热情。由于比较开明的家庭氛围,斯坦贝克被允许暑假在附近农场里打工,之后早年在史布雷寇斯牧场和农民工一起工作。在那儿,斯坦贝克感觉到了移民生活不和谐的一面以及人性黑暗面。和他们深入真实的接触使他态度从冷漠转向同情和恭敬。斯坦贝克对女性的态度最初是在青春期形成的。
斯坦贝克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家里。《圣经》是基督徒神圣的手稿,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西方社会和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产生了持续影响。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已使基督意识成为文化宝藏和道德规范。文学,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注定要受《圣经》的影响。不管是对文学思想的趋势、行动、理论,是对作者的世界观、美学观,还是主旨、主题、形象、技巧,十字架总是有影响的。很多作家可以很好的融合《圣经》中的暗示、基督精神和自己的思想,斯坦贝克也不例外。在《愤怒的葡萄》斯坦贝克从《圣经》中借鉴了神话部分,对乔德妈妈和罗莎香的描写就是很好的例子。把圣经形象融合到本小说中,乔德妈妈的形象是对圣母玛利亚光芒的歌颂,她勤劳、坚持不懈、好心地,甚至在黑暗情况下都闪闪发光。她为家庭考虑,为别人担忧,反映出《圣经》推崇的友爱;她是个极具代表性的伟大母亲。另一个女性角色罗莎香最终也成为了人道主义的化身。她孩子的死是她人性的重点。“罗莎香”是圣经中的名字,代表古老巴勒斯坦里一种生长在肥沃平原上的玫瑰。起先很自私的女人根本不配这个名字,但她随后抛弃她自私的欲望,通过牺牲自己给个快死的中年男子喂奶。这让读者想起了旧约中的所罗门之歌。
与其他美国男性作家一样,在斯坦贝克的主要作品里,女性角色的参与是有限的。但使斯坦贝克出众的是其大多时候女性观都是积极的。原因在于斯坦贝克相对幸福的婚姻生活,他的观点更适中。斯坦贝克理解同情当时那些毫无生计、生活拮据的女人。这在他三篇短篇小说中表现尤其明显,《白鹌鹑》、《菊花》、《长山谷里的马具》。斯坦贝克生动地刻画了三个普通妇人,她们分别在其生活中表达出摆脱男性控制的强烈愿望。她们痛苦地挣扎,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值得那个时代英雄的称号。很多学者还猜测《菊花》的女主角,伊莉莎·艾伦,是根据斯坦贝克的第一任妻子卡罗·亨宁。
2.写作背景
斯坦贝克的文学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这样的划分可以粗略地体现他的女性观的巨变。
第一个时期发生在 1930年左右,这时斯塔贝克借鉴他在那的生活经历,开始写“加州小说”系列和尘暴区小说。他的故事中总是有挣扎的角色。此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女性角色包括《人鼠之间》中的柯莱的妻子、《菊花》(1937)中的伊莉莎、《愤怒的葡萄》中的乔德妈妈和罗莎香。然而,这三部小说中,斯坦贝克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经济大萧条时期,女性被严重歧视,所以作者仅仅把柯莱的妻子和其他女人描绘成性爱工具。这让人思考斯坦贝克对女性到底有多尊重,毫无疑问,少之又少,因为这个时期,女人用途有限,她们没法下田,没法做体力劳动,她们唯一的用途就是做个妓女。柯莱的妻子每天闲荡,一直作弄着工人,这最终导致了其注定毁灭和农民工梦想的破灭,但伊莉莎反而是个贤惠的妻子,大门不出,唯一的慰藉就是她精心栽培的菊花,而菊花都被丈夫忽视,被修补匠丢弃。她们确实有她们自己的梦想,当那些梦想都像泡沫一样破灭了。她们努力着去改变命运,寻求尊重,获得成功,但这都没法改变她们悲惨的命运。
当约翰·斯坦贝克的《菊花》在 1937年出现的时候,佛兰克林·罗斯福再次当选成为总统。美国从经济大萧条中复苏并迅速发展。女性作用更为积极。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农业调整法案只使大牧场主和大公司受益,很多的佃户农民由于银行的大量生产被逼进绝境,被迫背井离乡,寻求新生计。斯坦贝克亲自体味了痛苦的游民生活。通过移民,见证了农民无望的绝境,明白了问题非常严重。《愤怒的葡萄》讲述乔德一家并同时描述了美国社会及经济背景的小说,生动传达了农民的愤怒和血泪。不论情况有多艰难,乔德妈妈总是展现出她的坚定、体贴、勇气和刚毅。她是整个家庭的支柱,并总向别人伸出她那强有力的手,这表明了女工高尚的品格。对乔德妈妈大手笔的生动描写使其更加突出,并很好地使农民阶级的改革精神放大化具体化。罗莎香的转变也暗示了从弱者到工人阶级的转变。还有,这充满同情,义愤,对极端贫困的 20世纪 30年代有了个全面真实的描述,明显有着同情。
在斯坦贝克的文学生涯中,20世纪 40年代是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二战后社会生产力发展、公共财富大量增加,美国价值观发生变化。斯坦贝克对暗斗、小心眼这些亚健康现象进行刻画,对乐观生活方式进行赞扬。他这段时期的代表作品的核心思想是研究金钱、文化和人性的关系。《珍珠》(1947)中的胡安娜和《甜蜜周四》中的苏西都是中期戏剧的极具代表性的女性角色。
在 20世纪 50年代的开端,斯坦贝克离开了加州,在纽约定居。他当时的写作被生物理论严重影响了,特别是被生命循环理论。在这个时期,他的事业没有以前那么顺利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有用虚实结合的办法刻画善恶之争的《伊甸之东》(1952),代表道德退化、表现作者对美国精神危机的担忧的《烦恼的冬天》(1961)。他认为战后的美国很富有,根本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贫困问题,但是出现了道德衰落的征兆。玛丽和玛吉就是这种类型。对财富的渴求逐渐使本来是个贤妻良母的玛丽促成她丈夫伊桑的沉沦。玛吉,想要保住自己的钱,诱惑伊桑毁灭。那复杂的描述表现了斯坦贝克消极的女性观。他似乎和伊桑一样对人性都很失望,但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艾伦·霍利的身上,一个未来的女人。
3.男女平等主义
当《人鼠之间》出版后,因为在此书中他对女性的描述完全不公平,有些人说斯坦贝克是个反男女平等的人。不久,当他出版了《愤怒的葡萄》,很多人又把他看做女权主义者。这两个观点前后矛盾,但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男女平等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斯坦贝克,改变了他的女性观。
女权主义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性运动,目的在于为女性建立同等权利和合法保护。女权主义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理论,还有关于性别差异、女权活动和利益的人生观。南希·科特把女权主义定义为对男女平等重要性的信仰,使社会建造的性别阶层无效。斯坦贝克生活的年代,第一批女权运动出现了。1919年,美国各个州的妇女获取了选举权。斯坦贝克通过自身的观察,对妇女所处的地位表达了同情,公开支持男女平等主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经济的复苏,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道德慢慢开始沦丧,加上上述提到的各种原因,斯坦贝克写成了《烦恼的冬天》,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女性的态度慢慢从乐观转向悲观了。
三、结语
无论美丽还是平庸,可敬还是可恨,她们共同组成了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形象。尽管数量不多但她们却必不可少。女性角色的最大意义在于与其中的男性形成完美呼应。女性角色的存在有效的解释了斯坦贝克作品的主旨,传神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苦难、绝望和悲剧为这些女性赢得了我们的同情;铁一般的意志,务实精神,坚定不移的信念、雷厉风行的个性使她们成为出色并且意义重大的角色;自身的局限,自私和贪婪遭到我们唾弃的同时又为她们感到可悲。矛盾的形式下展现的是相同的本质,在相似性反映出斯坦贝克对于女性的大体印象的同时,她们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反映出斯坦贝克对于女性认识的变化。细致地分析了斯坦贝克代表作中女性形象之后,我们大概可以得出斯坦贝克对于女性的态度:起初相对冷漠和草率,转而怜悯关切,接着是乐观和敬重,最终转为失望焦虑但仍然充满希望。
[1]Peter Lisca.The W ide W orld of John Steinbeck[M].RutgersUniversity Press,1958:206-207.
[2]John Steinbeck.OfMice and Men[C]//Harold Clur man. Famous Am erican Plays of the 1930s.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1974.
[3]John Steinbeck.The Chrysanthem ums[EB/OL].http:// amb.cult.bg/american/4/steinbeck/chrysanthemums.htm
[4]John Steinbeck.The Grapes of W rath[M].New York, 1969.
[5]John Steinbeck.The Pearl[Z].New York:Viking Press, 1947.
[6]John Steinbeck.Sweet Thursday[Z].New York:Viking Press,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