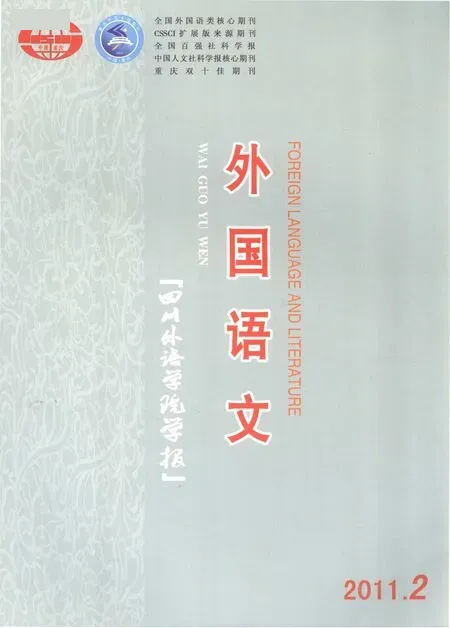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迁移现象论析
黄姣玲
(上饶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江西 上饶 334001)
1.引言
“迁移”一词原为教育心理学术语,指已获得的知识、技能、学习方法或学习态度对新知识新技能习得和解决新问题的处理所产生的影响 (朱智贤, 1989)。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影响称为“正迁移”,是指“在一个情境中学到的知识能够帮助在另外一个情境中的学习和表现”;消极影响称为“负迁移”或干扰,是指“先前的知识阻碍了一个人随后的学习和表现”(Or mrod, 2006)。笔者在这里用“迁移”概念来讨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影响问题。
2.外语教学中的迁移现象
1980年,晓生先生提出了外语教学中如何对待“本族语”即母语的问题,对“外语的外部言语和本族语的内部言语、外语的外部言语和本族语的外部言语、外语的内部言语和本族语的内部言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完全排除本族语的影响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很难做到;相反,“本族语的言语经验对学外语是很有益处的”。但是,晓生先生尚未正式使用“正迁移”的概念,而且对于本族语在学习外语中究竟有哪些好处,文章在理论上也没有详细说明。齐玉珉 (1984)先生也对用外语表达时的正负迁移问题作过论述,用大量的例子说明了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负迁移现象。但对什么是正迁移?外语教学中如何运用正迁移?文章却语焉不详。1996年,束定芳、庄智象在《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一书中指出:“具有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的外语学习者,其外语交际能力的获得相对容易些。同样,如果学生的母语与目的语语言结构上越相近,文化背景越相似,交际能力的正迁移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就越大。”他们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母语交际能力”在“外语学习”中的“正迁移”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母语在英语教学中的正迁移呢?有论者认为:“以汉语为母语进行英语教学,其正迁移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用汉语翻译作为教学手段;用母语来比较语言现象,讲解英语的语法规则;解释抽象的词语的意义。”(何声钟等, 2000)并就“解释抽象的词语的意义”举例说:“英语中有些词语的意义比较简单,如 get up,说 rise from bed or from a sitting position,学生可以理解。”但抽象一些的词语如 sad,认为 depressed in spirits or causing sorrow or depression学生理解起来不容易,而用汉语“忧伤”解释就一目了然。但是笔者认为,上述论证并不准确。按照作者所引奥德林(1989:27)所给的定义:“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共性而引起的迁移称为‘正迁移’”。这些用母语翻译目的语、解释语言现象、解释抽象词的意义都不一定是“正迁移”;相反,由于外语教师自身水平的差异很大,这种翻译和解释如果不准确的话,有可能对目的语的真实含义或真实意义构成伤害。事实上,任何第二语言的学习都或多或少存在母语的作用和影响,不能认为只要是有作用,离不开,就断定是“正迁移”。只有在充分理解“母语文化”的具体内涵时,正确区分哪些是积极影响 (即正迁移),哪些是消极影响(即负迁移),才谈得上是对母语正迁移的运用。
3.母语文化中的迁移现象
本文之所以要用“母语文化”而不用通常说的“母语”,那是因为在外语教学中,说“母语文化”比一般地说“母语”适应性更广泛、含义更丰富。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它有使用范围的广泛与否,而其本身却无所谓优劣和正误;文化则是一种包含一定价值评价的社会现象,文化中包含着语言中的各种要素,并以一定的语言为中心展开自己的全部内涵。当两种语言文化在碰撞和交流时,迁移现象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虽然“母语文化”内容极其多样,涵盖极为广泛,但主要可以从语言习惯、生活情趣、思维方式、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
3.1 语言习惯
汉语和英语(以及几乎所有拼音文字)的差异无疑是巨大的。以汉语作为母语的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受到的负迁移比比皆是。例如,在英语教学中,在表达“肯定”与“否定”的概念时,汉语与英语是有很大区别的。有时汉语用否定的地方,英语用肯定表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翻译成英语应该是“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be done by”;“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则是“Say all you can and say itwithout reserve”。有时汉语用肯定的地方,英语却用否定表达:“活到老,学到老”用英语说是“No man is too old to learn”;“越小心越好”在英语中一般说成“You can never be too careful”。如果是对话中的肯定与否定问题,就更应该注意了。当一方用否定式提问时,汉语的肯定和否定与英语正好相反。例如:问者说:“你不了解这件事,对吗?”汉语说:“是的,我不了解”,英语却说“No,I don’t”(不,我不了解);汉语说:“不对,我了解”时,英语则说“Yes,I do”(是,我了解)。这时候如果用汉语的语言习惯去理解英语或翻译英语,就会造成错误,产生负迁移。
然而,即使是从语言习惯来说,汉语也并不都在学习英语过程中产生负迁移,两者还是有许多因为具有“共性”而产生正迁移的例子。例如汉语中除了短语或感叹句、祈使句以外,一般句子中都应该有主语、谓语和宾语,或者至少应该有主语和谓语,主谓搭配、动宾搭配应该适当,这在英语中也大致相同。因此,用汉语中习得的关于句子成分的知识来分析英语的句子成分,就可以产生正迁移。汉语中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的现象司空见惯,英语中这一类现象也屡见不鲜。了解汉语的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也有利于学习英语的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可见,虽然从大的语言系统来看,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二者差异很大,但不同语言之间毕竟有相通之处,有共性存在,那么汉语文化习惯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产生正迁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此外,还有些人说到汉语和英语在词的发音上也可以存在正迁移现象,如英语的 give一词的发音和中文的对应词“给”(gei)的发音基本相似,他们提出的理论依据是“中文相似于英文,语言相似于语言”的“趋同论”(徐立群,2000)。
3.2 生活情趣
汉语文化与说英语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汉语文化中偏爱“红”,结婚叫“红喜事”,新娘要穿红衣,新郎要戴红花,床上用品也要大红大紫;事业兴旺叫“红火”,人们受到重视叫“走红”,年轻貌美的女子称为“红颜”,《红楼梦》中贾宝玉住的小楼叫“怡红院”;现代的“红色”更是“革命”的象征,红旗、红心、红军、红区、红歌、红宝书等等都是用来指称革命的。相反,汉语文化中对“白色”则有所忌讳,人死亡后扎白花,披白布,丧事叫做“白喜事”。英语文化中对“红”则没有多少好感,因为“红色”在英语文化中象征暴力,象征喧闹,英语文化对汉语文化忌讳的“白色”则没有那么多讲究,在婚礼场合,人们更多的是穿白色的婚纱,象征着爱情的贞洁,而教堂的庄严肃穆赋予了婚礼神圣的色彩。此外,英语文化对“绿色”比对“红色”更为宽容,正因为如此,英译《红楼梦》要把贾宝玉住的小楼翻译成“怡绿院”(潘学权,2003)。如果不懂得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容易产生学习中的负迁移的。汉语中很多见面语 (或称为“问候语”)往往会涉及实质内容 (例如“你到哪里去”、“吃过了吗”等等),表示对被问方的某种程度的关切;英语文化则相反,见面语大多不涉及实际内容,是一种真正的“寒暄”(Austin,1962)。如果用汉语文化的观点看英语文化,会觉得说英语的人缺乏人情,有点“虚情假意”;如果从英语文化的角度观照汉语文化,又会认为说汉语的人过分关心他人隐私,让人们感到不快。这时候就必然要发生学习中的负迁移。
但是,即使就生活情趣而言,使用汉语的民族与使用英语的民族也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因而可能发生母语文化在英语学习中的正迁移。就人类本性而言,趋利避害、趋吉避祸是共同愿望,因而就一定能在语言文化上找到某种共性,在汉语和英语中出现的大量委婉语就是最好的例证。例如,中华民族对于吉庆的语言或吉庆的数字具有某种偏好,对于不祥之语或不吉利的数字存在忌讳,说英语的民族也是如此。中国人对“死”、“病”之类的语言心存忌讳,宁可用“老”、“走”、“升天”等说法代替“死”,对于因为正义事业而死者则用“殉职”、“捐躯”、“牺牲”、“就义”等表示尊敬;英语中也存在这种现象,把死亡说成是 to sleep、to be bone to sleep、decrease expire、breathe one’s last、say hello toMarx、go west、join the majority、pass away、pay the debt of nature、reach a better world、grounded for good、making the ult imate sacrifice、to do one’s bit、to lay down one’s life、be with God等等 (Faerch.C&Kasper. G,1984)。汉语用“贵恙”、“欠安”、“不适”等来表示“病”;英语对“病”也有各种说法,如用 trouble代替 disease,用VD代表“性病”,用 BO代替“狐臭”,用 TB代表“肺结核”等。汉语文化中对“六”、“八”等数字有偏爱,成语中涉及“六”、“八”的时候大多呈褒义,关于“六”,有“六畜兴旺”、“身怀六甲”等等,民间还有“六六大顺”的说法;关于“八”,则有“八方支援”、“八方来客”、“八仙过海”、“八面威风”等等。新时期因为广东话的“八”与“发”同音而使“八”受到更多人的青睐,汽车牌号、门牌号码、电话号码中的“八”在有些城市甚至进行拍卖,需要者必须花高价竞买。相反,汉语中涉及“三”、“四”时则贬义较多,“三心二意”、“三教九流”、“四面楚歌”、“四平八稳”等都不是什么好词,“三天打鱼,四天晒网”、“颠三倒四”、“朝三暮四”、“说三道四”更是把三四连用表达强烈的贬义。英语中对数字也有类似的用法,例如对“4”和“13”的忌讳,因为“4”的英语读音与“错误”相似,而且英语中有许多四字词 (four-letter words)用法不雅,所以“4”便不是吉利数字,有些语言学家还专门对四字词进行避讳,如用 copulation代替 fuck,用 urinate代替 pigs,用manure代替 shit,甚至用 abdomen代替 belly,以致有的专家认为,现代英语中“禁忌语用得最多的场合”,就是对四字词 (four-letter words)进行避讳(江希和,1983)。“13”在英语中也非常受“歧视”,在很多球队中没有 13号,在某些小区的楼群中没有 13栋,在某些楼房的楼层中没有 13层和 13室,等等。“13”之所以不好,既有《圣经》故事的影响,还有人们心目中对这一数字存有偏见有关。
3.3 思维方式
汉语文化与说英语的民族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大的。贾德江引傅雷先生的话说: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 mentality殊难彼此融合。贾德江先生断言“分析型思维与综合型是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由此而来的中国人重“意合”思维,西方人重“形合”思维;中国人重顺向思维;西方人重逆向思维,中国人重主体思维、西方人重主客体融合思维的传统在语言文字方面也得到充分反映(贾德江,2002)。如果学生对这些思维传统不加辨析,就容易产生负迁移。
汉语文化在学习英语时的正迁移表现在:两种语言在概念、判断和推理时存在很多共性,因而可以引发“共识”。在概念上,两种语言都既有大量指称实际事物的“具体概念”,又有不指称任何具体事物而只是反映事物共性的“抽象概念”,还有在客观世界中无法找到真实存在的“虚概念”。前者如“桌子”、“苹果”、“太阳”、“中国”,次者如“用具”、“水果”、“统治”、“幸福”,后者如“神仙”、“金山”、“摇钱树”、“龙王”,等等。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概念,如“table”、“apple”、“sun”、“China”,“appliances”、“fruit”、“rule”、“happiness”,“ Immortals”、“angle”、“the goose that lays golden eggs”等等。懂得汉语中的“具体概念”、“抽象概念”和“虚概念”的性质和用法,对学习或使用英语中的同类概念是有好处的,容易产生正迁移,在判断和推理上也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形式逻辑中的“格”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通用的。(Searle,1969)
3.4 历史传统
历史传统方面也存在学习的负迁移。“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称呼年长的对方为“老”是一种尊敬,例如张老、李老、谢老、郭老等等;称老张、老李、老谢、老郭也很常见。它们通常都带有褒义,至少没有贬义。使用英语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则不尽然,他们对 old(老)十分敏感,英美老年人不喜欢 old people以及 aged甚至 the elderly等称呼,宁愿人们称呼他们为 senior citizen(年长的公民)或golden age(黄金年代的人)。在公共汽车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老、弱、病、残、孕专座”的字样,这体现了汉文化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但如果把他们对应译成英语,恐怕很难为英美人所接受。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他们的公共汽车上虽有类似的座位,但上面写的是“Courtesy Seats(优待座位)”,这样可避免让人感到尴尬。如果受负迁移的影响,就有可能将“老、弱、病、残”直译成英语,从而贻笑西方人。又如英文中的“individualis m”和“privacy”在英语文化中受到高度的尊重,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与它们对应的词,只好把这两个词翻译成“个人主义”和“稳私”。但在汉语中“个人主义”是个贬义词,常常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而“隐私”常常给人以不好的联想。受母语文化的影响,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就不像在英语中那样有高度的正面意义。
在历史传统方面母语文化的正迁移表现在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和历史文化,因而在学习外语时有利于帮助理解。例如对思想自由的向往,使中国的老庄和西方的柏拉图都对“逍遥”情有独钟(庄子写了《逍遥游》,柏拉图把自己的学派称为“逍遥学派”);对“论辩”的爱好,使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许多流传青史的著名辩论,中国有“义利之辩”、“有无之辩”、“本末之辩”、“体用之辩”、“理气之辩”、“濠梁之辩”(庄子与惠施观鱼之辩)、“白马之辩”、“鹅湖之辩”(朱熹与陆九渊在铅山鹅湖的一场著名辩论)等等,英语国家也有“一多之辩”(世界的本原是“一”还是“多”)、“心物之辩”(世界的本原是“心”还是“物”)、“名实之辩”(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关于概念本质的长达近千年的辩论)、“正义之辩”(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现代美国的罗尔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与形形色色的对手之间的论辩)、“真理之辩”(西方从有哲学以来即存在的究竟什么是“真”的辩论)、“经验之辩”(即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长达数百年的辩论,与此相关的是归纳派与演绎派的长期辩论)等等。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如果对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对西方的这些历史传统也就容易理解。
3.5 价值观念
中国和英语世界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最典型的莫过于“家”“国”观念,中国长期以来把“国”当成“家”,国家国家,“国”和“家”是合在一起的。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尤其如此。国家的事就是皇帝的“家事”,而皇帝的“家事”就是最大的国家大事。崇奉统一,注重亲情,是汉语文化的重要特点。“父母官”、“四海皆兄弟”等语言表达的是把国人当成家人的亲切。这种价值观直到今天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但在英语文化中,“家”和“国”是严格分开的,“家”是个人空间,涉及的是“私人权利”;“国”是公共空间,适用的是“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利”的严格保护和对“公共权力”的严格限制是英语国家(也是西方国家)的通常做法。与此相关的是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理解、对“共性”和“个性”关系的理解、对“求同性”和“求异性”关系的理解,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都有重大的不同。(刘绍忠,1997)
那么,在价值观方面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有没有可能产生正迁移呢?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那就必然在语言文化中得到反映。例如,任何文化都对“真理”、“正义”、“美丽”、“和平”、“诚信”、“自由”、“友爱”、“民主”等美好的字眼加以倡导和褒扬,对“虚假”、“邪恶”、“丑陋”、“战乱”、“欺诈”、“奴役”、“凶残”、“专制”等等丑恶的东西加以贬斥和鞭挞(Green,1996)。在这些方面,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是基本一致的。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全球化,更是把世界各国各民族融为一体,“生态”、“环保”、“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全球伦理”、“全球道德”、“全球价值”等概念呼之欲出,不同文化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的机会。这些都有可能对语言学习的正迁移产生良好影响。
4.结语
事实上,语言学习并不是完全的接受过程,在学习中是需要“创造”,需要“生产”。这里的“创造”指语言学习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知识背景对某些字、词、短语和句子进行的个性化领悟;“生产”指语言学习者对特定语词所作的区别于他人的理解和处理。它们在语言学习中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需要特别的注意或提示。在外语的学习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高一虹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 (Brich Fromm)的“生产性人格”理论,通过对 52名中国外语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实验,提出了“生产性外语学习”的概念。高一虹 (1994)认为:“在目的语学习的过程中,目的语与母语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相互促进;学习者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生产性外语学习中,母语和母语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可见,充分重视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迁移现象,因势利导,努力利用母语文化的正迁移,尽可能减少负迁移,是每一个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予以注意的问题。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英语专业大学生不但对于英语文化了解不多,就是对中国文化也了解有限,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中“文化意识贫乏”的现象。不少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比较注意语言的实用功能,而不太注重中西文化的互动,忽视了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整体培养,客观上不利于激发学生参与跨文化交际活动。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有很大弊端,为了培养合格的建设祖国的全面发展的外语人才,重视语言的文化内涵,加强外语学习中母语文化的正迁移,尽可能减少负迁移,让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和“生产性学习”,势所必行。
[1]Austin,J.How toDo Thingsw ithW ords[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Faerch,C&G.Kasper.Pragmatic knowledge:Rules and Procedures[J].Applied Linguistics,1984,4(3):214-225.
[3]Green,G.Pragm atics an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M].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1996:166.
[4]Or mrod,J.E.教育心理学 [M].彭运石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Searle,J.Speech Acts[M].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6]高一虹.生产性双语现象考察 [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1):59-64.
[6]何声钟,熊腾,姚小平.英语教学中的迁移现象[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0(5):32-35.
[7]贾德江.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166-193.
[8]江希和.现代英语中的委婉语[J].现代外语,1983(3): 14-19.
[9]刘绍忠.语境与语用能力[J].外国语,1997(3):24-31.
[10]潘学权.文学翻译与文化变形[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3(4):80-83.
[11]齐玉珉.用外语表达时的正负迁移问题[J].天津教育, 1984(11):41-44.
[12]晓生.外语教学中如何对待本族语[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1):104-107.
[13]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92.
[14]徐立群.英语词汇习得与母语迁移 [J].教学与管理, 2000(1):56-57.
[15]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 [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