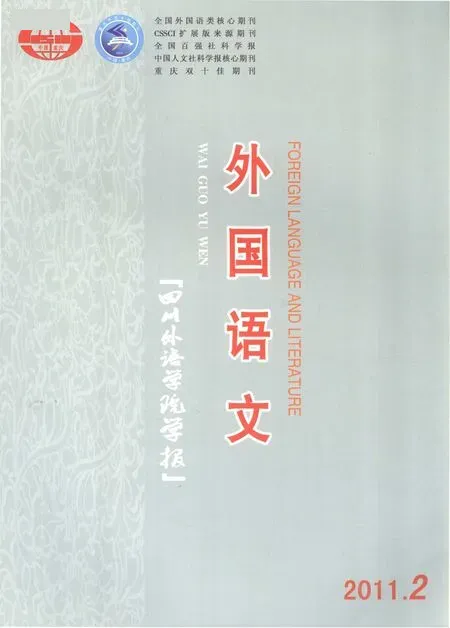主人公成长的困惑伊斯兰女性的悲哀——《风的女儿》的成长主题初探
毛新耕
(湖南理工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一、引言
成长是青少年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是美国文学关注的一大焦点。这类“叙述青少年成长过程、讲述青少年成长经历的小说”[1]的“成长小说”反映了青少年遭遇的成长困惑、获得的心灵慰藉、肩负的社会责任。20世纪 6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自我觉醒,女性的能动性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外国文学界 (尤其是青少年文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突显了女性寻求自我价值,实现身份认同的积极主题。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如芮渝萍[2]、李琳[3]、苏翠英[4]开始对美国成长小说进行分析研究,概述美国成长小说的重要特征,分析一批美国成长小说如《棕色姑娘,棕色砖房》、《华女阿五》、《典型的美国人》的成长主题和叙事风格。不过这些小说的背景大都是美国本土,对于其他地区、其他文化的研究甚少。我们认为: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中的青少年在遇到困惑和难题时表现出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特色,他们的成长同样值得关注。苏珊·费雪·史戴伯斯 (Suzanne Fisher Staples)的女性成长小说就是这些不同文化中的小说代表。她的小说主要叙述了南亚穆斯林地区青少年成长的历程,对巴基斯坦、印度陌生文化中的女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尤其是在她的成长小说《风的女儿》(Shabanu:Daughter of the W ind)(1989)中“对半游牧民族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展示了不同于我们文化的深层一致性,她将莎巴努的内心冲突写得活灵活现”[5],体现了人性真实的一面,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史戴伯斯的成长小说《风的女儿》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敏锐的观察,结合作者多年合众国际社驻亚洲记者经历,通过巧妙构思,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平易流畅地讲述了生活在巴基斯坦的焦利斯坦沙漠游牧家庭中的一位 12岁少女莎巴努成长中的困惑、叛逆、迷惘,对生活的希冀,对自由的渴望,反映了穆斯林女性的悲哀命运——无奈与服从。该书获得了与安徒生童话奖齐名的纽伯瑞文学奖银奖(1990)、美国图书馆协会评选的年度最佳青少年图书奖、《纽约时报》评选的年度最佳图书奖等荣誉。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结合人格成长理论,分析莎巴努作为一名有着其特定生活环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代表从起初对生活的向往、自我意识的觉醒,力争改变命运的追求到仍旧无法挣脱宗教、种族束缚,最终选择向命运妥协的无奈。
二、童真的幻灭与成长
青少年要想真正获得成长,必须经历的重要阶段就是昔日童真的幻灭。童真的幻灭往往是青少年成熟的起点。人生的转折在于从快乐清纯、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进入人生的难以抉择,以及面对现实冲突的迷惘与困惑。不论童年时代的记忆多么美好,最终只有正视现实的世界,青少年才会真正得到成长。《风的女儿》的主人公莎巴努的成长转折契机就在于她作为伊斯兰教传统文化和男性主宰的社会束缚捆绑下的女性,是毫无怨言地接受父母包办婚姻的现实,还是离家出走,去过上自己渴望独立的生活。
莎巴努生活在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家庭中,是家中的二女儿。姐姐普兰即将出嫁时,莎巴努才 12岁,还沉浸在欢乐的童年生活中。她深爱着自己的父母、家庭,脑海里根本没有婚姻、生儿育女的概念。莎巴努的童年仿佛没有任何掺杂,只有纯粹的幻想,简单的节奏。她任性地认为只要能与自己心爱的骆驼为伴,跟随父亲四处赶集奔波生计,这样的世界才是美妙的。然而,残酷的现实不由得她任意选择,就算这样简单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当自己从小依仗的母亲对她说:“莎巴努,你还像风一样野,你必须学会服从。否则,我会为你担心的。你不再是个孩子了,过一年你就要订婚。即使你不同意,你也必须学会服从。”[6]28伊斯兰教的女性必须绝对服从真主的旨意,以真主制定的行为准则为典范,遵守自己的信仰。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真主的赏赐,分享真主的财富;所以,“服从”对于伊斯兰教的女性来说就是一个最具份量的旨意。虽然莎巴努已经开始意识到昔日纯真的童年即将远逝,但她仍抱着一份对未来的幻想,这幻想实质上已经开始预演着主人公童真的幻灭。作者笔下的莎巴努从一出生就注定只能拥有一个短暂的童年。此外,这群游牧民族的女性必须按照男性的愿望塑造,传播着歧视女性的文化背景,穆斯林政权的男性统治等,对女性的偏见被圣训化,妇女应当是“贤妻良母,是‘怀孕的袋子’和献身的母亲”[7]。女性必须蒙着面纱,不出闺门,与外界隔绝;不准参与任何社会事务,不具有任何政治权利,必须承担几乎所有的家庭责任和重担。同时,伊斯兰教穆斯林女性还受着层层的道德束缚,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标准和伊斯兰教教义,婚前必须保持贞洁,恪守规矩,婚后保持忠贞顺服,接受丈夫的耳提面命,特别对于青春期的少女来说,婚姻更是控制在父权之下,早早地准备嫁妆,以生男孩为荣。
史戴伯斯正是将莎巴努置身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下,通过一系列的遭遇让她从一个天真叛逆、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女一步步地接受现实的冲击,心灵的成熟,品味到自己童年纯真梦想的幻灭和即将难逃的宿命。一开始对婚姻没兴趣的莎巴努知道自己和姐姐的婚姻已被父亲一手包办。渐渐地她接触到现实,体会母亲对自己的教诲。父亲为了筹备姐姐的嫁妆,违背承诺,卖掉心爱的骆驼,莎巴努因此对父亲产生恨意,现实与自己的幻想冲突进一步加剧,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梦想的生活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令莎巴努的童真受到更大冲击的是在去市场卖骆驼的途中遇见一个为追求真爱而私奔的少女,却被追捕无情地伤害,莎巴努满脑的困惑,在心里产生疑问:难道少女就不能追寻自己的幸福吗?莎巴努的童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现实冲击下逐渐褪色。这一切不仅反映了游牧少女根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婚姻自由,也代表着每一个人孩童时幻想的和现实的生存与应尽的责任的冲突。因此,莎巴努感到无可奈何,她从天真堕入迷惘,从单纯的儿童生活早早地进入复杂的成人世界。
莎巴努两次被包办的婚姻实质上都象征着她童真的幻灭:第一次是婚姻不由自己作主,莎巴努体会到自己的童年一晃而过。第二次为了成就姐姐的婚姻,被迫放弃自己的爱情,嫁给已有三个妻子的大地主,来换取家庭的宁静与和谐,这意味着她童真的完全幻灭。在成长小说里,爱情本来是性爱的升华和最私人化的情感领域,也是莎巴努曾经极度渴望并天真地以为即将拥有的领地,可是在这一块领地里,莎巴努也未能成为伊甸园中自由的夏娃。这一事实深刻地揭示出在被宗教文化层层包裹下的女性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面临着男性中心意识的沉重压力,她们失去一切可以保有平等和尊严的空间,甚至被剥夺了幻想平等的权利,而年少的莎巴努正是在渴望独立与社会期望的矛盾对立中学会了成长。
三、成长中的引路人
成长是青少年的生命存在状态,青少年必须经过成长走向社会。成长是在追求希望中的跨越,预示着精神的磨砺与蜕变,所以成长在追求希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遇到焦虑与困惑。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认知,影响着青少年成长的轨迹,他们是青少年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李琳认为:“成长的引路人是美国成长小说的一个重要构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每个人的成长都不是孤立完成的,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这些人从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识。在观察这些人扮演的社会角色过程中,青少年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角色意识和生活方向。”[3]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容易感受到迷茫,不知所措,他们通过观察生活中自己周围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向。莎巴努在成长过程中随着心智的逐渐成熟转换着自己的榜样。从最初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父母亲,到最后激发她自我意识觉醒的夏尔玛姑妈,莎巴努领悟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c Erikson)把人的成长分为包含特定发展任务的八个阶段:(1)信任与不信任 (婴儿前期);(2)自主与羞怯 (婴儿后期);(3)自力性与罪恶感(幼儿期);(4)勤奋与自卑 (儿童期);(5)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 (青少年期);(6)亲密与孤独 (成人前期);(7)繁殖与停滞 (成人中期);(8)自我整合与绝望 (成人后期)[8]。这一理论把各阶段视为一种二元对立的过程。个体只有综合心理、生理和社会三方面因素,才能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从而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品质。埃里克森认为,在孩童心中创造“基本信任”的感觉是构成其“同一性的基础”。基本信任是一种对自身和世界的肯定态度,这种信任感的建立不仅需要母亲对孩子的细心照料,更有赖于母亲对所属社会群体文化认同及她被这个群体所信赖的感觉。
莎巴努童年时期,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没有概念,给她直接影响的便是父母,而心中对父母的信任感则反映了她对这个社会群体的信任。所以从一开始,父母在莎巴努的成长道路上扮演着启蒙老师的角色,父亲给予她温暖的父爱与对家庭的责任。作者在这里埋下伏笔,虽然她埋怨父亲操办自己的婚姻,牺牲自己的幸福,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服从安排,因为她热爱自己的家庭,她有责任维护家庭的和谐,这些都是对父亲有责任感的继承。与父亲的果断,敢于承担相比,作为遵从伊斯兰教下的母亲只是扮演着“三从四德,贤妻良母”的角色,而这些与莎巴努心中渴望的生活和内心的叛逆个性相违背,她一面听从父亲的安排,一面对生活感到困惑,在纠结之中重新寻觅新的引路人。这种状态在人的成长理论中可以解释为:青少年喜欢问“我该做什么,怎么做?”之类的问题,处于从“完美典型”的幻灭到“角色混乱”。步入青春期的莎巴努渴望在特定社会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便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时,夏尔玛的出现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夏尔玛有着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她是穆斯林文化传统的“叛逆者”,敢于违背社会对女性的种种要求和限制,在莎巴努心目中,夏尔玛是她心中崇拜的偶像,有她向往的独立、勇敢和坚强。夏尔玛反对家庭暴力,不容忍因为未能生男孩而对女性产生偏见。离开虐待自己的男人,自立自强,不惧怕任何的伤害,带着女儿相依为命,因此她受到人们的排斥和孤立。从夏尔玛的身上,莎巴努清晰地意识到在很多表面看起来不可能违背的事情是可以做到的,这种认识激起了莎巴努自我意识的强烈欲望。她欣喜自己有夏尔玛这样的亲戚。所以,她开始彷徨自己的人生,疑惑自己是否能够同夏尔玛一样敢于反抗。根据拉康 (JacquesLacan)的理论:“人生通过认同于某一形象而产生自我的功能。人的自我发展历程就是不断认同的历程。”[9]对于被压制成被排斥的个体来说,需要有一个理想的目标个体可以认同,从而摆脱社会强加的“他者”形象,实现真正的自我。莎巴努内心深处认同夏尔玛,而夏尔玛也不断激励着莎巴努去不断追寻自己的人生。她告诉莎巴努“不管发生什么,你还有你自己,你还有选择的余地。这一点极其重要”[6]225。
莎巴努在夏尔玛身上领域到自我意识的存在,正如拉康把自我看作虚无,把欲望看作“存在的缺失”,正是因为莎巴努对自由、独立、自我意识的缺乏,促使她为了自我得以存在,必须不断与目标认同,构建自我,决定重新审视自己,踏上离家远行寻找自我的艰辛成长之路。莎巴努追求自我的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可以理解为两种:一是父母,这也是每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初的学习榜样;二是作者史戴伯斯对新女性赋予的新特质——独立坚强、敢于追求自我的精神。从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领悟到史戴伯斯在莎巴努身上寄托的对女性的期望和理想:不管生活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下,都不应该轻易向命运低头,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勇于向不公的现实发起挑战。
四、困惑中的两次选择
人的成长历程需要面临无数的选择,选择放弃亦或选择坚持,选择逃避亦或选择承担。人往往容易徘徊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产生困惑、迷茫,但人生成长的关键就是学会选择。摆在莎巴努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跟随自己内心对自由的欲望,向夏尔玛看齐选择逃离;二是放弃自己梦想和幸福,服从安排,嫁给地主。
心理学家马斯洛 (Maslow)认为,真正实现自我的人是要自信和自主的,这些人在一定范围内,完全能够控制住社会的压力进行思考与行动。他们保持着一种脱离自身文化内部的独立,并不故意地违反社会准则以表示自主。实际上,有关服装、礼貌以及他们认为琐细的其他事情,可能是完全常规的。当自由的问题(通常伦理道德的问题)呈现出个人重要性的时候,他们才会决心向社会的法度和规范挑战[10]。作者史戴伯斯笔下的莎巴努在经历了童真的幻灭,积极地寻找自我意识之后,内心原本叛逆的激情更加跌宕、澎湃,渴望自由和欲望更加激烈。脑子里闪现出布哥提斯(Bugtis)少女被捕杀的画面,耳边又不断听见夏尔玛的忠告:“做自己”。于是,莎巴努的内心再也无法宁静,她在内心十分纠结:“当他们要我嫁给地主时,没有人为我感到抱歉或受惊。没有人问过我的感受。”[6]237她在已经浮现的自我受到压抑时,力图摆脱社会文化和父母强加的期望和禁令,选择带着心爱的骆驼米胡向自己预想的未来踏出第一步。史戴伯斯首先让莎巴努选择了离家远行,寻找自我。在读者们都认为女主人公离自己幸福不远,为莎巴努而感到庆幸时,作者笔锋一转,莎巴努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第二次选择。
埃里克森认为,人成长前期是从“理想的我”过渡到“现实的我”[11]。莎巴努的第二次选择则是让她真正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选择离家的路是艰辛的,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莎巴努本以为静悄悄地走出家门第一步,自由便已向自己招手,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她。让沙漠民族引以为豪的,她最挚爱的骆驼米胡脚受伤,无法再向前行走。一瞬间原来对生活的无限遐想顿时烟消云散,绝望和无助如期而至。她希望父亲快点追上她,带她回家,原谅她那对自由不切实际、令家庭蒙羞的渴望。莎巴努折途而返,做出了第二次选择——接受安排,服从伊斯兰民族的一切一切。尽管她多么不情愿,但为了骆驼的安全,为了家庭的平和,为了姐姐的幸福,她无奈地做出了痛苦的选择。即将步入成熟的莎巴努便是正处于埃里克森的人格成长理论中的“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阶段。在这一阶段,无奈地跨越了“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之间的鸿沟,不得不接受自己所属社会或集团的价值观念,容忍社会的不足,并按照一定的社会角色规范去行事,在社会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
莎巴努热爱沙漠,但同时深爱自己的父母。当自己姐姐不幸的婚姻降临到这个家时,莎巴努不得不在叛逆的个性与对父母的爱之间妥协。莎巴努只好第二次选择嫁到地主家,这使她认识到人生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失落。莎巴努的两次选择象征着她的两次人生。一是追求自我的精彩人生,二是放弃自我,放弃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无奈向宿命妥协的卑微人生。最后的选择也表明:她没能与束缚的宗教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同时也让读者体会到宗教严格制度下的女性命运的悲哀。作品旨在惊醒千千万万的女性同胞去努力挣脱命运不公的枷锁,追寻自己的幸福。
五、结语
艾哈迈德认为:“穆斯林女性的典型特征是个个披着头巾,听从男人征服,虽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但仍然需要西方文明的拯救。”[12]《风的女儿》女主人公莎巴努经历童真的幻灭,离家出走寻找自我,最终无法摆脱家庭和文化传统礼俗的束缚,挣扎在成长的困惑与痛苦之中。她的成长故事是巴基斯坦、印度等内陆贫困地区女性生活的典型。受尽宗教的文化束缚下的女性,虽然有着强烈的欲望去寻找自由、自主,但处处受到宗教和社会的压制。在这样一个被宗教文化意识植入的民族生活中,她们遭遇的命运只有妥协和服从。主人公成长的困惑正是伊斯兰女性的悲哀。因此,如何摆脱宗教文化历史的束缚,如何摆脱本民族的陈规陋习、羁绊,如何为自我选择成长的道路,对每个青少年的成长来说都是一大挑战,是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特别对于巴基斯坦的女性来说,这甚至是更加危险的道路。
《风的女儿》拓宽了人们对成长小说的主题和视野,它把视角放在不被众人所关注的巴基斯坦、印度这样一些贫困地区,从一个少女的成长经历让读者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同情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但同时也能从小说中听到一个弱小民族里女性的呼声:她们同样有理想,有意识,渴望独立自由的人生,不愿成为男人欲望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她们也曾努力寻找机会,追寻幸福,只是宗教传统的那堵城墙,她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冲破。
[1]贺爱军,段汉武.青少年文学研究的三维视角[J].外国文学研究,2007(3):174-176.
[2]芮渝萍.文化冲突视野中的成长与困惑——评波·马歇尔的《棕色姑娘,棕色砖房》[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6):102-108.
[3]李琳.《华女阿五》:成长小说中的一朵奇葩[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6):106-111.
[4]苏翠英.拉尔夫·张的心路历程——谈《典型的美国人》的成长主题[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版),2007 (4):93-95.
[5]Warwick,E.D.,Jones,T.E.Shabanu:Daughter of the W ind(Book)[J].School Library Journal,1989(11):128-129.
[6]Staples,S.F.Shabanu Daughter of the W ind[Z].New York:DellLaurel-Leaf,1989.
[7]韩风鸣.宗教历史中的女性地位[J].广西社会科学学报,2002(4):67-69.
[8]Biehler,R.&J.Snowman.Psychology Applied to Teaching[M].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9]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89.
[10]杜·舒尔赫.成长心理学[M].李文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56.
[11]Ericson,E.H. Identity:Youth and Crisis[M].New York:Norton,1968:27.
[12]Ahmad,Dohra.Not Yet Beyondthe Veil—Musl im Women in American PopularLiterature[J].Social Text, 2009(99):105-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