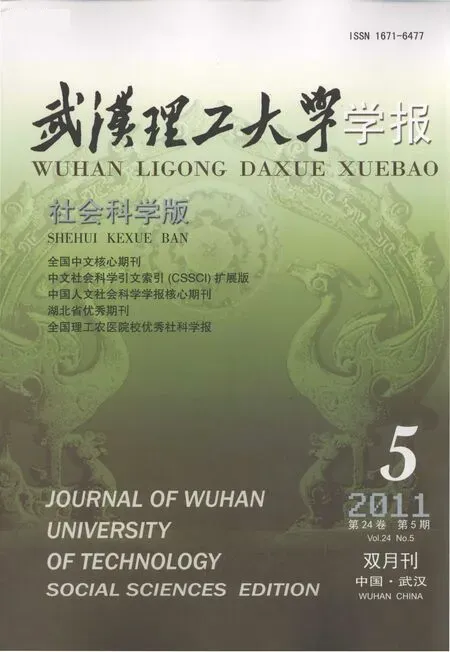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
杨爱华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74)
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大统一中间的一段分裂动荡时期。然而,这种缺乏统一中央集权的分裂状况却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在这段被有些学者誉为“小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涌现了诸如祖冲之父子、刘徽、陶宏景、贾思勰、裴秀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以及他们所留下的优秀的科技成果。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人们关于科技价值观的思考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可谓是别具一格,不同凡响。
一、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日益彰显
与先前的秦汉及后来的隋唐相比,缺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使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自由与解放。这一时期的很多科学研究活动并不是在中央集权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为实现某一具体目标有组织地展开的,而是科学家从个人的兴趣出发,注重享受穷根究源和理论探讨的乐趣,自愿自觉而为之的,从而使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得到了极大的彰显。朱亚宗先生在《中国科技批评史》里写到:“中国古代在先秦时期即有墨家与名家的纯粹理论兴趣,后来虽然长期中断,但到汉魏之际又萌发一种自觉的科学主义思潮。汉魏之际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时代。哲学抽象思辩的发展,文学独立意识的自觉,书画艺术的突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已是众所周知,但是史学家们毫不例外地忽略了这一时期的一个重大思想变化:从汉末经世致用的科学价值观到魏晋科学主义价值观的转折。”[1]23冯天瑜先生也指出:“魏晋南北朝的科技却一反传统,具有一种‘非实用’趋向。刘徽的《九章算术注》是一部纯理论探讨的数学著作。它不但推证了原书各面积、体积公式的正确性,而且还在推证过程中,提出了'以盈补虚'与'出入相补'原理来贯通各公式之间的关联,从而将《九章算术》的几何知识构造成一个理论体系。祖冲之父子推证球体体积的方法以及推算圆周率的巨大成功也具有‘作纯理探讨’色彩。”[2]
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比如,祖冲之父子、刘徽、赵爽、陶宏景等等。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大都没有受到为实现既定目标的干扰,而是进行着一种自由自在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式的探讨。尤其是作为数学家的刘徽和赵爽更是从理论探讨和对科学的问根究源中获得了纯粹的科学乐趣及对科学美的享受。
刘徽的数学观包括对数学根源、数学价值以及数学方法等方面的思考。作为一个数学家,刘徽对数学的感情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和兴趣。他除了从事传统意义上的数学应用工作外,还从纯科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和探求数学的根源:“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3]220作为一个数学家,刘徽从本体论的角度去“总算术之根源”,这就表明刘徽对数学的感情远远超出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观,进入了一种为数学而数学,追求数学的纯粹自身价值的高超境界。而且,刘徽还感叹当时少有数学爱好者,他以“当今好之者寡,故世虽多通才达学,而未必能总于此耳”[3]220来表达其意。刘徽认为科学研究的动机重要的是兴趣,而不是表层的理解与掌握,因此他感叹的是“好之者”寡而不是“知之者”寡。在序言末尾,刘徽用“博物君子,详而览焉”[3]224来表明他眼中的读者应该是“博物君子”而非实用之徒。
在数学的价值问题上,刘徽认为数学美的价值要高于其实际应用价值。这一点在《九章算术注》的序言中可以得到印证:“徽以为今之史籍且略举天地之物,考论厥数,载之于志,以阐世术之美。”[3]223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徽从事数学研究的动机和目的是发现和阐述它的美妙。对科学美的追求是发掘科学终极价值的主要目标,也是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正如著名数学家彭加勒所说的:“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4]以阐世术之美直接表达了刘徽对纯粹数学美的价值追求。在《九章算术注》中,刘徽将数学的理论价值置于其实际应用价值之上:“且算在六艺,古者以宾兴贤能,教习国子。虽曰九数,其能穷纤入微,探测无方,至于以法相传,亦犹规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难为也”[3]220。刘徽在这里指出,古人赋予数学的功能是选拔与培养人才及教导贵族子弟,但是他认为数学更有穷纤入微和探索未知的功能,至于现成的算法传授与知识教育功能则是简单的和表层的。可见,刘徽注重的不是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他追求的是数学的纯粹理论价值,是一种对未知进行探索的价值满足。
在数学方法的问题上,刘徽认为数学方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许多数学问题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在理论上都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根源:“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者,知发其一端而已。”[3]220因此,他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提出数学公式或者原理,而是更加注重对数学进行理论研究,辩证地挖掘数学的内在统一性。正如钱宝琮指出的:“魏晋间大数学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释,对于抽象的数学概念与具体的解题方法给以简明的解释,在数学理论方法上有着辉煌的成就。”[5]《九章算术》里有很多定理和公式都是正确的,也一直被人们广泛使用,单纯从应用的角度而言,无需再多加补充。但是刘徽却对各种定理和公式进行修正和补充,不仅不遗余力地去证明这些定理和公式,而且还尽可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证明这些定理和公式,探讨同一公式的不同等价形式。这正因为他不是为了单纯地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进行数学研究,而是执着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动机与兴趣。
这一时期另一个著名的数学家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非常注重数学原理的证明和阐释。在赵爽之前的一些数学典籍中,包括《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许多原理都是只有结论没有证明,这些结论可以满足数学在生活和社会中的实际应用目的。但是赵爽却不遗余力地对这些结论性的定理与公式进行推导和证明。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就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勾股圆方图(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了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对数学定理和公式的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纯粹的科学兴趣,如果不具备超越实用的价值理性精神,是不可能从事这种复杂烦琐的数学证明工作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大数学家刘徽、赵爽对数学发自内心的兴趣就体现在他们不仅追求提出数学定理和公式,还乐于证明定理和公式,并且乐于探讨同一定理和公式的不同形式以及采用不同的方法证明同一定理和公式,这与其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是分不开的。
这种对纯粹理论的兴趣和追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表现在数学领域,同样也表现在医学、物理学等领域。在医学领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用“六经辨证”挖掘病因,诊断疾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王叔和把脉象归纳为20余类,归纳是科学理论方法的初步形态,他试图把脉诊从传统的经验层次上升到理论高度。杨泉的《物理论》则表明中国古代科学具有理论化的要求与意向。
二、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多是在工匠传统下产生的,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大部分是在实践生产和生活中因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价值观是以实用和功利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为主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中虽然价值理性的成分已经显现,但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仍然盛行且占据主导地位。工具理性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国家是科学技术服务的重要对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或社会存在,把国家作为自己服务的第一对象。”[6]278
这一时期农学服务的直接对象是农民和农业生产,但农业是立国之本,所以,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是为国家服务的。发展农业技术是为了让人民力田,力田则是让国家易于治理,贾思勰就持这样一种“以农为本”的立国农学观。贾思勰生活在北魏由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逐步走向经济衰落和政治腐败的时期。这使他感到恢复和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是巩固政权的前提条件,而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就是其基本途径。他肯定西汉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认为农业科学技术可以为国家“开其资财之道”[7]18,因而发展农业生产对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贾思勰注重结果而不欣赏春花的美丽:“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存足。”[7]32贾思勰欣赏的是秋实而不是悦目的春花,这与刘徽对科学美的追求和科学价值理性的享受简直是天壤之别,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他持有的是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
天文学领域,中国古代天文学以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为主要内容。观测天象的目的是认识人事、预测人间的状况,尤其是认识行政状况以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制定历法同样也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权威意志,为统治阶级服务,“古代天文历法,更是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治的科学”[6]279。历法的制定和颁发意味着代天行事,谁颁发历法,谁就可以代天行事,这就是接受天命的象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历法就是天命和皇权的象征。魏晋南北朝时期总共编制了23部新历法,这一时期的历法多产是与其体现各统治者的权威以及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实用与功利目的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还体现为一些科学著作明确提出科学讲究的实用性,主张科学应该为社会服务。西晋年间的《孙子算经》在序言中强调数学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应用性:“向之者富有余;背之者贫且寠。”[8]数学首先应该为社会政治服务,同时数学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学问。如果掌握了算理并且遵循它,就能使人富足,而违背了算理则会导致贫穷。重实用而轻理论,重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功利价值而轻科学的自身价值,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这种科技价值观深深植根于古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之中。……为了有效应付自然灾害与社会问题,人们不能不注重实际,崇尚务实,不能不淡漠难解近渴的纯粹科学理性”[1]117-118。
三、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彰显的原因及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能够孕育和产生这样一种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思潮,是与当时社会背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在政治上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在经济上因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而带来全面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文化多元化,这种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是促使价值理性精神孕育和产生的肥沃土壤。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政治背景是与之前的秦汉和后来的隋唐相比的一个明显特征,而这一特征却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发展背景有着相似之处:“希腊文明在政治上是分散的,由许多割据的小城邦组成。一个地区的城邦政府只有有限的被侵蚀的土地,能够集中的财富有限,不可能像埃及的法老那样有无孔不入的官僚机器让每一项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服从国家的利益”[9]。正是这种分散的政治格局催生了人们思想的开放与自由。此外,魏晋玄学是价值理性思潮产生的哲学背景。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但玄学与其他流派“为政治而学术”的宗旨不同,他们崇尚和遵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原则,其理论水平很高。而且玄学超越的精神境界和抽象的“辨析明理”对这一时期科学精神的培育和科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玄学“为学术而学术”精神境界孕育了刘徽等科学家“为数学而数学”的价值理性精神,玄学抽象的“辨析明理”的逻辑思潮催生了刘徽“析理以辞”的注重理论探讨的科学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价值理性思潮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纯科学思潮在世界的知名度及影响相比较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是在整个中国古代也始终只是一股涓涓细流,它常常处于脆弱的随时可能被强大的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价值观所湮没的境地。但是,它的存在却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发育和成长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推动作用。正是刘徽对科学理论的纯粹兴趣与追求,才使得他能够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对《九章算术》各种定理、公式的证明和修正这种远离实用的费时、繁琐而又抽象的理论工作。而这一时期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仍然保持着它特有的中国传统,为传统应用型科学成果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并行不悖使得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涌现科学家最多的历史时期之一。“纵观科技发展的漫长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往往以一种创新和总结交替出现的形式而向前演进。……大致说来,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先秦时期以创新为主,至秦汉时期则以总结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以创新为主,隋唐时期又以总结为主,宋元时期又以创新为主,明清时期又以总结为主”[10]。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和丰富的科技成果不仅为隋唐时期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于推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学理论的发育和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1] 朱亚宗.中国科技批评史[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2]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56.
[3] 李继闵.九章算术导读与注释[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4] 彭加勒.科学与方法[M].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
[5] 钱宝琮.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597.
[6] 席泽宗.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7] 大寨大队理论组.齐民要术选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8] 算经十书[M].钱宝琮,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63:279.
[9] 多恩.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王鸣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65.
[10] 周翰光,戴洪才.六朝科技[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