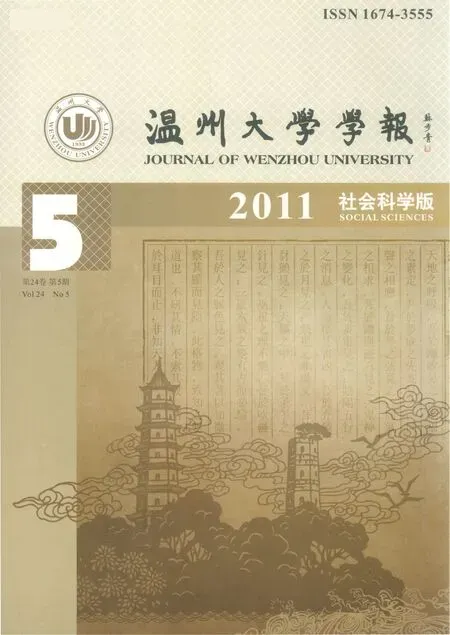“自然”而“命不可勉”——从方法论视角分析王充关于“命”的观念
王永哲,何丽君
(1.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浙江衢州 324000;2.南昌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38)
“自然”而“命不可勉”
——从方法论视角分析王充关于“命”的观念
王永哲1,何丽君2
(1.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浙江衢州 324000;2.南昌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38)
在方法论视角下,王充“命”观念表现为自然客观化的逻辑进演。“自然”是对人格意志的排除;“自然”挂靠在“气”之上而令事物有“性”、“命”之特征,因此,“性”、“命”也是“自然”;人格意志归根到底也是“自然”。故而王充认为:“命不可勉”。
王充;“自然”;自然客观化;“命”;“命不可勉”;方法论
王充的“命”观念备受后世争议,学术界对其研究也一直没有停止,并且成果不断。
在研究工作中,诸多学者都引用了王充思想中的另一观念“偶”。萧萐父、李锦全在他们所编的《中国哲学史》中概括:“人、物各自受气,或厚或薄,这是‘偶’,受气后命运终身不变谓之‘命’。”[1]王晓毅则认为:命运的必然性是无形的,而在有形的世界中,人们所能目睹的命运,无非是些偶然事件的遇合[2]。日本学者佐藤匡玄则试图把命和偶然性统一起来,他认为:“从人的立场看,社会的遭遇虽然是一个不能以因果关系来看待的偶然,可是其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内在原理的自然法理即必然,那就是命。”①参见: 文献[4].王雪通过研究王充的道家思想,提炼出“偶”和“自然”的联系:“物偶自生的内在根据是天道的自然无为,元气同样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3]韩国学者金东敏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得出结论:“人的命或气,在此自然法则中根据自然无为的活动而诞生时,必然会按给定的命运存在于人生之中。”[4]其研究对命、自然和气的统一做了一定的工作。杨萍、王全权把“命”的统一性推向深入,他们认为:“自然”就是“命”,性又是自然之载体,性的载体是气,性命有统一的趋势,王充的思想由“自”、“偶”,到统一的“命”,最终完成自身学问的一统,其逻辑进演亦在这里完成[5]。
在研究方法上,2009年之前关于王充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思想史角度出发进行的,它能使读者清晰地了解王充思想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最近的研究偏重于方法论角度,指向王充思想的内部,分析其思想形成的逻辑进演,这将有助于更加准确地了解王充的思想。从方法论的视角来审视王充的“命”观念:“命”是王充思想进演的逻辑终点,而其逻辑的发生是从自然开始的。自然是人类认识活动所指的对象,每一个认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主体进行着主观客观化和客观主观化的过程。在人类认识的历史长河中,自然一次又一次地被设置,设置之后的自然又不断地被更新。认识主体所做的努力都在于能够实现关于自然的一个更加真实的描述之目标。人们对自然的逐步认识是自然主观化的过程,自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设置起来,而人的认识活动实际上就是这个设置的展开。王充穷三十年之力设置一个不存在人格意志的自然,这样的自然的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客观化的过程。依照常识可知,自然客观化的进程是以自然主观化的结果为起点的,因而整个过程都伴随着主观的因素。王充的自然客观化过程却在于努力展示出一个不存在任何人格意志的自然。王充把这样的自然客观化过程进行到底,从而导致了“命不可勉”的囚笼。
一、“自然”是对人格意志的排除
总体看来,王充的“自然”是以道家思想作为标准的。《论衡》中的《自然》开篇就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或说天生五谷以食人,……不合自然,……试依道家论之。”[6]277。“自”除了是“本来”的意思之外,还隐含有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意思。因此“自然”在王充的思想中可以理解为“本来如此”之意。“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6]48万物的生成,是本来就存在的过程,个体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样也没有任何意志的因素,这就是“自”。人的产生过程也是如此:“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6]47人的产生甚至与夫妇都没有因果关系:“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6]47王充清楚地知道,万物以及人的生成只是一个开始,每一个体在生成之后的道路会表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但是即便如此,万物生长收藏的过程也均是“自”,即,和外物不存在因果联系。王充这样解释谷草的死亡:“世谓秋气击杀谷草,谷草不任雕杀而死。此言失实,夫物以春生夏长,秋而熟老,适自枯死,阴气适感,与之会遇。”[6]34秋风的吹拂不是谷草死亡的原因,谷草的死亡乃是谷草自身的规律。人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而逐渐形成了关于自然的观念,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人所描述出来的自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人格意志的因素。在此,王充并没有直接否定人们认识自然的努力,但他要把人格意志与所描述的自然分离开来,意在描述出一个更加真实的自然以经得起更多的推敲。一方面,对于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件,人们都在寻找因果联系。而对于自然事件,如果去寻找它的因果联系就等于是把主观意志带入了自然。这是王充所不认可的。按照徐复观的理解:“王充否定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7]仔细想来,这样的因果联系也经不起推敲:秋气的吹拂就一定是谷草死亡的原因吗?气温的下降算不算?雨水的不足算不算?这是不确定的。既然不确定,那么反过来说也能成立:秋气之所以吹拂是因为谷草的死亡。这样一来,因果就没有确定的逻辑位置了。另一方面,对于世界统一性探索的努力从人类文明开端就在进行着。不同时期的人们都在寻找这个“统一”,并且希望这个“统一”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于自然的认识的起点是对于自然的初步设置,而主观因素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主观因素正是我们所带入设置对象的本来就有的人格意志因素。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我们认识的对象中把人格意志因素排除,让认识对象独立起来,不与主观因素相关。王充的自然就是经过这样一番客观化努力的结果。相比起人格的自然,它具有了更加确定的标准。
万物的生长收藏过程是没有人格意志因素的。对于有情欲的人来说,人类寒而求暖、饥而求食和险而求安等,都是人本来就具备的特性。这个特性和万物的特性相遇,则“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6]277这种没有人格意志的状况,道家称之为无为。“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6]278万物,乃至人类,生于天地之间,却并不是天地宇宙意志作用的结果。只要是“自然”,必然“无为”。
“自然”是特征,“无为”乃是“自然”本有的特性。王充把自然和人格分离开来,造就了认识活动和认识内容相脱离的态势,而实际上,只要存在认识活动,主观意志就必然发生作用,人格意志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引入,从而对认识的结果造成影响。而且,像认识这样的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天地之性,人最为贵。”[6]22王充一方面努力避免人类认识的对象被人格意志影响,一方面又坚持以人为中心来进行价值判断。这使得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二者之间存留着一个不小的空隙,王充用“气”、“性”和“命”来填充以联系起二者。
二、“自然”因“气”、“性”和“命”而充实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如果只是说“自然”,“自然”并没有实在的内容,它只表示功能特性,这是道家的自然。王充虽然以道家继承者自居,却也对之有所批评:“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6]280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实在的物事来检验自己的观点。王充思想中的“自然”是挂靠在“气”之上的。“自然”是功能特性,并且天地宇宙都具备这一特性。而天地宇宙物类众多,“自然”虽然已经统一起天地宇宙,毕竟,“自然”无形、无象。因此,必须设置一个与“自然”须臾不相分离的概念以作为自然的挂靠,并且这一概念还必须能够统一起具体物事。这个概念就是“气”。天地是气,“天地,含气之自然也。”[6]166“万物自生,皆禀元气。”[6]349天地是含气的自然,自然地生成的万物都领受着元气。对于天地宇宙的生成顺序,以及万物的产生过程,王充只是一笔带过;但是,对于天地之气和万物之气之间的联系或者怎样联系,王充则施以浓墨重彩。王充的中心观点是:“凡天地之间气皆统于天,天文垂象于上,其气降而生万物。”[6]343统一天地宇宙的物事就是“气”。其实,天地宇宙众多的物事已经在“自然”的统摄之下,“自”(即,个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没有任何意志的因素。)就足以解释物事之间的联系。然而,把“自然”挂靠在“气”之上有助于说明天地宇宙的运动变化:“元气所在,在生不在枯。”[6]226因为“含气之类,无有不长”[6]166。气的变化的特征以及挂靠于其上的“自然”之特征,使得万物的运动变化及其各自的联系得以解释。万物各自的生成是因为各自的气而自生:“夫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矣。”[6]281气的运动形成万物的生长收藏。人也不例外,“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6]317生命之开始和终结都是元气。显然,“气”贯穿于生命之始终。概而言之,王充关于气的观点可以这样表述:气由天所统领,天的气下降而生成万物,从而万物各自具备其特性;万物的这个特性正是形成万物的气所具备的,不同物类由不同类的气形成,并且遵循该物类气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自然”。这样一来,物类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大大地冲淡甚至避免;并且对万物的生成问题,王充用“自”和“偶”就说明了:“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6]47“天的合气,物偶自生矣。”[6]48人的产生是“自”、“偶”,物的产生也是“自”、“偶”。人格意志被避免了,世界万物的联系也变得简单多了。
韦政通认为:王充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证明天人之间不相感应[8]。于是,王充在逻辑起点把天道和自然这样设置:“夫天道,自然也,无为。”[6]366从而,在论述的开端就否定了天的意志。“万物自生”、“自然”就是这个意思。王充虽然以道家的继承者自居,却认为道家的自然之说缺乏说服力。于是,王充为自然找到“气”这个挂靠,进而初步解决了天地万物的生成问题。万物由气所生成,死后又复归于气,而人可感觉到的实在的生活都在生和死之间。也就是说,万物和人的变化运作虽然是本身所禀的气之自然的运作,但是个体具体的形态、功能却是各不一致的,其遭遇也是各不相同的。在王充的思想中,这些都是“性”、“命”的范围。
因为“气”的自然之特性,令事物之间极少存在或者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而事物个体的时空又各有千秋,这些个体差异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性”:“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6]16王充没有论述性之为何物,而是主要就性的作用展开论述:“死生者,无象在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蚤死。”[6]18性的特性决定了与生命相关的气到底是渥厚还是少泊,进而决定体质的强弱和寿命的长短。和其它物类相比,“天地之性,人最为贵。”[6]22人的生命特征不仅仅表现出体质之强弱寿夭,而且人还具备着特有的思维和意识,人还有价值判断、善恶之别:“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6]24-25人性的善恶可以导而变化。在这一层次的性,乃是挂靠在人这一更加实在之物上;并且,这一层次的性与人的行为相联系。行为所在的环境正是生活的环境,生活环境能够直接影响“性”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一层次的性仍然与气有密切的联系:“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6]28至此,从逻辑上来看,上述的因果关系已经十分明了:“性”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气。王充的思想到达“性”的阶段之后,开始逐渐地引入环境的因素。在环境直接、显明的影响之下,“性”可能会发生改变。人性是如此,禽兽之性亦不无可能:“凡含血气者,教之所以异化也。”[6]27在这一层面,王充不遗余力地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直接作用。王充清楚地知道,气是不可能改变的,原初之“性”也难以改变,至于说寿夭之数,则只能任由之。但是,在生活经验之内,能被主观直接作用的这一层面的“性”,王充愿意,并且十分肯定它能够依据人作一定程度的改变。这是“自然”能被主观应用的最终层面。人的产生、万物的产生均是自然,且与天地之气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天地同样也没有意志,“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6]278没有意志的事物不存在主观能动性,不能有意识地对外物发生作用。但是,这样的事物相对于它的外物确实是在运动变化的,那么运动变化的原因只能来自内部。“自然”之含义正在于此。而且,人有意志这一事实,也是实在的“自然”。虽然物的产生不是为人服务的,但是人的需求却必然促使人对于物的作用。如果说,天地之“自然”不干人事的话,那么人有意志、并能在意志的指导之下有所作为这一“自然”则导致天、地和人的相遇。更甚者,这一“自然”能够改变其作用的对象,同时也不断地改变着自身。在自然客观化过程的这一阶段,王充的思想是最为生动的,其中交融着意志和自然的关系、意志能动地对自然发生作用的论述。但是,在论述的开端,王充却是拿“自然”来反对意志的。意识到意志的扩张很有可能颠覆其逻辑起点,王充的逻辑十分严谨。并且从事实上来看,对于天地宇宙来说,人能够改变的事实实在少得可怜。而且,关于意志的作用,王充的时代还存在着许多的伪文和妄言。无论东方文明或者西方文明,自其产生之初就在为寻找世界的本源而努力,这样的努力伴随着相应的信念:世界是统一的。所以问题就集中在“世界统一在什么上?”。王充的努力也在于此。自然挂靠在气上,则世界统一的支架已经建立起来,而真正努力的内容则是如何用这个支架来解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自生”、“自然”已经解释了一些事情。“教而导之”显然是意志,而“自然”却是极少意志的。或者也可以把意志纳入自然的范围,则“自然”就极可能失去其本意。就意志而言,个人的意志是千差万别并且冲突不断的。从整体来看,个人意志的作用则几乎可以忽略。只要个体的作用可以忽略,意志作为“自然”而存在就是安全的,而且绝无冲击整个自然之可能。这是自然客观化之可能的关键,并且大有希望彻底贯彻。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都得面对现实,而且是无奈地面对。个人的意志虽然能够起一定的作用于“性”,却只能是更具规模的“自然”的组成因素。在王充的观念中,这更具规模的“自然”就是“命”。“用气成性,性成命定。”[6]21和“性”一样,“命”也伴随着气。“命则性也。”[6]18命与性是同时为人所具备的:“命,谓初所禀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则受命矣。”[6]41王充的“命”的观念是自然客观化的必然结论,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说:“自然定律并没有颁布什么将发生,而是告诉我们,什么已经和惯于发生。”[9]21他进一步强调:自然定律只不过提供事物将在其中继续存在的某种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中的无限多的可能性的哪一个将变成实在,人的能力从来也无法绝对地决定[9]34。之所以无法决定乃是因为“自然”。即便是人的主观努力,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格意志范畴内的主观能动性为人所特有,并且,人也能够决定一些因素,比如说操行、技艺;但是,人们所处的环境及其变化是自然的,构成环境的诸因素也是自然的。因为诸因素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所以操行之贤与仕宦之遇均是“自”,而且“遇”或者“不遇”是独立进行的:“故遇,或抱污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6]1
三、“自然”而“命不可勉”
“气”、“性”和“命”三者之间,“性”、“命”均是形而上的,必须在形而下的“气”上才能展现出来,“气”是“性”和“命”的挂靠。“性”是空间维度的特点,“命”是时间维度的遭遇,“性”、“命”的相遇则形成时空,即宇宙,宇宙就是自然。一般观念的宇宙由具体的事件和事物构成,王充认为具体的事件、事物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性和命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冯友兰说:“行善者不必有福,为恶者不必有祸。人受祸受福,全视其遭遇有幸有不幸。王充若只就此点论则与其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相合,于事实亦相符。”[10]但是,王充要把自然“贯彻到底”,自然客观化的过程是要努力展现“自”的过程。而人的意志因素所占的比例,对于其生存的环境来说,实在渺小得可怜;更何况,人的意志也在“自然”的范围之内。从历史记载的事件,以及遭遇这些事件的人和物可以看出,这些有意志的人在事件中几乎没有可能彰显出其个体的意志。这样一来,如此众多的历史材料又成为了王充思想中“自然”的挂靠,并且帮助王充完成其自然客观化的逻辑过程。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律没有意志的成分,人们虽然十分渴望知道什么将要发生,所做的工作却只能是解释已经发生的。在王充的思想中,具体是偶然的,无数的偶然就形成了“自然”,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自然、社会之整体由个体共同构成,单个个体意志能决定的范围十分微小。个体与个体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自然”,又正是这些“自然”构成了社会整体的“自然”;而且,包括这构成社会整体的“自然”的过程,也是“自然”。“自然”之特性就是“自”,那么每一个体之“自然”过程是独立进行的,并且独立进行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仍然是“自然”,其中也绝无意志起作用的空间。人生的遭遇也不例外:“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生死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6]8人生的遭遇由命,命也是“自然”,王充提到了三种不同的命:正命——谓本禀之得吉也,故不假操行以求福吉自至;随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遭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6]19。顺着王充的思想推论可得:即使福吉、凶祸也均是“自”,是自然进行的。正如《论衡·偶会》所说:“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它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6]33这就是王充自然客观化的结果——“命”。
自然客观化到这个阶段,天地万物就都在“自然”之范围中了,凡事、凡事之阶段,均是自然,且各无因果联系。人想要做些改变的意志也是在自然之中,是自然而行,绝不会产生与之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结果。那么,结果就只能是——“命不可勉”。
四、结 语
“王充的逻辑思想体系是一个论证的逻辑思想体系。”[11]239并且“王充对论证的要求的论述,与形式逻辑提出的论证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11]235通过方法论的视角,进入王充思想的内部,我们能发现王充思想严谨的逻辑。正是因为严谨的逻辑论证,王充才在逐步取消人格神的存在的过程中又走入不可把握的“命”:不存在人格神就是自然,自然的彻底客观化而导致绝对的“偶”,“偶”不可把握,这就是“命”,“偶”却又成了必然。在方法论的层面,王充的“命”观念实际上展示着由形式逻辑而发展为辩证逻辑的论证过程。
王充的认识论将自然清晰化的过程是在认识主体的主观中进行的,其入路是自然客观化:一方面是主观的活动,一方面要把人格意志排除在自然之外。王充的自然客观化在逻辑的开端就纠缠在不可回避的矛盾之中。随着认识之过程的推进,这一矛盾在方法论的层面上逐渐展开,必然会陷入各种各样的不可自拔,“命不可勉”只是其中的一个归宿。
[1] 肖萐父, 李锦全. 中国哲学史: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344.
[2] 王晓毅. 王充命理学体系[J]. 孔子研究, 2001, (6): 47-53.
[3] 王雪. 王充道家思想探析[J]. 安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4): 36-40.
[4] 金东敏. 关于王充命定论的二重结构(制度)的考察[J]. 当代韩国, 2004, (春季号): 18-23.
[5] 杨萍, 王全权. 王充天体论、人性论和性命轮中的伦理思想探析[J]. 淮海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3): 40-42.
[6] [东汉]王充. 论衡[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7]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 第二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58.
[8] 韦政通. 中国思想史: 上册[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4: 365.
[9] [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 自然哲学概论[M]. 李醒民,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下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72.
[11] 周云之. 中国逻辑史[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Fate Cannot Be Compelled” Because of “Originally So”——Analyzing Wang Chong’s Notion of “Fate” from Methodological Angle
WANG Yongzhe1, HE Lijun2
(1.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Qu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Quzhou, China 324000; 2. Institute of Culture, Nanch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chang, China 330038)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angle, Wang Chong’s notion of “fate” embodies in the logical deducing of objectification of nature. “Originally so” does not be influenced by human’s will. As a specific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expression of “primordial qi”, “originally so” grants things with their typical “property” and“fate”. From this point, “property” and “fate” could be regarded as “original so”. Then, human’s will could also be come down to “original so”. For these reasons, Wang Chong held a notion that “fate cannot be compelled”.
Wang Chong; “Originally So”; Objectification of Nature; “Fate”; “Fate Cannot Be Compelled”; Methodology
(编辑:朱青海)
B234.8
A
1674-3555(2011)05-0071-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5.010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9-10
王永哲(1976- ),男,湖南永兴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