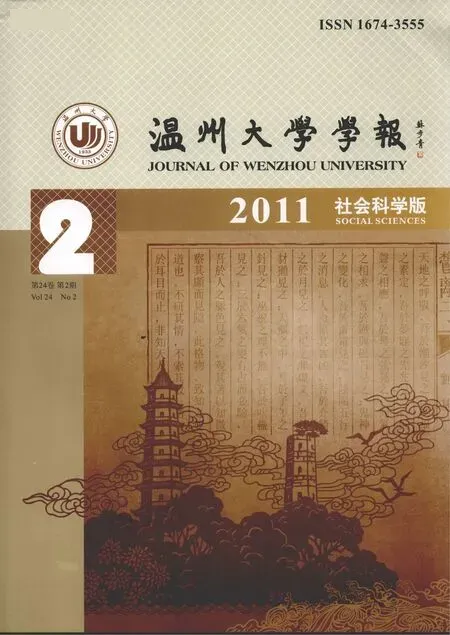沧桑往事的文化省察—— 论“老作家”写在“新时期”的反思散文
徐阿兵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158)
沧桑往事的文化省察
—— 论“老作家”写在“新时期”的反思散文
徐阿兵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158)
一批“老作家”在“新时期”陆续发表的反思散文,不仅体现出明确的文化承担意识,而且在对文化的反思和比较中抒写了丰富的伤痛和欣喜之情。他们对沧桑往事的文化省察,彰显了散文诚与真的诗学品格,本身也应当成为可贵的文化遗产。
新时期;老作家;散文;文化反思;诗学品格
“新时期”以来,回忆和叙述既往苦难的作品陆续面世,蔚为壮观。现行的文学史著作,通常将此描述为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发展过程,并将小说作为论述的重心,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①参见: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还有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②参见: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实际上,散文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逊于小说。“多年没有过的轻松感、解放感、喜悦感与悲愤感交织于散文作家心头,使这一时期散文大都有一种悲怆而昂扬的基调,有一种与整个‘伤痕文学’一致的震撼力。”[1]当作家们尽情地抒写心头感慨时,“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也就在对自身命运的省察中复苏并建构起来”[2],并将作家们导向对于个人之外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问题的深思。尤其在巴金、季羡林、杨绛、陈白尘和韦君宜等“老作家”那里,回归正轨的生活状态,不仅润泽了他们沉滞多年的笔头,也激活了他们沉积已久的记忆与思考,促成了一种颇具反思力度的散文的诞生。
一、老作家的文化承担意识
“文革”刚刚结束,年逾七十的巴金立即不辞劳苦地投入写作,其持续不断的劳动成果后来汇编成《随想录》③巴金. 随想录[C].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自同一版本, 不再一一作注.。伴随着思绪的铺展和思考的深入,巴金的创作意图也越来越明确:“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萦绕于心的苦难和耻辱感,使得本当安度晚年的老人无法心安理得。凭借着生命不息、追问不止的强烈意志,巴金焕发出了一股新鲜的生命力,“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满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文艺事业的信心”。
大致说来,《随想录》的内容及其预想读者可以粗分为三类:第一,悼亡和怀友之作,为亲友而写;第二,谈论文艺作品以及相关问题,明确地写给“读者”;第三,论及文化现象和社会时闻,借以警醒“人民”和“子孙后代”。三部分内容的交叉点,则是揭示和反思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及祸害。这种交叉的紧密程度,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巴金反复强调,“文革”“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作为灾难的见证者,“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写下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在《纪念》和《“文革”博物馆》等篇目中,他还郑重地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尽管巴金的设想迄今未得实现,但我们不妨说,《随想录》本身就已经是一座由苦难和文字筑就的丰碑,那上面镌刻着一位老作家的热情和良知,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与巴金相似,季羡林也明确地将使命感、责任感标示为自己的创作动机,但他更加强调一种忧虑感:“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①参见: 季羡林. 牛棚杂忆[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于自同一版本, 不再一一作注.周围年轻人的健忘(其实又何止年轻人,应该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健忘),更让他觉得“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但是“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所以,当《牛棚杂忆》“终于出版问世”以后,季羡林有理由认为,“我总算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韦君宜则在其《思痛录》中以老病之躯剖示了心路历程。从奔赴延安到迎接解放,从日常事务到编辑工作,她始终难以释怀的,首先就是自己的盲从:“我并不愿意做却还是做了。这可以算作盲从,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②参见: 韦君宜. 思痛录: 露沙的路[C]. 修订版.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自同一版本,不再一一作注.。以反省这种盲从为中心,韦君宜对“斗争哲学”和“幼稚病”的回溯、对规模不一的历次“运动”的比较,尤其是对“红卫兵-知青”一代的身份转变及其复杂意味的探究,无不让人感受到清醒而焦灼的文化忧虑意识。
季羡林曾经谈到,他一直抱着两个期待,希望有人能把自己“文革”中曾受的灾难或者对他人施行的折磨写出来,直至期待落空、自己写成《牛棚杂忆》,仍未放弃那两个期待。他相信,惟有“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才能“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而从《干校六记》起,不论笔涉闲暇还是劳作、离别或者病痛,杨绛都尽力隐去一己之喜怒哀乐。至《将饮茶》③参见: 杨绛. 将饮茶[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下文论及该作品均出自同一版本, 不再一一作注.,她更加努力地隐去作者的影子,也更加明确地以说真话为追求,倾向于以个人的智慧和识见在生活中求得安宁,哪怕是卑微和平凡的安宁。杨绛当然不希图借“隐身衣”使自己无忧无虑,她所向往的是,“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国王的新衣好”。其中对假、大、空的针砭和警戒之意,已十分显豁。实际上,这也正是一批老作家不约而同的努力方向,他们试图复活一个古老的信念:“修辞立其诚”。这种“讲真话”带来的“自我意识强化”,“展示了主体精神的特殊性、丰富性,使散文回复到散文自身,并以此构成新时期散文重要的美学特质。”[3]
二、文化反思中的伤痛与欣喜
由上可见,这些老作家们具有一种大致相近的苦难意识。过去所见证和遭遇的苦难,不仅让他们依然深有痛感,更使他们心存警惕,因而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立此存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腔忧虑。他们希望当下总结的经验、教训能够有助于避免乃至杜绝类似的灾难再次上演。他们的创作意图,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观古明今”、“鉴往知来”庶几相似。但他们并未拘囿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传统信条,而是时刻以切实行动去“穷本究源”。
陈白尘完成《云梦断忆》,正值“伤痕文学”风行一时,各类质疑也从未歇止。他的回应是:“伤痕文学不是不该写,而是写得不够:我们还没有反映十年动乱的深刻而伟大的作品出现!不把造成十年动乱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深挖出来,我们这社会主义社会要前进,四个现代化要实现,那是缘木求鱼!所以伤痕文学是应该存在的,但不应该加上引号。”[4]108-109他承认“断忆”诸篇触及了往日的伤口,又说:“我决没有在那些旧伤口上抹盐,倒是企图涂上些止血剂的。是否做到,自不敢必。而且重读时颇感文笔有些油滑之处,是极不该的。希望读者不要当它‘一笑散’。”[4]109其所谓“油滑之处”,常常是伤痛已极之时,不禁就语带讥诮,一抒心头的自伤自嘲自哀自怜。他肯定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在抚摸伤口时很难做到不动声色、无动于衷。而一旦“有动于衷”,必将导致辞气浮露、甚或消减话题的严肃性,这都是对“读者”极不负责的表现。因而他对自己所做的检讨和批评,首先正是一种自我定位和自我评价:“断忆”只是一组历史素材,其使命在于为往事存真;其次更是一种呼唤和期盼:希望以“断忆”为“砖”,引出他人之“玉”。
季羡林的反思由十载“牛棚”的经历所激发,但并不限于那十年。他如是总结自己的“思想转变的过程”:首先,是“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然后就自觉地在思想改造中深挖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感”,直至后来确立党派信仰以至于“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季羡林揭示出“改造”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巨大影响,其中不仅有无可奈何的幻灭:“可怜我们虔诚地学习了十几年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头来成了泡影。”也有始料不及的突变:“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我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更可怕的却是从“人”到“鬼”的沦落与麻木:“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糊起来。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回顾以往的灾难和痛苦,季羡林无法省略那场灾难为什么能发生这一问题,但他的答复是:“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倘若定要在他笔下找寻上述问题的答案,那么首先必须提及文化恶根的遗毒。比如在写到“牛棚”中“晚间训话”时,他就自然而然地由当前的“抓小辫”和“思想汇报”想到了历史上的刀笔师爷和封建皇帝。其次,季羡林发现,在持续不断的运动和斗争中诞生了一种叫做“派性”的“新的‘物质’”,它“一经产生,便表现出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谁要是中了它的毒,则朋友割席,夫妻反目”。其中对文化恶根的历史警惕和当下关注,堪称敏锐而痛切。
巴金虽然身为这些作家中年事最高者,但却是最为勤勉和多产者之一。巴金以其风烛残年的余力,不可思议地聚拢了一束火把般的光亮,艰难前行。他苦苦思索着“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之类问题,最终醒悟到,“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尤为可贵的是,巴金并没有将“封建主义”一股脑儿全推给那些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然后就此作罢。他清醒地认识到,“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决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在巴金看来,“文革”之得以发生和推进,实在与“封建主义”的流毒有着直接关联。流毒肆虐之下,人们的思想日见混乱,不是变为神,就是变为兽与奴。巴金用全部的经历和心血为人们指明了一条坚实的路:“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也为自己留下简洁的座右铭:“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不过,这些作家在灾难的废墟上所捡拾到的,并不全是伤痛和教训的残砖断瓦,其中还有令人欣喜的吉光片羽。对季羡林来说,那些“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将会使他“三生难忘”。在巴金看来,“文革”中固然多有苦难,但也有“难友”的互相慰藉让人难以忘怀:“它应该是爱,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积极的东西罢。许多许多人活下来坚持下去,就是靠了这个。许多许多人没有活到今天,但是他们把爱、把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而且通过我们留给后代”。显然,并非来自他人的某一次举动使他们共同倾心赏识,而是那些举动中闪现出来的价值和美德,让饱受苦难的他们共同感受到了希望和信念。“这些价值和美德的结合造就了我们的生活范型,通过这些范型我们的自由得到发展和实施,这被称为我们的‘文化’。”[5]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作家们为价值和美德的流失而深感痛心,为其在逆境中的闪光而暗自欣喜,正是一种着眼于社会发展和价值传承的文化关怀。
在《云梦断忆》里,陈白尘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人情的温热与光亮,这些不可“异化”的因素是作者的注目之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忆眸子》①陈白尘. 忆眸子[C] // 陈白尘. 对人世的告别.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588-593. 下引该书, 均出自同一版本,不再一一作注.。作者从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写起,以人们看自己的眼神来描写人们的心灵。涉及人物不少,但让作者记忆犹新的首先是小姑娘。她三岁时还天真地喊“我”为“爷爷”,两年后就十分“懂事”、十分义正词严地呼“我”为“大黑帮”了。这使作者比挨了批斗还痛苦。另有小男孩,大约也只三四岁,他没有“敌情观念”,表演歌舞和游戏,以期“我”有所反应。然而“我”只能在他离开后才后悔不已,自己竟然“不敢鼓掌一下回报他的美意。”历经十余年磨难,作者没有为自己患得患失,却仍在为那两个小孩而左右思量:他既担心“在他们幼稚心灵上所刻下的仇恨或同情,是否还起作用?”又表示“希望从那小姑娘和胖娃娃一辈的青年们明澈如水的眸子中透视到我们新中国的未来”。这种忧虑和期望相交杂、难分彼此的情形,或许可借“断忆”首篇得到解释。作者写道:“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可歌可泣、可恼可恨的事自然很多。但回忆总是蒙上层彩色玻璃似的,因而也是如云如梦,总觉美丽的。因此,即使可恼的事吧,也希望从中找出些可喜的东西来。”从“可恼的事”中“找出些可喜的东西来”,这与作者在提及的为旧伤口“涂上些止血剂”的“企图”如出一辙。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吗?绝对不是。如果将整部《云梦断忆》视为一个敏感而又执着的知识分子在文化萧条时代的心灵片断,那么它所记录的正是人在逆境中的失落与希冀。那些“可恼可恨”中分明饱含着作者的文化忧思,而“可歌可泣”、“可喜的东西”中则寄托着百折不挠的信心与期望。
三、文化比较的得与失
从文化上探寻灾难根源、关注灾难后果的同时,有些作家出于专业习惯和学养的引导,有意无意间拓开了文化比较的视野。杨绛的《将饮茶》即明显表现出对异域文化资源的参照,字里行间贯注了一份独特的自信心。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她记述了从自己被“揪出来”以至一切都“颠倒过来”的情形,但并不咬牙切齿,反而是力求平和、甚至是略带感激地援笔写来。正是在西方成语的启示下,她别出心裁地为这一段经历添上一个“乌云与金边”作为副标题:
按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孳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应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
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作者写亲身经受的“摧残和折磨”、“同情和友情”,都平实可感,绝无夸大渲染之辞。但在平实的话语中藏纳抗争的韧劲和复活的热情,却非常人所能企及。这既需要对既往人事的睿智洞察为基础,更不可缺少从文化比较中提取的同质因素作为信念。因此,杨绛的写作意义主要不在于复现某些史实,而在于提供一种“文化地”看取苦难、超越苦难从而蔑视苦难的方式和可能。
季羡林学问广博,尤精于“东方学”。他在《牛棚杂忆》中自谓,“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先是盛赞了一番东方人民的智慧和幻想力造就了东方文明,转而写道:
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然后又辅以许多的细节比较。这无疑从文化的角度揭示出灾难的严重性:想象力一旦误入邪恶的歧途,非但不会给文明增添任何成果,反而只会留下巨大的痛苦和阴影。至于描述“文革”中的两派斗争,则纵谈英国两党的“费厄扑赖”、法国大革命中领导人的头衔、美国总统竞选时的欢呼和辩论;他显然希望通过文化比较而让人们看清派系斗争的不可思议。
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为中国文化所做的预言。在“附录”部分,季羡林用他的心灵之镜,照见了 20世纪的八十多年历程。以其学识之广博和精深,他当然是最有资格做出客观评价的人。然而,刚刚为20世纪慨叹了一句“天凉好个冬”之后,他立即转而写道:“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从之前不无悲凉的慨叹到眼下信心百倍的预测,这一跨越的幅度之大,简直让人难以理解。在此前后,季羡林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言论和文章,力倡“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西方不亮东方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①有关文章参见: 季羡林.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C].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此处且不论季羡林所归纳的东西方文明相互兴替的“规律”是否会如其所愿地延续下去,也不去追究他所描述的弊端几乎都能在今日中国大地上找到程度最甚的例子,单说他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述,其中就显然省略了对传统文化负性面的检讨。今天再读《牛棚杂忆》,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既然传统文化的恶根有可能在“文革”中结出恶果,那么“文革”的恶果是否可能在此后绽放出“恶之花”呢?对此,我们需要警惕。
四、结 语
本文所论及的几位老作家的反思散文创作,总其所有,仍然未能从文化的特性、根源和发展、变异的角度完成对既往苦难的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当然,这一任务是艰巨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有望完成;将之强加于几位幸存的老人身上,无疑是一种苛求。在最直观的意义上,他们的这类反思散文,恰似聚集在一起的镜子,以良知和智慧之光,共同照见了历史的幽暗与崎岖、文化的丰富与复杂。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们不仅以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彰显了散文创作中诚与真的诗学品格,而且,他们对沧桑往事的文化省察,本身也是一种可贵的文化遗产。
[1] 曹家治. 作家精神自由与新时期散文创作[J]. 当代文坛, 1989, (2): 2-6.
[2] 李文莲. 论新时期散文中自我意识的苏醒与重建[J]. 山东社会科学, 2010, (4): 79-83.
[3] 孙安菊. 新时期十年的散文及审美追求[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7, (3): 40-46.
[4] 陈白尘. 后记[C] // 陈白尘. 云梦断忆.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83.
[5] 乔治·麦克林. 传统与超越[M]. 干春松. 杨凤岗,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11.
Cultural Introspection on Hard Episodes in the Past—— Study on Proses of Introspection by “Old Writers” in “New Era”
XU Abi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350108)
Prose of introspection contributed by “old writers” in “new era” (1976–) not only embodied the unambiguous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but also expressed great sufferings and rejoicing through the introspection on and comparison of culture. Their cultural introspection on the hard episodes in the past marks “honesty” and “authenticity”, the poetic characters of prose, and merits the title of valuable cultural legacy.
New Era; Old Writer; Prose; Cultural Introspection; Poetic Character
(编辑:刘慧青)
I206.7
A
1674-3555(2011)02-0062-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2.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6-25
2010年福建省教育厅B类社会科学项目(JBS10042)
徐阿兵(1981- ),男,江西瑞昌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