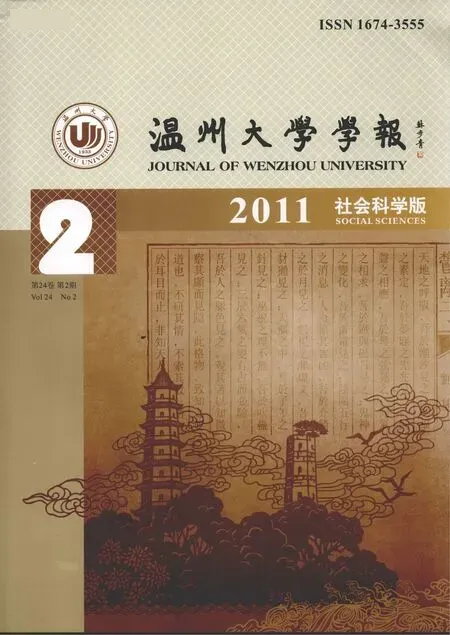暧昧的传统节日保护
韩 雷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暧昧的传统节日保护
韩 雷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传统节日保护已成为当下中国民俗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保护却很少正视其中的信仰问题,对民间信仰欲言又止。传统节日保护蜕化成怀旧的冲动;传统节日中的身体性被遮蔽,以致我们的传统节日保护走向暧昧的境界。唯有正视传统节日中的民间信仰和身体维度,宽容理解民众的信仰,彻底激活传统节日活动中的身体感,中国的传统节日保护才是真保护。基于民间信仰的视域我们重新审视了温州的拦街福。
传统节日;民间信仰;暧昧;身体感
温州拦街福始于清代同治年间。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在1956年举办过一次拦街福,后因被批判定性为迷信活动而辍止。2002年4月,拦街福被恢复。拦街福是温州民众春季拦街祈福的传统习俗。诚如刘魁立先生所说,“大家在一段时间里,一条街一条街地举行祭祀性活动,既是各家各户的祈愿,也是对外的展示和祝福。我以为这是我们本地的乡亲在二月初一(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朔日),面对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不测所作出的主动反应。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在自然界或者社会生活中,或许会有天灾人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免要向大自然打招呼,向大自然表示我们的一种祈愿。当然,这同时也会把自己的精神力量激励出来、动员起来。”[1]作为传统春节后续性的节日,拦街福给温州民众搭建了一个娱乐兼商贸活动的平台。当下温州市政府和民间都在积极恢复乃至保护拦街福,其祈神禳灾的民间信仰内容属于被保护之列吗?“节日文化所以能够一代代地传承和延续下来,除了世俗性的内容(如随季节转换和农事更替而出现的休息休整、娱乐、穿新衣、吃美食等)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它具有某些神秘性和神圣性(如对天地、神灵的崇敬;对先祖的追怀与祭拜,亦即对传统的认同)。”刘锡诚先生进而指出,“这一点,在最近以来对节日文化研究中,似乎被忽略了。”[1]
媒介上的传统节日保卫战尚未熄火,就有专家学者在为中国传统春节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未雨绸缪。不管是保卫战还是“申遗”预演,相关领域的学者都在潜意识里或无奈地回避民间信仰的问题。这种来自学术共同体的暧昧并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具体言之,我们的传统节日保卫战要保卫什么?是传统节日的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诚然物质和精神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既没有完全摆脱物质的精神,也没有撇净精神的物质。传统节日的物质层面与过去相比可谓丰盈多了。传统节日的精神层面却因仪式的除魅而失去昔日魅力;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传统节日中的民间信仰与主流意识形态很难兼容并存,以致我们的传统节日保卫战陷入不尴不尬之境地。因此,中国的传统节日保护滑向暧昧境界就在意料之中了。我们对温州拦街福的恢复与保护也难以摆脱类似的意识形态难题。
一、暧昧的怀旧冲动
作为营造“时空以外的时空(time out of time)”的传统节日,在当下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了使民众的日常生活实现某种变轨,有限地脱离惯常的单调、贫乏等,为下一阶段的生活“充电加油”。说到底,就是在物质和精神都贫乏时让民众丰富一下,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和精神欲求;在当下物质上的满足不再是问题时制造些娱乐或狂欢,做一些跟日常生活不同的事情,刺激早已被大众文化轮番轰炸的神经末梢。但是,这一切都在消费逻辑主宰的生活世界里发生了位移,传统节日即使不是被乾坤大挪移,也是为经济粉墨后登场,变成以GDP为主导的市场晴雨表,跟民众的娱乐变轨只能眉来眼去。因此,传统节日活动中的身体行为被置换为消费的符码,节日期间的旅游蜕变成变相的购物,民间艺术展演和游戏也因赤裸裸的功利性而被过滤成单一色调,没有了民间生命力的悸动和野性。传统节日活动中的行为不只是被置换,还被改造成一种可以连续消费的符码。传统节日的身体性无疑建构着我们的节日体验和情感记忆,这是其他媒介永远无法替代的。传统节日被赋予过度消费的潜能,但消费并不能打包传统节日的所有功能。如果以经济效益作为节日保护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那么,这样的保护注定是暧昧的,跟真正的节日保护几乎没有关系。
近年来因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一些地方政府就自然想到了跟节日有关的“黄金周”。2008年国家假日办改革方案刚刚颁布实施一年,不料这些地方政府很快就要推倒重来,取消或变更原本分配到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假期,继续推行过去“五一”放假一周的制度。这种朝令夕改的行为招来不少媒体的批评和讨论。传统节日曾经的辉煌不再,原本与之相关的小农经济已经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虽有幸成为国家法定节日,但相比较而言,传统节日在拉动内需上却赶不上“五一”劳动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宣示我们对传统节日的怀旧是暧昧的,传统节日沦为经济的大功率发动机,虽能为GDP攀升锦上添花,于赓续传统文化之精髓却未能雪中送炭。恢复黄金周的利益冲动无疑给一厢情愿的传统节日保护带来了诸多质疑。如果我们不能坦诚地正视传统节日本身以及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命运走势,我们的所做所为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跟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传统节日在当下渐趋边缘化是可以理解的,传统节日的元素有的已经融入到其他新兴文化中去了;我们之所以强调传统节日之于现代生活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不想失去自己的文化之根和身体记忆——时时回首审视考量传统节日,会给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带来灵感和活力,也满足了人类的怀旧情结。
二、欲言又止的民间信仰保护
中国目前的传统节日保护,其暧昧之处就在于:我们虽呼吁保护的重要性,并从历史文献中找证据,但从来不敢光明正大地讨论民间信仰保护,最多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跟传统节日中的民间信仰和主流意识形态打情骂俏,同时也在撩拨民众的怀旧情感。传统节日的主要内容都跟信仰或者说民间信仰有关,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时空以外的时空”。中国的非制度化宗教是非常发达的,它们在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当代情境下更是如此。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与文化研究系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长期调查研究中国民间信仰,他认为,“民间信仰不能说是一种宗教,而是把来自各方面的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指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老百姓和三大宗教的传统都有关联,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习俗。任何乡村都有三个教,还有第四个教——巫教,我也叫无名之教。这些民间信仰和佛儒道巫多少有点关系。民间信仰还要把对空间、时间的理解加上。”[2]在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遭遇重创之前,民间信仰对中国传统家庭的影响随处可见[3]。走进中国传统民居,迎面而来的是贴在门上的彩印或手绘的门神,门神的作用是保护家宅和家庭成员,避邪驱鬼。挨着门的地方摆放着土地爷的供桌,土地爷保护全家平平安安,并且监视着家庭成员恪守宗教道德和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天官则供在院子里。给家庭带来财产和富裕的财神通常置于厅堂或正房里。不可不提的是灶王爷,灶王爷总供在做饭的炉子上面或旁边,他在年末要向天上的最高神——玉皇大帝报告该家庭及其成员一年的行为举止,以决定这个家庭应该得到奖赏还是受到惩罚。在那些对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家庭里,还供奉观音菩萨或其他神像,以保佑家庭幸福。在危机来临或遇重大事件,如出生、婚丧或传统节日时,人们在家里供奉众神的神龛,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每当此时,神圣、崇敬的氛围就会弥漫在家庭生活的各个角落,于是家庭就成了宗教活动的场所[3]。
其实,民间信仰就是民众超越苦难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信仰具有韦伯所说的超越性[4]。任何文化都有超越性。中国的祖先崇拜是在起源处设定超越性,即祖先是我们的榜样和目标,他们的事功值得我们效仿,他们的灵魂也会在另一世界护佑着子孙后代。与中国祖先崇拜不同,西方的上帝是在人类(凡人)之外设定超越性的,他既跟任何人都有关系,又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所以他能为人类牺牲,能做到公正无私,能解脱人类的苦难。相比之下,中国民间信仰的超越性有一定限度,仅仅是为了功利性的实用,但尚未发展到实用主义哲学的思辨层面。中国民众的超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而且生活世界中的超越性是有等级的。民间信仰天然的合法性就奠基于这种有差别的超越性之上。合法性就是超越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对普遍性的认定,如一些信仰就不是一个人的信仰,具有超越个体的特质。民俗研究就是对民众的生活进行研究,民俗研究的现代性包含民俗研究和民俗学研究两个层面。自然整体的神圣化对生态环境乃至传统节日的保护,可能比政治法律层面的保护更为有效。政府或者说官方行为如何规范诱导这一神圣化过程,同时又不跟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这是相关学者首先要研究的课题。成功有效的传统节日保护应该跳出单一思维或单一学科的局限,综合运用民间信仰方面的知识积累。换句话说,民众如何完成这一神圣化过程?在诸神退位的时代,欲重返神圣现场要遇到的抵抗和诱惑委实太多了。在笔者看来,从相对的各自言说到主体间能进行交流的神圣化过程,日常生活应该是一个神圣化的绝佳突破口。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拦街福不但为温州民众营造了一个神圣的时空,也为其建构了一个融商贸、饮食、民间游艺等于一体的世俗展演平台。
如果民间信仰研究能呈现事实,乃至呈现其背后的道德,即天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能自然大方地出场,不必为了寻求合法的生存空间而再改名租外壳,民间信仰以民俗宗教的名义被纳入国家的宗教政策体系,一些相关的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按照笔者的理解,对日常生活世界神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超越,虽然这种超越没有基督教或佛教那么彻底,但这种超越更具人情味和烟火气。理性是一种解析的力量。当理性不再以直观(哪怕是个体保存本能的直观)的形式看待事物,而是从直观物质的本体内部实质看待事物时,理性则是一种具有溶解性的力量,其作用与溶剂相似。理性能够理顺感觉到的概念,而这些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建构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当它的解析力对这些概念实施分析和溶解的时候,它就使我们陷入一个表象的世界,一个不坚固的影像世界。信仰通过非理性突破这一坚固的理性世界。我们周围世界被理性凝固着,一切凝固的都将烟消云散,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幻象,世界很快又被另一种理性所占领。没有信仰我们一无所有。如是,我们只能生活在完美的虚幻或者虚幻的完美之中。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种虚幻感。
中国传统节日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即使社会发生过很大的动乱,只要民间信仰所营造的神圣空间没有被破坏殆尽,传统节日的味道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辛亥革命以降,包括“五四”在内对传统中国的节日文化曾人为地加以改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传统节日之味依然那么令人怀念,人们的观念不管怎么革新,诚如鲁迅这样新文化的旗手还是照样过旧历新年。据鲁迅日记记载,在这一天为了不违背官方规定或者显示出自己对旧的东西的决绝之态度,于旧历新年去上班,但回到家之后依然祭祀祖先,陪儿子海婴去饭馆吃饺子[5]。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变动的转型期,外来文化纷至沓来,原本脆弱的传统文化包括节日文化中的信仰等,在历尽“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已分崩离析,风光不再,追逐新鲜时髦的文化消费暂时收编了传统文化。我们传统节日文化之味愈来愈淡了,以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都发生了危机,谭嗣同所梦想的大同世界好像就在我们身边,文化已经全球化。当代中国有识之士心怀忧虑,不仅在各种媒体上大声呼吁保护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而且欲借“申遗”的东风,使政府在切实保护的实践层面上有所作为。
但是我们在加入这样忧心忡忡的大合唱之前有没有深思过,我们当下为什么对传统节日感觉到其味道愈来愈淡了,其原初的生鲜感在渐趋麻木的舌尖消失殆尽?我们的传统节日保卫战到底要保卫什么?这些问题不想明白,我们的问题可能只是伪问题,我们的保护也是伪保护;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助推传统节日文化的衰落。因为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些东西无可避免地消逝了,即使你抢救式地加以保护也是枉然;有些东西只要人类在生活世界中还需要,即使没有主观上刻意的保护,任其发展,它们也不会真正离我们而去。
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重新审视拦街福之于温州民众的意义。拦街福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无疑包含了很多民间信仰方面的东西,比如拦街祈福等等。拦街福在中断近六十年之后被重新启动,既满足了年老一辈的怀旧心理,也让年轻人在节日娱乐中认识并初步理解感受了拦街福。拦街福中的信仰层面也日渐凸显出来,虽然今日之拦街福跟过去之拦街福已有所不同,其实这种变异或发展是很正常的,只要拦街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没有被完全遮蔽,某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创造性改进都是正常可行的。换言之,拦街福之所以是拦街福而不是其他地方性节日,其拦街祈福的民间信仰内涵可以转换成禳罪祈福,甚至包括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忏悔,从而为温州的生态建设构筑一道精神防火墙。总之,拦街福中的信仰层面绝对不能被随意格式化。
三、暧昧的身体维度
面对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民间信仰维度,学者们要么选择暧昧之模棱两可,要么选择集体沉默,而生活世界中的民众为了满足一己的信仰诉求却在明修栈道。传统节日的身体维度暗昧不彰,也必然遮蔽传统节日保护的根本目的。历代学者们对传统节日的描述已经很详细很全面了,对节日的构成也研究得很到位。既然如此,我们在谈及传统节日保护问题时,就没有必要故意回避其信仰维度,一味“犹抱琵琶半遮面”。传统节日之味愈来愈淡,在笔者看来不外乎两个层面的淡,一则我们的口腹之欲早就在日常生活的饮食中获得了满足,节日期间的饮食已经没有了新鲜感和吸引力,按照物质匮乏年代的标准,民众现在每天都在过年;二则,民间节日中信仰被淡化了,换句话说,民众的精神诉求得不到满足。如果说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过各种民间节日是为了改善伙食,是吃不饱时的理想和奢望,在守望和距离中期盼节日丰盛的饮食,那么当这些都已经不成为问题,民众就转向对精神层面的诉求。但是传统节日的精神诉求在当下很难获得满足,因为传统节日的狂欢性已经被电视网络等媒介所取代,也就是说,传统节日的狂欢性被虚拟化,民众的身体被悬置,精神上狂欢已经很难通过节日来满足了。剩下的就是节日中的民间信仰了。然而这在中国历史情境下是不能光明正大地摆在台面上的问题,因为我们倡导的是无神论,民间信仰得不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在此情境下谈论民间信仰是很尴尬的,除非这种民间信仰如祭祀祖先崇拜神灵能被披上合法性外衣。传统节日无奈告别民间信仰的神圣性内容,再加上传统节日活动中身体感的丧失,其日渐被边缘化几乎是一种历史宿命。
一言以蔽之,我们若想真正保护传统节日,至少要保护节日的两个层面,即物质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第一个层面保护相对较为容易,物质是精神的载体,民间节日饮食等物质层面同时承载了大量的民间信仰,过端午节不吃粽子等节日性食品总让我们感到好像没有过节一样,这说明物质绝对不仅仅是物质,粽子不仅仅是粽子,它包含的文化内涵是靠吃来体验的,我们这方面的身体记忆不能省略。借助食物和饮料的选择以及提供和食用这些饮食的方式,民众通过共餐活动结合成了群体。每个人和自己正在食用的食物是同一的;通过象征性地咽下引发共鸣的物质,庆祝活动的参加者们为自己赋予了编码在那些物质当中的特殊意义[6]。节日饮食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当传统节日饮食文化被简化成方便面等速食之后,民众就愈加迫切需要体验原初的食品之味,借助饮食与祖先进行精神交通。第二个层面却很难保护,但这一层面又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节日如果只有物质上的满足,而没有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诉求,那这种节日肯定不会有生命力的。传统节日所包蕴的民间信仰之意义就凸显出来。民众祭祀祖先的形式可能要改变,如清明节为了防止火灾,禁止扫墓上坟时用火,最好改成以鲜花祭祀祖先。民众原本通过烧火纸产生的烟雾来与神灵沟通的,但现在已经慢慢被改变了。有学者说民间烧纸祭祀祖先都几千年了,突然禁止民众烧纸,是不是太急功近利了。但习俗毕竟要与时俱进,清明扫墓也不例外。
民间信仰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想革除陋俗实在很难。当民众不能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获得满足时,最先寻找的目标就是民间信仰,因为这是民众的精神防火墙,能帮助他们应对来自生活世界的灾难和问题。传统节日中的民间信仰也是如此。我们无法想象,若一个传统节日的信仰被完全格式化,这样节日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当我们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民间节日中的信仰问题,我们的传统节日保护就是一个伪问题,我们的保护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暧昧的。这种暧昧的保护让我们徒然地看着传统节日衰落下去。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七夕节乞巧的内容已然被技术时代所淘汰,因为不会有未婚女孩在七月初七的夜晚去乞巧了,人之精巧手艺被机器之巧所取代。七夕节原有的文化内涵被当下民众所淡忘几乎就是宿命。所以说,有些东西无论怎么去保护都注定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最多作为一个标本被展示在橱窗里,成为我们文化记忆的符号。中国的传统节日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假期,应考虑到其中承载的文化内涵。韩毓海认为[7],今天中国人已经不太会过年了,人们过年就是看春节晚会,没有亲身参与活动,仅是看客——几个伪农民在那里表演。全国人民冷冷清清看电视,这是无法营造节日氛围的。回家过年应该有利于重构城乡关系格局。毋庸置疑,身体体验的可行性也在考验着温州的拦街福。
这里的“身体”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身体,而是文化刻写的身体;“身体成为阅读和理解文化书写的新场域,成为一套由编码和象征复杂地编织起来的文本。……无论是口头的传统,匠人手头身上的技艺绝活,还是民众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节日、仪式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方式、感觉倾向、行为方式与规范,往往都是在耳濡目染中习惯成自然,成为刻骨铭心的知识和文化模式。”[8]因此,只有当身体感和神圣感被激活之后,我们才能打通或重构与祖先心有灵犀的传统节日文化通道。
四、结 语
节日的实质不是外在的欢声笑语,而是发自内心的温馨滋润。“喧嚣扰攘并不能成其为节庆,相反,它还可能破坏了节庆的气氛。”与此不同,“一种为恰当的节庆所不可缺少的特殊情趣,是某种预期的心理意识”[9]17;它来自对生命的默思和对亲情的热爱。为什么特别是在节庆的日子里,我们需要“回家看看”同亲人们团聚,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为的是能够通过亲情的交流领悟生命诞生的恩赐、体会万象更新的意义。所以,传统节日是普天之下普遍共享的生命感恩,这是节日最深刻的人类学意义:正如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可能去爱别人,一个缺少亲情体验者无法拥有真正人性的同情。节日因此拥有一种神圣性和宗教意味。事情正是这样:“为使节庆假日能从人类的辛勤努力中产生,必须加添某种神圣的成分。”[9]41我们若能真正宽容理解传统节日中的信仰维度,让鲜活的身体而不是虚拟的身体加入到节日中的欢乐或狂欢之中,我们的传统节日保护才能走出暧昧的怪圈。
[1] 刘魁立. 我们的节日, 我们的歌[J]. 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6): 1-4.
[2] 劳格文, 黄晓峰. 中国的民间信仰[EB/OL]. [2010-07-11].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 2&NewsID=7138.
[3] [美]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 范丽珠,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41.
[4] [德]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14.
[5] 鲁迅. 日记[C] //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82.
[6] [美]理查德·鲍曼.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 杨利慧, 安德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95.
[7] 韩毓海. 从基层重建中国多元文化时空观[J]. 绿叶, 2008, (7): 68-74.
[8] 彭牧. 民俗与身体: 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J]. 民俗研究, 2010, (3): 16-32.
[9] [德]约瑟夫·皮柏. 节庆、休闲与文化[M]. 黄藿,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Vagu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HAN L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has become a hot subject in China’s folklore research. However, issues of beliefs in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s have seldom been fairly faced or even been talked fully. The protection has been deteriorated to the nostalgic impulse; the bodyness in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s has been covered, which lead to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protection is going to the state of vagueness. To protect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effectively, Chinese should take actions to treat folk beliefs and body dimension fairly, to consider folk beliefs with a tolerant and understanding attitude, and to arouse the embodiment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activities completely. Based on the view of folk beliefs, the grand culture activities of the Lanjiefu in Wenzhou were newly surveyed.
Traditional Festival; Folk Belief; Vagueness; Embodiment
(编辑:赵肖为)
K892.1
A
1674-3555(2011)02-0018-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2.00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12-3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一般项目(10CGSH06YB)
韩雷(1970- ),男,安徽颍上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