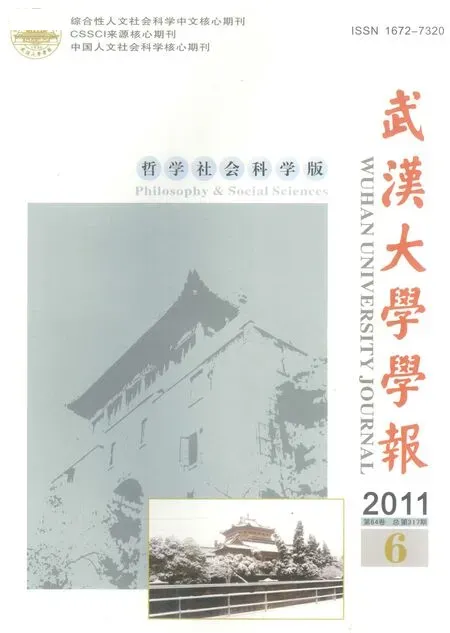梯级寻租格局、法团主义结构与政治寻租型腐败的治理之道
谢志平
腐败被视为政治之癌。在政治学看来,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腐败是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力干预经济活动,设立租金并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以往的研究,主要将腐败视为寻租的结果和个体行为,着力探讨个体腐败现象的动因、影响、防治机制与制度等。本文着重于理论分析,试图运用寻租理论的基本原理,将腐败视为寻租的条件,从科层组织体制的内在制度结构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外在制度结构两个方面,探析政治寻租的个体行为在行政体制内触发的扩张机制以及在行政体制外引发的扩散机制,并据此提出政治寻租型腐败的治理建议。
一、多层次寻租格局理论及其启示
寻租理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在讨论垄断、关税和政府管制所造成的社会损失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租”,或者叫“经济租”,在经济学里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按照经典的总体均衡理论,只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要素流动在各产业之间不受阻碍,任何要素在任何产业中的超额收入(即租)都不可能长久稳定地存在,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配置资源之“手”会将机会成本与现实收益拉平。一般把对市场要素天然存在租金的追求称为“寻利”(Profit Seeking),但如果通过人为设置流通障碍,形成对既定租金的垄断、提高或保护,其活动的性质就变成了“寻租”。托利森认为:“寻租是为了获得人为创造的收入转移支付而造成的稀缺资源的耗费。”①Robert D.Tollison.“Rent Seeking:A Survey”,in Charles K.Rowley(eds.).Public Choice Theory Ⅱ.Vermont: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3,p.71.他认为,寻租是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政府干预导致人为租金的创造。斯蒂格里茨认为:“‘寻租’这个词一般用于描述个人或厂商投入精力以获得租金,或者从政府那里获得其他特殊好处的行为。”①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7~508页。只要政府有授予租金和其他特殊优惠的权力,厂商和个人就会发现,从事寻租活动是合算的;政治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作出反映,政府决策因而被扭曲。从资源配置角度,布坎南指出:“寻租是指那些本当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②Robert D.Tollison & Roger D.Congleton(eds).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Rent Seeking.Vermont: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1995,pp.56~57.他认为,寻租从总体上看没有配置价值,是一种社会浪费。
寻租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布坎南在《寻租与寻利》一文中认为,寻租活动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旦政府创造出一种人为的稀缺性,潜在的进入者将通过游说政府给他们以优惠的差别待遇来进行寻租。这便是寻租的第一个层次,也是早期的寻租理论所讨论的主要内容。如果政府职位的薪水和额外收入包含有经济租金,如果薪水和额外收入高于私人部门类似职位的待遇,潜在的政治家和官员将会花费大量的资源来谋取这种政府职位,这便是寻租的第二个层次。布坎南认为,对于寻租分析来说,第二种层次的寻租更为重要。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是指个人和集团为保护对自己有利的差别待遇或避免对自己不利的差别待遇而展开的活动,例如通过政治程序制定对本集团有利的税收政策③Robert D.Tollison & Roger D.Congleton(eds).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Rent Seeking,p.371.。布坎南认为,在寻租活动的每个阶段寻租者都是受理性动机支配的,但资源同时在三个层次上都被浪费了④Robert D.Tollison & Roger D.Congleton(eds).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Rent Seeking,pp.56~57.。
在此,寻租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层次寻租活动的格局,它表明:第一,寻租活动是一个社会连带行为,某个个体的寻租活动会引发群体寻租或避租活动⑤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为维持已获得的垄断地位而进行的寻租,防止他人对自己已获租金的侵蚀,这称为“护租”。另一种是防止他人寻租有可能对自己造成损害而进行的寻租,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寻租”,一般称作“避租”。,只要是利益相关者,在理性思维指导下,均会或迟或早卷入。第二,寻租活动源于政府管制,这种政府管制既可能是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也可能是对政治活动本身的管制。租金既存在于私人物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产市场,也存在于公共物品市场和政治市场。第三,寻租活动以对物品的竞争性提供为前提,以对租金的排他性占有为目的,以对租金耗散与租金收入的平衡为行动边界。寻租的目的不是获得垄断,而是通过获得相对的垄断地位谋求租金,而谋求垄断的机会是存在的并且是公开的,但参与寻租竞争的边界是租金收入与支付成本的均衡。
寻租理论所展示的多层次寻租格局,其理论原点和归宿点均限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严格来说是探讨市场的个体行为与政府管制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之归类为“经济寻租”。问题是,如同布坎南强调指出的那样,“潜在的政治家和官员将会花费大量的资源来谋取”某个占有大量资源的“政府职位”的行为,这种寻租是以占有政治职位蕴涵的租金为目标的,本文将之归类为“政治寻租”。那么,这种政治寻租的触发逻辑是怎样的呢?它又会产生怎样的扩散效应呢?
二、梯级寻租格局:科层体制内政治寻租型腐败的扩张机制
一般来说,政府的组织体制是基于理性原则设计的韦伯式层级管理结构,它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⑥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8~323页。:一是分工明确和设计合理的职位体系和等级结构,具有专业化职能的行政部门各司其职,在上级的指令和协调下运作。二是行政官员以官僚为职业,其选任基于专业技术资格,进入官僚部门必须通过专门的考试或凭借资质证明,官员是上级任命而非选举,官员的报酬是固定工资,升迁以业绩和资历为基准。三是整个官僚组织强调形式化和规则约束,行政程序依据法律规范而设立。第一个基本特征强调了科层组织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威贯通结构和命令服从结构,第二个基本特征强调了科层组织官员的晋升来自上级任命,第三个基本特征强调了科层组织的规则具有刚性,是基于理性而非经验。
从纵向来看,这种层级管理体制形成了一种“压力型体制”和行政逐级发包体制①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86页。。在“压力型体制”下,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各级政府组织向下级组织和个人层层分解任务指标,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配之以相应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奖惩措施。层层压指标、定任务,各级组织也就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在行政逐级发包体制中,政府的行政事务从中央逐级向下级地方政府发包,一直发包到最基层的地方政府,而解决行政事务的资源并不必然连同打包。每一级承包方只对直接的上一级负责,并以满足它的要求为主,因为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级承包方的去留。上级和下级政府的事权不是分工关系,而是层层发包和监督、职责高度重叠和覆盖的关系②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在这种自上而下高度集权的压力型体制或行政发包体制下,政府官员的激励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锦标赛模式③Edward Lazear & Sherwin Rosen.“Rank-Ordered Tournaments as Optimal Labor Contrac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89,pp.841~864.。从职务晋升路径来说,地方官员从最低行政职位一步步提拔,进入一个典型的逐级淘汰锦标赛结构。它最大特点是,进入下一轮的选手必须是上一轮的优胜者,每一轮被淘汰出局的选手就自动失去下一轮参赛资格。为了进入下一轮,每一位参与人必须在本轮获得胜利才有资格,这给地方官员施加了很大压力,形成一种非常激烈的晋升竞争④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89页。。由此,在这种科层结构中,无论是同级官员,还是纵向序列的官员,都像被编号一样,处在一场连续不断的晋升锦标赛中。具体到晋升操作制度,我国政府官员选拔制度一直是“领导推荐—组织考察—上级任命”。在这个三段式程序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是第一个程序,即“领导推荐”。一旦有了领导推荐,组织考察和上级任命大多只是履行一个手续,走一个程序。可见,领导推荐在我国的官员晋升微观程序中是至关重要的,它往往直接决定一个官员能否晋升、晋升快慢和晋升到什么岗位。
如果排除那些保守的政府官员,即使“有些官员在他们加入官僚机构的第一天就是保守者,即使他们处于很低的层级”⑤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假设进入官僚体制的都是权力攀登者,他们总是“寻求权力、收入以及声望的最大化”。他们赢得晋升的行动路线有两条⑥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第99页。:第一,“他可以取悦其上司”;第二,“他可以在那些用于评价其晋升资格的客观标准上获得好分数”。很明显,第一条路线是投机主义做法,而第二条路线则是靠扎实的真功夫。如果实施第一条路线的成本小于第二条路线的实施成本,或者实施成本可以得到某种方式弥补,则对于任何官员都是一种绝美的诱惑⑦在我国,中央对每一级别的行政干部的任职都有最高年龄的限制,实行强制退休制,从政者必须在一定年龄升到某个级别,否则就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了。所以从基层晋升到省部级干部通常要走“快车道”,或者起点比较高。近年来国家对干部任职的年龄要求越来越趋于年轻化,这使得晋升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直接影响人们的竞争策略与行为选择。。事实上,科层组织体制结构决定了取悦上级相对于取悦社会服务对象具有更现实的意义,因为上级是特定对象,而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社会人群,何况上级掌握了自己的职业未来。但因为官僚组织有严格的刚性规则,因此任何非正式方式取悦上司,都面临着很高的实施成本,结果则只有考量弥补实施成本的出路,由此会自然形成政治寻租型腐败。
政治寻租目的并不在于占有职位,而在于占有职位后获得超额的租金。只要不是行政发包体制最低一级官员,那么作为“治官之官”,可以将“取悦上司”的成本发包或转嫁到下级,向其索贿以对冲自身利益损失。在权威结构关系中,如果上级官员有索贿需求,下级官员的供给将是无限的,因为下级官员晋升大权掌握在上级手中。由于支出了贿赂成功取悦了上级,他或她获得了晋升优先权。但是,除非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否则对于任何官员而言,这个晋升成本也需要寻找转嫁对象。于此,索贿需求再次向下级发出,如此类推直至最基层或最低层的政府官员。最基层官员身处权力末端,具有最强烈的晋升动机,因此他或她会尽力满足上级索贿要求,但他或她的成本对冲,就只能指望政府管制的社会主体了。由此从理论可以总结,在中央与最基层地方政府之间,任何一级政府官员的政治寻租行为,因为晋升压力和对冲成本的考量,在体制内均会向下传导,形成多层级寻租格局。本文将这种体制内政治寻租腐败称之为“拉力”型腐败。在拉力型腐败结构中,原发点处于科层体制中上层,自上而下倒逼,上梁不正导致下梁歪,这种腐败往往导致窝案和群发现象。
与之相对的还有一种“推力”型政治寻租腐败结构。在布坎南第二个层次的寻租活动中,他提到如果有些政府职位对市场有很强干预权力和很广泛干预范围,占有很丰富资源,能够方便地创租(Rent Creation)或抽租(Rent Extraction)①创租是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增加企业利润,人为地创造租,诱使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抽租是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创租和抽租是政府官员主动设租的行为。参见F.S.Mcchesney.“Rent Extraction and Rent Creation 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7,1,pp.101~118.,那么在政府内部,官员们就会“花费大量资源来谋取这种职位”。批准官员取得这种职位的权力在上级政府官员那里,因此下级这种主动性谋取官职的寻租行为,同样会为上级具有批准权的官员职位带来经济租金。同样,因为上级具有批准权的官员职位能够带来额外收入或经济租金,引得同级官员对该职位产生兴趣,也会“花费大量资源来谋取这种职位”,于是政治寻租活动再次被提升到更高行政层级,并产生同样的传导效应。可见,只要存在着政府权力垄断和政府职位特权,只要存在着经济发展行业和区域不平衡,以及政治发展区域不平衡,只要政府职位分配权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自下而上的“推力”型寻租活动就会此起彼伏,跑官、买官、要官现象就难以禁绝。因为在政治锦标赛中,一旦遭遇一次晋升竞争失败,就会连带失去下一轮晋升机会,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而决定能否胜出的依据,往往并不在于竞争者的绝对业绩水平,而是在整个职官序列中相对业绩水平的排名。潜在职位晋升者不能无视别人的政治寻租行为而让自己处于竞争劣势的地位,要么投入资源展开寻租竞争,要么投入资源谋求避租。如此一来,低层级官员政治寻租行为,通过科层体制将不断在横向层面展开竞争,并不由自主将上级官员卷入寻租竞争中来。在这种推力型腐败结构中,原发点处于科层体制中下层,自下而上推动,无论官员愿意与否,最终可能都将身不由己被卷入其中。
可见,政府作为科层组织,其独特的权威结构和激励机制,形成独特的压力型体制和政治锦标赛模式,导致体制内任何个体的政治寻租会引发连锁反应,触发纵向与横向层面的寻租竞争,形成体制内的梯级寻租格局。当然,如果晋升成本仅仅在体制内上下级进行成本转嫁,缺乏外在资源补充,这种传导链条最终会断裂。那么,政治寻租的成本最终有没有合适的外部消散空间呢?
三、法团主义结构:科层体制外政治寻租型腐败的扩散机制
从历史来看,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传统中,以政府主导的政治力量从来都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全面统领着社会的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先天发育不足,后天成长不良。也正因为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传统,形成了如今的法团主义社会结构。
法团主义理论模式最早源于西方政治学界对拉丁美洲及南欧权威主义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其分析研究重点是强权政府与大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一般来说,法团主义指的是一种体制现象:代表功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之间建立常规协商关系,它们为有关公共政策提出意见,作为交换,国家要求它们必须说服其成员与国家合作来实现政策有效实施②张 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页。。根据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差异,法团主义体制有两种安排形式,即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③Pilippe 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in P.C.Schmitter & G.Lehmbruch(eds).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Beverly Hills:Sage,1979,pp.7~52.。前者说明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关系,在其中国家作用是主要的;后者则代表自下而上的组织关系,其中社会力量主导着关系秩序。在国家法团主义体制中,决策权主要由政府来掌握,这种法团主义政治结构,“通过一种代表制度,将有组织的社会经济生产者团体整合起来,形成有组织的合作与互动,并实现社会的动员与控制。”④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64页。从经验来看,这种国家法团主义结构更适合中国的描述。
西方研究中国法团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戴幕珍(Jean Qi)深入探讨了在财政改革激励下政府单位、集体企业、工人、社区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和合作的内在机制①Jean 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1995,144,pp.1132~1149.。戴幕珍指出,中国地方法团主义的演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新动向,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有选择的私有化加强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把扶持对象和范围扩展延伸到私营企业。地方政府运用对合同及资源的控制以及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把私营企业整合进法团主义的框架之内②Jean Oi.“Local State Corporatism”,In Jean Oi(eds).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林楠(Lin Nan)以天津大邱庄为个案的研究指出,地方权力与稳定的利益集团结合,已经在中国基层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形式:一种既非市场,亦非正式组织的形式,它反映了现有政体、社会关系、家庭网络和文化背景的渗透结合③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这种法团主义的框架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等社会组织的庇护关系模式,大卫·文克(David Wank)称之为“共存庇护主义”(Clientialism)④David L.Wank.“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of Market Clientelism:Guanxi and Private Business in a South China City”,The China Quarterly1996,147,pp.820~838.。他认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原先私营企业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单向依赖”,已演变为一种“共存依赖”关系。一方面,政府官员依赖私营企业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合作关系,以及获取贿赂受益等;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仍然具有很大控制权力,如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对私营企业主社会地位的影响等,因而私营企业主往往也依赖政治权力获取资源,并利用权力的庇护关系避免政治和政策的任意干涉。这种庇护关系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加强了国家渗透与协调社会的能力,导致了人们对现有制度的认可,促进了社会群体的分化,减弱了社会自主的集体行为的能力⑤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页。。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来看,由于存在非对称性的组织权能,因此,它们之间表现出明确的支配性功能协作关系⑥支配性功能协作关系主要用来描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权力关系上的支配性和功能关系上的协作性。它不同于两者之间单纯的权力支配与功能从属关系,也不同于权力与功能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形成这种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在权力与能力上形成的矩阵关系都不对称。请参见谢志平:《关系、限度、制度:转型中国的政府与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184页。。
很明显,这些有关中国的法团主义结构理论鲜明地呈现出政府与社会组织——包括私人企业、各种市场中介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及其他公共组织——之间的控制与合作关系。这种控制与合作关系,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保证了经济可预期地发展,保证了文化有序的多元,保证了民主可控性的推进,应该说它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得以稳定、持续、高速发展的体制支柱。但同时,这种社会关系结构也毫无疑问为行政体制内政治寻租腐败提供了方便的制度外渠道和社会扩散的传导网络。
法团主义结构的形成逻辑,是通过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与合作,实现社会稳定与可调控发展。政府基于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可以主动地、方便地实现资源占有的延伸,对冲政治寻租成本,并扩大利益占有。但是,这样赤裸裸做会触犯既定的约束制度,造成明显的制度不公。因此最可靠的方式是形成官员与企业、各种类型的公共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政府需要这些企业、组织的配合来解决民生问题和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组织与政府合谋,可以享受政策上的优惠,以及稳健的政治环境。在这种关系中,作为个体的官员,无论是就政绩(民生问题解决和社会稳定),还是通过创租或抽租(政策优惠、稳健的政治环境),均能得到利益上的回报,因此很少会有人拒绝这种“共生性”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独特的景象,许多地方政府一把手如果异地调动,会伴有一些投资者随同转变投资场所,紧紧追随。不论这之间有无腐败,但厂商的利润与政府官员的政绩、厂商发财与官员晋升之间的紧密对应,使厂商和政府官员的共生关系鲜明地体现出来。有媒体报道,一些贪腐官员在刑满释放后,竟“意外”地收到了原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有的甚至公开炫耀(曾祥生、陈卫国:《腐败出现新怪象:受贿人出狱 行贿人送“坐牢补偿费”》,载《检察日报》2010年10月20日)。这说明厂商与腐败官员之间的共生关系已经超出了制度层面,深入到伦理与道德层面,不仅制度失灵,且相关的伦理与道德已被扭曲。。
可见,法团主义结构便利了政府及其官员那支“掠夺之手”对社会组织资源的汲取,它既是一套有效联结的社会结构,将社会资源整合起来,使社会按政府意志稳定而有序地发展;同时,它也架构了一套稳定的汲取资源的路径,通过这个结构平台,政府官员可以制度化地将体制内因晋升竞争带来的压力与成本向体制外耗散。换句话说,这种法团主义的社会结构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提供了体制外的物质保障与压力舒缓空间。如此一来,体制内的政治寻租腐败,将通过法团结构向社会扩张,一切与权力沾边的领域,可能盛行权钱交易;一切存在资源稀缺的地方,可能出现不正当交易行为。其结果,寻利之争让位于寻租之争,腐败不断地自我复制和自我强化,最终可能弥漫一切。
四、政治寻租型腐败的治理之道
传统寻租理论主要讨论的是经济寻租与腐败行为,政府官员与寻租行为是两个并不搭界的概念。但如果寻租者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特权或对自己有利的限制而展开寻租活动(经济寻租),而是为了竞争可以获得贿赂的职位而展开寻租活动(政治寻租)并产生腐败,就形成政治寻租型腐败。因此,政治寻租型腐败是在政治寻租过程中产生的腐败现象,它不以收受贿赂为限,必然通过公共权力去影响、占有或控制超额的政治资源。总之,政治寻租型腐败一定是表现为对权力的不正当占有、对权力的不正当运用。
要治理政治寻租型腐败,必须从科层组织权威结构和法团主义结构这两个方面着手,破除导致政治寻租的结构因素,偏废任何一方,都将功败垂成。
就科层组织结构而言,破除政治寻租型腐败的关键在于重构政治权威链条下的官员责任关系,运用多样化的激励手段与方式淡化职位晋升的诱惑与压力,通过破除相对封闭的职官体系来增加政治寻租成本,同时对政府职位权力运行施加更多约束以消除政治租金。
第一,构建行政责任关系的多元结构。政府官员的行为产生了四种关系网络,基本关系是对上级官员的服从关系,第二位的是对下级官员的领导关系,第三位的是与同级官员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第四位的是与管理对象之间的服务关系。因此,行政官员需要承担的,不仅有服从责任,还有领导责任、合作责任,以及服务责任。如果官员晋升行为以伤害领导、合作与服务为基础,即使是服从责任做得再好,在制度设计上也应受到排斥和否定。因此,构建行政责任关系的多元结构,要强调在坚持服从责任基础上,引入领导责任、合作责任与服务责任的评价机制,并将这种多元责任结构制度化,做到公开与公正。如今,官员选拔制度改革向“民主推荐、群众评议、组织考察、上级任命”的模式转变,淡化了上级领导推荐这个环节,注入了更多社会评价成分。只要打破上级垄断职位分配的权力,对抑制政府官员的政治寻租动机和增加寻租成本产生较大影响,就能有效遏制政治寻租产生的腐败。
第二,提供行政激励产品的多元结构。政治寻租的目的是通过晋升获得更重要职位的租金,职位产生租金的原因是它潜在的外部效益,它是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破除晋升动机这个纠结的基点在于在制度上将权力与利益相对分离,权力可以带来利益,但制度应提供其他可以带来利益的产品。科层体制除提供权力晋升必要产品,也可以提供制度性的物质报酬晋升产品,还可以提供荣誉性名号晋升产品等等。权力争夺与个性有很强相关性,对不具备这种个性特点的潜在竞争者,可以改变自己的偏好函数,选择其他发展方向并得到相应行政激励产品的回报。一旦官员回报类型丰富了,竞争选择多了,权力竞争压力会得到有效舒缓与释放,从而有利于消除因此产生的政治寻租型腐败。
第三,创建职位任用模式的多元结构。政治寻租型腐败,无论是拉力型还是推力型,它的制度环境是上下级官员在一个相对封闭和稳定的职官序列中互动,形成对职位分配的合谋。可见,一旦官员任职缺乏必要流动,沉淀的结果是利益结构化和寻租制度化。要破除这种结构障碍,必须创建多种任用渠道和形式,打破封闭和稳定的职官体系。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实行灵活任职制度,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进行人事交换,在政府内部,通过“顶层设计”,实现中下层人事交流任职,包括异地交流、不同行业间转换任职等等形式。以前实行单纯由组织任命中高级干部制度,干部考察范围很局限,通过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可以打破身份限制和选拔范围,最大程度破除封闭的职官体系,极大增加政治寻租成本。此外,《公务员法》增加了岗位聘任制的新形式。任用模式多元化,还要强调加强官员交流、挂职锻炼、回避制度建设,在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不仅强调在发达地区就职经历与业绩,还应强调在不发达地区就职经历与业绩。官员任职,不能遵循落后地区到先进地区、再晋升重用的线性路线,主要看经历的丰富、历练的多样化和能力与业绩的相对比较。
第四,增强职位权力运行的多元约束。要消除政治寻租,打破租金产生的垄断因素、增加寻租成本是一方面,斩断成本转嫁路线是一方面,而消除政治职位租金、破除政治权力的机会成本与现期收益之间的落差则更为根本。政府官员前赴后继的政治寻租,无非是更重要职位带来的收益要高于机会成本,而职位带来的收益之所以充满弹性,是因为欠缺必要的硬性约束。因此,完善政府的预算约束制度,强化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度,落实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增强行政决策与执行的民主制度,可以有效规范政府权力运行,耗散政治职位租金,从而瓦解政治寻租冲动的基石。
就法团主义结构而言,破除政治寻租型腐败的关键在于重新厘定政府角色,调整政府行为边界与重点,通过制度完善来规范既定的社会结构关系,并建立多层次的协商机制。
第一,从政府组织社会到政府服务社会的转变。按照政治学常识,国家与社会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有着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为社会全面发展服务,因而相对而言,社会具有更根本的意义。政府作为国家机器代表,其功能不在于宰制社会,而是服务于社会发展本身。因此,在法团主义结构的既定条件下,强调禁绝政府的“掠夺之手”,限制政府的“管制之手”,增强政府的“扶助之手”,对于定位政府角色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对于明确政府行为的重点具有指导价值。由于政府占有大量资源,政府通过管制产生垄断,政府政策调控具有倾向性等等,对于社会组织都是租金,因此越是过程透明、平等对待、程序规范等,租金耗散越快。政府可以有新角色、新职能空间,但一定是在合乎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来履行,只有斩断那些伸向社会组织的肆意掠夺之手与非法管制之手,政治寻租型腐败的外在制度保障线才可能被切断,这是一切反腐败极为重要的外在条件。
第二,从社会结构调整到制度结构完善转变。现代化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即形成持续变化和开放的社会结构,以及形成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①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49页。,徒有前者是不可能自动转化为后者的制度成果的,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一个自在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法团主义结构是一种既定的社会关系,即便它是政治寻租的制度外温床,我们也不能漠视这个难以撼动的现实。这种结构提供了现代化发展必要的权威力量和秩序保障,它欠缺的是社会组织的活力。要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关键的制度安排是产权保护。只有明晰产权并坚决捍卫,社会组织发展的积极性才可以充分调动起来,政府也不能肆意占有、垄断和汲取社会资源,由此社会组织与政府合谋的租金就不存在了,共生庇护关系的基础瓦解了。在共生庇护关系破局后,构建与扩大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与机会,能够提高政府过程的民主性、透明度。此外,构建多元力量参与的监督体制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腐败而言,监督永远都是必要的。如果能够在选人、用人,在决策、执行等过程中按照制度要求操作,则腐败概率要小很多。因此,监督体制应该提前介入到行政过程中来,介入到行政过程关键环节中来。监督体制要形成多元力量参与格式,并要形成合力。腐败治理之难,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收集渠道单一。信息不对称需要通过信息公开实现,信息收集渠道单一则可以通过发展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得以丰富,公民、企业、媒体、政治组织等均是重要的监督力量。最后,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是重构法团主义结构的重要手段。如果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进一步增强,承担社会责任、订立社会规则、裁决社会纠纷、提供公共物品的治理能力得以提升,那么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协商机制重新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