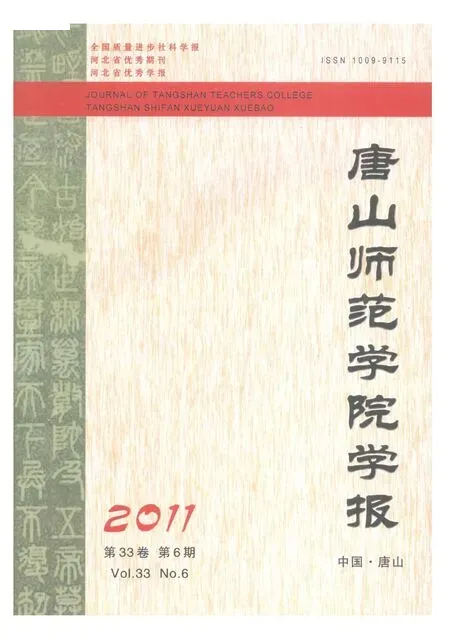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的几个问题
仝其宪,李智利
(忻州师范学院 法律系,山西 忻州 034000)
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的几个问题
仝其宪,李智利
(忻州师范学院 法律系,山西 忻州 034000)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从普通盗窃中分离出来,使之上升为行为犯,对其如何理解与认定,应穷尽已有的司法解释,寻求其解释的合理性与妥当性,并在此基点上探寻其立法精神与理由。
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解读;立法精神与理由
《刑法修正案(八)》已颁行实施几个月,此时对《刑法修正案(八)》的热烈讨论仍余音未尽。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刑法修正案(八)》的亮点颇多,值得一提的是对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修正:“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此可以看出,对盗窃罪的修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增设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方式;其二,废除了法定最高刑死刑;其三,删除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原有的两种法定最高刑情节。特别关注的是“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作为行为犯首次上升为法律。对此如何理解与适用,其立法精神与理由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前刑事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展开较为深入细致的探究,冀希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入户盗窃”、“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之解读应穷尽已有的司法解释
对“入户盗窃”、“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的准确理解,关乎到司法实践中的正确定罪与量刑,甚至于影响到司法公正与社会秩序。新法刚刚颁行实施,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作为依据,有学者急切地期盼“两高”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两高”的司法解释本来已经洋洋洒洒千万言之长了,解决新法带来的实际问题,我们不能动辄就期望“两高”的司法解释给出答案,应根据已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寻求解决办法,这种探寻问题的路径无法实现时,才可冀希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实际上,“两高”的司法解释不可能也没必要对刑法典的逐字逐条均作出较为明确的解释。对此有学者不无深刻地指出,理论研究更应当关注如何增强刑法典条文的普适性,如何通过理论解释来使刑法典保持持久、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而不能动辄求助于(或推责于)刑法典的修正或司法解释。时代在发展,纯粹理论推演中无法想象和难以预测的问题层出不穷。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全部等待和依赖刑法典的修正和司法解释,更为可行的和负责任的方式是对刑法典进行与时俱进的扩张解释[1]。因而我们应首先从已有的相关司法解释寻求较为妥当的答案。
对“入户盗窃”、“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的理解,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抢劫罪”的司法解释。拟归纳为以下理由作为支撑:(1)因为盗窃罪与抢劫罪均属于侵犯财产罪的范畴,两罪的犯罪目的均是非法取得他人的财物,侵犯的主要客体均是公私财物所有权。通常认为,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罪中最严重的一个罪,是以暴力、威胁等方法致被害人不敢反抗、不知反抗或无法反抗的程度,当场取得公私财物的行为。而盗窃罪一直是侵财类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犯罪,是采取“平和手段”秘密方法取得公私财物的行为。一般认为抢劫罪远远重于盗窃罪,在某些方面重罪可以统领轻罪,按照刑事法中通常的“就上不就下”原则,可以参考“抢劫罪”的司法解释得出对“入户盗窃”、“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的恰当解释;(2)最高人民法院如果对类似情形再出台司法解释,明显多余,同时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3)参照已有的司法解释能够达到合理的法律效果,没有必要再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也不利于罪刑之间的协调性;(4)出台过多的司法解释,不利于公民的掌握与适用,更不利于公民的遵守,有碍于公民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5)事无巨细、过分繁杂的司法解释有违法律应具有的简练性、抽象性、概括性与原则性品质;正如意大利刑法学家菲利所言:“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疏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2]由此,从终极意义上说,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存在完备而自足的法律;(6)过分明确细致的司法解释意味着僵化,适用起来更为狭窄、更是漏洞百出,在粗疏与细密之间应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力图达到刑法的明确性、协调性与相对完备性[3],这才能解决实际问题;(7)汗牛充栋的司法解释也无法穷尽纷繁多变的社会生活,期望司法解释能够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永远都是一种奢望;(8)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的司法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入户盗窃”参照“入户抢劫”做相应的解释有法律依据,也能够保持法律概念之间的协调性。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对“入户盗窃”、“扒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的理解与认定,完全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抢劫罪”的司法解释,无须再作出权威性的司法解释,这样也有利于罪与罪之间的协调性,有效地保护法益。
二、“入户盗窃”之解读
关于“入户盗窃”的理解与认定,参照 2000年 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入户抢劫”的解释。以此可以推理出,所谓“入户盗窃”是指为实施盗窃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的渔船、以车为家的汽车、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
在认定“入户盗窃”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户”的范围。“户”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二是“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进入他人住所须以实施盗窃犯罪为目的。盗窃行为虽然发生在户内,但行为人不以实施盗窃等犯罪为目的的进入他人住所,而是在户内临时起意实施盗窃的,不属于“入户盗窃”。三是盗窃行为必须发生在户内。上述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由此可以判断,进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盗窃的,因为它不符合上述“户”的范围,不属于“入户盗窃”。如果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的一个部分作为家庭生活而居住并具有相对封闭性,而进入其内实施盗窃的,由于它契合了上述“户”的功能特征与场所特征,笔者认为,应属于“入户盗窃”。
需要指出,“入户盗窃”中行为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复合行为,即入户行为和盗窃行为是具有牵连关系的两个行为,也就是说,入户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盗窃,入户是实施盗窃的必经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入户实施盗窃构成“入户盗窃”的情形,在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并无争议与歧义。但有以下几种情形值得注意:一是对于合法入户时并无盗窃犯罪的动机,而是临时起意实施盗窃是否构成“入户盗窃”呢?笔者认为,根据上述的有关司法解释与“入户盗窃”的认定条件,不应构成“入户盗窃”,因为“入户”的目的不具有非法性,可以按普通盗窃处理;二是对于事先就有盗窃犯罪的动机,行为人凭借特殊身份或以合法理由入户实施盗窃犯罪,笔者认为应认定为“入户盗窃”,虽然行为人是以所谓的“合法”形式入户的,但是他入户的目的具有非法性;三是对于行为人事先具有抢劫的动机而入户的,由于出现被害人熟睡或不在家等情形,转而实施盗窃犯罪的,因为具有入户目的的非法性,根据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认定为“入户盗窃”;四是对于行为人基于盗窃犯罪的目的而入户,之后却实施了抢劫的,应构成“入户抢劫”而不是“入户盗窃”;五是对于行为人基于盗窃犯罪的目的而入户实施盗窃犯罪,之后被发现,行为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如果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发生在户内,这种情形下,应认定为“入户抢劫”而不予认定为“入户盗窃”。那么,如果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发生在户外,这种情形下,根据上述的司法解释,只成立“入户盗窃”,而不属于“入户抢劫”。
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将“入户盗窃”作为行为犯,不以“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直接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其立法精神与理由,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行刑法已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虽然“入户盗窃”的严厉性和危害性不如“入户抢劫”,但它比“入户抢劫”发案率高,更为常见多发,严重危害了人们家庭生活的安宁,将“入户盗窃”上升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旨在从严惩处那些胆大妄为、有恃无恐而严重危及公民生活、工作安全的犯罪分子[4];二是随着人权保障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的生活空间的安全感,人们往往将家庭生活作为享有自由权利和隐私权的“避风港”。“入户盗窃”除了侵害他人的财产利益之外,还侵害了人们家庭生活的安宁,使人们丧失了生活的安全感,对此人们反响强烈;三是“入户盗窃”实际上是非法侵入住宅罪和盗窃罪复合形态,根据刑法基本理论,应择一重罪处罚,盗窃罪的法定刑高于非法侵入住宅罪,而较为轻缓的非法侵入住宅罪早已成为刑法上的一个独立罪名,相比之下,“入户盗窃”更具有可罚性,将它上升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有利于罪刑之间的协调性;四是“入户盗窃”与普通盗窃相比,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一般来说,“户”的特点具有封闭性、孤立性、自我保护性与外界关系疏远性等,也契合了西方人所说的“风也可以进,雨也可以进,惟独国王不可以进”的特质,因而,对于“户”外界因素不能轻易介入。就“入户盗窃”而言,行为人作案难度较大,其动机较为明确,对危害结果的追求较为热烈,显示出犯罪意识的坚定与执着,因而其人身危险性较大;五是“入户盗窃”过程中,一旦被被害人发现,常常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转化为“入户抢劫”,使被害人孤立无援、陷入十分危险境地,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对“入户盗窃”作为行为犯惩处,有利于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相应的防止了更为严重的犯罪升级。
三、“扒窃”之解读
关于“扒窃”的理解,根据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参考现行刑法第291条对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规定。笔者认为,“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场所秘密窃取他人随身财物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扒窃”,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1)其作案地点是公共场所。对公共场所的理解为供人休息、活动、休闲、游玩等的场所,例如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以及旅客列车、船只、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飞机等正在营运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其主要特征是往来的不特定人较多;(2)其作案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人们随身携带的现金或物品;(3)其行为方式是行为人一般徒手作案或借助刀片、小镊子等小型工具作案。具备以上情形的,应认定为“扒窃”。
上述的司法解释把“多次盗窃”与“扒窃”规定在同一个法条中即第四条中,两个概念交织在一起,很明显具有包容关系。而《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把“扒窃”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那么,如何界定“多次盗窃”与“扒窃”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应从上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的司法解释说起。对“多次盗窃”的理解,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多次盗窃”因司法解释的限定而又有了较为固定的含义,它所指的盗窃行为必须是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如果盗窃不是在户内或公共场所,则不能累计计算盗窃次数[4]。此观点基于对司法解释的严格解释与文理解释所得出的,为很多学者所赞同;另一观点认为,“多次盗窃”中的“盗窃”,不应仅仅是指“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两种形式,其还应包括其他形式的盗窃在内。只是其他形式的盗窃,要达到成立犯罪的“多次盗窃”的程度,也应当比照上述《解释》的第四条的规定,至少要达到“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的社会危害程度,否则就难以作为盗窃罪处理[5]。可以看出,此观点是基于对司法解释的论理解释所得出的,近期有学者所倡导。笔者认为第二观点较为可取,因为它能够较为妥当的解决实际问题。《刑法修正案(八)》把盗窃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为盗窃财物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等五种行为方式,如果按照上述观点一的主张,“多次盗窃”的行为方式仅指入户盗窃和扒窃,而《刑法修正案(八)》却把入户盗窃和扒窃从“多次盗窃”中剥离出来,三者成为并列形式,按照上述观点一的主张,“多次盗窃”就名存实亡了,这与《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模式不相符合。但按照第二种观点的主张,上述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把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剥离出来,因为“多次盗窃”还包括其他形式,其仍然存在,这样便与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模式相吻合。
对于“扒窃”的立法精神与理由,笔者认为,一方面,在公共场所扒窃的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人的财产利益,同时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扒窃分子时常纠集他人、流窜多地、横行乡里,严重侵犯了人们的财产利益,也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扰乱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由于这种滋扰群众行为的个案难以达到“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社会危害程度而不构成犯罪,而行政处罚因处罚力度不够并不凑效,即使以“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成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也关不了多长时间,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的几率更高[6];另外,对于大多数扒窃分子由于作案持续时间长、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已经养成了好逸恶劳、好吃懒做与挥霍无度的习癖,其人身危险性较大。据此,增设“扒窃”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有利于从严打击此类犯罪,有效地保护法益。
四、“携带凶器盗窃”之解读
关于“携带凶器盗窃”的理解与认定,笔者认为,同样可以参照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和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补充规定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解释。据此,所谓“携带凶器盗窃”是指行为人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盗窃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器械进行盗窃的行为。“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字义上来说,“携带”,《汉语大辞典》中解释为“随身带着”;“凶器”,解释为“行凶用的器具”,那么,“携带凶器”一词可以解释为“随身带着行凶用的器具”。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里的“凶器”是指枪支、匕首、刮刀等管制刀具,以及具有一定杀伤力的菜刀、斧头等器具[7]。笔者认为,不应明确的框定“凶器”的范围,上述杀伤力较强的器具当然应认定为“凶器”,但作为日常使用的菜刀、水果刀等物品,甚至一根普通的棍子、绳索、石块等均可以视为“凶器”。那么,判断这些器具是否属于“凶器”,应从具体案件来考量,行为人是否将所携带的器具产生了凶器的用途,并用于所侵害的目标,是否对侵害目标构成现实的人身威胁;二是依据刑法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主观上行为人必须对自己携带凶器盗窃有明确的认识,意识到自己是在携带凶器实施盗窃;在客观上行为人携带凶器进行了盗窃,也就是说,携带凶器属于盗窃行为的附随情形。这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认识到自己是在携带凶器盗窃,但客观上并没有实施盗窃行为,就不能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否则,属于主观归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行为,而主观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携带凶器,也不能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否则,有客观归罪之嫌;三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它器械盗窃,但有证据证明该器械确实不是为了实施犯罪准备的,不易以“携带凶器盗窃”定罪;四是行为人将随身携带凶器有意明示或暗示,能为被害人察觉到并构成威胁的,直接适用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五是行为人携带凶器盗窃后,在逃跑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适用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对于“携带凶器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其立法精神与理由,笔者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行刑法中将“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263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而“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相比,一般来说,其严重性前者稍弱于后者或者几乎相当。但依据现行刑法规定,对于“携带凶器抢夺的”转化为最为严重的抢劫罪处罚,而“携带凶器盗窃”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才能成立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处罚差别很大,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各罪之间的协调性。《刑法修正案(八)》将“携带凶器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较好地解决了上述矛盾;二是在“携带凶器盗窃”中,一定程度上强化与坚定了行为人的作案心理,在此强烈的心理支配下促使其排除一切障碍,将犯罪进行到终点,因而其社会危害性较大;三是在“携带凶器盗窃”中,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有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因而,当被被害人发现时,其行为往往转化为抢劫,造成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刑法修正案(八)》将“携带凶器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将犯罪行为扼杀于初始阶段,更有利于保护法益。
[1] 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刑评价——以“醉酒驾驶”交通行为为视角[J].法学,2009,(5):23.
[2] 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25.
[3] 张明楷.妥善处理粗疏与细密的关系,力求制定明确与协调的刑法[J].法商研究,1997,(1):15.
[4] 夏强.抢劫罪三题探微[J].当代法学,2001,(4):63.
[5] 董玉庭.盗窃罪客观方面再探[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1,(3):52.
[6] 黎宏.论盗窃罪中的多次盗窃[J].人民检察,2010,(1):24.
[7] 宋洋.《刑法修正案(八)》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立法完善之解读[J].中国检察官,2011,(3):41.
[8] 高铭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74.
(责任编辑、校对:王学增)
On Theft in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8)
TONG Qi-xian, LI Zhi-li
(Department of Law, Xinzhou Normal College, Xinzhou 034000, China)
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8) will separate indoor theft, a theft with lethal instruments and pickpockets from normal theft. And make them up for behavioral offence. How to understand and identify it, people should end the existing judicial explanation, seek the rationality of their explanation, and explore the legislative spirits and reasons on this basis.
intruding into another person residence to theft; a theft with lethal instruments; pickpockets; explanation; legislative spirits and reasons
2011-09-13
仝其宪(1974-),男,河南台前人,硕士,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犯罪学。
D924.36
A
1009-9115(2011)06-0120-04